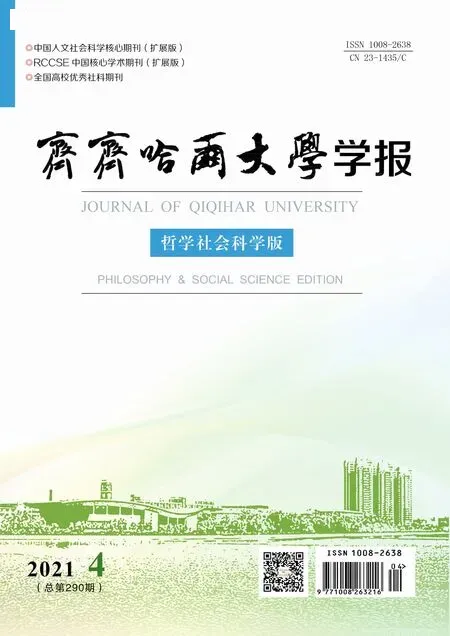智慧城市建设的文化内核
2021-12-31郑晓明
郑晓明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与法律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智慧城市建设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热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在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智慧城市或向智慧城市转型的各类城市接近600个,智慧城市的发展固然离不开信息技术,但轰轰烈烈的智慧城市建设如果被技术架空,成为冰冷而空洞的智能化巢穴,这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背道而驰的。智慧城市的“智慧”从本质上来看,是技术和人文的媾和,智慧城市的表征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新技术在人居环境中的渗透,阿尔伯特·梅耶等人认为包括智能技术、智能人才和智能协作三个要素。[1]但无论人类文明进化到什么程度,都无法从城市形态中抹除文化的印迹,文化传承是一条看不见的伏线,只要人类族群聚居的生活方式不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文化永远都是衡量城市发展层次和水平的重要指标。只有在审慎地传承和改造城市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触摸到智慧城市的内核。
一、地域化与同质化的共生:智慧城市文化符号的凝练
城市的形态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都需要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作为支撑。智慧城市以其对资源利用效率和族群生活品质追求的特性,在人类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高度的现代性和超越性,构成智慧城市的文化符号也应该体现出接纳城市资源配置的包容性和聚力生活品质营造的开放性,这不是简简单单地用现成的文化符号进行移植或嫁接,而真正需要从智慧城市建设的本源出发去凝练。城市文化符号的凝练,是地域化和同质化的共生。所谓地域化,是从城市本身的地域特征出发,任何城市都不可能脱离其地理风貌和社会历史遗存而发展,虽然智慧城市已经是人类城市文明发展进程中较高级的形态,但是形态上的高级并不能否定其产生的根基,一个以智慧城市作为自身定位的城市,无论其前一阶段是生态城市、技术城市还是知识城市[2],地理印迹和历史印迹都会为其贴上独特的文化标签,而这样的文化标签,正是在智慧城市文化符号的凝练过程中最大的凭仗。所谓同质化,是从城市发展的路径演变出发,作为智慧城市最关键特征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和智能感知系统,有着高度的可复制性特征,因此,智慧城市的实现路径,在技术层面高度同质化,无论是欧美的智慧城市,还是亚洲的智慧城市,如果允许其罗列出彰显智慧城市优势的特征,一定不会缺少高速网络信息传递、城市数据互联共享、数据分析和智能处理、智慧物联和高效管理等,这既使智慧城市建设拥有一条模式化的快捷通道,也造成了千城一面的潜在危险。
地域化与同质化,看似矛盾,但从文化的角度却可以理解为共生的关系。智慧城市的文化符号,从物理空间的层面,应该追求在保持传统地标建筑风貌的基础上,用信息技术增强文化表达的效果;或者反其道而行之,在用信息化手段填充各类新型地标建筑的基础上,增加视觉呈现中的历史文化元素。这两种路径是相反的,也是可以共生的。传统的地标建筑,已经超越了建筑层面,不仅仅以建筑的形式存在,而且出现在各种文化衍生物中,甚至本身就是城市文化符号的一种具象,天安门之于北京,自由女神像之于纽约,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都无须筛选而自然具有城市文化符号的意味,只不过,从文化符号分层的角度出发,偏重于视觉感受,是较为浅层次的文化符号,而深层次的文化符号,则需要从城市发展历史中一以贯之的城市精神出发去进行筛选和凝练。传统地标建筑作为文化符号不仅存在于有限的物理空间,也存在于无限的虚拟空间,这是智慧城市中信息技术发挥作用的主阵地,虽然信息技术运用本身的同质化无法杜绝,但技术是手段,文化符号本身是内容,技术手段的同质化并不代表文化内涵的同质化。对于缺少传统地标建筑的新兴城市而言,新型地标建筑的诞生必然伴随着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这足以提升城市的现代感,但无法凸显城市的文化特质,因此,在视觉呈现层面,必须要融入富有地域色彩的历史文化元素,这些元素可能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是一种市井俚俗,甚至可能只是一种纯粹的城市精神,他们的共性在于空间上的地域色彩和时间上的历史元素,它们无法独立地被打造成城市的地标,但是却可以借助信息技术依附于新兴地标建筑,呈现在城市公众的视野里。
从人际网络的层面,智慧城市为城市居民的沟通互联提供了无限可能,但人和人之间最稳固的关系绝不可能是虚拟层面的,因此,要在享受新型人际网络多元化和便捷化优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留具有地域化特征的人际网络的特质。智慧城市,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文化,这种治理文化不能靠运用智能技术和引进智能人才来实现,它绝不是斥巨资引入一个智能化的网络平台或者利用移动互联技术接入海量用户的终端就能实现,也不是培养一批兼具治理经验和技术特长的城市管理人员就能走出终南捷径,而恰恰需要关注在城市发展历史中经受时间检验而不被淘汰的那些较为传统的社会规则,我们称之为非正式居民人际网络生态。朱塞佩·格罗西等人认为“城市的作用是理解和倾听公民的反话语,让他们参与价值观和共同目标的定义”[3],城市治理水平要与建筑和技术的进步相匹配,必须延续一个城市在特定历史和地理环境下形成的非正式居民人际网络生态,在参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这种特定的非正式居民人际网络生态,可以补足正式的政府治理不便或不能触及的领域。抽取这种非正式居民人际网络生态的特征,用以凝练智慧城市的文化符号,则不必追求手段的标新立异,否则在成本上将会成倍增加,这对于任何一个以建设智慧城市为目标的城市都是一种经济上的伤害,有损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技术层面的同质化并不会导致地域化社会规则的变质,相反,沿用成熟的技术模式,反而有助于降低不同地域的非正式居民人际网络生态融合的难度,从而进一步推动文化符号的凝练。
二、族群与社区的分布:智慧城市文化意蕴的表达
人们关注智慧城市,更多地是把注意力放在建筑层面和技术设备层面,或者进而把目光延伸到城市治理层面,但事实上,从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来看,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才是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终极指标。关注智慧城市居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品质,了解其文化意蕴的表达,才是理解并真正把智慧城市建设推向纵深的关键所在。
一方面,智慧城市形成的各类新兴族群,为城市文化意蕴提供了承受的载体。传统的城市建设,因为线性的族群关系,人和人之间、空间和空间之间、人和空间之间的分布关系都是二维的,要塑造一种共通的文化意蕴,却缺少一种可以串接起各个族群的载体,这使得传统城市的文化特质呈现出一种隐晦性的特质,人们关注的城市文化意蕴,其实只是各个彼此之间相互割裂不发生勾连的单一族群的文化意蕴,芜杂、多元、混乱。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智慧城市,却真正可以将价值诉求、审美倾向、志趣秉性、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方面具有高度趋同性的城市居民筛选出来,为各类新兴族群赋能。从“鬼旋族”、“考碗族”、“隐婚族”、“低碳族”,到“H族”、“LOMO族”、“酷抠族”、“极客族”等等,形形色色的新兴族群,在智慧城市提供的生存空间里,展示着最为原始的城市底层文化意蕴。各个族群独具特质的文化意蕴,因为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打破了以地域区块分割为特征的线性的传统族群限制,构建起了智慧城市的网状族群文化意蕴,并且这种网状的族群文化意蕴,在表达层面几乎是没有障碍的,它们直接关联着智慧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每一个细微的表达,都是对居民生存状态变化的一种呼应。
另一方面,智慧城市构建的成熟网络社区,为城市文化意蕴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如果说新兴族群的衍生,只是为城市文化意蕴的表达提供了载体,尚且缺少一个对城市文化进行充分解构和重构的着力点,那么智慧城市构建的已经高度成熟的网络社区,就是应运而生的不可或缺的平台。城市文化意蕴的展示,视觉层面只是浅表层间,理念层面才是主阵地。现代城市无论如何追求极致的建筑美学,城市的建筑和布局都是高度雷同的,按照美国学者索亚的理论,无论是“福特式”的传统集聚型城市,还是类似于洛杉矶的“后大都市”[4];无论是保留规整、集约、向心的传统结构模式,还是在无序、琐碎、流动状态下对城市空间进行复杂的重构,城市的形态终究不能超脱人类群居的特性,因此,城市文化意蕴的个性化诉求,更依赖于个性化的理念空间。成熟的网络社区,既为城市居民文化意蕴的孕育提供了雨露和阳光,也能为文化意蕴的改良和升级提供锤炼的平台。依托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城市网络社区,可以对城市居民文化意蕴的细微表达做深度的数据挖掘,构建精确的模型,并进行精准的干预,这使得智慧城市的文化意蕴,在理念层面存在着畅通的发展路径,有助于提升文化意蕴表达的效率。
无论是族群还是社区,都是智慧城市形态下居民的重要生存状态。族群和社区的分布,关系一个城市居民沟通模式的布局,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可以产生迥异于日常生活经验的两种不同效果,即“深层效果”和“表层效果”。[5]如果我们保持对智慧城市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关注,就会发现,无论是“深层效果”还是“表层效果”,探究其影响一个城市宜居性的方式,都离不开创新性的沟通模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族群为经,以社区为纬,交织而成的网状沟通模式,才是深度挖掘城市文化内涵,准确定义城市文化意蕴的科学布局。
三、“场域”与“惯习”的交融:智慧城市文化心理的阐释
智慧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空间,按照布迪厄的理论,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并不是对其建筑或道路实体进行剖析,而要将城市的整体发展放置于“场域”和“惯习”交融的复杂环境中。对智慧城市居民生存状态和生活品质的关注,决定了智慧城市的文化心理一定是以智慧城市居民适应并享受着的特殊的充满文化表达张力的新场景的构建为基础。[6]
现代城市的机械疏离,向来是文明进程中物质与精神背离的一种必然结果。技术创新赋予了智慧城市较为复杂的生态系统,生活品质的可持续性和生活资源配置的可操作性,都是这种生态系统的特性,从“场域”的角度来看,这种生态系统恰恰就是多种关系叠加的总和。正如布迪厄所言“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这些争夺旨在继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7],从文化心理层面,这些争夺的直接表现是对旧的生活场景的颠覆和新的生活场景的塑造。我们很难用某一两个名词去定义智慧城市居民生活的新场景,因为它们是主观和客观争斗的一种妥协,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关系结构,涵盖了对环境满意度、物质满意度和社区融入度等一系列指标的测度。旧的生活场景所留存的那些固有的关系,在智慧城市建立的技术世界都被认为是可以被数据化、被模拟的,因此,也都是可替代的。以精确的分析和推演为依托的城市生活新场景,正是在对旧场景的固有关系的解构和模拟中,建立起一种心理上的优势。这是城市居民在智慧城市建设的特定逻辑要求下做出的妥协,无关城市居民个体的情感选择,而是一种经过筛选的集体意识。它使得智慧城市的文化心理,从根本上体现出一种矛盾和对立。
但是我们无法忽略的是,这种主观和客观的对立,最终需要在一个临界点上取得一种平衡,这就是城市居民的“惯习”,“惯习”具有的历史性因素,使得新技术的接受成为对历史文化传承的一种背离。与“场域”的建构不同,城市居民的“惯习”更加侧重个性的表达,更加关乎居民个人的情感选择。它试图在城市发展的灵魂塑造中追寻一种“城市精神的重估”[8],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不同城市形态的“场域”中形成的“惯习”做简单的空间转换。智慧城市建设的文化内核,最终要服从文化传承的需要,正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城市“致密而紧凑”的独特构造,是“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因此,把城市居民的“惯习”视为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能更加协调好智慧城市发展变革中“场域”的变化,在这种交融的关系中,才能追寻到城市居民的心灵走向,合理地对其文化心理进行阐释。
总之,智慧城市应该是在人文理念的框架下,以适应城市居民实质的或虚拟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探索和追求更高资源利用效率、更高族群生活品质的一种城市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