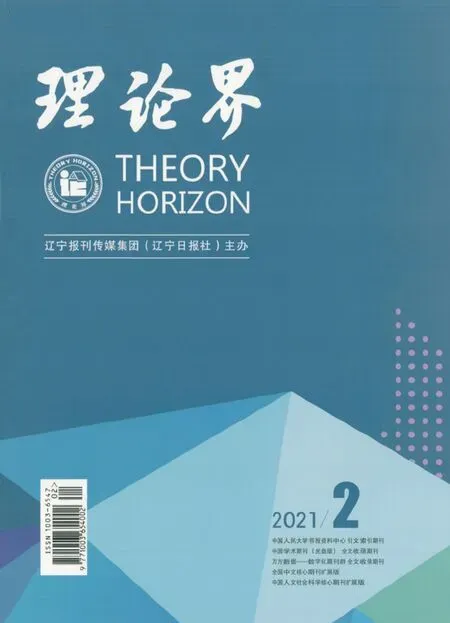科技创新风险与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2021-12-26黄斌
黄 斌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代以来,科技发展全方位地改变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临床医疗、国民健康、生态环境、国家安全、经济贸易等各领域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21 世纪以后,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3D打印、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量子力学等现代科技正蓬勃兴起,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之间的边界也随之模糊不清,呈现出加速度走向深度融合之势,进而引发多维复合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急剧地改变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运行规则,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认知范围与活动空间、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与发展条件,为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与福祉。然而,人类与科技之间的关系问题,犹如马克思论述的劳动异化过程,即人类在创造科学技术的同时,科学技术也逐渐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并反过来对人类施加控制和约束。〔1〕而且人类所耗费的力量越多,其所创造的科学技术的异化程度就越加严重,也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裹挟、形塑人类的生存样态。基因工程、核武开发、网络技术等都已显露出脱离人类驾驭的征兆,增加着人类被支配、奴役和宰制的风险,甚至积蓄了足以毁灭人类的巨大力量,〔2〕从而深刻地影响了科技发展的方向与前景。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与重要基石,美、中、欧、日等许多国家都将之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然而,从科技创新领域的一系列新进展和新动态来看,科学家们从事不符合伦理行为的科技事件时有发生,科技创新风险的危害及其破坏性也由此不断激增和聚积。2012 年,一些研究人员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无视人的知情权与尊严,骗取中国6~8岁儿童食用安全性存疑的“黄金大米”进行人体试验。〔3〕2017 年,在动物实验迄今未能得到安全有效验证的情况下,一项所谓的“活体人类头颅移植计划”几乎要冒险进行,后因各方强烈反对改为了“人类尸体头颅移植”。〔4〕2018年,贺建奎等伪造知情同意书,在缺乏医学可行性论证及伦理审查的条件下,盲目采用CEISPR-Cas9技术对人类胚胎基因进行编辑并诞生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双胞胎,〔5〕此举导致各界的“恐慌性热议”,并被《科学》杂志评为当年国际上影响最恶劣的三大科学事件之一。〔6〕上述一系列的负面科技事件中,无不暴露出一些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缺乏责任、违背科学精神、偏离科研初衷、觊觎不适当利益等伦理问题。一些科学家的道德缺失导致“损信任、毁科研、砸声誉”的科学悲剧,严重破坏科技创新的社会形象,亵渎了科技活动的纯洁性与庄严性。因此,在科技创新中,科学家如果不在创新与风险两者间作出恰当的权衡,就会衍生新的风险或是使潜藏着的风险更大化,也就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负面道德后果。更令人不安的是,在效益和效率的激励下,一些科学家迷恋于科技创新的效用性而完全忽视不良后果,因“盲目创新”而产生的“破坏性创造”屡禁不止。因此,规避科技可能导致的各种潜在风险与社会危机,使科技创新更可持续地造福人类,已成为至为紧迫的时代课题。
二、科技创新风险的内涵及典型特征
英文中的“创新”(Innov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Innovore”,最早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7〕科技创新就是超越常规的观念、方法与模式,在已有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取得新成果、新发明、新技术,它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市场应用这个“三螺旋”结构持续演化的成果,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应用到生产体系并创造新价值的过程。〔8〕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超越技术:不断变革的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9〕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开始进入了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它正颠覆几乎所有行业,彻底地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管理和治理体系。然而,虽然今天的科学技术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密集创新时代,但存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科技创新项目的难度与复杂性、创新者自身能力与知识储备的有限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如未及时化解和校正,相应的科技创新活动不但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会滋生新的风险类型,并体现出新的特征:
1.风险生产:具有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传统社会的风险是一种生成性的“外源风险”,主要是由外在的自然灾害(地震、洪水、瘟疫与饥荒)所致。与之不同的是,科技社会的风险是一种人工生产出来的“内在风险”,它的发生发展与运行逻辑都存在显著的“人为性”,与人的决策和实践紧密相关。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那种‘人造风险’,它们源于科学与技术不受限制的推进。”〔10〕随着科技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社会乃至自身的认识日益深刻,人类对外部世界、社会运行以及人类自身之生物组织的干预也就越大。然而,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以及一些捉摸不定的因素的影响,使得科技创新风险的发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也难以被完全排除。更为重要的是,科技创新风险的不确定性有时候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2.风险呈现:具有内在关联的耦合性。当今科技时代与以往时代最本质的区别是,各种性质迥异的“高精尖”科学技术开始发生深度耦合与全面会聚,复杂性与关联性空前增强。正因如此,原本存在于特定领域和狭小范围的科技创新风险不再是孤立地爆发,而是相互连接、相互交织、彼此耦合。事实上,现代科技创新同时涉及了多个创新主体、多种行业领域与多种科学技术,其所产生的风险是在多因素共同激活下呈现的综合并发症。科技创新风险摧毁了以规律和经验建立起来的风险计算逻辑,并以风险耦合链的形式进行表征,这一耦合链中的各个环节相互驱动、交叉关联、彼此影响,其中任何环节的“微小扰动”都可能使潜在的风险转变为现实,进而产生难以预估的严重后果。科技创新风险作为风险社会的重要构成之一,极易引发社会风险的连锁反应,触发经济风险、政治风险、金融风险与环境风险等并发成“风险事件群”;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系统的基础与机制,甚至使整个社会处于瓦解、崩溃的边缘。
3.风险扩散:具有时空影响的广延性。科技的快速发展,全面推进了人类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比如时空压缩、流动快速、传播立体化等,都现实地构成了科技风险扩散的最好方式和渠道。一方面,层出不穷的科技成果极大地扩展和增强了人们行为的范围、强度与规模,使某些包含着巨大风险之可能的科技成果,不仅会直接影响当代人的生存发展,而且还可能危害未来世代的生存基础。〔11〕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创新成果的普及性应用,人类正在迈向政治上相互联系、经济上相互依存、社会上深刻互动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亘古未有地勾连起来。正如贝克(Ulrich Beck)所言,科技风险在其扩散中体现出一种“飞去来器”的效应,那些风险生产的施害者或从中受益的相关者迟早也会受到风险的报应。〔12〕因此,任何科技创新风险所造成的影响都可能以一种“总体的”或“整体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甚至酿成全球社会的恐慌、失序与混乱。
4.风险后果:具有破坏极强的致毁性。传统经验技术时代,技术创新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人类社会的形塑是浅层次的,此时的风险后果极为有限,具有较大的单一性、局部性和可控性。随着科技创新的日益深入,人类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认识愈加深刻,并以空前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改造自然世界。但当下诸多科技创新的核心特征是为了谋求利益和效益的最大化,这是科技创新的内在动力,但当这种内在动力没有受到伦理和法律的规制时,科技就会无任何约束地前行,进而带来诸多不可控、不可弥补的巨大风险,甚至具有诱发“人类整体灾难”之可能。与之同时,科技创新已直指人类存在的根基,深入改造与干预人类自身生命体的自然组织——基因结构,整个人类从物质基础、社会结构到进化模式都将因之发生关键的乃至根本性变化。但这种可以直接改变或更新人类群体生命性质的操作,一旦运用不当,不仅将对人类的身体构造、心理能力及精神特质等带来严重的消极效应,还可能直接威胁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整体存续。〔13〕
三、科学家异化是科技创新风险的重要根源
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在成就人类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使人类自身沦入了科技异化的危险之中,科学家的异化亦随之日益凸显。英国前技术部长本(A.W.Benn)曾指出:科学和技术是权力的最新表现形式,掌握它们的科学家则有堕落为“新型工头”的危险。〔14〕我国学者李醒民写道:“在不良的社会大环境与失范的共同体小环境的影响下,部分科学家若不能严格自律,极易干出种种违背科学规范和泯灭科学良心的事情,沦为人人唾弃的异化人。”〔15〕科学家异化不但会扭曲科技发展的初衷与方向,更可能成为科技创新风险的“催化剂”与“放大器”,进而贻害科学、毒害社会。
1.经济异化:科学家可能将科技创新异化为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在科技创新活动中,科学家对个人利益的关注是一种合理预期,这并不意味着风险事件的必然发生。但科学家对个人利益的过分顾及与不当追求,都会不适当地或可能不适当地引发科技创新的行为偏向,如不予以鉴别与控制,科技创新风险就会快速增加。随着科技职业化的不断发展,科技创新由一种追求真理的活动,逐渐转变成一种可让科技人员获得种种荣耀与福利的职业。贝尔纳(John Desmond.Bernal)曾指出:“科学家为了他个人的生计以及取得成为他自己主要生活动力的工作领域,从长远来说他们不但不能得罪施舍金钱的‘雇主’,还必须设法去主动讨好他们。”〔16〕其结果是,科学家与雇主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在这种金钱关系的背后,一些科学家在功利性心态的支配下,为了获得课题、项目、基金、奖励、专利、成果转化利润以及发表SCI 论文等,越来越忽略科技创新中所潜藏的风险,这种唯利是图的科技创新势必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更大的危险与灾难。
2.政治异化:科学家可能将科技创新异化为迎合政治意图的手段。在科技感十足的创新型社会中,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宗教信仰、传统习惯与文化观念等方面虽存在差异,但基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科技创新在政治事务与公共决策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科技创新的发展战略及部署上,一些科学家或是与权力直接结盟,或是为政治权威所左右,或是出于对某些政治团体的“忠诚”,他们的职业动机不是着眼于人类的整体利益与公共价值,而是将科技创新各指标体系的设计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牵连在一起,打着科技创新的“引领性”和“收益性”的幌子,实则为“别有用心”的政治诉求提供“学术辩护”,导致科技创新难以与社会公众的合理需求相符合。正如巴伯(Bernard Barber)所言:“科学不可能不受社会中其他因素(当然,包括政治因素)的控制,科学自由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自我控制之特殊形式的问题。”〔17〕在科技创新与政治文明的复杂纠葛之下,科学的独立性原则和自主性要求很难得到贯彻与适用,一些科学家早已不是基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而创新,而是利用科学权威与知识声望为某种政治意图提供辩护,故意虚夸某些科技创新的价值与作用。诸如此类带有“政治偏向”的科技创新,不仅会导致科技资源的浪费,而且可能导致科技创新风险的聚集放大。
3.精神异化:科学家可能将科技创新异化为追逐社会功利的坦途。回溯历史,人类追求科学精神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技创新的进步史,凡科学精神繁盛之地,必是科技创新的战略高地。何为科学精神?任鸿隽阐释科学精神的要素为“崇实”与“确贵”。〔18〕竺可桢把科学精神概述为“只问是非,不计厉害”。中国科学院在《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指出:“科学精神本质上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与捍卫,也是对创新的尊重。”〔19〕默顿(Robert K.Merton)则把科学精神定义为四种规则——普遍性、公有性、无偏见性、有条理的怀疑论。〔20〕因此,科学精神作为科学活动中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是求真精神、怀疑精神、民主精神、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等诸多方面的综合。科学家是科学精神的承载体与执行者,需要通过科学家具体的行为来体现。但是,一些科学家的灵魂腐化与道德沦丧,致使科技创新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野心、谄媚、虚荣与贪婪等不正之风,科技创新风险由此迅猛增加。一些所谓的“科学家”甚至打着科技创新的旗号从事科学诈骗的勾当,这不仅严重损害了科学家的社会形象,也使科技创新的健康推进失去了根基与保障。
四、科技创新风险的消解:告别“异化”,多路径增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科学家作为科技创新活动最直接的行为主体,其不仅是科技创新行为的推动者,还是科技创新思想的提供者,他们对科技创新风险具有更深远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因而对其创新行为的善恶及其价值在道义上负有直接责任。施韦伯(Sam Scheber)说道:“科学事业主要设计从未存在的物体,我们必须为我们创造出的这些新奇物承担道德责任。”〔21〕因此,多路径增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可有效防止科学家异化,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和弱化科技创新风险,推动科技创新活动朝向负责任创新的方向前行。
1.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培植科学家道德责任的重要条件。人文精神是对“价值”和“善”的追求,是一种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与批判精神,〔22〕主要回答“应当怎样”的问题。科学精神是对事实的“真”的追求,是一种基于客观理性基础之上的精神气质与思维方式,主要回答“是不是真”的问题。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体两面,两者之间依存伴生、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然而,随着科学在认识自然和财富创造上的巨大成功,人们日益把科学视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轻视甚至完全忽视人类存在的目的与意义,由此导致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者间的失衡,并形成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种极端思潮。人本主义恣意鼓吹非理性主义,刻意强调人的地位与价值,把一切科技风险及恶果归咎于科技进步。而科学主义则特别张扬科学的威力,盲目夸大科学理性的功能与力量,甚至纵容科学家任意从事“无禁区”的科学探索。因此,只有彰显人文精神、尊崇科学理性,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共建,以人文指引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促进人文发展,才能将科技创新和伦理价值、社会义务与历史责任等进行连接,因而也是培植科学道德责任的前提基础与重要条件。
2.责任驱动与民主决策的联姻:提升科学家道德责任的关键动能。科学家作为科技创新的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如果不能拥有对他人、社会乃至未来世代负有责任关怀的意识,其所主导的科技创新就可能突破应有的边界和限度,进而演变成为对人类生存具有巨大风险的祸害。然而,一些科学家对科研自由和学术自主性的沉迷,常常加剧了科技创新对社会责任问题的忽视,从而破坏整个科技创新链的完整与健康。事实上,科学家只有以责任为科技创新的价值原则,把所有科技创新活动都置于责任的聚光灯下加以考察和透视,才会如实反映创新的不确定性及自身知识的局限,严肃评估创新过程各个环节可能产生的风险及不良后果。要想科学家充分践行社会责任,就必须打破科学领域的机构化和官僚化,破除科学界的封闭性和科学本位主义,让更多的科学家和公众知情、评估和评判相关情况,甚至直接参与决策过程。把科学家、公众、媒体、企业家、政府组织等不同人群的意见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他们在科技创新中各自发挥他们的功能,促进科技创新踏上民主决策之路。责任驱动将激发整个科学家群体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的根本改观,民主决策能为科技创新营造务实健康的环境氛围,责任驱动与民主决策两者的携手联姻,能有力提升科学家的责任担当,进而确保科技创新风险的尽量减低。
3.伦理约束与法律监督的互补:夯实科学家道德责任的基本保障。一些作为主导科技创新形态和走向的科学家,他们的所谓创新不但没有促进人类的兴盛繁荣,反而点燃了地狱之火,成为了开启潘多拉魔盒的人,因而越来越凸显了对科学家进行伦理规范和约束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伦理对科学家科技创新活动的规约,需要确立以下几个原则:第一,审慎原则。审慎原则要求科学家对科技创新活动持续地顾及和不断审思,对可能引发的创新风险保持高度的慎重与警觉,必要时放弃或限制那些难以评估其风险的科技创新项目。第二,生态原则。科技创新项目不应以伤害其他生物及其生态环境为前提,要大力发展绿色科技,对自然界要存有敬畏之心,既要创造财富又要保护环境。第三,安全原则。要对科技创新设立禁区,防止盲目启动那些不符合伦理的、有着巨大安全风险的创新项目。伦理规制对科技创新风险的规避虽有重要作用,但缺乏刚性的约束力,还需要法律与之双管齐下。然而,由于法律法规的制定程序繁琐漫长,与科技创新之间经常存在“步调不一致”的尴尬。一些科技创新尚未进入法律视野,处于立法上的空白地带,而旧有的法律法规在应对科技创新风险方面往往容易失灵、失效。只有伦理约束与法律监督的整合互补,才可由内而外地夯实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更好地消解科技创新风险的发生发展。
五、结语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驱动发展”,无不凸显了科技创新在推进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科技创新在显著提升人类生活质量和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使人类频繁地陷入了其所引发的风险和危机之中,给人类社会的进步造成了许多障碍和制约。科学家作为科技创新的设计师与执行者,对各类风险理应具有前瞻性的科学预见和预警能力,在道义上有责任去阻止风险成为危险。因此,为避免科学家对创新精神的曲解和对创新成果的滥用,就需要谨防科学家的异化与腐化,多路径积极增进科学家的责任担当,以尽可能地降低科技创新风险对每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冲击与危害。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科学家作出怎样的努力,由于科技创新本身往往是容许试错的,是在不断纠错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而且科技创新过程与科技成果运用的每个环节都存在着不确定性,有的科技创新风险并不只是由科学家单独产生的,而是与诸多社会因素相互综合的结果,科学家对其所产生的风险不可能也无法完全预计。因此,为了有效消解科技创新风险,除了增强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感,更需要全社会与科学家携手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