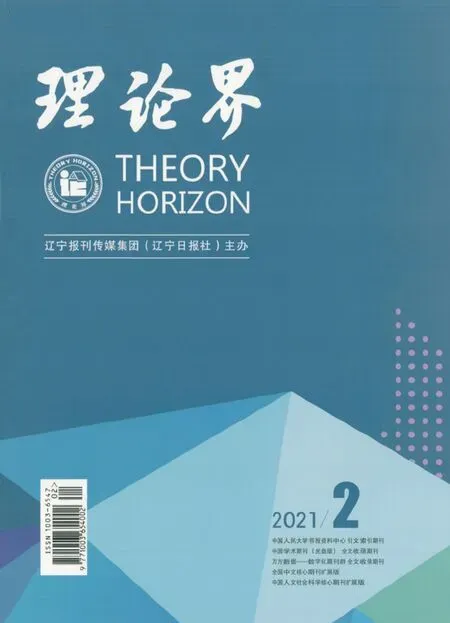孔子“仁之方”的四种进路
2021-12-26安会茹
安会茹
仁是孔子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并且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也最多。“仁”这一概念虽然在孔子以前的古文献中已经出现,但孔子却是第一个赋予了它以丰厚的道德伦理内涵。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到仁,弟子也多次问到仁,但是孔子从未正面回答什么是仁。孔子都是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告诉弟子“仁之方”,即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如在《论语·颜渊》中,就有颜渊、仲弓、司马牛问仁,孔子对三者的回答却各不相同。对颜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对仲弓,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司马牛,孔子曰:“其言也訒”。如是等等,每次回答都是针对不同人提供不同实现仁的方法。至于仁本身,正如《论语·子罕》中所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很少谈及。孔子虽不常言,但是从仁之方做起,经过下学而上达的工夫,却也可以达仁。程颐有言:“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1〕《论语》中关于仁之方的论述,可以说比比皆是。在孔子与其弟子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实现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从爱入仁、从敬入仁、从孝入仁、从忠入仁、从恕入仁、从礼入仁等等。这些都是针对不同人,孔子给予的不同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法。但总的讲来,如何实现仁呢?通过对孔子这些论述的归纳总结,“仁之方”的进路大致表现为以下四种方式。
一、强恕而行以达仁
关于“仁”,《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亲也。从人从二。”段玉裁先引《中庸》:“仁者,人也。”又引郑玄对此句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然后再引《大射仪》中的“揖以耦”及注:“言以者,耦之事成于此,意相人耦也。”“耦”,《说文解字》:“耒广五寸为伐,二伐为耦。”所以,“偶(耦)”与“奇”相对,有“对”“合”“配”等义,都强调彼此双方。两人见面相揖为礼,彼此互致敬意与问候,便是“相人偶”。其后,段玉裁释:“按人耦,犹言尔我亲密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由此意可见,仁,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你与我,也就是自己与对方,这两者之间要亲密,要互敬互爱。
关于“恕”,《说文》:“恕,仁也。从心,如声。”孔颖达疏又有:“于文,如心为恕。”关于如字,《说文解字》:“如,从随也。从女从口。”关于女,《白虎通》曰:“女者,如也。引申之凡相似曰如。凡有所往曰如。皆从随之引申也。”可见,如字有“相似”之意,如心,就是如其心,即以己心虑人心,要时时用自己的心去体会和感受他人的心。可见,“恕”与“仁”从本义来讲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所以孔子在教导弟子为仁之时,特别强调恕道。如前面提到的仲弓问仁,孔子的回答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为仁之道,不外乎存心;存心之要,莫过于敬恕。出外办事如同会见宾客,自然不敢有所疏忽;役使百姓如同举行重大祭祀,自然不敢有所怠慢。时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人以非礼待我,我不乐意,因此,自己也不可以非礼待人,能如此行事,私意自然不能藏其中,人与人之间自然能和谐相处。此意即是由恕入仁。另外,孟子更明言:“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则直说:“恕即为仁。”〔2〕恕即是仁,是从心上而言。己之所恶,即是人之所恶,不可强加于人。开始虽不能安然有如此之行,但是努力这样去作,私欲就会日渐而少,天理则会日渐而明。天理已明,则知“万物皆备于我”,于是仁体可得矣。
由恕道入仁,是从根本上求仁。仁就是人与自身以外的人事物的统一,就是说想到自己的同时也要想到他人,所以实现仁的根本还在于自己的那颗心。《论语·雍也》中记载,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君能广施恩惠济民于患难,尧、舜至圣,犹病其难也。”〔3〕意思是说,如果从事功论仁,认为如能够广施恩惠于天下之民,能济万民于苦难之中,使其各得其所,这等为人才是仁,那么即使像尧、舜那样既有德又有位的圣贤人也很难做到。因为仁者的心是没有穷尽的,但是力量却是有限的。如果博施济众才算是仁,尧、舜也不能完全避免黎民有饥馁之忧,其心也会歉然而不乐!又何况他人呢?概子贡的求仁之方是从事入手,是舍本而逐末。而所谓的仁者,是纯乎公理,没有丝毫私利掺于心。所以,看普天下之人,都与己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如果自己有所成立,便不忍他人处于颠危,必思以引掖,使其同有所建树;如果自己显达,便不忍他人处于穷困,必思以扶持,使其同归于通达。此等立心,是天地一家、万物一体的气象,虽不能遍物而济之而无一遗漏,但其心已契仁之体,故曰为仁。孔子之论,是从心上求仁,此为求之本,所以至简而至易;子贡之论,是从事上求仁,此为求之末,所以至繁而难成。尧、舜之所以为圣为贤,也是基于其在心体上求仁,其事功虽不能遍物而爱之,但是其心却常在安民。《群书治要·说苑》有曰:“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圣人之于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则孝子不敢以其物荐进也。”即仁之本体,全在一颗公心而已,所以圣人求仁,绝不远求,只是将己之心比人之心,圣人治天下,也是推此心以安民。由此也不难理解孟子的王道之治,其实质亦是推此不忍之心以安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赵歧注曰:“先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伤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于转丸于掌上也。”〔4〕即天下虽大,治理虽难,但其理却简,就是一颗不忍人之心而矣。此不忍人之心,即是孟子讲的“四端”。此四端依孟子看来,如人之有身一样,乃人之本有。因为是人之本有,所以扩充此四端也是人人皆能的事情,若将此一念不忍人之心扩而充之,则如始燃之火,不可扑灭;又如刚涌之泉,不可壅塞。用之家则家和、用于国则国安、用于天下则天下太平。其势虽浩大不可挡,但起源只是一念不忍人之心而已。
二、由学成智以达仁
求仁要从心入手,同时求仁也须依靠学。孔子特别重视学,《论语》开篇就是《学而》。关于“学”,《说文解字》释:“学,觉悟也。”另外,《白虎通·辟雍篇》有“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以觉释学,似无疑义,但关键是要觉悟什么呢?孔子曰:“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达,通也。上达,谓通于天道而畏威”。〔5〕即要通过形而下的人伦日用之学以通达形而上的本体之道。另外,《论语·子张》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显而易见,学的主要目的不是掌握某种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要通达形而上之道。
另外,熊十力在谈到中西哲学差异时也谈到这一问题。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一般人的印象是西方哲学重在求知,中国哲学重在求善,所以中国哲学以伦理道德见长,西方哲学以科学见长。熊十力认为,这只是对哲学表相上的理解,哲学与科学不同,哲学所求之真,“乃日常经验的宇宙所以形成的原理,或实相之真。此所谓真,是绝对的,是无垢的,是从本已来,自性清净,故即真即善”。〔6〕即伦理道德在本体上是与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熊十力接着说道:“中人底修养是从其自本白根,自明自了,灼然天理流行,即实相显现。而五常百行,一切皆是真实。散殊的即是本原的,日用的即是真常的。如此,则所谓人与人相与之际,有其妥当的法则者,这个法则底本身,元是真真实实,沦洽于事物之间的。”〔7〕这一法则就是实相,即是真理,即是道。平常的人伦日用方面的修养与实践就是为了达到这一实相之真,为仁自然也是为了达到这一实相之真。因此,为仁要达到这一目的必然要通过学习,因为“好学近乎智”,不学习就没有智慧。
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昼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终日就所学以思而不达,则不如须臾之所学而有益。因为所学的圣贤之道犹如日月之光,能顿开诸智而破诸障。故学是费时少,而益处多,行仁自然不能离于学。离乎学,脱乎智,则可能耳不辨音、目不识途,对仁的认识可能就失之偏颇,不知如何行仁。宰我有志于仁,但不明为仁之道,所以有“井有仁焉,其从之也?”(《论语·雍也》)之问。由此,孔子向其阐述为仁也要有智的道理:济人爱人本是仁之心,赋之于行动,则是智是事。仁人行仁有爱心也要有智慧,有智以行仁,则仁无流蔽,无智以行仁,则可能会害仁。可见,行仁必须有智,无智难以有仁。《论语·公冶长》记载: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刘宝楠在《论语正义》引多家之言释“知”为“智”。令尹子文在任职方面能做到“进无喜色,退无怨色,公家之事,知无不为”,〔8〕显然他已经做到了忠,然而他荐子玉代己为帅,丧军败国,不能称之为智,所以更不能称之为仁。陈文子虽能“避恶逆,去无道”,以保自身之洁,但他上不能谏君以止昏,下不能阻崔子以止恶,徒自洁其身不能有济于世,所以不能称为有智,故也不可称之为仁。
可见,智为仁之先导,无智便不可为仁。《礼记·中庸》有“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人虽非生而知之,但若笃志好学,不肯自安于无知,则自然能对事物之理有一定认知,从而达乎智。但是仅仅是知之,由愚变为了智,如果不能付诸行动,还不能称之为仁,必须将所知践行于生活,知行合一,才能称之为仁。《礼记·学记》所说“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即是此理,仅仅明了道理,徒能为人言说,还不能为人师,更不是仁,还要把这些道理纳入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才能为仁。而如何纳入、如何实践,则要知耻,即是要常怀愧耻之心,永不言弃,勇于改正自己的过失,从而自立自强。这种勇于改正过失的精神就是勇。可见,智为仁之先导,为仁必须先由学以明理,因为不明道理便不知如何为仁。另外,《论语·子罕》中有:“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也是以智开头。朱子释:“明足以烛理,故不惑;理足以胜私,故不忧;气足以配道义,故不惧。此学之序也。”〔9〕因为有智慧的人,才能明白事物之间的原理原则,才不会疑惑,才能对行为的方向与目标非常明确,义无反顾,进而付诸行动,既不会有忧虑,也不会有所畏惧。智是仁的基础,有了智才能知道如何行仁,所以班固根据人的修养把人分为三等,从高到低,依次是“圣人、仁人、智人”,仁人是比智人更为高的一个标准,有智不一定有仁,但有仁必然有智,智是我们成为仁人的基础,有了智慧,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仁,能不能成仁,如何成仁等问题。所以,《论语·阳货》有“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仁主于爱,本为人之美德,但如不好学以明理,则心可能为爱所蔽而陷于愚。即爱心也要用智作引导,使其适中而行,否则可能徒具一颗爱习却铸就大错。
故《论语·子张》有“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学务在求仁,然而仁不会自至,必先由学以明理,并且要笃信好学,坚定志向,如有一理不明,则必勤问慎思,如此仁德自然就在其中了。可见,求仁之道,不外于存心,存心之功,不外于务学,学在是,则心在是,心在是,则仁在是。
三、推己及人以达仁
“仁”的本义就是关于人与他人的关系的学问。他人的延伸义也并不完全指人,而是指与自己相对的,其他的一切人事物。所以自己与自己以外的一切人事物合二为一就是“仁”。程颢在《识仁篇》中又明言:“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即仁在本体论意义上,与世间万物是一个整体。那么,如何回到仁这一本体呢?《论语》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推己及人,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扩充开去,进而爱世间的一切人和物。
墨子提倡“兼爱”,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并且,他还主张爱无差别等级,不分厚薄亲疏。有些人就此而厚墨薄儒,认为儒家爱有差等,不及墨家高一层次。实际上不然,儒家也主张“泛爱众”,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道:“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泛爱众”就是博爱一切人事物,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就这一理想来讲,儒家的爱是没有差等的。另外,孔子有大同理想,此理想不比墨子的“兼爱”有丝毫逊色,所追求的也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但大同理想的实现也要从“亲亲”开始。大同世界追求的是仁之体,但大同世界的实现却要通过“仁之方”。“仁之体”与“仁之方”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作为二程弟子的杨时,也极力阐明“仁之体”与“仁之方”的区别,并反复教导学者依“仁之方”以求仁,而避免直言仁体。杨时强调:“盖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后能为仁也。其曰为仁,与体仁者异矣。体仁则无本末之别矣。”〔10〕既仁在体上是万物一体,无本末之别,但是仁之现实表现并不如此,人与人之间有尊卑贵贱之别,要达仁之体,岂能无视此差别。并且杨时认为,如果只强调仁之体,忽略仁之方,则有墨子“兼爱”之流弊。孟子曾言:“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墨子主于“兼爱”,视天下之人远近亲疏无差等,此理想固然甚好,但却忽视现实之差别,则会使人置至亲而不顾,所以说是无父也。所以,儒家不仅讲体也讲用,不仅有理想,还有实现理想的方法,这一方法就是“爱自亲始”,就是“推己及人”。就这一方法来讲,可以说儒家是“爱有差等”的。
《论语·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万事有本有末,若徒务其末,则徒劳而无功,所以做事当在切要处用力,根本既立,则道理自然发生。孝、悌则为行仁之本,人能孝、悌,亲吾之亲,则可及人之亲,敬吾之长,则可及人之长,至于安抚万民,养育万物,皆从此孝悌之心扩充而来。《孝经·天子章》释天子之孝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所谓“爱敬”,是天子自身躬行爱敬之道。“不敢恶于人”“不敢慢于人”是天子施化天下,使人皆行爱敬,不敢有恶亲之行。孔传曰:“君能爱敬己亲则能推己及物,谓有天下者爱敬天下之人,有一国者爱敬一国之人也。”〔11〕即为君者,要行博爱、广敬之道。然此道也要从爱亲、敬亲开始,然后推己及物,行博爱、广敬之道。
另外,《孝经·圣治章》中有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为万善之本,百德之源。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教育之恩德,可比天地,对己之父母若无爱敬之心,对他人也难以升起真正的爱与敬,往往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的伪装造作,自己不去体察而已。识得此理,所以仁爱大道的实现,自然要从亲亲开始。孟子有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此句把仁之体与仁之方的关系诠释得最为透彻。亲亲、仁民、爱物,统而言之,均归于仁,并且亲、民、物三者在体是上合而为一,但是在实现方式上要从亲亲开始,进而推亲亲之爱以仁其民,再推仁民之心而爱乎物,从而最终达到“民胞物与”之境界。可见,“推己及人以达仁”是儒家“仁之方”根本体现之一。
四、外束于礼以达仁
仁虽为人人本具之德,但由于人受外物所诱,其心而有失于仁。要达于仁,实质就是导其心。导其心除了上述所言之外,还要通过礼的外在约束。
颜渊曾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颜回是孔子的入室弟子,对颜回的回答也是最深刻的回答,学者往往从此句中窥见孔门弟子难以得闻的“性与天道”。朱注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12〕明德、仁慈是人们本自具有的。现在人们失于仁,并非真正丢失,只是由于后天习欲的影响,使其不得显而已,所以只要把这些贪欲、习气等去除,本具仁德自然显现。那如何去除呢?就是“克己”,即克制自己的习气,让自己复归、复返于仁。
克己之所以需要礼的教化,究其根本则在于礼乃缘情而制。既人有财、色、名、食之欲蘊于内,就有喜、怒、哀、乐之情现于外,如无节制,人必离道日远,所以人要节其欲,即使其欲望有所节制,但不是要灭人欲,而是使人的欲望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荀子·礼论》有言:“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儒家特别重视伦理,因为人无伦外之人,人总是处在一定伦理关系之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总之,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任何人的活动,都要凭借一定的社会关系,都要借助社会的力量。而每个人在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同时,他首先还是一个自然人,每一个人总是本能地追求着自我欲望的满足,在追求自身满足的同时,势必造成对他人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如果人的欲望没有节制,不断受外界刺激而膨胀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冲突,不稳定的因素也必然会产生。如何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和谐?这是礼应运而生的缘由。礼并非随意而设,其本质是“天之节文”。《春秋左氏传》:“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即礼是按照天地之常道所设,与道相通,是人们行事的依据。如果人时时均依礼行事,其心虽不能立刻达于道,但如从此行持开始慢慢内化,也会逐渐达于道。
进而,颜渊又问孔子行持方法,孔子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只要不合乎礼的,眼不看,耳不听,口不言,心不为之动,如此时时依礼,自然能归于仁。在这里,礼属于一种外在的约束,这种外在的约束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这与孟子所言“徒善不足以为政”的道理实质是一样的。人虽有向仁之心,但也需要外在规矩的约束。《孟子·离娄上》:“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人竭尽目力,再接着用圆规、墨线等器具制作方圆平直,制器之法就不可胜用;人竭尽耳力,再继之以六律来校正五音,作乐之法就不可胜用;人竭尽仁心,再接着施行仁政,仁德就会遍布天下。礼之用与此同,人有仁心存于内,外有礼法束于外,其离仁就会越来越近。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即人有聪明之资质,又有资深之学问,实为难得,但若没有仁爱之心守之于内,以至于私欲膨胀,此智始有但终究必亡,此智又何益之有?如若智及之,又能以仁守之,其德可谓全矣,然处事临民之际,不谨其容,自亵其体,不依礼教行事,则不能感民之敬,只能启民之慢,虽有智与德,但不能化人。礼的作用能启发人内心的恭敬,如举行祭祀大典,必须配有庄严肃穆的祭祀之乐,人的举手投足也要合乎礼仪,如此才能启发人的恭敬之心。可见,礼虽属外在,但却能启发人的内在感情,如此兼本末,合内外,则道愈全、仁日近、道日隆。
五、结语
在《论语》中,孔子“仁之方”的体现是多方面的,以上四种进路是对孔子“仁之方”的归纳总结。做到了这四方面,也就做到了“爱”“敬”“孝”“敬”“忠”等美德。但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四种进路也是相通的,彼此之间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恕道本身就包含着推己及人,包含着要依礼而行,而这一切又都不能离开学。这四者之所以相通,就涉及了儒家更具有一般性的概念,就是“道”。孔子曾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道”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仁之方”的四种进路之所以相贯相通,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依道而行”。孔子曾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德”“仁”“艺”四者从“道”与“器”的关系来看,是一个由“道”到“器”的形而上成分逐渐降低的过程,学习的根本在于“志于道”,“游艺”“依仁”“据德”的目的都是为了“达道”,所以真正做到“依道而行”,也就掌握了实现“仁”的方式方法。所以孔子的“仁之方”可以不仅仅是上述四种进路,也可以归纳出其他的方法,只是这四种方法更具代表性。《周易·系辞下》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王弼注曰:“途虽殊,其归则同;虑虽百,其致不二。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13〕天下大道,至真至简,如果真正做到“依道而行”,在通往“仁”的道路上就会通权达变,游刃有余,不拘泥于一种方法,一种途径。这也正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所谓的“仁之方”,“仁之方”才会呈现出不同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