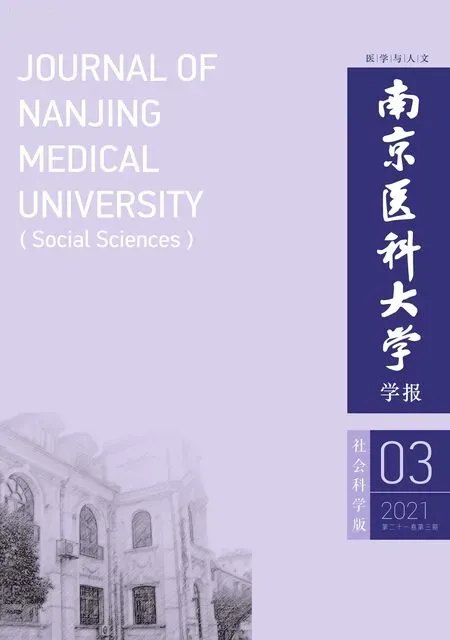月子中心监管对策研究
——基于母婴权益保障视角
2021-12-24张晨韵陈钰琪李跃平张雪晖陈玉菁
张晨韵,陈钰琪,李跃平,张雪晖,陈玉菁
1.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卫生健康研究院,福建 福州 350122
月子中心,又称月子会所,《产后母婴康复机构行业管理与服务指南》将其定性为“产后母婴康复机构”,《月子中心服务团体标准》定性为“母婴保健服务机构”,《母婴生活护理服务质量规范》定性为“母婴生活护理服务机构”,《母婴保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定性为“母婴保健服务场所”。综上,月子中心功能基本定位为生活照料、护理、保健、康复,一些文献还将其归入健康管理服务产业范畴[1]。
伴随着产褥期保健观念转变、生育政策调整、国家政策支持,月子中心行业发展潜力巨大。然而,由于现行监管机制不完善,近年来接连发生母婴权益受损事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例,以“月子中心/月子会所”为关键词搜索全网,截至2020年8月31日,最终纳入分析消费者起诉月子中心终审案件86 件(只统计终审结果,若仅检索到案件的一审文书,则默认一审为终审)。2014年4 件,2015年6 件,2016年8 件,2017年4 件,2018年21 件,2019年28 件,2020年暂为15 件。案件发生集中的前三名地区为上海、北京、山东。因而十分有必要再度审视月子中心监管现状,规范行业发展。
一、月子中心现行监管主体与标准
(一)现行监管主体
由于实践中月子中心的实际经营范围除最基本的住宿、餐饮、护理等服务外,还包括美容美体、摄影、婴儿早教、母婴用品销售等,确定监管主体的难度较大。根据相关立法推知,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后,月子中心监管主体理论上主要应包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营业执照备案登记、餐饮部分的食品经营行政许可、价格监督检查等;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住宿部分公共场所及服务人员的卫生行政许可等。国务院2019年发布的《关于促进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婴幼儿照护指导意见》)指出,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发展改革、教育、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应急管理、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指导、监督和管理。月子中心的服务对象包括了母、婴,理论上应至少按照《婴幼儿照护指导意见》中的“营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标准来监管,其主要监管部门应为卫生行政部门。这也与《母婴保健法》中确立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母婴保健工作的原则相符。
实践中,由于月子中心为新兴行业,长久以来相关立法与政策始终未直接明确月子中心的监管主体,造成各地区各部门对月子中心监管体制的解读与做法不同。但根据公开报道,大多数地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承担着最积极的角色,如黔南州[2]、玉林市[3]、上海闵行区[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本文纳入分析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例中,19 件提及监管部门,其中16 件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4 件被告为同一家机构的系列案件,因无法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取得联系,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手段为“将被告列入经营异常名录”;1 件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督月子中心是否存在食品卫生问题;1 件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为消费者和月子中心调解),1 件为工商局(现职能并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受理消费者关于月子中心店面墙体名称、广告宣传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不符的投诉,2 件涉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机构进行调查并作出督导意见书,建议停所整改。
(二)现行监管依据
1.立法
目前作为月子中心监管依据的相关主要立法有《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作为消费者与月子中心纠纷解决依据的许多民事法律规范,虽通常不直接作为监管依据,但不妨作为检验监管效果的参考。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此类案件援引频次较高的民事法律规范主要有《民法总则》《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当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实施,《民法总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担保法》同时废止,相应内容经完善吸收至《民法典》中。
2.标准
截至2020年8月31日,以“月子/母婴/育婴/产褥期”为关键词,检索“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共检索相关标准41 部,均为“推荐性”标准,虽无法作为监管直接依据,但亦可成为重要参考。其中3 部国家标准,1 部全国性行业标准,其余为地方标准;19部属于家政(家庭、居家)服务类规范,仅6部属于专业母婴护理机构的技术、运营、管理规范标准:《母婴保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河北《产后母婴护理机构服务规范》、陕西《家政服务指南产后母婴护理服务机构运营规范》、江西《月子中心服务质量规范》、湖北《月子中心基本规范》、天津《月子护理机构服务规范》。
3.其他
虽无法作为监管直接依据,但同样可成为重要参考。包括政策文件,如2019年《淮北市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等;行业协会文件,如2015年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产后母婴康复机构行业管理与服务指南》、2019年上海市健康产业促进协会《月子中心服务团体标准》等。
二、提示监管漏洞:月子中心母婴权益受损案例归纳分析
监管不力的直接结果便是母婴权益受损,主要可基于《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寻求事后救济。下文将基于母婴权益受损类型对相关案件(由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纳入案例数量有限,因而除法院公开案例外下文还将分析新闻报道中的典型案例)进行归纳,以期为监管部门提示监管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一)人身安全权受损
20 件案例涉及母婴在接受服务过程中身体受损害,提起违约/侵权之诉要求赔偿,其中14 件月子中心对损害结果负有责任。这些情形包括:①护理人员对婴儿脐部保护、护理不当,造成脐炎、脐带非正常脱落,引发新生儿败血症、心肌损害等严重后果;②推定员工感冒传染婴儿,引发肺炎、心肌受损;③护理人员未对婴儿患病前期症状加以重视,对病情加重负有责任;④护理人员喂奶致婴儿严重呛奶送医抢救;⑤婴儿洗澡时,因员工操作不当致取暖器灼伤婴儿面部;⑥机构明知产妇乳腺胀痛、乳头水肿,未提醒原告就医,而是继续提供乳房护理服务,加重原告病情;⑦机构未做好消毒工作,致使多名婴儿感染轮状病毒;⑧护理人员护理不当,致使婴儿感冒并引发支气管炎、肺炎;⑨护理人员未尽谨慎注意义务提醒黄疸值不断增高的婴儿监护人及时送医,以至延误诊疗造成脑部病变;⑩护理或清洁不到位引发婴儿肛周脓肿;⑪婴儿在吸完奶瓶后不久突发异常状况送医不治死亡,机构因不申请死亡原因司法鉴定且无法提供监控视频等证据,被推定为存在过错。新闻报道的损害及威胁母婴健康的典型案例还包括:①武汉某月子中心误用酒精清洗婴儿口腔[5];②上海某月子中心多名婴儿、产妇及家属、护理人员发生急性出血性结膜炎[6];③南京某月子中心厨房发生液化石油气泄漏爆燃事故致多人伤亡[7];④产妇及家属因月子中心内甲醛含量明显超过《室内空气质量标准》要求,入住后不久便出现不适症状[8]。
(二)其他合同权益受损
除人身安全权受损外,许多案例也提示了月子中心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导致母婴其他合同权益受损。
17 件案例中,消费者认为月子中心提供的服务与合同约定的标准不符,其中9 件月子中心被认定为违约。①月子餐中有异物;②未按约定提供接机服务、住宿条件达不到约定标准;③未按其宣传的标准提供食材,未按约提供婴儿游泳服务,入住期间机构内装修给消费者带来影响;④未按约提供医生巡诊、催乳师催乳服务;⑤专家团队、专业设备未达到约定标准;⑥未尽保持室内卫生义务致使苍蝇在婴儿脸上爬行;⑦未按约提供理胎发和拍摄新生儿照服务;⑧承诺消费者入住月子中心后退部分款,后未按约退款。以上案例中,月子中心提供服务与合同及宣传不符的行为,在侵害母婴合同权益的同时,也侵害了母婴作为消费者的真情知悉权、公平交易权,其中2 件案例因机构提供的服务与合同及宣传严重不符构成了对消费者的欺诈,消费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了惩罚性赔偿。
35 件案例因月子中心原因无法履行合同,消费者要求解约、退款和/或赔偿,均得到法院支持。①4 件案例中,机构因无法按时提供月嫂、房间等原因无法履行合同;②29 件案例中,机构因未正常营业、停止营业甚至注销无法履行合同;③1 件案例中,消费者因机构未能提供相关服务的合法资质证明文件而要求解约;④1 件案例中,消费者因机构擅自变更约定的服务地点而要求解约。这些案例中,消费者的真情知悉权、公平交易权更是被严重侵害。
15 件案例中,消费者提出解约退款未果诉诸法院,法院支持其中10 个案件中的消费者退部分、全部或双倍返还款项,这些消费者理由包括:①消费者因得知其预定的月子中心有多名婴儿感染患病、机构被刑事调查等消息后基于内心不安提出解约退款;②消费者因胎儿染色体异常引产无法履约;③消费者因妊娠糖尿病无法赴海外生产;④消费者因签证被拒无法实现海外生产坐月子;⑤消费者因有早产风险要求取消次日赴海外生产及坐月子服务合同;⑥因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消费者担心感染风险而要求解约;⑦消费者与机构约定一年内未怀孕则机构退还消费者意向金,后机构未如约退款;⑧消费者因家庭关系等私人原因改变出国生子初衷要求解约退款,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虽认定合同关系未能正常履行的责任在消费者,但认为月子中心提供的格式合同明显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负担,且机构未能举证证明对上述条款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因此支持机构退还消费者大部分预付款。
(三)其他可能侵害母婴权益的常见情形
1.不正当价格行为
尽管月子中心的价格行为属于《价格法》规定的市场调节价,但仍应执行合法、正当的价格活动。实践中遭遇的月子中心不正当价格行为不少,比如广告宣传价格与实际价格不符,涉嫌《价格法》第14 条第4 项的“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侵犯了消费者的真情知悉权、公平交易权。
2.泄露客户信息
月子中心将客户资料泄露给其他母婴摄影、亲子游乐馆、早教机构、母婴用品销售等关联商家,消费者对此举证困难,个人信息保护权受损。
三、基于母婴权益保护视角的监管对策建议
政府重视、分工明确、监管有效,是母婴保健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9]。下文将从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依据、监管手段等方面提出完善监管的建议。
(一)理顺监管主体
1.实践中落实主要监管部门
尽管早在《母婴保健法》出台时,已提出母婴保健工作主管部门为卫生行政部门,但正如前述,各方对于月子中心主要监管部门的认识并未统一。如西安市人大调研报告建议将卫生行政部门与商务行政部门共同作为月子中心行业的主管部门[10];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报告建议将卫生行政部门列为行业主管部门[2];更有专家建议可仿照比较成熟的养老机构监管模式,由民政部门主管月子中心[11]。但新近《婴幼儿照护指导意见》从政策层面明确了婴幼儿照护服务应由卫生行政部门牵头监管,因而各地必须将月子中心的牵头监管部门统一为卫生行政部门。
2.强调其他重要监管部门的地位和职能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前述,长久以来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月子中心监管中实际承担着主要职责。但由于《婴幼儿照护指导意见》中的婴幼儿照护机构同时包含了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机构,且强调普惠优先,因而文件才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置于监管主体末位。月子中心可归于营利性婴儿照护机构,其服务对象、范围超出了婴儿照护机构的范畴,其超出部分中的许多营业事项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范畴。因而,无论从法定职责还是实践做法,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理应作为月子中心重要监管部门。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绝大多数的月子中心母婴人身损害案件,均可归因于照护人员素质问题,而其中许多人员甚至是“持证上岗”。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因负责育婴员、母婴护理员、保育员、家政服务员、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厨师等的资格准入与培训,其在月子中心监管中的重要性应被强调。
关于民政部门,诚然,月子中心与营利性养老机构在服务需求、经营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不同点却也显而易见:即便营利性养老机构也带有强烈的公益性,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同时,民政部门的主要职责为保障基本民生,促进资源向薄弱地区、领域、环节倾斜。而月子中心完全为市场运作,对象为中高消费人群,其监管不应照搬养老机构,民政部门在月子中心监管中的作用显然无法与前述重要监管部门相比。
关于监管部门之间如何形成良好互动,《婴幼儿照护指导意见》中有提及,同时可借鉴比较成熟的养老机构多部门共同监管工作方式,如2019年广东省《关于进一步做好养老机构登记备案和监管工作的通知》第三部分。
(二)确定监管对象范围
1.传统模式月子中心
传统模式月子中心主要为母婴提供集餐饮、住宿、照护为一体的服务。传统模式月子中心在实践中登记的名称五花八门,给消费者进行消费选择造成困难。“中国裁判文书网”纳入案件中44家属于传统模式月子中心,除2 家隶属于民营医院而没有独立的机构名称外,注册名为“产后母婴护理服务”“母婴护理(服务)”“母婴服务”“月子服务”“产后调理”“母婴健康管理”公司22 家;注册名为“家庭服务”“家政服务”公司7 家;注册名为“护理服务”“护理之家”“健康管理(服务)”公司6 家;注册名为“健康咨询服务”“健康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贸”公司7 家。为避免因监管对象“名不符实”造成监管盲区,实践中监管部门不能仅凭登记外观而必须以机构实际提供的经营活动范围确定监管对象。更为重要的是,监管部门应规范月子中心的冠名行为。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企业应根据其主营业务,依照国家行业分类标准划分的类别,在企业名称中标明所属行业或者经营特点。据此,月子中心的冠名无非两种思路:一是遵循行业分类,传统模式月子中心行业归类可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的“居民服务”,但其究竟归属“居民服务”中哪一小类(“家庭服务”“托儿所服务”抑或“其他居民服务业”)尚未确定,因此不宜以“家庭服务”“家政服务”冠名,更何况月子中心实际提供服务远超传统家庭(家政)服务范畴;二是遵循经营特点,如果传统月子中心以经营特点冠名,那么无论名称是“护理”“健康管理”等都应加上“母婴”(或“月子”“产后”)字样,以体现其服务对象为母婴的经营特色。而案例中一些传统模式月子中心以“咨询”为名,这既非以行业分类也非以经营特点冠名,实际上属于超范围经营。
2.创新商业模式月子中心
月子中心属于商业利益驱动的新兴行业,发展过程中创新动力更足,增加了确定监管对象范围的复杂性。①移动月子中心。为了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传统月子中心利用移动互联网新技术拓宽了经营范围与营销模式,提出“移动月子中心”概念,即居家也能享受月子中心提供的母婴健康护理、医师上门巡视、产后身心恢复课程、月子餐送餐等服务。费用通常较传统模式月子中心降低不少。但其提供服务的项目、方式多种多样,其监管部门、方式较传统月子中心有较大不同,实际上增加了监管难度。②海外生产。从监管角度,由于实际生产、坐月子的地点在海外,同时这些机构大都注册为咨询类公司(纳入案件中涉及海外生产坐月子的案例为20件,涉及的12家机构注册名为“健康咨询”“商务咨询”“医疗咨询”“咨询服务”“国际<投资>咨询”),国内监管部门根本无法实地监督检查,仅能监管其提供咨询服务的行为。从消费者角度,尽管我国现行法律并未禁止海外生产,却可能面临诸多风险,包括长途飞行可能造成的安全健康风险,当地法律政策的限制和变动风险,当地月子中心涉嫌违法行为(如税务欺诈)而停业的风险,客户因出国心切而被卷入签证欺诈、诈骗医院的风险,实际待产和坐月子服务与合同描述不符的风险等,而权利一旦受损,因侵害行为发生在海外,权利救济亦较难实现。
(三)制定强制性监管措施
现行关于月子中心的相关标准均为推荐性标准,无法成为监管的直接依据,实践中,至多按照一般宾馆住宿、饭店堂食、商品服务销售监管。然而,产褥期母婴的特殊生理状况亟须强制性监管依据予以保护。具体建议如下。
强制设置医务室、配备医护人员。现发展阶段,除少数月子中心由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举办外,绝大多数为普通民营资本举办,很少主动申请行医执照(比如某调查走访的8 家机构中,仅1 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12]),而产褥期的母婴对于医疗服务需求非常旺盛,月子中心为满足需求却未取得执照开展医疗服务,便涉嫌非法行医。例如北京市朝阳区原卫计委认定某月子中心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为产妇开月子汤水,通过足浴方式为产妇治疗疾病,为婴儿治疗湿疹的行为违法,给予行政处罚[13];又如韩国在产后照护发展的早期阶段,其产后护理中心被归类为“服务企业”,以至于其提供出诊医师医疗服务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服务法》[14]。或许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我国台湾地区的产后护理之家被要求必须具备医疗资质。同时,应根据机构规模强制配备相应数量符合资质的固定执业护士和(巡诊)医师,避免贻误抢救时机、拖延病情等严重后果。某调查显示,12.5%的护理专业学生毕业后愿意去月子中心就业[15],却碍于大多数月子中心不能挂靠护士证。若强制要求月子中心设置医务室,则可解决月子中心无法挂靠护士资格证而流失护理人才的问题[10]。要求月子中心至少配备相应数量的巡诊医师,为妇儿常见病、多发病提供医疗服务,医务室亦可成为医师的合法执业机构,杜绝当前许多医师“走穴”月子中心,游离于卫生行政部门监管之外。
设置其他服务人员的配备标准。除医护人员,月子中心其他从业人员素质也直接决定母婴健康权益。必须强制月子中心根据不同规模配备育婴员、公共营养师、(若有提供餐饮服务)厨师等各类人员。制定涉及母婴健康的环境、设备等硬件配备,以及涉及母婴健康的服务、管理,尤其卫生、消毒管理的强制性标准。与普通公共场所相比,月子中心对于环境、设备的要求显然更高,必须制定更为严格的标准。大致框架和内容可借鉴《产后母婴康复机构行业管理与服务指南》《月子中心服务团体标准》以及前述6 部专门规定月子中心机构与服务管理的标准。强制月子中心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合同并规定合同要素。具体可借鉴《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第11 条,《淮北市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第30条等。
(四)完善监管手段
监管部门除承担行政许可、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职责之外,还应充分发挥行政指导等现代监管手段的优势。
监管部门协同行业组织对从业机构和人员进行工作指导。比如相关监管部门强制要求月子中心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的同时,还应出台合同示范文本指导合同行为;针对月子中心频繁曝出的感染事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指导采取改进措施,消除各类感染隐患[12];目前一些行业组织已开展了对于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如第一届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开设的产后母婴康复适宜技术培训班。
监管部门协同行业协会对机构进行评级。我国台湾地区从2013年起由卫生部门每年组织对产后护理之家进行评鉴定级,评鉴结果分为合格(优等、甲等、乙等)及不合格(丙等、丁等),并向社会公布[16]。目前我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做法,如上海市健康产业促进协会出台《月子中心服务团体标准》,首批达标机构已入选。这无疑能使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得到更为充分地发挥。
监管部门应向民众宣传科学的产褥期保健知识,引导理性消费。这也是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获得消费知识权的应有之义。《婴幼儿照护指导意见》提出婴幼儿照护服务以“家庭为主”,产褥期妇女与婴儿的照护也以家庭照护为主要方式,因此监管部门首先有义务为这些家庭提供充分支持和科学指导,否则将引发许多安全、健康问题。如某调查显示,59.3%的妇女报告了至少一个与怀孕和产褥期可能有关的健康问题,一定程度上与产后中国传统饮食和行为有关[17];如新闻报道了新手母亲因盲从某婴儿睡眠商业机构的指导放任3 个月龄婴儿长久趴睡而窒息死亡。因此,消费者对于月子中心的消费选择应是建立在监管部门已经提供了充分、科学的支持之上的不冲动、不跟风、结合自身特点和需求的选择。同时,许多文献肯定了在月子中心推行科学产褥期保健的积极意义[18-19],因而消费者即便选择在月子中心进行产后恢复和婴儿照护,相关监管部门同样也有义务为这部分人群提供科学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