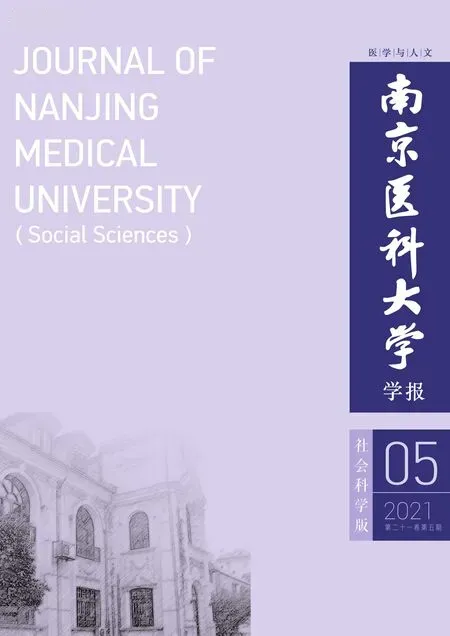博济医院研究综述
2021-12-24朱素颖
朱素颖
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网络中心,广东 广州 510120;2.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120
博济医院始建于1835年11月4日,是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被公认为近代医学入华的源头,开启了中国医学的新篇章。也正因此,博济医院是医史学界探讨“西医东渐”的一个重要节点,研究文章汗牛充栋。本文以国内外所刊博济医院的论述文章为考察对象,对关于博济医院的研究进行整理、回顾和述评。
一、1949年以前与1949年至1980年
第一代医史学者都在个人撰写的中国医学通史中阐述了博济医院的建立和发展,将其作为“西医入华”“西医东渐”的一个关键环节,介绍其在中外医学交流、西医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文章或专著中关于博济医院的资料比较分散,篇幅也很短小,对事实的介绍极为简略,许多具体史实没有详细说明。1909年丁福保的《历代名医列传》是较早提到博济医院的专门著作,他在当中为博济医院的嘉约翰与黄宽两位医生作传[1]。此书不到5 万字,使用浅显文言文写作,被评价为“少而精、简而专”[2],丁福保关于嘉约翰的列传,篇幅不长,前后不过4页,但这是目前已知的首位西洋医生被中国学者作传,首创之功不可没。丁福保对嘉约翰给予了高度肯定:“各国医生割症之多,无出先生右;先生之割砂淋,尤为全球巨擘”“粤人无贵无贱,无不知有嘉医生其人也”[1]。1909年,余学玲在《医学世界》上发表《中国人始留学欧洲习医术者黄公绰卿行述》[3],对其生平事迹进行了简单的阐述。文末写道:“凡所叙述,皆一本事实,博济医局诸先辈,倘犹有存者,亦当能知其梗概也。”丁福保在《历代名医列传》中转录了此篇[1]。
陈邦贤在1920年版的《中国医学史》一书中,将英国人合信来广东著《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全体新论》等书作为西洋医学输入中国的开端,博济医院记载为嘉约翰创办,时间定在合信之后。主要记载了嘉约翰翻译医书,开展包括女医教育在内的医学教育,以及黄宽的事迹贡献,记载不详尽,西洋医学输入中国在此书中为“第九章”[4],博济医院的记录几乎占了全部,但此章共3 页。王吉民在1932年版的《中国医史》一书中介绍了博济医院的奠基阶段,篇幅约15 页,以伯驾、郭雷枢、雒魏林等人早期活动为中心,主要材料来源于《中国丛报》和广州以医传道会的年报[5]。陈邦贤在1937年进行了《中国医学史》第二版的修订补充,较第一版有较大改动,将内容分为上古医学、中国医学、近世医学、现代医学、疾病史5 篇,叙述中国医学之起源与演变、医术之发展、外国医学之传入等问题[6]。在此修订版中,陈邦贤依旧将“西洋医学输入中国”独立一章,将博济医院作为外人设立医院的起源,但记载得也很简略,博济医院占了约一半以上的篇幅,此章亦不过5 页。关于“西洋医学之输入”主要引用张星烺于1934年所作的《欧化东渐史》,并补充嘉约翰和黄宽的事迹概况[7]。陈邦贤对其评价为:“这篇记载,虽然有一点尊崇外人,似乎失却民族的自信力;但是对于西洋医学的输入,是很确实的史料。”陈邦贤书作于巴黎和会后,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思想倾向不可避免地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表达出民族复兴、文化复兴的深层诉求,而使得他在医学史书写的探索过程中更重视中国人的成就。张星烺1934年所作的《欧化东渐史》提纲挈领,“西国医学之传入”独列一段,当中关于伯驾建医院一事仅有一句[7]。此外,李涛在1940年的《医学史纲》中提到博济医院的篇幅仅有4页,虽然他对中国整个新医建立阶段的介绍也不过10页,但从公元13世纪到1933年间的所有医院中,博济医院所占比重最大[8]。这些论著中关于博济医院的记载,都不成体系。
王吉民在《伯驾利用医药侵华史实》[9]和《美帝利用教会医师侵华史实》[10]两篇文章中,认为伯驾以医药传道为名、行调查情报之实,博济医院本质上是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工具,但在一系列对伯驾政治阴谋的揭发与控诉中,他依旧阐述和肯定了博济医院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具体贡献与成就,将博济医院的日常医疗工作与西方的文化侵略进行了区别。王吉民发表于1951年及1954年的这两篇文章足可为1949年至1980年间关于博济医院医史研究的代表。其余相关的文章不多。
目前,关于博济医院本体研究的专门论著主要有两本,作者都是外国学者。一本是博济医院原院长嘉惠霖所撰《博济医院百年》。嘉惠霖为内科医生,1909年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前往岭南大学工作,1930年开始主持博济医院事务直至1948年退休,1949年离开广州回美国,嘉惠霖在广州行医40年[11],对博济医院事务极为熟悉,因此,他于博济医院建院100年之际,利用业余时间广泛收集博济医院资料,总结了博济医院的百年历史,用英文撰写了《博济医院百年》一书,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此书综合运用了许多英文第一手资料,以及医院历史当事人、见证者的口述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是,他未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此书内容庞杂,条理不清,记载混乱,仅可看作回忆录而非历史学著作。
另一本专门著作为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Sara Waitstill Tucker 博士所作的博士论文《The Canton Hospital and Medicin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1835—1900》,以博济医院与19世纪中国医学的关系作为讨论中心,此论文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很多观点放至今天仍未过时。例如“在普遍仇视西方的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医疗互动具有怎样的特殊性,使得西医在中国能够从包裹着它的更常见的中西关系模式中脱颖而出?从这个问题出发,可以进入一个日益壮大的领域——技术转移与文化变迁。进入这个领域,也就接近了另一个问题——技术转移的效果在哪里,是加强还是削弱了,以及是否可能在一个给定的范围内统一对这种技术影响进行评估?”作者认为,“博济医院的历史表明,西方技术至少在特定的形势下——比如现代西医有能力在秩序混乱的十九世纪中国,受到普遍欢迎及具备相当的建设性。当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各种不同技术被接受的程度差异,应该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此论文最大的优点在于大量使用美国所存的教会档案,遗憾在于较少引用中文资料。
二、1980年至2000年
博济医院的研究在中国真正得到蓬勃发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期间的成果大部分以人物传记为研究范式,阐述博济医院发展史上重要人物的活动和经历,研究集中在第一第二任院长伯驾及嘉约翰身上,人物研究构成了博济医院发展史研究的主体部分。
(一)关于伯驾的研究
关于伯驾的研究最为丰富,这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中国学者中首先出版的专著是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随后,他又出版了《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这两本书是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开山之作,详细介绍了鸦片战争以来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全过程,包括传教士的医疗活动,将传教士传记作为展现近代中国的一幅全息图。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中,顾长声以博济医院的传教士医生作为典型,考察了教会在华的医疗事业情况,对大部分传教士医生的个人贡献和成就动机给予了肯定,认为他们拥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崇高的宗教信仰[12]。在《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中,顾长声专门为博济医院的创办者伯驾设立了一章,他引用了大量的英文原始档案文献、书信日记和口述材料,为伯驾进行了人物评传,其中广州新豆栏医局(博济医院前身)是该章节的重要段落,从中可以看出伯驾在华的医疗活动是博济医院草创阶段的完整反映。与前一本书相比,这本书对博济医院的活动介绍得更为详尽,补充了一些具体细节,使用较多的篇幅强调了伯驾利用医学进行传教的目的[13]。
美国人爱德华·V·吉利克于1972年写作了《伯驾与中国的开放》一书,此书对伯驾来华开展医疗传教事业及参与美国对华外交事务的过程记载得极为详细,这是此书最大的特点,相关英文文献、书信日记,使传记、研究观点和史料互济互证、相得益彰,具有珍贵价值。爱德华·V·吉利克是韦尔兹利学院的历史学教授,抗战期间曾经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任教,书成于美国,这使得他拥有了与其他中外学者都不一样的学术眼光,对伯驾的评价更为中肯与客观。在汗牛充栋的关于伯驾的评传中,此书是一本标志性的著作。他通过博济医院来思考中西关系,思考中西文明的冲突,认为现代西方医学传教士改变了中国医学的实践传统,医学作为美国传教机构的基本角色,是西方福音进入中国土地的一个完美例子。2008年此书由复旦大学董少新翻译介绍进入中国,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谭树林的《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活动研究(1834—1857)》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弥补了中西方学者材料运用各有侧重的缺陷,对中西方学者在伯驾及其主持的博济医院的第一阶段工作进行了比较研究,此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对过往国内外所有关于伯驾的研究进行了完整的文献综述,但是通过这一系列事实对伯驾进行客观评价上没有新突破。北京大学陈琦在《痛与不痛——麻醉术的传入》一文中,对伯驾操作的中国第一例麻醉术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考据,对既往研究所忽略的具体日期、手术所用乙醚和麻醉仪器的来源等信息,进行了严谨辨析,认为近代中外医学交流的标志性事件——第一例麻醉术的成功时间应是1847年10月4日[14]。该论文在回答博济医院所发生的技术转移问题上作了迄今最为深入的探索。
(二)关于嘉约翰的研究
关于嘉约翰的研究成果较伯驾薄弱,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王芳的博士学位论文《嘉约翰与晚清西方医学在广州的传播(1853—1901)》[15]是目前仅有关于嘉约翰的中文专门论著。这篇文章对嘉约翰来华后的工作及贡献做了详细的梳理,以此填补西医入华未尽之空白。嘉约翰为人无私,建树至伟,他在华工作47年,当中有45年主持博济医院,因此尽管该文的研究以嘉约翰的医事活动为中心,但是博济医院的医疗诊治和经营管理情况、博济医校的教学活动和博济医学生参与中国社会生活转变的过程都得到了较好的补充。
外国学者方面则有卡罗琳·麦肯德利斯的专著《苔花如米小——嘉约翰的伟岸一生》,据美国弗兰德斯大学历史系教授许光秋评价,这是一本极为出色的嘉约翰传记,著作囊括了嘉约翰所有的出版物及1854年至1900年间博济医院的年报数据[16]。但是这本书出版的数量很少,仅少数图书馆有藏本。另外一些关于嘉约翰的论述文章都是期刊学术论文,基本上都是从医学传教及中西文化交流这个角度展开的,主要有中山大学梁碧莹的《嘉约翰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17]、福建中医学院王尊旺的《嘉约翰与西医传入中国》[18]、广州医科大学郑维江的《嘉约翰与早期博医会》[19]、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王芳的《嘉约翰与晚清广州医疗建筑》[20]等,对他的具体历史活动进行实证研究。
(三)关于关约翰的研究
随着博济医院的历史档案得到进一步发掘,博济医院第五任院长关约翰近年来也进入了国内学者的视野。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王惠贤专门就关约翰的生平贡献进行了研究,硕士论文《美国传教医生关约翰与博济医院(1885—1914)》[21]对关约翰的个人背景和工作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结。由于关约翰处于世纪交替之际,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第二代医学传教士的代表,他在博济医院工作期间作出的调整与改革,能够对博济医院如何处理和适应时代潮流这一历史问题作出具体解释。广州本土学者陈晓平也曾在《澎湃新闻》的“私家历史”栏目对关约翰的医事活动进行了详细补充,《中国第一例剖宫产手术的背后》[22]一文篇幅短小,问题意识却非常大,从媒体视角、医生视角、本土视角三个方面,立体呈现了中国第一例剖宫产手术这一标志性事件,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材料分析能力与卓越的史见史识。
(四)关于黄宽的研究
黄宽是我国第一位史载的留学欧美医学生,他的事迹多为人所提,但限于资料,至今没有一本专门性论著。1954年,王吉民发表《我国早期留学西洋习医者黄宽传略》[23],对余学玲1909年的记载进行了进一步补充扩展,并列出了黄宽年谱。1992年,张慰丰发表《黄宽略传》[24]。2006年,中山大学刘泽生发表《首位留学美英的医生黄宽》[25],此文第一次完整描述了黄宽的学习经历,并详细补充了他的社会关系——非同寻常的岳家,最大的创见在于就性格对他个人事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评述,其叙事风格平易浅白,可读性极强。之后对黄宽研究有较大发展的是北京大学张大庆,《黄宽研究补正》[26]使用了过往从未有人使用的黄宽在爱丁堡大学留学时的档案资料,对黄宽所获学位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另外,北京师范大学王华锋在《黄宽: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27]一文中,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对黄宽进行阐述,这一点台湾学者苏精在《西医来华十记》之五记《黄宽的西医生涯与中西文化夹缝》[28]进行了扩展,此文使用了迄今最详尽的史料,阐幽发微,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
(五)关于其他人物的研究
此外,博济医院发展史上的一些标志性人物,如伯驾的学生关韬,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以及将博济医院带至历史新阶段的李廷安等人,国内外也有多篇相关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有中山大学刘泽生的《中国近代第一位西医生——关韬》[29]、英国皇家历史学院院士黄宇和的《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第二军医大学华伟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医学》[30]以及广州中医药大学李永宸的《公共卫生先驱李廷安的中医情缘及其对岭南地区医学发展的贡献》[31]等等,这些文章大多是期刊学术论文,对人物的生平、学医教研经历、成就贡献等进行钩沉及梳理,补充了博济医院发展史上的未详之处。由于李廷安为我国第一位公共卫生博士[32],李永宸对其学术思想及年谱进行了详细的修订整理。
三、2000年至今
中国医学史改变研究方向,从博济医院开始。新千年后,主流医学史学出现了大转弯。台湾“人文组”院士、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梁其姿首先以《十九世纪的广州牛痘接种业》一文,对近代广州地区广义的医疗文化进行了探讨。她以博济医院为中心,对如何呈现“中国医学现代化”的复杂方面,作出了具体示范,从而明确提出从医学史的角度出发,重新建立新的历史观,以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准去追溯和定义“现代性”的问题[33]。梁其姿的一系列文章标志着中国医学史研究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其后,不少关于博济医院的著作都转往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方向。大量书信、日记、实物、图像、游记、文学作品以及新的档案材料被采用,资料来源更为拓展和丰富,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特征非常明显。典型成果有美国弗兰德斯大学许光秋的《美国医生在广州——中国的城市现代化(1835—1935)》[16],此书以博济医院为中心对广州的政治、经济、社会进行深刻考察,视伯驾、嘉约翰等医学传教士为中国现代化的推动者。许光秋将博济医院置于全球史视野之下进行研究,认为其是全球现代化的一个要素,是全球现代化发展中的一场运动,并率先关注了博济医院在公共卫生、女权运动和慈善活动方面的积极影响,首次明确提出了博济医院的研究工作对中美外交关系政策制定的参考性作用,较好地回答了医疗技术的变革如何推动社会变革,医疗创新的广泛应用如何推动社会转型这一新问题。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的Freerk Heule 则在《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and Peter Parker,Two Early Nine- teenth-Century Missionary-Ophthalmologists in China:a Case of(Inter)Cultural Anthropology》一文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以郭雷枢及伯驾两位传教士医生为主角的布面油画作品展开分析。作者本意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出发探讨19世纪早期中国的医学和思想交流,结论认为郭雷枢和伯驾是早期科学家群体的真正成员,他们帮助塑造了现代中国。论文提到了中国医生更关注的另一点:跨文化的医学关系及中西方医患关系的异同,认为西医学进入中国之初便建立了良好的医患关系,这是基督教、免费医疗、人性化管理、规避医疗风险及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观念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博济医院相关文物的研究
博济医院延续至今已180 余年,除了各种文献资料、照片外,还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物,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图书馆。这些器物史料作为博济医院最原始的生存资料,近年来已被各历史学者独立使用,从具体器物入手能考察博济医院的历史踪迹和文化意义,以小见大,更能牵涉宏大,挖掘出众多叙事宏大的历史题材,开启学术场域的重大变局。
博济医院文物比较集中的地方有耶鲁大学医学院图书馆及神学院图书馆、伦敦盖伊医院、中山大学医学博物馆、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史馆、中山大学校史陈列馆以及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上海民国医药文献博物馆等。耶鲁大学医学院图书馆除了藏有博济医院1935年前的所有年报和伯驾手稿外,还有伯驾聘请广州以绘西洋画闻名的画家关乔昌所绘制的患者病理生理画像110幅中的86 幅。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则藏有嘉约翰留下的部分书籍档案。伦敦盖伊医院藏有关乔昌留下的其余患者画像。关乔昌是中国西洋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他的这批医学人物画作已有多篇博硕士论文及期刊学术论文从不同角度进行专门分析。如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胡艺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清代西洋肖像画研究》[34]中对这批画作题材内容、表现风格、创作年代以及人物背景进行了考证分析,揭示了关乔昌一系列包括患者肖像画在内的画作,在中国沿海西洋美术的兴起和发展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历史作用,填补了博济医院在美术史和医学史交叉研究上的空白。
中山大学医学博物馆、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史馆、中山大学校史陈列馆等所藏博济医院文物最为丰富,既互有重复又互为补充。此外,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继承了原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所藏的博济医院部分文物,包括中国第一位女西医张竹君的毕业证书。可惜的是原馆长王吉民藏于该馆的第一本西医期刊《西医新报》已散轶[35]。上海民国医药文献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完整展示民国时期医药文献的专业博物馆,为民间机构,由医药实业家上官万平创办,收藏了大量与医药相关的书籍、杂志、报纸、广告、证书、文件、处方、信札、照片、商标、药械等,其中为博济医院专门列出一个展柜,包括当年博济医院所使用的家具、药械、广告传单、医护证书、照片、报纸、书籍期刊、地图等文物。中山大学朱素颖曾在《孙中山就读博济医院教学机构名称辨析》[36]一文中,使用了上述几家博物馆的器物史料,辨析得出:今大量出现的“南华医学堂”从未作为官方名称存在过,该名称来源于时人翻译混乱,后以讹传讹流传至今。
除了可移动文物外,博济医院尚遗留下建于不同时代的近现代建筑多栋,该建筑群现已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及广州市越秀区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建筑和纪念地、纪念碑等史迹,也逐渐开始被建筑史的研究者所使用。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孙冰便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广东省医院建筑发展研究(1835年至今)》[37]中,较为全面细致地梳理了广东省医院建筑的发展历程,其中博济医院建筑作为近现代医院建筑的代表,布局、风格、气候适应性和鲜明的岭南建筑特征得到了比较好的归纳和阐释,为博济医院在建筑史和医学史的跨学科应用进行了新的探索,但该文写作上比较粗糙,一些材料应用不明所以,注释也有较多不规范之处。博济医院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博济楼迄今仍是该院的一张文化名片,对其进行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因此朱素颖在《博济医院博济楼建筑之缘起、背景及特点研究》[38]一文中,将博济楼放在广州近代城市建筑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研究,补充了建筑过程、人物相互关系等历史细节,对其建筑美态、功能作用、现存面貌和未来发展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归纳。除了伦敦盖伊医院外,笔者走访了上述所有博物馆和院史馆,实地考察了馆藏文物及进行田野资料的采集。
五、展 望
在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博济医院发展过程上,前人与时贤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这些研究极其分散,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旨趣作出不同问题意识的具体实证研究,缺乏统一的宏观讨论,从来没有一个凝固的主题将这些广泛的研究内容加以整合,各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开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尚有许多研究质量不高,甚至是人云亦云、滥竽充数之作,漠视学术规范,不断重复抄袭前人成果,即便是材料也是千篇一律,换个题目就将前人成果署名出版,遑论问题意识、研究理念及方法上推陈出新,此等盗名窃誉之风切不可长。
历经180余年,作为一个划时代的象征,博济医院遗留下来的材料非常丰富,但是投入的研究力量还严重不足,尚有大量的空白等待填写。如何更贴切地使用现代化进程的视角,通过呈现博济医院的“新陈代谢”,来体现近代中国医学的百年巨变?如何以博济医院为中心,完整地展示近代医学知识在广州地方社会的积累全过程?如何以博济医院为立足点,在不同的文化视野下考察西方医学的全球化?是否可能从商业、政治、文化等角度,分析博济医院在广州地方社会扮演的角色?是否可能以博济医院为切入点,对中国医学史的百年研究进行深刻反省和审视?能否抛开博济医院的地方性,总结出中国医学史上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相对其他研究对象,博济医院的院产至今还存在,并继续对广州乃至中国医学史产生重要影响,能否对博济医院进行更大范围的田野调查,利用历史人类学等各种史学新方法,对博济医院的既往问题进行新的诠释?器物史料背后是否蕴藏着更深刻的符号意义,是否能够从中得出博济医院医疗物质和日常生活的勾连关系以及探讨思想观念的流动过程?博济医院是否可以加入殖民权力和医疗空间的讨论,在进一步拓深和扩展殖民医学上做更多的尝试?
这已有的坚实的研究基础和丰富成果以及可预见的未来,都让人产生更为乐观的期待,随着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新的研究方法的不断涌现,以及历史学整体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关于博济医院的研究将会对构建中国医学史乃至中国历史研究的特色产生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