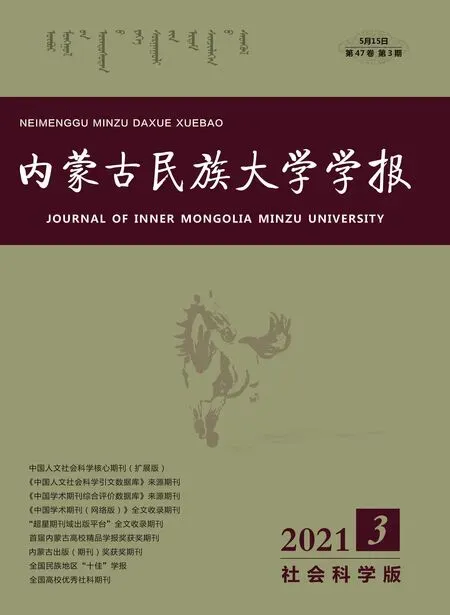阿来小说的人物“腔调”
2021-12-23王妍
王 妍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43)
阿来作品的诗性总是令人难忘,那种悱恻却透明的忧伤缠绕在人物身上。好在这些人物多是他故乡里那些他最为熟稔的乡亲,错综而鲜活的感受中和了诗性的缥缈、虚浮,呈现出独特的生命纹路。阿来立足于“嘉绒”本土,这片坦荡、包容的自然空间造就了他大巧若拙地看待世界的眼光与面对问题的方式。虽然,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也影响着人物的生命走向,但阿来用他的冷静与才情,在变动不羁的时代中始终坚持一种写作的纯粹性,“文学的教育使我懂得,家世、阶层、文化、种族、国家,这些种种分别只是方便人与人互相辨识,而不应当是竖立在人际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当这些界限不止标注于地图,更是横亘在人心之中时,文学所要做的,是寻求人所以为人的共同特征,是跨越这些界限,消除不同人群之间的误解、歧视与仇恨。文学所使用的武器是关怀、理解、尊重与同情。”[1]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没有深沉的算计,总是用貌似简单的直接来面对烦扰的世事,做着理解起来似乎也十分简单的事件。他们朴拙而旷达,有时愚钝,有时睿智,在不断的行走与寻找之中展开对于世界与自我的问询。
一、出走与弃绝:稚拙行走的阿古顿巴
文学最能触动我们的往往是原初的风景,而阿古顿巴作为藏民族的精神典范,在他的身上显示了藏民族的根源性格。阿古顿巴,也有译为“阿古登巴”,四川阿坝藏区称作“顿巴俄勇”,“俄勇”为舅舅之意,“阿古”是叔叔的意思,“顿巴”是导师的意思。据传阿古顿巴是后藏①江孜县人,原是贵族庄园主陆卓代瓦家的农奴。他用计惩戒了欺压乡民的庄园主,将其骗到雅鲁藏布江淹死,并因此逃离家乡流浪四方。在流传下来的故事中,阿古顿巴聪明机智,他利用人性中的贪婪、吝啬和愚蠢,运用智谋巧妙地戏弄富商、对抗权贵,为贫苦的农奴伸张正义。这些流传下来的故事短小精悍、轻松幽默,却又主题雷同,寄托了旧时代广大农奴向强权复仇的精神诉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阿古顿巴是如何在藏族家庭的火塘边一代代被言说、叠加,成为一种象征和指代,他作为民间智慧的集大成者,早已超出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古顿巴对于阿来人物谱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更像是藏族文化传统中的“发愿”。在这个形象身上不仅展示阿来的自我文化定位与人文关怀,而且也作为小说建构的重要因子屡屡出现。在《格萨尔王》中,阿古顿巴就直接出现在与格萨尔王的对话之中。此外,我们还从《尘埃落定》的傻子、《月光里的银匠》中的达泽、《格萨尔王》中的说唱人晋美、《格拉长大》中的格拉、《达瑟与达戈》中的达瑟和达戈、《云中记》中的“半吊子”的祭师阿巴等人的身上,找到阿古顿巴式的记忆与表达方式。
《阿古顿巴》是阿来早期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发现阿来最初的小说观念的形成和成熟。我最早注意到阿来短篇小说人物的‘拙’性就是这篇作品。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说,阿来小说所呈现的佛性、神性、民间性的因子,在阿古顿巴这个人物身上有最早的体现”。[2]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文本中阿古顿巴的“拙”与小说形式的“拙”相得益彰。阿来并没有对这位导师叔叔进行“新历史主义”式的颠覆性重构,而是沿用了故事的口吻写道:“产生故事中这个人物的时代,牦牛已经被役使,马与野马已经分开。在传说中,这以前的时代叫做美好时代。而此时,天上的星宿因为种种疑虑已彼此不和。财富的多寡成为衡量贤愚、决定高贵与卑下的标准。妖魔的帮助使狡诈的一类人力量增大。总之,人们再也不像人神未分的时代那样正直行事了。”这种充满复杂思辨意义的开头,在后来的《行刑人尔依》和《格萨尔王》中沿用下来。不仅如此,阿来还用了“很少出现”“也未出现”“就不”“尽量不”等大量否定性的词汇对传说中的“空白”进行填补。他铺陈得很仔细,也很诚恳,却在短短几千字的篇幅里套用传说中《给国王算命》②《房子和锯子》《贪心的商人》《分饼子》《阿古顿巴的宝藏》等故事作为叙述的线索。阿来也曾坦言套用这些故事的原因“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村庄,不同的人群里面都有关于阿古顿巴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他是真正代表民间的。”[3]在整体性力量如此强大的时代,只有那些执拗地保持个体姿态的人,固执地连接民族历史过去与现在的人,不断对抗人群的同化、抵御欲望的侵蚀、反叛既定命运的人,才是对当下的世界构成真正挑战的人。阿来用看似漫不经心又近乎沉闷的语调写出了阿古顿巴的一生,加上作者的内秀,使得小说在淡化寓言故事训诫意味的同时,使我们感觉着阿古顿巴身为凡人的犹疑与困惑。
阿来是一个少年老成的天才,孤独和敏感成就了他创作的独特韵致。他的作品有着坚实的文化内核,并注重人物的精神诉求。不同于后来《尘埃落定》《空山》对于宏阔历史的追求,《阿古顿巴》则更倾向于人物的内心体验和自我审视。在阿来看来,只有小说中的人物变成有血有肉的“生命”,小说才有了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讲,青年的阿来书写的是一个成长中的阿古顿巴,在阿古顿巴身上混合了善良与软弱、敦厚与嘲讽、坚定与犹疑,而他的孤独、敏感与迷茫中也渗透了作者阿来少年时的切身体验。虽然阿来基本遵循了传说故事的线索,但阿古顿巴的身份从农奴变为领主的儿子,他的故事就是从背弃拥有巨大世俗权力和话语权力的贵族阶级真正开始的,而这个叛逆者却是一个笃厚纯粹的人,他并没有深奥的计谋,总是用最简单的方式破解看似复杂的机关。同时,他也是一个矛盾的、被凡俗情感缠绕的普通人:他渴望“平静而慈祥的亲情”,却弃绝了贪婪冷漠的领主父亲,走上了崎岖的漫游旅程;他一直追求真理和自由,却听从良心的召唤,被一个没有关系的瞎眼老妇人所羁绊;他深爱着领主的女儿,为其解决了困境,却无法自证身份,形销骨立被当作乞丐。阿古顿巴是一个高尚的智者、隐忍的英雄和孤独的凡人,“是具有更多的佛性的人,一个更加敏感的人,一个经常思考的人,也是一个常常不得不随波逐流的人。在我的想象中,他有点像佛教的创始人,也是自己所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叛徒。”[4]阿来在阿古顿巴身上倾注了纯粹的、智慧的力量,这也是真理与民间传承的力量。
阿古顿巴在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两极间不停往返,而阿来的书写也在“传说”与“现实”之间游弋,甚至不惜借众人之口在“乞丐般”“瘦削落魄”的阿古顿巴面前,描绘传说中“国王一样的雍容,神仙一样的风姿”的阿古顿巴。阿来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传说中是被理想化、无所不能的阿古顿巴,而真实的阿古顿巴却在无望的爱情和恼人的亲情中迷失,两个形象之间的巨大落差,揭示了“传说”的虚妄,而恰恰是那个犹豫落魄、忠诚软弱、有着爱与被爱能力的阿古顿巴,却是最为生动而真切的生命图景。这也是人类自我成长的寓言:人生而混沌,在曲折中经历,在挣扎中澄明,在不断弃绝中走向完满。最后,阿古顿巴在黎明时分“又踏上了浪游的征途”,小说的结尾写道:“翻过一座长满白桦的山岗,那个因他的智慧而建立起来的庄园就从眼里消失了。清凉的露水使他脚步敏捷起来了。月亮钻进一片薄云。‘来吧,月亮。’阿古顿巴说。月亮钻出云团,跟上了他的步伐。”这个充满诗意和浪漫的结局,正像“月亮”在藏族文化中圆满与安详的寓意一样,阿来为弃绝了亲情和爱情之后的阿古顿巴,安排了一条轻逸的道路。
二十年后,阿来重塑了这个想象中十分美好的结局。在《格萨尔王》中,阿古顿巴与格萨尔王相遇时,他依然是那个瘦削、愤世嫉俗、走起路来“像风中的小树一样摇晃不已”的阿古顿巴。在相隔二十年的两个文本中,阿古顿巴出实入虚、自由“穿梭”,最后逃遁到故事中,成为“还在不断创造新的故事,继续在故事里面活着”而“不死的人”[5]232。实质上,这不仅是阿古顿巴形象的延续与深化,也显示了阿来对于文学的忠诚:阿古顿巴矛盾的性格、生命的苦行都没有改变,也不会终结。阿来清醒地意识到:在民间传说中不断被润色、填补的阿古顿巴早已失去本来的面目,他因“活在每个讲故事人的口中和脑子里”[5]232而不断被塑造、被理想化,并成为英雄,而潦倒真实的阿古顿巴则被故事淹没,遁入“无从捕捉”的黑暗。在这个意义上讲,阿来解构了故事的绝对权威,消解了阿古顿巴的神性,还原了一个复杂立体而又矛盾挣扎的阿古顿巴。不仅如此,因为“长得像阿古顿巴”并对“世事懵懂不明”而成为神授说唱艺人的晋美,与阿古顿巴隔空相映,在梦境与现实之中穿梭。晋美脸上挂着阿古顿巴“那种愤世嫉俗的神情”,不断追问。值得注意的是,在《故事:阿古顿巴》一节中,阿古顿巴留下的那顶普通的帽子和晋美华丽的“仲肯”帽子形成了互文关系,前者反映了与权力疏离乃至对抗的态度,而后者则代表了某种权利的获得。格萨尔、晋美、阿古顿巴跨越千年的时空,在现实与梦境之中共生、交流,突破了古老的神话定式,并对神话故事进行了人性的关照和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讲,晋美也与作者阿来有着灵魂的共鸣,他们“将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行间”[6],他们都是孤独而稚拙的行者,背负着寻求和延续民族文化的深沉使命。
事实上,阿来小说有着很强的延续性,他似乎偏爱阿古顿巴传说中“贪财商人的下场”这则故事。阿古顿巴让人帮忙扶住旗杆的故事在《阿古顿巴》《尘埃落定》《空山·喇叭》中都出现过,只是被戏弄的人物身份分别是商人、僧侣、喇嘛,而且故事书写得一次比一次详细、生动。在《空山》中阿来甚至给这个故事做了注解:“他用聪明捉弄那些自以为比他更聪明的人”。旗杆并没有倾倒,只是人自寻烦恼罢了,命运也总是在捉弄自以为聪明的人,也许,是我们想要的太多,才会一步步坠入欲望的深渊,沦为时间的灰烬。在阿来小说中,这些带有明显指向性的故事构成了互文性,不断深化了他对人物形象性格塑造以及对自我精神情感表达的需求。
二、对照与审视:大智若愚的“二少爷”
阿来曾在《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中说过:“在塑造傻子少爷这个形象时……我想到了多年以前,在短篇小说中描绘过的那个民间的智者阿古顿巴……于是,我大致找到了塑造傻子少爷的方法,那就是与老百姓塑造阿古顿巴这个民间智者的大致方法。”《尘埃落定》中麦其家的二少爷与阿古顿巴这个形象之间拥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血流,他们都是天生的智者,在世俗的喧嚣中始终保持独立的姿态;他们拒绝与权力合谋,注定要出走、游离,并给予异化的世界、迷失的人们以警醒。相较而言,阿古顿巴身上更多体现的是理想的沉醉,从他的朴拙中传递的是一种沉重的使命与责任担当;而二少爷的身上更多呈现的是世俗欲望的狂欢与嘲讽。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尘埃落定》是围绕着权力展开,欲望、暴力、复仇等因子与罂粟交相呼应,在土司们心中熊熊燃烧。所谓的虚实、锤炼、境界、风格是成熟阿来的精神追求,而这个时候,傻子二少爷则是沿着感觉的惯性自在地滑行。傻子并不仅仅是权力家族——麦其土司家的一分子,而是作为对照,去映衬和嘲讽这个“聪明人”太多的世界。有时,他会带着几分讥讽,去旁观那些自以为聪明或者被认为聪明的“聪明”人如何去使用和争夺权力。麦其土司、茸贡土司、土司太太、大少爷、尔依、塔娜、桑吉卓玛……除了圣人翁波意西外,每个人物都洋溢着生命的复杂与并不掩饰的贪婪,这种直白、酣畅的“拙”意在阿来以后的作品中并不常见。
与其说,傻子二少爷是阿来为当代文坛创造的一个经典人物,不如说,傻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和姿态。傻子看世界,有着人类混沌未开的懵懂,封闭而又透明,却更接近生命的本质,他看得兴致盎然。“傻子”的身份赋予他教化之外、随心所欲的自由,“我当了一辈子傻子,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7]378“傻子”既是这个故事的参与者,也是一位叙述者、旁观者。他不断地消解、颠覆、反抗,他的边缘视角也成就了新旧交替时代的话语策略。阿来将一群野心勃勃的土司置于历史的死角,看他们如何被躁动不安的欲望所驱使,在财富与权力中心醉魂迷,却无力转圜。我们甚至可以想象阿来在写作《尘埃落定》时是愉快的(虽然他难免为人物的命运而惋惜),其行文酣畅而又不乏炫技的快感。
大量史料的沉积使得阿来对土司世界实在太过熟悉,但他却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努力捕捉人性的幽微,用鲜活的生命来填补碎片化历史的空隙。阿来畅快地书写了一个“比聪明人更聪明”的傻子,而聪明的麦其土司却时常陷入迷茫:“父亲对自己置身的世界相当了解。叫他难以理解的是两个儿子。聪明的儿子喜欢战争,喜欢女人,对权力有强烈兴趣,但在重大的事情上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而有时他那酒后造成的傻瓜儿子,却又显得比任何人都要聪明。”[7]157傻子二少爷经常以十足愚蠢的语言说出深刻的哲理,以滑稽的方式反衬出悲剧的效果,智中有愚,愚中见智,二者相互转换,而我们只需顺着“傻子”好奇的目光,四处打量。
历史突然加速,“我就知道要慢慢来,可事情变快了”,而傻子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月亮在天上走得很慢,事情进展得很慢,时间也过得很慢。谁说我是个傻子,我感到了时间。傻子怎么能感到时间?”[7]262他的简单甚至愚钝中包含着民族的原始文化智慧,使得他能够自动地廓清遮蔽世事的雾障,在社会历史剧烈变动、孕育着重大变革的关口,二少爷成为了“聪明的傻子”并“能决定许多聪明人的命运”。“我”常常被置于这样的语境中,傻子每天早上醒来都在追问“我在哪里?”“我是谁?”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只有傻子才会“在睡梦中丢失了自己”而“心里十分苦涩”[7]179。在危机四伏的土司制度下的末日,众人为权力、金钱争斗,陷入了欲望的癫狂之中;傻子却处在真诚的自我矛盾之中:他一面混沌懵懂,一面洞察世事,未卜先知;他讨厌为权力争斗的自私嘴脸,却放不下权力的诱惑。在他这里,伟大与渺小、高贵与低贱、成功与毁灭、聪明与愚蠢……自然而然地纠缠在了一起,借用拉格维斯《侏儒》中的一句话:“这个模样显出了我的真相,既不美化,也不走样。也许它并非有意要生成这样,但这恰好正是我所要的模样。”[8]最终,那象征着土司无上权力的高大官寨在炮火中化为碎石,而傻子二少爷却提前预言了自己的死亡。他是“新生事物的缔造者”,也被认为是“跟得上时代的人”,在他被俘虏时,“整个山谷,都是悲伤的哭声”。我们发现,阿来又一次近乎执拗地展示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迷恋,傻子热切地等待,甚至不惜与仇家同谋,来完成自我殉道式的死亡,仿佛这场扑朔迷离的仇杀,只是成就“傻子”生命轮回的重要仪式。在以往的解读之中,我们常常关注于主人公壮丽的死亡场景,却忽视了“会当上麦其土司”的傻子的死亡并非源自历史车轮的碾压,他选择在传统的血亲复仇中慷慨赴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不与历史合谋的态度:他拒绝被时代同化,宁愿与麦其家族一起消失,使一切恢复到“尘埃落定”的生命原点。
我们发现傻子二少爷身上的双重性:一方面,他是芸芸众生或者说是原始人性的化身,有着旺盛、强悍的生命力,并饱含朴拙的“痴气”,同时也具有人性的弱点;另一方面,傻子的身上兼具深邃的民族文化渊源以及东方文化的智慧,他被万物皆空的思想所警示,能够超越已有秩序和道德的规约,也清楚在现代性的历史车轮之下土司制度终将覆灭。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是历史的宣谕者。“土司二少爷只是思维不同于常人,行为有些怪异,貌似有点傻,但其实出奇制胜。某些人在一方面表现出超常智慧,他在另一方面就会迟钝。有时演员特容易表现出‘大智若愚’的感觉,‘大智若愚’其实也是有机关的,我只希望是一种自然情绪流露,不去刻意把他当成什么样一个人来表演。”[9]我们感觉到,傻子二少爷既是作者阿来、阿古顿巴、书记官翁波意西,也不是“他”,“傻子”已经超出了我们通常的感知范围,具有了寓言的意味。傻子已经脱离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路数,他保持了人类混沌未开的本真状态,用生命自觉来感受万物;而书记官翁波意西更像是“傻子”的理性、智慧的另一面,二者共同揭示了生命的本质。甚至可以说,傻子构成了阿来式独特的人物腔调与风格:智性朴拙、自在混沌。
三、“蒙尘”与癫狂:达瑟与达戈
大的故事必须要有宏阔的历史作为支撑,而历史的变动之中也必然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中,阿来却用心灵捕捉文字的温度。在《空山》卷三《达瑟与达戈》的开头,作者深情地呼唤着名字“像是箭镞一样还在闪闪发光”却“已在传说中远去”的达瑟。阿来把达瑟描绘成了像阿古顿巴一样“身材高大而动作笨拙迟缓”的人,他“忧伤绝望”并带着“肤浅而又意味深长的笑容”。达瑟与“遥远谷地中的废墟”同名,也是一个颇具寓言性的人物。他把书放在高高的树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看到这里,我们禁不住联想起《迷惘》(1935年,卡内蒂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彼得·基恩教授,一个坚信一切真理皆在书中的“书籍拜物教徒和痴迷的学者”[10]。与基恩教授一样,达瑟也过着自我封闭的生活,他对知识有着最纯净的崇拜,坚信一切的真理都在书中。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达瑟却不是一个坚决而彻底的家伙,他并没有对命运做出预判的能力和勇气。学校复课后,他也曾试图回到城市,这种“回归”不仅意味着他可以继续完成学业,更预示着他将拥有干部身份,永远地离开机村。在返城的路上,他也一度拥有了“行走在虚空之中”的轻盈,读这段描写的时候,我们禁不住想起了弃绝人世情感出走的阿古顿巴。可是,阿来的立意显然并不在于此,他要用现实彻底地贯穿梦想,所以达瑟发现学校“高大轩敞”的图书馆里“书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些东倒西歪的木头架子”,他下定决心“我不想回来念跟文件一样的书了”[11]299。这种执拗,不仅是对特定历史阶段文明异化的驳诘,还有现实层面对干部身份的自动放弃。然而,达瑟并不能像阿古顿巴一样隐匿在故事中,虽然他一度在梦境中“差不多走入银河的灿烂星光中去了”,但梦终究会醒,“在梦境中摔倒的他躺在地上,明亮的银河高悬在天上”。达瑟拒绝了叔叔为他铺就的升官之路,然而,在现实中,他的自我隐遁并没有帮他找到命运的出路。当阿来把达瑟的树屋和达戈的兽皮屋放在一起时,这个象征着趋向封闭的理性空间和极度扩张的欲望世界相互映衬,也揭示了癫狂时代中“善”与“恶”的合谋。甚至可以说,离世索居的树屋是文明萎缩的标志。“树屋倒下,那些书不知所踪后,达瑟就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达瑟了。”甚至在几十年后,阿来再次让达瑟出现在故事中,并用悲悯的眼光审视这个委顿落魄的老人。达瑟有两个不成器、偷电线的儿子,自己也“不过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他的命运昭示着那种被乐观的理想主义所充斥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一味沉溺于知识的消极状态往往只能导致最坏的结果。
联系起阿来在《空山》中多次使用“蒙尘”这个词语:“狭小贫困,让人心灵蒙尘的机村”;“而今,寺庙颓圮,天堂之门关闭,日子蒙尘。人们内心也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什么美好存在了。”[11]114在这个“蒙尘”世界中,单纯憨直的格拉(《空山(卷一)·随风飘散》)死了,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再也没有机会长大,被杀死在谣言的重压之下。在传说中,誓死不分离的痴情男女触怒了天神,化为了达戈和色嫫“永远遥相对望的两座雪山”;在现实中,当前途无量的班长惹觉·华尔丹为了爱情脱下军装来到机村时,这个曾经在部队里有着“灵动脑瓜”的军官就成了众人口中的达戈(傻瓜的意思),而拥有美丽嗓音的色嫫也似乎并没有不可抗拒的魔力。在达戈与色嫫的爱情羁绊中,达戈痴恋着色嫫,色嫫也并非不喜欢达戈,只是当爱情、忠贞乃至信仰都被放在现实砧板上加以锤击时,在“一个一切都变得粗粝的时代,浪漫爱情也是这个时代遭受损毁的事物之一。”色嫫美丽、矛盾又虚荣,成名的诱惑让她着迷,她不想浪费自己的美貌,一直试图努力进入与外界文明接轨的“新生活”,然而在男权的社会中,她的梦想注定找不到正当的出口。从现实的角度说,达戈与色嫫的爱情一直是错位的。对于色嫫而言,爱情(或者男人)是一种动机,是她梦想达成的一部分,色嫫需要的是城市里俊美的军官;而对于达戈而言,爱情是他追逐的目标,他努力依靠传统技能来给予爱人幸福。达戈一直想成为最好的猎手,但他为了达成色嫫的愿望却没有遵守猎人的规矩,再三地向异化的文明妥协,最终导致他既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也丧失了作为男人的尊严。
可是,我们的分析还要继续,我们还要说达戈,说他一直被研究者所忽视的“羊癫疯”。我们往往会把达戈打破人猴的千年契约的行为看作是良知的泯没;而“羊癫疯”这种家族的疾病,也被机村人看作是达戈杀孽太重的惩罚。事实上,古老的村庄或者部族陷入疯狂,并不是从在丰收之年对同宗的猴子举起猎枪时开始的,而是在土司们种植罂粟、抢夺地盘、不顾人民死活的时候(《尘埃落定》);在全村人共同构陷没有父亲的外来人格拉,并用带有怀疑与仇恨的谣言杀死这个孩子的时候《狗孩格拉》);在落入消费时代的陷阱,疯狂挖掘虫草、采毁松茸的时候(《三只虫草》《蘑菇圈》);在都市过剩的欲望导致乡村价值的混乱,灭绝岷江柏的时候(《河上柏影》)……即使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价值的失范、理性的损毁等同于病理层面的癫狂,但这些作为民族文化断裂、乡村伦理的崩溃、文明信仰的贫乏等时代病象的表现却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层面上讲,达戈是疯狂时代病像中病态的人,标志着外界焦虑的内在转向,就像德尚所预言的那样:“我们胆怯而软弱,贪婪、衰老、出言不逊。我环视左右,皆是愚人。末日即将来临,一切皆显病态。”[12]他和达瑟一样,并不甘于走上世俗意味上的康庄之路。达戈从已经没有森林的家乡出走,拒绝部队提干,来到机村。“羊癫疯”这种疾病的背后隐匿着他的自我分裂与冲突:希望与绝望、刚毅与懦弱、谦卑与高傲、忍耐与狂暴,也表达着人类在面对世界、面对自然尤其面对自己的时候那种茫然、冲动、乖戾、嚣张、绝望以及由此而生的深深的孤独感。遗憾的是,机村不仅是“蒙尘”的机村,而且是天火之后被人的欲望之火毁灭的机村。
总的说来,无论是痴人、愚人、疯人还是智者,他们都是时代的边缘人。达戈这个名字意为“利箭”的人,他读书读得半通不通,既没能刺穿世事的虚伪,也没能照亮失落的猎人朋友,连自己后来都坠入生活的烦扰之中,成为了一个酒鬼。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心田日渐荒芜,这也许不是源自知识的孱弱,也有时代的阻隔与自己接受的偏差。阿来用文字收拢时光,保持着一股子率性与天真,“世间也有一种奇人,生时不能开悟,但朴拙固执也是一种成就。”[11]598达瑟与达戈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智者,也不是愚人,他们只是不愿与时代合谋却无法置身事外的可怜人。时代有着不可逆的自我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讲,达瑟与达戈都是当代的阿古顿巴。在达戈的冲动、乖张的背后展示了一个末路英雄所面临的残酷境遇,而达戈世代遗传的“羊癫疯”既一方面加重了他的孤独与绝望,也在更深层面上映射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癫狂与断裂。从达戈身上我们看到了时代巨大的吞噬力,达戈不断地举起猎枪来反抗被强加的命运,并成为“机村最后一个与猎物同归于尽的猎人”[11]328;而从达瑟身上则更多地展示了人在面对世界、面对自然尤其是面对自己时的空洞与茫然,达瑟用书籍构建了一个迷茫时代的海市蜃楼。达瑟与达戈坚韧地逃避同化,拒绝与蒙尘世界同流合污,并成为了自己的英雄。
一般说来,人物书写是最具生命的艺术,通常我们关注的是人物内心的抗辩和挣扎,而忽视阿来在朴拙单纯的人物身上的心灵留白。在他看来,对错、善恶、智愚是在不停流动着的并追随生命一起变化,世界本不美好,与其做无谓的批判,不如包容和解,真正的文学创作是“在成熟的时候,要保持天真;在复杂的时候,依然要保持简单。”[13]他们在浩荡的内心世界中痴迷、徘徊,保留着精神世界的那份真与纯。
总的来说,阿来的笔下人物常为某种情愫所牵系,或坚韧刚强、或忧郁困惑、或大智若愚、或执迷不悟……我禁不住将他笔下的人物和《清明上河图》中的众生熙熙之相联系起来,虽然阿来关注的并不是外在毫微毕现、惟妙惟肖,也很少直接运用心理描摹,但他注重在动态的历史、环境中来把握人物,关注他们在失重的世界中抗辩、挣扎、背离,并最终走向和解,这想必是阿来众生平等的关怀与悲悯所致。在不断地追问与驳诘中,阿来的人物书写凸显了他对于生命、人性以及历史的深邃认识。阿来曾经说过“尘世间的幸福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目标,全世界的人都有相同的体会:不是每一个追求福祉的人都能达到目的,更不要说,对很多人来说,这种福祉也如宗教般的理想一样难以实现。于是,很多追求幸福的人也只是饱尝了过程的艰难,而始终与渴求的目标相距遥远。所以,一个刚刚由蒙昧走向开化的族群中那些普通人的命运理应得到更多的理解与同情。我想,我所做的工作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此。呈现这个并不为人所知的世界中,一个又一个人的命运故事。”[14]他关注那些藏族乡村中常见却不被人重视和关注的人,而往往是这样的人反而会从世界中感知到更为丰富的东西:那些貌似喜剧的生存状貌之下的苦痛,生命渴望与人性阴影之间相互冲突的悲哀。
阿来写得非常细心,也非常老实,“这片土地上所有时期生存的人,他们的前世今生我都关注”[15],他把藏地鲜活的生活样态袒露出来。阿来笔下的人物并不是完美的英雄,他们时常陷入理想的迷茫、现实的困惑,也偶尔耽于梦想;他们不时地用虚幻的想象来支撑着人生意趣,我们却不难从他们古怪的动机中感受到“理想”本身所包含的无限凄凉。无论是阿古顿巴、傻子二少爷、银匠达泽、行刑人尔依、狗孩格拉、书呆子达瑟还是阿妈斯炯、“半吊子祭师”阿巴……,都是痴人在写拙人、写憨人。阿来一直坚持文学的笨工夫,他固然有自己的人物腔调和选择,但有的时候他就像是初习写作的人:行文诚挚、恳切甚至还有些茫然。显然,在快速演进的历史现实之中,他也无法为“无以自适者”提供一个并不虚妄的未来。可是,这却不影响我们对阿来笔下人物的喜爱,我们喜欢他们的真与憨、矛盾与茫然……
[注 释]
①习惯上,藏区按方言划分可以分成卫藏、康巴、安多三块,以拉萨为中心向西辐射的高原大部分地区叫作“卫藏”。卫藏又分三块:拉萨、山南市称为“前藏”,日喀则市则称为“后藏”,整个藏北高原称为“阿里”。前藏和后藏之间的孔道,就是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尼木峡谷。
②有的故事中名字叫《国王的座位》,叙述语词虽有区别但内容基本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