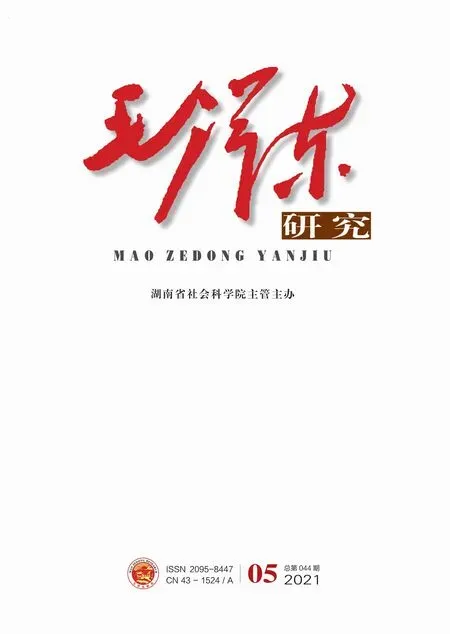《新民主主义论》传播及其历史影响(1940—1946)
2021-12-23黄日
黄 日
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正确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它不仅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一座理论丰碑。以1946年6月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为界,此前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权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和前途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交锋,三方发表了大量带有论战性质的文章,此后关于“主义”的直接争论明显有所减少。因此,对于《新民主主义论》自1940年发表至1946年之间的传播问题研究具有其特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而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新民主主义的话语建构、民国知识分子阶层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认识和《新民主主义论》跨域传播三个方面(1)参见:李永进:《〈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蒋积伟:《抗战时期新民主主义话语的建构》,《党的文献》2015年第4期;李晓宇:《民国知识阶层视野中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4期;王毅:《民国知识界言说中的〈新民主主义论〉》,《党的文献》2016年第3期;程美东、裴植:《抗战期间〈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传播及反响》,《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2期;叶美燕:《国统区人士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批判及其实质》,《党史与文献研究》2018 年第4期;李龙如:《〈新民主主义论〉的伪装本》,《湘潮》2009年第9期。。厘清中国共产党是针对什么样的对象,选择什么样的路径,通过什么样的过程传播《新民主主义论》,分析其传播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有利于深化和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一、《新民主主义论》在抗日根据地的传播
抗日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论》传播的主阵地。为统一全党意志,坚定抗日根据地各阶层坚持抗战的信念,党针对不同主体,采取不同方式传播《新民主主义论》,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逐步深入人心。
(一)覆盖多主体的立体式传播方式
第一,党员干部群体是新民主主义传播的主要对象。《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中的政治总纲领”(2)邓拓:《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晋察冀日报》1942年7月1日。,首先要在党内形成共识。因此,党面向党员干部群体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的宣传、动员和教育工作,以“提高全党政治理论的水准,思想上巩固党的队伍”(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7页。。
第二,工农群众是新民主主义传播的重点对象。工农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依靠力量和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党根据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觉悟程度、文化水平进行不同的宣传,在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基础上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各种方式传递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使得群众在自身的政治经验上来认识我们党的理论、政策、主张、口号的正确”(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引导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投身到抗战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中。
第三,党积极向党外人士传播新民主主义。全面抗战时期,党对统一战线政策作出调整,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积极联系社会各阶层的进步分子,将进步的党外人士纳入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中,反映党外人士的意见,与党外人士合作,这“给了中等阶层的人士以极大的鼓励”(5)罗迈(李维汉):《关于政权的三三制》,《共产党人》第11期,1940年10月。,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
第四,党重视向知识分子传播新民主主义。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但他们并没有与抗日民众很好地结合起来。然而,“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234页。,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党逐步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新民主主义改造,使文艺成为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媒介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页。。
(二)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传播路径
1.直接传播
首先,印刷出版《新民主主义论》的单行本与选集本。据统计,1940年2月至1946年6月,抗日根据地共出版发行了45个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论》(8)蒋建农、边彦军等:《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5—1767页。。1940年3月,延安解放社首次出版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单行本后,得到冀鲁豫边区、晋西北新华书店、晋察冀新华书店等多个抗日根据地出版社的发行,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1944年5月,国内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将《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第1卷的第1篇收录其中。
其次,通过教育的方式传播《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国民教育的指示,“确定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1942年2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将《新民主主义论》作为营团级以上干部学习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要参考书目(1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1943年,陈毅要求华中各抗日军政大学加强对团、营、连、排干部的政治教育,“以毛著《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整风文件为基本读物”(11)《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页。。194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选印关于中国问题基本常识与共产主义基本概念的十余篇书目,其中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位列参考书单的第一位(1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再次,通过解读、阐释的方式进行传播。《新民主主义论》公开发表后,艾思奇、张仲实、吴玉章、张如心等一批党的理论家们在《中国文化》《解放》《共产党人》《解放日报》等重要的报刊媒体上公开解读和阐释新民主主义理论,进一步扩大了《新民主主义论》在抗日根据地的影响力。
2.间接传播
相较于直接传播的形式而言,党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间接传递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更容易引起工农群众的共鸣。党在总结群众工作的经验中发现,“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很大”(1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4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诞生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文艺作品,文学类有《小二黑结婚》《活在新社会里》等,歌剧类有《白毛女》《血泪仇》等,秧歌剧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歌曲类有《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等,这些文艺作品拓宽了新民主主义的大众传播渠道,广泛动员工农群众参与到革命和抗日根据地建设中。
此外,通过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传播新民主主义。1940年3月,《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首次提出“三三制”原则,许多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等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被纳入到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设中,有力团结了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增强不同社会阶层对抗日根据地的归属感,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
(三)自党内向党外扩散的传播过程
《新民主主义论》正式发表后,成为了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行动指南。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上阐释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内涵,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3页。。3月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提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15)《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11页。。紧接着在3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首次提出“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原则。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在关于实现“三三制”的指示中提出,“以真正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政权,为我们党的中心任务”(1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积极调动边区各阶级、阶层参与民主选举。除陕甘宁边区外,其他抗日根据地同样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积极推进新政权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得到了抗日根据地各界的积极拥护和主动参与,就连之前持反对意见的地主,态度也发生了转变,有的说:“过去村公所尽都是帝国主义,现在仁义了”;有的说:“边区上了轨道了”,“边区的章程越来越好了”(17)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89页。。
然而,在《新民主主义论》取得抗日根据地广泛认可的时候,党内却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1941年10月8日,王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批判《新民主主义论》有关将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的内容,当即遭到凯丰、陈云等与会人员的反对,有力维护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正确主张。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一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改造,逐步认识到文艺作品与革命动员之间的关系。刘白羽认为,作家要“学习马列主义,掌握党的政策;最好的方法,是把自身投入劳动人民的熔炉”(18)刘白羽:《与现实斗争生活结合》,《解放日报》1942年5月31日。。何其芳提出,要将文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一翼。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延安诞生了一大批反映群众呼声、符合革命需要的新民主主义文艺作品,充分调动群众参与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热情,扩大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抗日根据地的辐射面和影响力。
在国际、党内、党外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1943年《新民主主义论》在抗日根据地的传播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首先,共产国际解散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传播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其次,毛泽东在1943年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其影响力不断提高;此外,1943年《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中国共产党更需要通过阐释新民主主义思想,以应对国民党的理论进攻。上述因素客观上促进了《新民主主义论》在抗日根据地的进一步传播。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1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页。,标志着新民主主义在抗日根据地的传播达到一个高峰。在大会上,刘少奇称赞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2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1页。。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2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有力回应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进一步扩大了新民主主义的影响力。
(四)对抗日根据地社会各界产生深远影响
《新民主主义论》的传播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共鸣。邓拓在阅读《新民主主义论》后,激动地表示:“这本书太好了,是划时代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解决了。”(22)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编:《晋察冀日报史:1937—1948》,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页。当即热情赋诗《读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初稿》。任弼时表示:“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及有关战略问题的著作……各种政策之掌握,才爱戴佩服。”(23)《任弼时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18页。陈毅高度评价《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光荣代表”(24)《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页。。谢觉哉在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提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25)《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页。。周文认为,公文改革同样也要朝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发展(26)周文:《谈谈公文改革》,《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0、31日。。
随着《新民主主义论》的传播与新民主主义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党外人士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并主动投身到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当中。乡绅李鼎铭也是党外民主人士的典范,1941年年底,他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为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说:“共产党对于民众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27)李鼎铭:《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解放日报》1943年9月9日。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认为:“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诸种论文,那就是中国的真正命运。”(28)续范亭:《感言》,《解放日报》1943年8月16日。
《新民主主义论》对抗日根据地知识分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茅盾指出,《新民主主义论》“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是当今文化发展的指针,因此“可说是中国新文化史上一件大事”(29)茅盾:《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演说)》,《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1940年7月。。在张如心看来,《新民主主义论》“更是天才卓绝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是我们党最宝贵的资本,是中共对于中华民族人民解放事业,及全世界马列主义的事业,最有历史意义的贡献”(30)张如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解放》第127期,1941年4月。。吴玉章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继《论新阶段》后,“我党第二个有历史意义,最伟大的文献”(31)《吴玉章文集》(下),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3页。。
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论》的传播对于凝聚党内共识、团结党外人士、争取广大民众和指导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反映了《新民主主义论》在解放区的影响力与覆盖面。它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沦陷区的传播
在国统区和沦陷区,《新民主主义论》一方面受到反动人士的诋毁和攻击;另一方面,党通过公开和秘密多种渠道,向国统区、沦陷区进步知识分子和民众传递了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正确主张,逐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
(一)以进步知识分子、上层人士为重点传播对象
1940年前后,国统区、沦陷区几乎封锁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以及抗日根据地的信息,普通民众较难接触到毛泽东的著作。为扩大《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沦陷区的影响力,党选择以进步知识分子、上层分子作为突破口,有针对性地传播新民主主义思想。知识分子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较强的民族意识,是社会中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社会阶层,因此具有争取他们的可能性。此外,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们和社会各阶层联系紧密,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有助于党的工作开展。1941年,彭德怀在北方局扩大会议中强调,知识分子“是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的桥梁”,要向他们积极传递“新民主主义、持久战、三民主义、游击战争、中国历史及其他各种知识”(3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36页。。
针对国统区、沦陷区上层人士的统战问题,陈云强调,“在一定条件之下,上层活动有决定意义,如果上层不动,则下层难动。上层的推动往往是下层工作开展的便利条件”(33)《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争取上层人士,对于党在国统区、沦陷区的工作开展具有重要意义。1943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山东分局作出指示:“要特别注意质量,印发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两书,到敌占区、游击区广泛散发,并用一切办法保障送到觉悟知识分子及伪军伪组织上层分子手里。”(3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页。
为扩大党在国统区、沦陷区的影响力,抢占舆论高地,党通过多种形式向民众们传播新民主主义。在国统区,通过宣传新民主主义对抗国民党文化复古主义,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在沦陷区,通过宣传“抗战到底”和新民主主义政策,揭露敌人阴谋,坚定民众继续抗战的信心。
(二)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传播渠道
1.公开传播
首先,公开出版《新民主主义论》的单行本。皖南事变前,《新民主主义论》曾在国统区公开发行,例如1940年重庆的红星出版社、南昌文艺印书馆、长沙人人出版社都发行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单行本,在国统区引起了购买的热潮,供不应求。同年,新疆日报社翻印《新民主主义论》达20000册。除了单行本外,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群众》周刊也对《新民主主义论》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转载。
其次,通过进步刊物传播。1937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间,在上海租界,一批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采用化名的方式,通过进步刊物公开宣传新民主主义思想,包括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上海周报》、中共上海文委领导的《求知文丛》,还有《哲学》《职业生活》《新知十日刊》等进步杂志,为扩大党在沦陷区的舆论阵地、传播新民主主义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2.秘密传播
首先,通过伪装本进行传播。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新民主主义论》的伪装本主要有以下五种类型。第一种,以宗教典籍为名,例如《大乘起信论》;第二种,以史学著作为名,例如《文史通义》(35)田建平、张金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第三种,以古代小说为名,例如《虞初新志》《水浒传》《七侠五义》(36)程美东、裴植:《抗战期间〈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传播及反响》,《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2期。;第四种,以言情小说为名,如《满园春色》(37)张其武:《〈新民主主义论〉的又一伪装本》,《中国边防警察》2007年第9期。;第五种,以政论书籍为名,例如《中国往何处去》。这些《新民主主义论》伪装本的命名方式多样,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便于在国统区、沦陷区进行秘密传播。
其次,秘密组织读书会、研究会宣传新民主主义。1943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华岗化名林少侯前往云南大学任教,秘密成立西南文化研究会,团结了闻一多、费孝通、吴晗、李公朴等著名知识分子,组织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等党的文献,提高他们的政治认识。在浙江玉环,地下党在玉环简师成立秘密读书会,向学生介绍《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38)中共玉环县委党史研究室编:《榴岛晨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玉环知识青年的成长历程》,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2页。。
再次,建立秘密的出版机构开展宣传工作。1940年5月,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刘宁一、陈公琪与陆贤向在上海成立“北社”秘密出版机关,从宣传《新民主主义论》开始,陆续出版了一些政治性小册子,扩大了党在沦陷区的影响力(3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同年,他们出版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小册子,向沦陷区文化界积极宣传新民主主义。
此外,成立秘密的新民主主义社团。1945年1月,昆明的进步青年成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它的章程明确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作为奋斗目标。1945年8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在昆明等地建立了“新民主主义联盟”,这些组织以新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协助党在国统区开展群众运动。
(三)国统区、沦陷区曲折的传播过程
《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后,很快引起了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其理论的关注,国民党政要陈安仁在文章中提到,《新民主主义论》“登在各报,后来印成单行本,可说是风靡一时”(40)陈安仁:《与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民族文化》1941年第5期。。正由于《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力在国统区日渐扩大,1940年6月13日,国民党中央图审会很快发布了关于查禁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的代电,谓:“凡遇有宣传此类名词之文字,应一律检扣或删削。”(41)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此外,国民党组织了一大批反动文人,以《抗战与文化》《尖兵》《中外导报》《湖南教育》《振导月刊》等国民党所属的刊物为宣传阵地,对《新民主主义论》发起了激烈的理论进攻,企图混淆视听。为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回应污蔑与质疑,彰显自己的理论主张,1940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国统区文化运动的指示中强调,“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4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7页。。党创造性地采取了多种传播形式,将《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中逐步秘密传播开来,影响了一批开明知识分子。
在沦陷区,日军在实行文化封锁政策的同时,还在社会各阶层中散布“共同防共”“中日亲善”“剿共灭党”等反动言论。为坚定沦陷区人民的抗战信心,传递党的理论主张,地下党和进步知识分子积极开展《新民主主义论》的传播工作,一方面,利用“孤岛”上海的宣传阵地,对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阐释,争取沦陷区的知识分子阶层;另一方面,将《新民主主义论》以伪装本的形式发放给民众,增强了中共在沦陷区的影响力。《新民主主义论》的宣传行动很快引起汪伪政权的警觉,他们在《大东亚周刊》《新进》《东亚联盟》《华北文电》等反动宣传阵地对《新民主主义论》发起进攻。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越发频繁,党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举步维艰。为进一步争取国统区的民众,应对国民党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进攻,1941年5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明确提出“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抗其复古主义文化,以三大政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解释的和我党所实行的)击破其反动政策”(4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以正视听。
针对沦陷区的宣传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41年3月发布《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扩大“共产党的抗日目的和政策”宣传(4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上海租界,开始加强文化管制,沦陷区新民主主义的传播阵地随即从公开全面转为地下。
1943年,《中国之命运》发表后,国共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及其前途的争论日趋激烈。针对《中国之命运》,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等著作,有力揭露了蒋介石言论的错误实质,这些文章被印刷成册秘密发往全国,对国统区的上层人士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解放日报》还介绍了胡宗南等人对这些文章“争相阅读、读后表现沉默”的情况,这一场争论没有使新民主主义丧失舆论阵地,从而更凸显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前往延安进行访问,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成就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一些中国记者返回国统区后,发表了关于延安的客观报道,例如赵超构在《新民报》上连载十万余字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通讯,后整理成《延安一月》出版。这部著作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增进了国统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政策的了解,在国统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亲赴重庆开展了长达43天的谈判,在此期间,毛泽东与多位国民党政要、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国际友人等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向他们传递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赢得了许多国统区人士的赞誉,极大地促进了新民主主义思想在国统区的传播。
(四)争论中扩大在国统区、沦陷区的影响力
随着《新民主主义论》在国统区、沦陷区影响力的扩大,部分反动人士在各自的舆论阵地对《新民主主义论》阐述的多个理论观点展开攻击,包括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革命的领导力量等内容。但究其根本,争论最核心的焦点还是在于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之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0页。,缺少其一,都是伪三民主义,这无疑触动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汪伪政权的敏感神经。国统区方面,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的《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国民党“理论家”叶青的《与毛泽东论三民主义》,中央日报社社长陶百川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文章和书籍都希望通过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批判,以达到维护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主张的目的。日伪方面,杨原的《毛泽东新旧三民主义之批判》、均鹤的《斥所谓〈新民主主义〉论》、王恕的《中共现行“新民主主义”路线的驳论》等文章,也在试图通过反驳《新民主主义论》争夺关于“三民主义”的话语权。
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争论与批判,无法掩盖理论本身的真理魅力,《新民主主义论》在传播中争取到许多进步知识青年和民众拥护和认同。棨武生动描绘了他在阅读《新民主主义论》时的心理活动:“我们远处上海的青年,读到这个文献,其欢心鼓贺的心情,也许与二十三年前芬兰湾口大城中的战士,读到‘远东来信’时仿佛相像的吧!”(46)棨武:《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研究与学习》,《学习》第2卷第5期,1940年6月。身处“孤岛”上海的地下党员和开明知识分子着重围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发表了多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见解。姚溱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现阶段不可不建立的中国新文化”(47)阿隼:《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学习》第4卷第3期,1941年5月。。哲学家陈垦表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必须和必然为中国今日新文化的内容”(48)陈垦:《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学术中国化》,《四十年代》创刊号,1940年7月。。上海的《职业生活》杂志连续组织了三期“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特辑”,其中何逸清提出要“通过组织上海文化界的统一战线”,以“建设上海的新民主主义新文化运动”(49)何逸清:《建设上海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职业生活》第2卷第25、26期,1940年4月。。这些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文章在沦陷区文化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使《新民主主义论》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和认同。
在国民党的封锁下,《新民主主义论》仍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开来,赢得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赞誉。1940年,邹韬奋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时,如获至宝,到处向朋友滔滔不绝地讲述书中的内容。冯契在阅读到《新民主主义论》后,产生了强烈的理论认同感,影响和促使他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道路(50)刘明诗:《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1页。。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前往延安考察后,写作《延安归来》一书,客观介绍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成就,受到国统区民众的广泛欢迎,发行量达10万余册,极大促进了新民主主义思想在国统区的传播(51)王纪刚:《这里是延安——中国共产党对外如何讲好革命故事?》,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4页。。
三、《新民主主义论》传播的历史影响
《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一时期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新民主主义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中国革命应走的光明大道,统一了全党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其次,它的传播加强了全国各解放区政策的统一,成为了各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最后,《新民主主义论》的传播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引了更多人投身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从而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一)统一全党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认识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党内也曾出现过许多争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明,使中国革命遭受过很大的损失。甚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内对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形成共识。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问题,党内长期存在两种错误认识,一是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互相割裂的“二次革命论”,在两个革命阶段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放弃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领导权,犯了右的错误;二是将两个革命阶段混为一谈、空想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犯了“左”的错误。这些言论在党内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新民主主义论》在总结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完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主张,表明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为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南。《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和传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大道,给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有力的精神武器。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总结道:“这些问题,过去在党内曾经是混淆不清、发生过许多争论的,但现在已是非常清楚而确定的了。”(5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页。
(二)成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指导原则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指导下,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实践,取得了一系列的历史性成就。第一,“三三制”政权成为展示新民主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窗口。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指导下,抗日根据地充分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参与政权建设的积极性,提升了政权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增强了各阶层对抗日根据地的归属感,真正将“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5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4页。。抗日民主政权“真正自上而下的实行民主,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示范于全国,使之与敌、伪、顽占区有基本上的区别”(5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7册,第251页。,成为了全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
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为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1942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导方针,大力发展公营经济,重视发展民营经济,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外,“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提高了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主动性,保存了地主阶级的积极性。党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也有效缓解了抗日根据地经济困难的局面。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对于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维持抗战基本需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坚定、专业过硬的干部队伍。党在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新型学校。这些学校以马列主义为主要课程,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基本内容,锻造了一批又一批可堪大任的革命骨干。
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实现了解放区的全民抗战总动员,实现了解放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实现了解放区各阶级的大团结,也因此实现了抗战一元化的领导”(55)《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成功实践,为党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也为新中国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三)吸引更多人投身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
随着新民主主义的广泛传播,抗日根据地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参与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队伍中。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仅有的4万余名党员,到抗战结束发展成为“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此外,抗日根据地有力聚合了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5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1027页。。1944年秋,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在结束对延安长达数月的访问后表示,中共党员干部已经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共产党员,不是内战时代及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员”(57)[美]斯坦因著,李凤鸣译:《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页。。
在国统区和沦陷区,《新民主主义论》没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和汪伪政府的查禁与封锁而石沉大海,也没有因为反动文人的谩骂与攻击,就丧失了自己的舆论阵地。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传播,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许多进步人士通过阅读《新民主主义论》,了解到中共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主张,破除了对中共的误解,看到了新中国光明的前途与希望,逐渐被吸引到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曾任新五军副军长的邢肇棠于1941年主动加入晋冀鲁边区,成为了临时参议会的副议长,他说,我是孙总理的信徒,哪里有真正的三民主义,我就到哪里(58)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409页。。闻一多读到《新民主主义论》后说道:“我们一向说爱国,爱国,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读了这些书,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59)闻黎明:《闻一多传》,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0—441页。1946年6月,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打破了许多民主进步人士对蒋介石最后的幻想。“两个中国之命运”,孰优孰劣,人们心中已然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