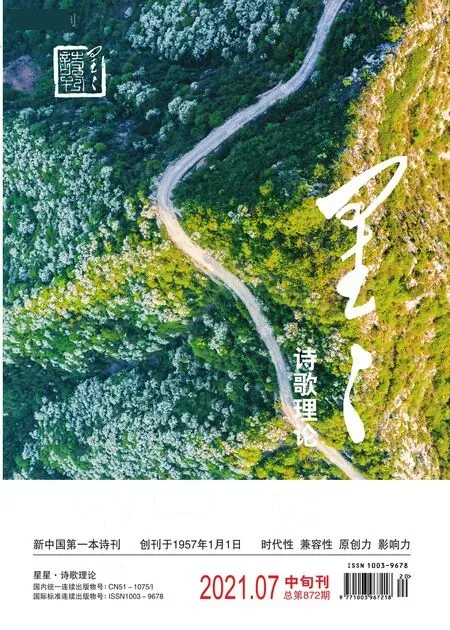不待雕琢而丽者,自然之性情
——读慕白诗集《出门见山》
2021-12-21>>>瞿炜
>>>瞿 炜
王国侧有骄傲的霸气,但慕白却是谦逊的。
我最初认识的是王国侧,他虽来自文成山区,那却是王佐之地,刘伯温的故乡。王国侧的名字,大约就蕴含了这么一层意思——他悠闲地躺在山间的田地之间,内心却如“在王者之侧席,运筹帷幄”。但那是属于诗人的想象,或者竟也是一位农人的想象——我猜想王国侧的父亲在给儿子取名的时候,一边在田间劳作,一边就这样想开了。他虽是农人,却有诗人的基因,并让儿子得到了继承,而将他的名挂到了中国的诗坛上。王国侧的第一本诗集,就是以“王国侧”为署名出版的。人们似乎并无惊奇,那是一位农人的后代对诗歌女神最初的奉献。这最初的奉献里,有着他最朴实的倾诉,也有一点自以为是的骄傲。我还记得他将诗集赠我一本时,眼里有狡黠的笑意,意思是,他与刘伯温吹过来的诗风并不遥远,可以说相当接近了。刘伯温在他的《感怀》里说:“槁叶寒槭槭,罗帐秋风生。凄凄侯虫鸣,呖呖宾鸿惊。美人抱瑶瑟,仰视河汉明。丝桐岂殊音,古调非今声。沉思空幽寂,岁月已徂征。”王国侧的“今声”也足以“惊宾鸿”了。我相信正是这一点朴实的自信,使他在诗之国游荡了这么多年而终不悔。
我不知道王国侧是在什么时候突然“悔悟”的——我说的是他对自己的名字的看法。突然有一天,他以慕白之名,出现在众人面前。自从叫慕白那一天起,他就要追寻李白了。追寻李白和成为李白,是两回事,但都不是容易的事。李白有一首《赠汪伦》,后来慕白也写了一首《兰溪送马叙至乐清》。这首送马叙的诗被很多选本收入,也在他最新出版的诗集《开门见山》(“中国好诗第六季”,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第一版)中。在这本诗集中,慕白不仅“送马叙”,也还有《赠崔完生》《别张二棍》《阿拉善歌送娜仁琪琪格》等。中国历来不乏友人间的赠别之诗。慕白有意要用新诗来继承古典的诗歌传统。
慕白与马叙,这两位来自温州地区一南一北的诗人,能说同样的方言,彼此十分熟稔却性格迥异。他们之间的友情并不属于例外,况且同在一个地区生活,那种离愁别绪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多余。但问题就在这里,偏偏慕白在送别马叙时就有了离愁,而这离愁是来自对彼此命运的不确定的一种感慨——“命运如水,谁能准确预测自己未来的流向”。慕白曾说起这诗的缘起:他们一同参加一个诗会,而慕白不慎摔伤了腿,幸有马叙一旁关照。可是不久马叙要先期回温,慕白感到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兄长般关照自己的人,这离愁便如江水滔滔而来。可贵的是,在整首诗作中,慕白很好地控制了情绪和细节的叙述,他将所有的感情寄托在雨中的芭蕉上,寄托在“上午十点一刻的这场雨”中,显得既有江南烟雨般的愁绪,又有“低缓,宽阔”的“内心宁静”。由此而见出慕白的重情重义,其情义如雨滴,点点滴滴地在他的诗行中呈现。这首诗完美地表现了慕白在诗歌创作上的艺术追求,即“自然之性情”,不事雕琢,天然而美丽。从这一点来说,他是继承了李白的传统,或者说接近了这一类的传统。他善待朋友,与人为善,所以他的这首送别诗也特别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我读他的这首诗,觉得那与他话别的朋友不是马叙而是我。这就是共鸣的奇妙之处。否则,这首诗便只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与我们,与读者就毫无关系了。
诗贵在诚。刘伯温被封为“诚意伯”,但我想,慕白的诚意,要大于此。封号只是一种虚饰,而慕白的诗,却是发自心声。慕白不再以王国侧自居时,他的“骄傲”褪去了,代之以诚意和谦逊。在他出版于2015年的诗集《行者》中,他不仅写了自序,还写了后记,又意犹未尽地写了跋。他想通过这些文本来诠释自己的初衷。他说:“名之行者,只是一种状态。或者说,我还在走,没有抵达。”他还说:“不需要掩饰脚印的浅显,自我见证。我有爱,除了爱,最多算遗憾。没有恨。”收录在这本诗集里的作品,大多是他行走山水之间的“游吟”,如《桐君山上》《湘湖图》等;另一些则是写给友人、母亲、儿子以及他的故乡包山底的抒情诗。他的诗没有什么自命清高的呐喊,也没有什么遣词造句的深刻,他只是真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抒发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正如这首《与子书》,直率、真实,便是慕白的特色了。这一类的《示儿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里并不鲜见,有些寄托了诗人的壮志未酬,有些则要子孙保持凌云之志,像慕白这样坦率而直白的,大约只有陶渊明和苏东坡了。陶渊明说:“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苏东坡说:“人家生儿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有儿鲁且直,无灾无难到公卿。”慕白也是这样想的。
有一句话说,人如其诗,诗如其人。慕白的诗与人,正是应验这句话的。
慕白的为人,可以说是直率、直爽的,他的诗,亦如此。他不故作深奥,不虚情假意。他的坦诚也反映在他的诗里。他有一种朴实的气质,这种气质来自他的故乡包山底。在文成山区,包山底尤其偏僻贫穷。慕白实际上是遭受了这种穷山僻壤所带来的各种困难,甚至还有身份上的某种挫败感,但慕白却用诗不断地赞美故乡,其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自信。他总是反复强调他生命中的那个山坳。这种自信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他有一首诗《我出生在一个叫“包山底”的地方》,他说:
我的包山底很小,小如一粒稻谷
一粒小麦、一颗土豆
躺卧在我灵魂的版图上
我用思念的放大镜,把一粒乡愁
放大成960万平方公里的热爱
慕白常说自己的诗歌创作是在寻找一种更简便的表达方式,他声称自己“语言水平不高,词汇量太少”(当然这只是他的一种自嘲,而非矫情)。他的这种谦虚实际上也是来自他内心的强大力量。慕白的诗,其鲜明的特点也在于此。我必须反复强调他的直白、直率的诗意特点,正如他之为人。他看到了生命的卑微与尊严。当然,他所有的陈述本身就是对生命与灵魂的隐喻。
慕白与我,也是几十年的朋友了。多年来,我一直在阅读他的作品。他能够有勇气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坦诚的状态,是令人敬佩的。
附:慕白的诗二首
兰溪送马叙至乐清
“从一个晴朗的地方到一个下雨的地方,
实际上只需要一次短暂的睡眠。”
兰在雾里,芭蕉在雨中
兄弟,上午十点一刻的这场雨
再次令人失望,脚下的流水
也不会再次让我们回到秧田里
回到我们失去的彼岸,钱塘江的源头
你低头坐进车子的身影
让我想起了古代友人江边送别
无言探向水面的沉默
水到兰溪,三江汇流,悄然合一
有如人的中年,低缓,宽阔,内心宁静
月夜漫步,中流击水,西门的桃花正好
今天第一班的汽车,或者最早的轮渡
也赶不上昨晚江边灯火中的盛宴
风很轻,一滴水不能和一条鱼
在同一个地方再次相遇
江的对岸,有人在流水中弹奏起古琴
小城故事,一次又一次重复那相同的别离
孤独的水流过一条兰溪,你又为何行色匆忙
于是寂寞滚滚流淌……
兄弟,兰溪,钱塘江的中游水系
各种各样的人行走在地上,没有人叫得出名字
命运如水,谁能准确预测自己未来的流向
这是一条别人的江,有人在上游点灯
以心为界,明天是谷雨,我也将启程
回到包山底。只是,我不知道今夜的江水
会在何时把我的深思喊醒
与子书
你只要真实地活着
有梨子吃就分别人一个
不够了就留着自己吃
喜欢大的就大的
喜欢小的也没有关系
不管云山雾罩,还是离题万里
在众多张嘴中说出自己的话
没有人听也不要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