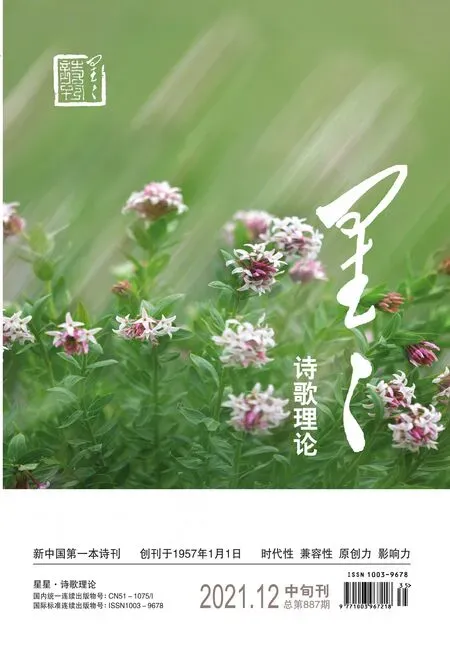“悲风为我起”
——王家新近作片论
2021-12-21>>>胡亮
>>> 胡 亮
如果有人想去看看陈子昂,他的读书台(位于金华山顶),他的埋骨地(位于独坐山麓),我总是乐于主动当一个导游。不是陪同,而是尾随;不是义务,而是渴望。王家新先生想去看看陈子昂,可以说,不过是对我的再次玉成罢了。2020年11月19日,涪江就要进入枯水期。但是我们知道,“涪江”上游就是陈子昂,就是从不间断或收缩的某种汹涌。精神与风骨的汹涌。这类说法并无修辞上的“出奇”,但“出奇”又算得了什么,较之于用空间来克服时间,从而艰难地回溯到那些痛苦而伟大的灵魂。“像杜甫当年那样(如果你能/渡过那些凶险的湍流!)”。杜甫之所以要去寻访陈子昂遗踪,小而言之,后者乃是前者祖父杜审言的“密友”,大而言之,后者乃是让前者心有戚戚焉的“儒家英雄”——如果没有记错,这个术语,当是出自宇文所安。前文的分析,当然有证据,比如杜甫的《陈拾遗故宅》。陈子昂当过右拾遗,相当于副拾遗,杜甫当过左拾遗,相当于正拾遗,都是芝麻大的小官儿。
除了上文已有征引的《谒陈子昂墓》,王家新的近作,还有《郁达夫故居前》和《雨雪中访平江杜甫墓祠》。从这几件作品,可以清楚看出,诗人总是不惮于这样的“重复书写”。“富春江”,流自郁达夫的“笔下”;“汨罗江”及“两岸黑瓦残枫/和飘拂的苇草”,流自杜甫——或屈原——的“诗里”。这样的“重复书写”,乃是修辞上的一再偷懒,却是精神上的多次淬火。技术上的日日新,会不会诱发精神上的朝三暮四?很多年以前,我与于坚先生在信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见过塞尚的作品吗,那看起来真是‘伟大的重复’。”其实,岂止是塞尚、莫奈、梵高都通过不厌其烦的“重复书写”,分别建立了“蓝睡莲谱系”“麦子与向日葵谱系”。而王家新,则建立了“痛苦者与游牧者谱系”。所谓“游牧者”,化用自萨义德的“游牧主义”。前述种种“谱系”都是实心的“精神谱系”,而非空壳的“修辞博览会”,故而最终能够“静静航行于另外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除了屈原、陈子昂、杜甫和郁达夫,连诗人在《“解体纲要”》中写到的报废汽车,全都从属于这个“痛苦者与游牧者谱系”。《谒陈子昂墓》写到的“闪电般的遗骨”,不就是《“解体纲要”》写到的“钢铁垃圾”?《雨雪中访平江杜甫墓祠》写到的“针尖似的细雪”,不就是《“解体纲要”》写到的“飞雪”?屈原就是陈子昂,陈子昂就是杜甫,杜甫就是报废汽车——这是一个幽灵小分队,所有幽灵,都可以相互替换。我们还强烈感受到,王家新早已隐秘、谦逊而又骄傲地实现了“叨陪末座”。也就是说,诗人自己,就是那个躲在小分队里面的蒙面幽灵或隐身幽灵。或许还有另外的解读角度,屈原、陈子昂、杜甫和郁达夫甚至报废汽车,全都是诗人自己的“镜像”。“你的枯眼合上,而泪从我这里涌出”。客体可以主体化,主体可以客体化。这个时候,在我耳边,就不得不响起南宋学者蔡梦弼关于杜甫的断言:“虽伤子昂,亦自伤也。”或法国作家福楼拜的金句:“包法利夫人,当然就是我”。
王家新近年来,似乎从“西学”转向了“中学”。除了献诗给杜甫,他还研究过雷克思洛斯对杜甫的出色翻译。联想到王家新的早期作品,比如《中国画》,就不能不引发我们的猜疑:这位诗人的文学接受史,先是一部东游记,再是一部西游记,如今又是一部东游记?这个猜疑并没有太大的价值,总体来说,王家新不过是在不断提升“中学”与“西学”的“民主性”,也就是余光中先生所谓的“毛笔”和“钢笔”的民主性。《中国画》醉心于东方美学趣味,《雨雪中访平江杜甫墓祠》痛心于古代文人厄运。正是缘于这个显而易见的差异,我宁可把《帕斯捷尔纳克》与《雨雪中访平江杜甫墓祠》归为同类作品也不愿把后者与《中国画》视为同类作品。不论是早期,中期,还是近期,王家新均曾多次献诗给西方诗人,尤其是阿克梅主义诗人。这些西方诗人,毫无疑问可以一点儿也不违和地列入“痛苦者与游牧者谱系”。甚至可以反过来说,《雨雪中访平江杜甫墓祠》,不过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续集、后传或姊妹篇。《“解体纲要”》中,“而它的德国造发动机,/人们修理后也许会另有他用,/像是心脏移植。”让我暂时抛弃“作者意图”,试错式抛出“读者意图”或“读者想象”——这架“德国造发动机”,或可移植到一架将要抛锚或解体的汽车上?
尽管我对王家新的几首近作和旧作,已有一些臆断,却仍然困惑于《谒陈子昂墓》的结句:“他只能永久立在那苍凉的幽州台上了——/那遥远的、断头台一般的/幽州台!”对陈子昂而言,只有一座“失意台”,在王家新看来,却是一座“断头台”。前者彻悟了生命的有限,后者惊觉了生命的大限。从“失意台”到“断头台”,此种比喻或联想,堪称“加强比喻”或“超级联想”。在王家新写出《谒陈子昂墓》之前,我已经领教过诗人这种大跨栏一般的方法论。记得当天上午,我们前往独坐山,王家新忽然叫停了汽车。停车处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卵石滩”,在他看来,却是一个“刑场”或“屠宰场”。附近的瓦房、柚子树、还有同行的青年,都见证了他即兴的“加强比喻”,或即兴的“超级联想”。为什么诗人要大比例增加“幽州台”或“卵石滩”的“悲剧性含量”?难道,他已经把两者都当成了“痛苦者与游牧者谱系”的瘦弱基座?
王家新也许不会驳斥上文的“过度诠释”,却很有可能会反对下文的“避重就轻”或“声东击西”——他在前述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凛冽感、挫败感和创伤感,与其说是对历史的“直接的痛定思痛”,不如说是阿克梅主义的“间接的遗产”;与其说是“困境”,不如说是“被压迫妄想症”;与其说是“凭吊”,不如说是“认领”;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气质”;与其说是不可拒绝的“礼物”,不如说是主动收养的“孤儿”;与其说是代言者的“面具”,不如说是个人的“胎记”;与其说是“诗学的承担”,不如说是“承担的诗学”;与其说是尖锐的“社会学”,不如说是九条牛都拉不回来的“美学”。这些结论,均非定论。恰好是在笃信与狐疑的回返往复之间,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下面这个事情。王家新和我登上了金华山,就着两块石碑,读到了杜甫给陈子昂的几首献诗。其中,我是向来推崇《陈拾遗故宅》,王家新却更愿诵读《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两首都是五言古风,前者十联二十行,后者八联十六行。王家新读到后者的第十五行时,忽然发出了难以自控的赞叹。我跟着他念了几遍,舌苔发苦,齿牙生寒,觉得这行诗果然是好,进而觉得这首诗果然是好。好在情怀,而非章句。《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第十五行,其实呢,只有普普通通五个字——“悲风为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