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至20世纪中叶德国的中国音乐文献研究
2021-12-19蓝颖
蓝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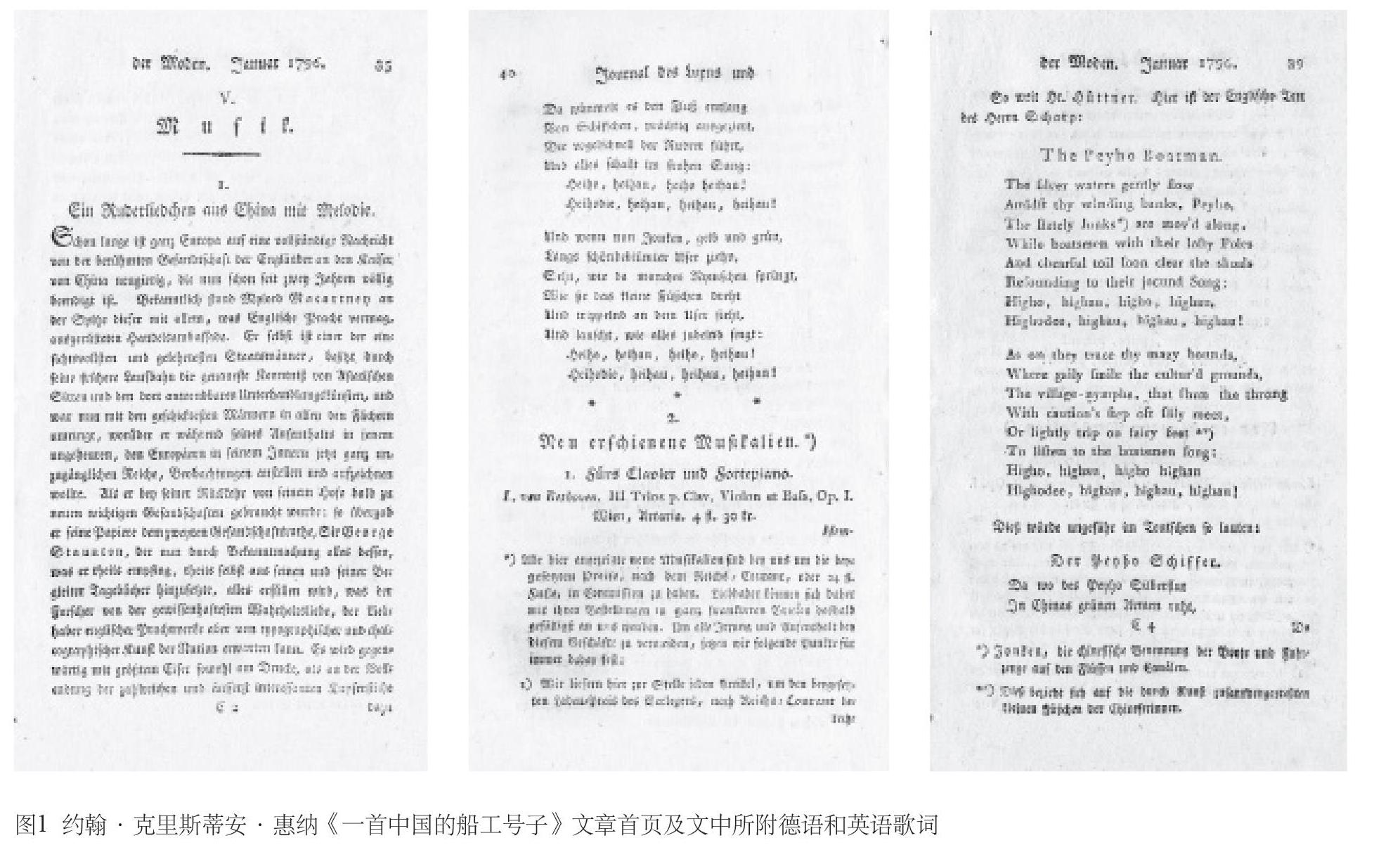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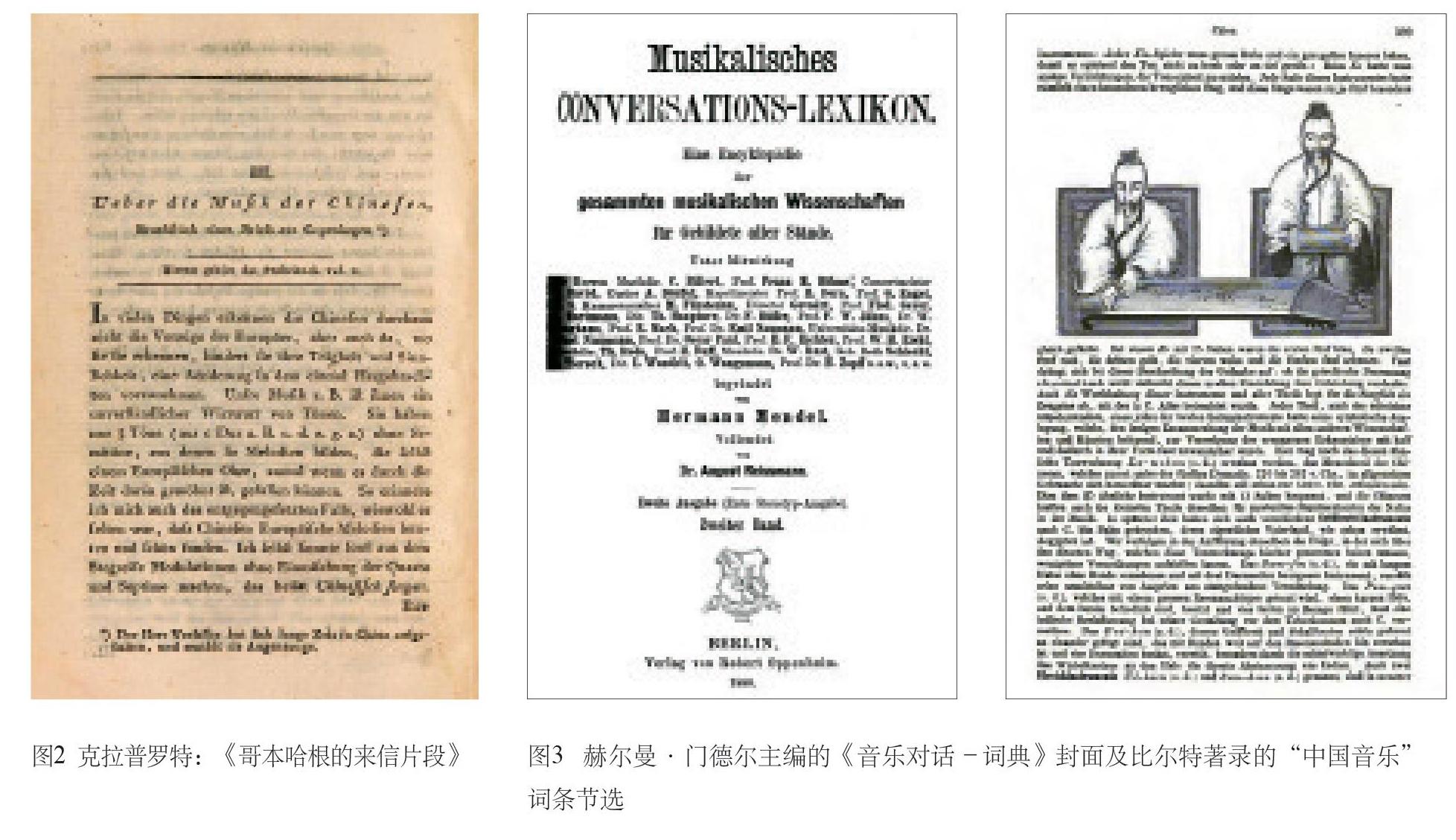

【摘 要】 德国的中国音乐研究滥觞于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时已颇具规模。但近现代中国音乐德语文献不仅在中国国内,甚至在德国本土都极易被忽视。中国音乐在德语世界中的传播途径,实际上是在历史和地理的范畴下对音乐本体进行“揉碎与重构”的过程。通过以主题为范畴,时间为顺序,对19至20世纪中叶中国音乐的德语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可相对完整地勾画出该时期中国音乐的“德渐”过程,充实中国音乐西文文献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中国比较音乐学科建设图景。
【关键词】 中国音乐;德语文献;搜集与整理
在关于近现代中国文明传入欧洲的相关历史研究中,有一项被忽略的内容—对中国音乐的西传研究。18世纪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神父翻译的关于中国音乐的著作—《古乐经传》(1754),应该属于欧洲研究远东音乐史的“开山之作”。此时期法国传教士为西方带来了较为系统的中国音乐知识,引起了西方的兴趣。因为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音乐的认识还停留在旅华西人所记录的信件、日记、旅游见闻等只言片语上。其中大部分记录描述中国音乐的文字还处于原始蒙昧状态,没有音阶,没有记音谱号,没有乐谱等,甚至用“噪音”来形容中国音乐。[1]但是这一点并不被大多西方学者所接受。德国学界认为,中国的建筑、绘画、雕塑、陶瓷、文学皆能达到精妙的程度,同在艺术殿堂的中国音乐怎么可能仍处于原始状态?这应该是由于二手文献传入欧洲时,旅人和传教士的汉语障碍、抑或是故意曲解所造成的“误解”,必须承认中国音乐的“美”在西方因为二手文献的“转义”被完全低估。
19世纪初,西方对中国音乐的认识逐渐从表面听觉感受到达旋律内核。而彼时德国在中国音乐研究方面,与法国相比,可以说远远落后。19世纪早期关于中国音乐的德语文献仍是基于其他欧洲国家传入的文献资料,诸如让 · 巴普蒂斯特 · 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钱德明、阿里嗣(J. A. von Aalst)所著的关于中国音乐的文献,皆是德国人了解中国音乐的重要窗口。德国“狂飙突进运动”(Sturm and Drang)后,这场暴风雨般的“文艺复兴”使得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德国在文化艺术上要确立自己的民族认同,建构自己的音乐学科,自然不愿再拾法国、英国等欧洲其他国家的“牙慧”。此后,德国为世界音乐研究保留了珍贵的中国音乐学文献,这些文献亟待我们去搜集与梳理。
近年来,赴德国留学、出访的国内学者为相关中国音乐德语文献的搜集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在留德期间致力于搜集和整理有关中国音乐的德语文献,曾金寿将此时期分为三个阶段:(一)研究雏形期(20世纪初);(二)研究的发展期(20世纪50—70年代);(三)研究的深化期(20世纪80年代始)。文章详细介绍了柏林音响档案馆所收录的关于中国音乐的文献与唱筒,以及20世纪初中德音乐交流的代表人物萧友梅、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王光祈等。[1]金经言在国内建构了德国音乐学体系,还转录柏林音响档案馆有关中国音乐的唱筒回国。他的《几部研究中国音乐的西文著作》详细论述了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音乐的西文文献,特别是德国学者的著作,比如艾希 · 费舍尔(Erich Fischer)的《关于中国音乐的研究》,汉斯 · 皮施纳(Hans Pischner)的《音乐在中国》,赖因哈德(Reinhard)的《中国音乐》,罗伯特 · 京特(Robert Günther)的《意蕴的魅力—古代中国音乐语言的记录》,基尔德 — 博纳(Gild-Bonhe)的博士论文《律吕正义续编—一本关于欧洲记谱法在1713年的中国的小册子》,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的《悬乐—中国青铜文化时期的编钟》,以及马丁 · 吉姆(Martin Gimm)的《段安节的〈乐府杂录〉》等。[2]笔者曾在马丁 · 吉姆生前所在的科隆东亚研究院工作和学习过,有幸在科隆大学东亚研究所馆藏图书中查到很多马丁 · 吉姆所搜集的珍贵文献,这些文献也成为本文的资料基础。宫宏宇在《柏林比较音乐学家与中国音乐—以霍恩博斯特尔为例》[3]中详细叙述了柏林音响馆收藏的有关中国音乐的文献。尽管如此,曾金寿还是在其文章《有关德文文献中的中国音乐研究》中说:“从今天德国的文献收集情况看,在20世纪前期收集到的音响及图像资料大量丢失,有关中国音乐的研究在王光祈先生之后也很难发现新人、新的研究成果。”[4]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笔者希冀在前人学者所获文献的基础上,再次梳理自18世纪起有关中国音乐的德语文献,尽量弥补这段时期的“缺憾”,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9世纪有关东方音乐研究的德语文献超过英语文献,但是相关中国音乐的德语文献却不够丰富。笔者根据《亚洲音乐目录考》(Bibliography of Asiatic Musics)所录1750至1950年的200年间西文文献进行统计,专论中国音乐的西文文献大概400条,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以及土耳其语,其中德语文献55条,而该目录总论中有关东方音乐的西文文献265条,其中谈到中国音乐的德语文献70条。德国对中国音乐的分类范畴大致包括:中国音乐史、少数民族音乐、宗教音乐、乐器、音乐美学、音乐评论、声音系统、音乐档案学、古代音乐记谱法、音乐图像学、音乐社会学,以及其他研究方向包括音乐心理学、音乐地理学、音乐教育和中国音乐名家名录等。音乐研究的分类繁多,按音乐范畴分类的话,不易系统化。如以时间为序加以梳理,可以在时空的语境中探寻中国音乐在德国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之变迁。因此本文文献整理的方法依然按照西方目录著录的传统方法:以年代为界,再以主要内容为次级范畴。这样既方便查阅,又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音乐在德国的发展史。本文所提及的大部分文献笔者都已找到原文,但也有部分文献原文至今还未寻到。即便如此,笔者还是列出遗失文本的题目。首先,这些文献仅从题目上就能窥探作者的研究角度;其次,也为未来文献收集列出寻找清单。值得一提的是,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音乐“德漸”过程中,德国汉学家的功劳最大。但是在整理资料时,笔者发现很多德国本土音乐家非常重视中国音乐,而他们的名字在国内却鲜被提起。如果中国音乐仅限于汉学平台的话,只能停留在“现象”层面,而只有跨学科、跨领域地进行本体研究才能真正了解中国音乐的域外传播史,并进一步推动中国音乐在异域传播与发展,从而建立中西音乐比较学科体系。笔者借助不同语种的音乐学目录资料,尽量将这一时期的德语文献全部找出,尤其是在欧洲学界非常知名、但在中国却鲜为人知的著者,将其著作和名字一一列出,希冀充实中国汉学、音乐学和艺术学的国际合作与研究。
一、1796—1900年间的
中国音乐德语文献
(一)早期的中国音乐引介与研究
18世纪以前,德国尚未确立自己的主流文化传统,更缺乏对异域文化的研究。因此德国对中国的认识,彼时主要基于在华大使、传教士、旅人、商人以及船员所记录的欧洲别国资料。1796年《奢华与时尚》(Journal des Luxus und der Moden)发表了约翰 · 克里斯蒂安 · 惠纳(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转译成德语的《一首中国的船工号子》(Ein Ruderliedchen aus China mit Melodie)[1]。文章描述了作者与斯汤顿(Staunton)一起记录这首船工号子的情景,并将号子的歌词译成英语与德语附录其中
(图1)。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中国音乐在欧洲的陌生化应算是最明显的,其主要原因应该在于没有统一的音乐体系,没有直观的听觉感受,这让欧洲听众很难产生共鸣。
乾隆五十八年(1793),作为英国出使中国重要成员之一的惠纳,是访华使团副史乔治 · 伦纳德 · 斯汤顿(George Thomas Staunton)爵士儿子的家教老师。旅华期间,惠纳将在中国的见闻写信寄给德国的朋友,有些信件被编辑出版,定名为《英国大使在中国和鞑靼部分地区旅游的消息》(Nachricht von der brittischen Gesandtschaftsreise durch China und einen Theil der Tartarei)[2],该书提到了中国的风俗、饮食、宗教甚至乾隆皇帝的相貌,有关中国音乐的内容位于附录部分。此游记由T.F.温克尔(T. F. Winckler)译成法文,并于1799年由J. J. 富克斯(J. J. Fuchs)在巴黎以《中国游记》为题出版。西人信件中探讨中国音乐的还有东方主义学家朱利叶斯 · 海因里希 · 克拉普罗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编辑的《哥本哈根的来信片段》(Bruchstück eines Brief aus Copenhagen)中登载的《论中国人的音乐》(Ueber die Musik der Chinesen)[1]。文章以欧洲音乐理论为基础,简述了中国音乐的音调差异,并着重讲述了彼时在广州港欣赏粤剧音乐伴奏,尤其是打击乐的情景。这篇文献非常珍贵,因为克拉普罗特的著作即使在欧洲也几乎被淡忘,直到最近才被提起。这样一位被“重新认识”的重要人物所著《哥本哈根的来信片段》对汉学研究也非常重要(图2)。
(二)本土音乐家介入中国音乐研究
1827年,德国著名音乐家格特弗里德 · 威廉 · 芬克(Gottfried Wilhelm Fink)在《科学和艺术百科全书》(Allgemeine Encyclop?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2]第16卷中著录“中国音乐”词条(Chinesische Musik)。他曾撰写过在欧洲影响巨大的《歌剧的本质与历史》(Wesen und Geschichte der Oper),是当时莱比锡甚至德国音乐的领军人物,他对中国音乐的重视,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音乐在当时欧洲的价值。由专业的德国音乐家撰写中国音乐词条,至少说明德国对中国音乐的研究不愿仅停留在对异域文化的兴趣上,而是希冀从专业角度对中国音乐内核进行探究。在由作曲家赫尔曼 · 门德尔(Hermann Mendel)主编、奥古斯特 · 赖斯曼(August Reissmann)撰文的《音乐对话—词典》(Musikalisches Conversations-Lexikon)中,也载有C.比尔特(C. Billert)著录的“中国音乐”词条(图3)。[3]
德国学界还借助法国、英国的文献来探寻中国音乐的内核,比如格特弗里德 · 威廉 · 芬克(Gottfried Wilhelm Fink)对东方歌剧的异域音乐元素深深着迷,他除了为中国音乐撰写词条,更在钱德明所译的中国音乐知识基础上,分析东方音乐理论,并在1831年《普通音乐报》(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上撰写《古乐理法:以印度和中国古乐之法为例》(Einiges über die Begründungsweise des ?ltesten Zustandes der Tonkunst, insonderheit über den Werth geschichtlicher Ueberreste der fürhesten gebildeten V?lker, namentlich der Hindostaner und Chinesen),此题目直译为《一些关于最古老的声音艺术的演变—特别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印度和中国》[1]。1868年,采凯(A. von Czeke)在《新柏林音乐报》(Neue Berliner Musikzeitung)也刊登了《一些关于中国人的音乐的知识》(Einiges über die Musik der Chinesen)[2],遗憾的是,两篇文献只在《亚洲音乐目录》索引中出现,笔者尚未查阅到其原文。此外,还有如德国浪漫主义音乐家奥古斯特 · 莱斯曼(August Reissmann)博士在1863年出版的《音樂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Musik)[3]中谈及了中国音乐。
德国学科建设尤为重视专业史建构,所以在音乐通史中撰写中国音乐词条,证明了德国音乐研究者对中国音乐的重视。这种重视使德国人当然不愿意再继续拾人牙慧,躺在别人的文献上了解中国音乐。德国人开始对中国音乐本体进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东西比较音乐学科”。
(三)多视角、广视野地接触中国音乐
德国对中国音乐研究视角一贯多元。研究中国音乐的德国学者并不限于汉学家、音乐学家,还有哲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等。不同领域的德国学者带来不同的研究角度,都对中国音乐学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1.乐器研究。1876年,卡尔 · 冯 · 谢弗特奥(Carl von Sch?fhautl)在《普通音乐报》上刊登《中国琵琶与中国音乐》(Ueber das Gut-Komm, eine Chinesische viersaitige Laute, und über Chinesische Musik)[4]。
2.中国民歌探索。德国学界认为中国民歌源头自《诗经》始。1880年,史陶斯(Victor von Strauss)所著《诗经:中国人的经典歌集》(Schi- King; das Kanonische Liederbuch der Chinesen)由海德堡的卡尔 · 温特出版社(Carl Winter)出版,原书共528页。除了翻译《诗经》内容外,该书还详述《诗经》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作者尤为看重《诗经》的民歌性质,并且希望通过对《诗经》的分析与德国民歌建立联系,不过书中也提到所谓《诗经》与德国民歌相联系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5](图4)。1884年,埃米尔 · 埃茨格(Emil Etzger)在《环球》(Globus)杂志上刊登了《中国人的音乐和歌唱》(Musik und Gesang bei den Chinese)[6],文章从历史的角度溯源中国民歌,并从音阶和节奏上对比中西音乐系统的差异。
3.中国戏曲中的配乐研究。曾任柯尼斯堡市立剧院(K?nigsberger Stadttheater)戲剧编导的鲁道夫 · 冯 · 格茨查尔(Rudolf von Gottschall)撰写了《中国人的剧场和戏剧》(Das Theater und Drama der Chinesen)[1],并由爱德华 · 特雷文特出版社(Eduard Trewendt)出版。此书非常明确地提到戏曲配乐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中西音乐体制的差异过大,使得西方译者无法将中国戏曲音乐恰当地展现给西方读者。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早期“中国戏曲”传入欧洲时会用与文学一词相并列的“drama”而非“opera”(歌剧)来翻译。
4.中国音乐体裁研究。1890年,曾创作《第18轻骑兵队游行进行曲》(Parademarsch der 18er Husaren)的“萨克森军事音乐”领域的权威康拉德 · 尼夫(Konrad Neefe),对中国的军事音乐非常感兴趣,并在《普通音乐报》上发表文章《古中国的军事音乐》(Die Kriegsmusik der Chinesen im Vorchristlichen Zeitalter)[2],这篇文章并没有摆脱对中国音乐的偏见,依旧是在欧洲话语内评价古代中国军事音乐。
5.音乐人类学研究。奥地利人类学、民族学家迈克尔 · 哈伯兰特(Michael Haberlandt)对东方民族学非常感兴趣。1884年,他在《维也纳人类学协会》(der Anthropologischen Gesellschaft in Wien)上发表《台湾原住民研究》(Die Eingeborenen der Kapsulan-Ebene von Formosa)[3],其中谈到了台湾原住民音乐。1898年,德国东亚学学者卡尔 · 弗洛伦茨(Karl Florenz)在德国东亚自然与民族学会发表会议论文《闽南民歌》(Formosanische Volkslieder nach Chinesischen Quellen)[4],讨论了土著语言与民歌之间的关系。
6.中国音乐调式研究。1888年,汉斯 · 维尔纳(Hans Werner)在《音乐新杂志》(Neue Zts. für Musik)上发表《中国音乐》(Chinesische Musik)[5];1889年,德国音乐家约瑟夫 · 西塔(Joseph Sittard)的《研究与特征》(Studien und Charakteristiken)[6]也谈及了中国音乐。居住在南京和北京两地、著有《上海土白形声考》《南京土白音节考》的著名奥地利数学家、汉学家、语言学家、天文学家翟乃德(Franz Kühnert)在《维也纳杂志 · 东方新闻》(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上发表《有关中国音乐的知识》(Zur Kenntniss der Chinesischen Musik)。这篇文章以阿里嗣《中国音乐》为基础,详细介绍了中国音乐的记谱方式,还宏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在西方研究中存在的诸多误解。文中指出,这些误解往往表现为西方文献中对中国音乐并不友好的记录,比如将中国音乐描述为“轰隆隆”鼓噪的低音,膝上的孩子“咕噜咕噜”的叫闹声,毫无旋律可言的乐鼓敲击等,但作者认为根本原因来自中西思维的差异,如果要真正理解中国音乐,需要了解中国音乐乐理知识、乐器构造原理、演奏实践以及音乐教育等,同时还需要音乐人具有数学上的敏锐思维。只有理解中国人的听觉系统,才能理解中国音乐,从而探究到中国音乐美之所在[7]。这篇论文让德国学界开始碰触中国音乐本体的内核。
二、研究资料由文本转成唱筒
(1900—1927)
进入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有机会来到中国,并通过留声机用唱筒直观地记录中国音乐,因此这个时期德国关于中国音乐学的研究视角更加直观与宽泛。
(一)录音技术促进中国音乐研究在德国的转向
这一范围中最重要的文章当属费舍尔(Erich Fischer)的博士论文《对中国音乐研究的贡献(来自柏林大学心理学院的录音制品档案馆)》(Beitr?ge zur Erforschung der chinesischen Musik(aus dem Phonogrammarchiv des psycholog. Instituts der Universit?t zu Berlin)[1]。1911年,德国音乐协会(Musik-Gesellschaft)将其转载于《国际文选》(Sammelb?nde der Internationalen)。这篇论文对德国的中国音乐学研究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因为之前德国对中国音乐的认识仅限于文本的视觉认知(图5)。
柏林大学心理学录音制品档案馆(即柏林音响档案馆),收录了不少中国音乐资料,其收录者包括汉学家、神父、医生、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等。收录者研究兴趣各异,这正有助于异域中国音乐学科建设,其中尤以劳佛尔(Berthold Laufer)的收录为最。劳佛尔在北京、上海录制过一些民间歌曲、京剧唱段和皮影戏的音乐伴奏,甚至还录了藏族歌曲。1906年,劳佛尔将其所录的蜡筒寄给了时任柏林音响档案馆馆长的霍恩博斯特尔(Erich Moritz von Hornbostel)。这些唱筒为欧洲提供了中国音乐听觉文献。费舍尔的论文对有关中国音乐研究的西文文献资料进行了详尽阐述。他认为,西方在音乐上遇到的一些复杂问题,在中国音乐中反而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中国音乐的结构形式与西方音乐一样有规律、成系统、具范式。这些认识让西人对中国音乐本体认知有了质的变化,特别是对早期西方因为转译文献而造成“中国音乐没有旋律”的“误会”做了进一步澄清。
借助录音技术的帮助,德国学者对中国音乐的认识不再基于文本文献,而是有了直观的理解,开始对中国音乐旋律进行记谱并在音调上进行分析。1901年,被誉为“芬兰音乐学之父”的伊尔马瑞 · 克罗恩(Ilmari Krohn)在《国际音乐协会杂志》(Internationalen Musikgesellschaft)发表论文《论杜赫德的中国旋律》(Ueber die Chinesischen Melodien von P. du Halde)[2],此文以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所记录的五首中国旋律为基础,从音乐视角进行专业分析。众所周知,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所录这五首中国旋律,不管当时著者带着怎样的感情色彩,都已成为欧洲人认识中国音乐的最早旋律记录。1922年,汉斯 · 费舍尔(Hans Fischer)在《音乐周报》(Musikalisches Wochenblatt)上发表《中国音乐》(Die Musik in China)[3];同年,奥地利作曲家、音乐博士罗伯特 · 拉赫(Robert Lach)在《序曲》(Auftakt)第2期上发表《中国音乐》(Musik in China)[1]等。只不过这个时期对中国旋律的分析都是基于西方乐理知识下的比较研究。
(二)德国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本体 — 审美 — 文学及其他艺术
自18世纪的“狂飙突进运动”后,德国文学艺术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德国音乐学科的建立也在10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经历了音乐本体→音乐美学→音乐与文学的演变,而这种演变也影响着他们对中国音乐的研究路径。
1.中国音乐本体特征研究方面
第一,旋律及结构。1921至1922年,俄国人约瑟夫 · 亚瑟(Joseph Yasser)前往上海指导“上海歌者”(Shanghai Songsters)合唱团。1924年他在《音乐速递》(Musical Courier)第88期发表《中国音调的节奏结构》(Rhythmical Structure of Chinese Tunes),同年12月,其德语版题为《中国旋律的节奏结构》(Rhythmische Struktur Chinesischer Melodie)的文章发表于《音乐》(Die Musik)杂志。1925年,《音乐新闻通讯》(Musical News and Herald)以《中国旋律的节奏结构》(The Rhythmic Structure of Chinese Melody)[2]为题进行转载。1919年霍恩博斯特尔为曲牌【朝天子】记谱,并在《音乐档案》(Archiv für Musikwiss)发表《朝天子—中国乐谱和演奏》[Chao-tien-tze (Eine Chinesische Notation und Ihre Ausführungen)] [3]。霍恩博斯特爾对亚洲艺术有着重要的贡献,他所著的文章对现代亚洲艺术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第二,乐器研究。欧洲对中国音乐、乐器都非常感兴趣,德国对中国打击乐的兴趣尤甚。在德国,对中国“鼓”的研究就如同中国“琴”的研究一样,受到普遍关注,比如1904年,曾在厦门海关任职的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904年在柏林举办的东方语言研讨会上发表论文《中国人对铜鼓的观点》(Chinesische Ansichten über Bronzetrommeln)[4],介绍了18年来自己在中国及中国周边地区对铜鼓的调查。1911年,夏德又在柏林东方语言研讨会(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发表会议报告《温柔的鼓》(Gentle Drums)[5]。
第三,地方戏曲的音乐伴奏。20世纪初叶,有一批在中国生活的德国人,随着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入,他们对中国戏曲的兴趣已具体化到地方剧种,如1910年V. A.沃尔普特(V. A.Volpert)的《鲁南地区戏曲表演》(Das Chinesische Schauspielwesen in Südschantung)[6]尤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以鲁南地区为研究中心。该文开篇点明“鲁剧”(Südschantung)的“鲁”是孔子的故乡,后围绕演员(Die Schauspieler)、中国戏剧舞台(Die Chinesische Theaterbühne)、服饰(Die Kostüme)、戏剧文本(Die Theatertexte)等范畴对中国戏曲表演进行概述性介绍。虽然该文的关键词为“鲁”,但是“鲁剧”的独特性只提及了地域文化背景,有关地方戏的表演特征却很少讨论(图6)。
第四,音乐体裁研究。德国音乐界历来重视“军乐”这种类型音乐,这类音乐研究的对象广泛,除了军乐演奏外,还包括宗教性质的仪式音乐、行军、娱乐以及各时期经典军乐作品。1907年,H.克劳斯(H.Krauss)在《德国军乐家公报》(Deutsche Militdr-Musiker-Ztg.)发表《古中国军事音乐和军事信号》(Altchinesische Milit?rmusik und Milit?rsignale)[1]。
2.中国音乐美学研究方面
中国音乐美学是德国音乐界的热点问题,从审美角度来探究中国音乐,是中国音乐研究在德国步向内核研究的标志。
第一,中国音乐美学的概述。比如,1903年W.科恩—安特诺里德(W. Cohn-Antenorid)在《音乐史月报》(Monatshefte für Musikgeschichte )发表《中国音乐美学》(Chinesische Musik-Aesthetik)[2],此文将中国音乐与中国国画相联系,着重阐释了“和谐美”(科恩—安特诺里德有关中国艺术的文章现存于柏林洪堡大学图书馆);1905年,A. 约翰—劳格尼茨
(A. John-Laugnitz)在《普通音乐报》发表《中国音乐美学的新贡献》(Neue Beitr?ge zur Chinesischen Musik?sthetik)[3];奥地利作曲家、拜占庭音乐权威埃贡 · 威勒茨(Egon Wellesz)于1919年在《曙光音乐报》(Musikbl?tter des Anbruch)发表论文《来自中国音乐的精神》(Vom Geist der Chinesischen Musik)[4]。
第二,中西审美差异。20世纪初,德国开始从中国音乐美学的概述入手寻找中西音乐审美差异之源,比如德国音乐学家阿尔伯特 · 费登塔尔(Albert Friedenthal)1907年在《普通音乐报》发表《中国人的听觉意识》(Der Geh?rsinn der Chinesen)[5]。文章指出,耳朵的听觉意识比眼睛的视觉意识更为复杂,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入手对中国人听觉感官进行心理分析,以此回答中欧音乐差异及陌生化问题。
3.音乐与文学及其他
德国学界认为,任何学科都不能在“孤岛”上习得,需要跨领域、多视野地建立联系。所以在研究中尤为看重音乐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比如音乐与绘画、音乐与文学等。德国著名音乐评论家、理论家和作曲家乔治 · 卡佩伦(Georg Capellen)1914年在《家庭与教堂音乐报》(Bl?tter für Haus-und Kirchenmusik)发表《从诗歌和音乐的角度看中国抒情诗》(Chinesische Lyrik vom Dichterischen und Musikalischen Standpunkt)[1],重点阐述音乐与诗歌的关系,以探讨音乐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卡佩伦一直重视音乐中“二元论和谐”问题,关注异域音乐风格研究,并将异域音乐元素投放于西方音乐之中进行创作,因此中国音乐很自然地成为他关注的话题。
(三)中西比较音乐
一谈到比较音乐,就会联想到柏林学派,想到王光祈。王光祈师从柏林学派的霍恩波斯特尔(Hornbostel)和萨克斯(Curt Sachs)。柏林学派对中国比较音乐理论影响深刻。除了柏林学派以外,另有一些有关中西比较音乐的文献。1902年,翟乃德针对中西比较音乐,写了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中国音乐和匈牙利音乐之间是否存在联系?》(Bestehen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esischer und Ungarischer Musik?)[2]刊登在《东方研究》(Keleti Szemle)第3期,集中探讨中国音乐和匈牙利音乐的亲缘关系,此后,中匈音乐的亲缘关系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1927年,法兰克福中国学院著名的汉学大师卫礼贤在法兰克福成立中国学研究院并主编《中国音乐》(Chinesische Musik)。同年,瓦特尔 · 霍华德(Howard Walter)、理查德 · 威尔西姆(Richard Wilhelm)等在该刊物上撰写《中欧音乐》(Chinesische und Europ?sche Musik)[3],阿诺 · 胡特(Arno Huth)在《序曲》上发表《法兰克福的中国音乐》(Chinesische Musik in Frankfurt)[4]。尽管如此,此一阶段的中国音乐学研究圈子在德国并不大,德国甚至欧洲对中国音乐依然非常陌生。很多文章依然是在前人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依旧给人“四不像”的感觉,这种奇怪的异域艺术的杂糅也让欧洲迫切地希望真正接触中国音乐的内核。
三、中德音乐人共促
德国的中国音乐学发展(1928—1949)
20世纪初,除了欧洲人与中国的交流进一步加强外,彼时中国人也有机会留学欧洲。萧友梅、王光祈等先驱将欧洲艺术带回中国,让国人有机会接触异域文化;同時他们也从专业的角度,用异域的语言将包括音乐在内的真实的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这让西方人在自己的语境中欣赏中国的音乐,而不再是自己臆想后的“误读”。此时,欧洲学者越来越接近中国音乐内核。
(一)德国音乐学科视域下的中国音乐
1.中国音乐发展史。德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建构专门史是一切学科的根基。德国学界对专门史的建构一直非常重视,音乐学也包含在其中。1932年,路易 · 冯 · 科尔(Louis von Kohl)在《汉学》(Sinica)发表《论中国音乐发展史》(T?nende Amtsembleme: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Musik) [5],文章承袭了柏林学派音乐史的阐述风格,将音乐起源追溯到上古时代,并指出欧洲音乐源自古希腊,而古希腊的音乐理论,尤其在宇宙观上与中国音乐理论非常相似。
2.中国音乐知识概述。1934年,路易 · 冯 · 科尔在《贝勒斯档案》(Baessler-Archiv)第2期发表《中国古代国家的基础与礼乐的意义》(Die Grundlagen des altchinesischen Staates und die Bedeutung der Riten und der Musik)[1]。1935年,K.伍尔夫(K. Wulff)在丹麦科学学院(Danske Viden-skabernes Selskab)的刊物《历史—语言学公告》(Historisk-filologiske Meddelelser)发表《中文的“乐”(音乐)与“乐”(欢乐)》(“Musik” und “Freude” im Chinesischen)[2],文章讨论了汉语“音乐”的美学和词源问题;卡蒂 · 梅耶(Kathi Meyer)《在音乐学论文集(第五卷)》(Sammlung Musikwissenschaftlicher Abhandlungen, Bd. 5)发表了《音乐的意义与实质》(Bedeutung und Wesen der Musik),该文第一部分涉及对中国音乐的介绍。1933年,诺林 · 托比亚斯(Norlind Tobias)在瑞典《音乐研究协会》(Svensk Tidskrift f?r Musikforskning)发表《中国乐器史的贡献》(Beitr?ge zur Chinesischen Instrumentengeschichter Svensk Tidskrift f?r Musikforskning)[3],文章对拨弦乐器琴、瑟,打击乐器板、鼓、编钟、云锣以及吹奏乐器笛子、唢呐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中国古代音乐中的五音、律吕作了说明。
3.中国音乐文献翻译。1928年,卫礼贤翻译了《吕氏春秋》(Frühling und Herbst des Lü Bu We),其中包含先秦诸子百家有关音乐的著述。1934年,《亚洲专刊》(Asia Major)刊登了德国汉学家何可思(Eduard Erkes)翻译的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直译为《唐之前中国戏曲》(Das Chinesische Theater vor der Tang Zeit)[4](图7)。
4.“德渐”过程中的跨视野研究。德国著名指挥家赫尔曼 · 舍尔兴(Hermann Scherchen)1936年在《音乐万岁》(Musica Viva)上发表《中国戏曲音乐》(Die Musik des Chinesischen Theaters)[5]的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摘要,中国戏曲音乐从18世纪被“误解”的聒噪的“咕噜”音变成了“正式”的音乐体系。中国音乐学也不再是欧洲汉学家的通识介绍,而是从音乐本体出发,获得了在西方的学术发展机会。1936年,亨茨 · 特雷格(Heinz Trefzger)在《汉学》发表《中国音乐》(Die Musik in China)[6]。亨茨 · 特雷格彼时为德国新锐汉学家,他研究的汉学问题多是此前欧洲汉学界很少注意到的。1938年,特雷格在同一期刊(《汉学》)发表了《唐代的音乐生活(618—907)》[Das Musik-leben der Tang-Zeit (618-907)] [7];1948年,特雷格又在《瑞士音乐报》(Schweizerische Musikzeitung)发表《论琴的历史、技术、记音符号和哲学》(Ueber das K in, seine Geschichte, seine Technik, seine Notation und seine Philosophie)[1]。事实上,特雷格推动了彼时中国音乐“德渐”的过程。
5.中国音乐与中国其他艺术之关系。1938年,威纳 · 斯派瑟(Werner Speiser)在《汉学》登载《宋时期的音乐创作》(Eine Komposition des Dschou Wen-Gu)[2]。斯派瑟时任科隆东亚博物馆馆长,深谙中国画并有非常多珍贵的中国画私藏。这篇论文主要探讨10世纪中国绘画中描绘的音乐表演场景。德裔美籍社会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东方语言学家艾柏华(Wolfram Eberhard)在《通报》(Toung Pao)1942年第37期增刊《古中国地方文化》(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3]的索引中谈到了中国音乐。
6.相关民俗学研究。1945年,民俗学家马蒂亚斯 · 艾德(Matthias Eder)在日本南山大学(Nanzan University)的期刊《民俗研究》(Folklore Studies)發表文章《中国岁时歌谣》(Das Jahr im Chinesischen Volkslied)[4],此文由作者艾德在北京所著。值得借鉴的是,文章开篇即界定什么是汉学,以此说明虽然此文题为“中国岁时歌谣”,但只属于民俗学范畴,并进一步界定民歌与民俗之间的关系(图8)。
(二)中国留德学生促进中国音乐学在德传播与发展
中国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异域传播发挥了桥梁作用,比如王光祈的研究,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在德国汉学界、音乐学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需要说明的是,王光祈的大多数德语文章都率先发表于卫礼贤创办的“中国研究院”的刊物《汉学》(Sinica,拉丁语为“中国”之意)。1927年,王光祈在《汉学》发表《论中国音乐》(Ueber die Chinesische Musik)[5],还配有插图。1928年,王光祈又在《汉学》发表《中国音乐记谱符号》(Ueber die Chinesischen Notenschriften)[6]。1934年,王光祈在波恩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戏剧(1530—1860)》[Ueber die Chinesische Klassische Oper (1530-1860 n. Chr.)] [7],并于1934年8月、9月和10月分三期刊载于《东西文化》(Orient et Occident)。
结语
音乐学是跨学科、跨视野的人文历史学科,西方学术界常将“音乐”看作建构社会文化的重要方法,中国音乐在德国的研究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学术逻辑的。可以说,中国音乐在德国的接受和发展史也是德国本土音乐学科发展史的一个侧影,对中国音乐的德语文献研究同样可以观照德国本土音乐学的研究发展脉络。德国视界下的中国音乐研究,既包含了文化的特殊性,又展现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共性特征。通过对19至20世纪中叶德语中国音乐文献的梳理,读者可以在德语音乐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范畴下动态地了解中国音乐在西方的接受和发展。
在文献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可以发现,德国的中国音乐研究滥觞于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时已颇具规模。同时,除了耳熟能详的德国音乐家霍恩波斯特尔、萨克斯以及拉赫曼(Robert Lachmann)等人植根于非欧洲的异域音乐比较研究外,还有在德国赫赫有名、在国内却较少提及的音乐大师格特弗里德 · 威廉 · 芬克、乔治 · 卡佩伦等在推动中国音乐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这段历史中有关中国音乐的德语文本撰写者并不全是音乐“科班”出身,他们兴趣广泛,视角新颖,多角度、广视野、历时与共时地探究中国音乐。通过梳理不同年代、不同德国撰述者的音乐知识和理论,可以了解到德国音乐学史已步入了本体研究 — 音乐美学 — 音乐与其他的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路径。
20世纪50年代后,中德音乐交流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德国音乐学者开始在音乐本体研究上观照中国音乐。中德音乐家的合作也在德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更加杂糅的“新中国音乐”(Neue Chinesische Musik)。“新中国音乐”在全球化背景下解构传统的“乐音”,建构“新声音”。这是在历史、地理范畴下对音乐本体研究的“揉碎与重构”。音乐学科已经迈向“本体 — 交叉 — 交互 — 创新”的广视野和多层面的研究时代。
本次德國的中国音乐文献研究,采取的是一种用“他者”的眼光审视自身文化历史,并反观“他者”的研究路径。“他者”视野下建构音乐学、特别是民族音乐学是学术逻辑发展的开端。人类对于音乐的理解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历史地理的多重语境下研究本土音乐,体现的正是音乐学的本体性和历史性。
[1] 因为对中国音乐的“陌生化”,有些记录对中国音乐的评价带有偏见,比如1807年詹姆斯·约翰逊(James Johnson)在其著作《东方航海家:1803、1804、1805、1806年乘坐“卡洛琳”号航行中国与印度的描述和评论》中提到中国音乐时写到,其无法用“music”来形容中国音乐。他甚至认为猫叫和狼嚎都比自己在广东听到的音乐协调。参见James Johnson, Oriental Voyager ; or, Descriptive Sketches and Cursory Remarks, on a Voyage to India and China in his Majestys ship Caroline,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03-4-5-6 ( London: Joyce Gold, Shon-Lane, Fleet-Street, 1807 ), 195.
[1] 曾金寿:《有关德文文献中的中国音乐研究》,《黄钟》2011年第4期。
[2] 金经言:《几部研究中国音乐的西文著作》,《中国音乐》1995年第3期。
[3] 宫宏宇:《柏林比较音乐学家与中国音乐—以霍恩博斯特尔为例》,《黄钟》2018年第1期。
[4] 曾金寿:《有关德文文献中的中国音乐研究》,《黄钟》2011年第4期。
[1] 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 “Ein Ruderliedchen aus China mit Melodie,” Journal des Luxus und der Moden 11 (1796): 35-40.
[2] 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 Nachricht von der Brittischen Gesandtschaftsreise durch China und einen Theil der Tartarei (Berlin: Voss, 1797), 190.
[1] 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Ueber die Musik der Chinesen,” Bruchstück eines Briefs aus Copenhagen, Asiatisches Magazin 1 (1802): 64-68.
[2] Gottfried Wilhelm Fink, “Chinesische Musik,” Allgemeine Encyclop?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16 (Leipzig, 1827): 373-383.
[3] C. Billert, “Chinesische Musik,” Musikalisches Conversations-Lexikon 2 (Berlin: Robert Oppenheim, 1880): 394-415.
[1] Gottfried Wilhelm Fink, “Einiges über die Begründungsweise des ?ltesten Zustandes der Tonkunst, insonderheit über den Werth geschichtlicher Ueberreste der fürhesten gebildeten V?lker, namentlich der Hindostaner und Chinesen,” 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 33 (1831): 785-793.
[2] A. Von. Czeke, “Einiges über die Musik der Chinesen,” Neue Berliner Musikzeitung 22 (1868): 139.
[3] August Reissmann,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Musik (Munich: Friedrich Bruckmanns Verlag, 1863-1864), 15-26.
[4] Carl Von Sch?fhautl, “Ueber das Gut-Komm, Eine Chinesische Viersaitige Laute, und über Chinesische Musik,” 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 11 (1876): 593-599, 609-614, 625-630, 641-646, 657-662, 671-679.
[5] Victor Von Strauss, Schi-King; das Kanonische Liederbuch der Chinesen (Heidelberg: Carl Winter, 1880).
[6] Emil Etzger, “Musik und Gesang bei den Chinese,” Globus 46 (1884): 376-380.
[1] Rudolf Von Gottschall, Das Theater und Drama der Chinesen (Breslau: Eduard Trewendt, 1887), 34-35, 68-81.
[2] Konrad Neefe, “Die Kriegsmusik der Chinesen im Vorchristlichen Zeitalter,” 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 (1890): 235-36, 245-46.
[3] Michael Haberlandt, “Die Eingeborenen der Kapsulan-Ebene von Formosa,” der Anthropologischen Gesellschaft in Wien 24 (1894): 184-193.
[4] Karl Florenz, “Formosanische Volkslieder nach Chinesischen Quellen,”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lkerkunde Ostasiens 7 (1898): 110-158.
[5] Hans Werner, “Chinesische Musik ,” Neue Zts. für Musik 55 (1888): 359-360, 369-370.
[6] Joseph Sittard, Studien und Charakteristiken (Hamburg, Leipzig: Leopold Voss, 1889), 187-196.
[7] Franz Kühnert, “Zur Kenntniss der Chinesischen Musik,”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14 (1900): 126-148.
[1] Erich Fischer, Beitr?ge zur Erforschung der Chinesischen Musik (aus dem Phonogrammarchiv des Psycholog. Instituts der Universit?t zu Berlin (Leipzig: Breitkopf & H?rtel, 1910). Reprinted in Sammelb?nde der Internationalen 12 (Musik-Gesellschaft, November 1911): 153-206.
[2] Ilmari Krohn, “Ueber die Chinesischen Melodien von P. du Halde,” Internationallen Musikgesellschaft 3 (1901): 174-76.
[3] Hans Fischer, “Die Musik in China,” Musikalisches Wochenblatt 40 (1910): 681-682, 693-694.
[1] Robert Lach, “Musik in China,” Auftakt 2, no.2 (1922).
[2] Joseph Yasser, “Rhythmische Struktur Chinesischer Melodie,” Die Musik 17 (December 1924): 193-98. (Music) In English as “Rhythmical Structure of Chinese Tunes” in Musical Courier 88, no.44 (April 1924): 44-45, and also as “The Rhythmic Structure of Chinese Melody” in Musical News and Herald 1 (1925): 6-9.
[3] Erich Moritz von Hornbostel, “Chao-tien-tze (Eine Chinesische Notation und Ihre Ausführungen),” Archiv für Musikwiss 1 (1919): 477-498.
[4] Friedrich Hirth, “Chinesische Ansichten über Bronzetrommel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 7 (1904): 200-262. Pub. separately by Otto Harrassowitz (Leipzig, 1904), 65.
[5] Friedrich Hirth, “Gentle Drums,” Mitt.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 14 (1911): 339-348.
[6] V. A. Volpert, “Das Chinesische Schauspielwesen in Südschantung,” Anthropos 5 (1910): 367-380.
[1] H.Krauss, “Altchinesische Milit?rmusik und Milit?rsignale,” Deutsche Militdr-Musiker-Ztg. 29 (1907).
[2] W. Cohn-Antenorid, “Chinesische Musik-Aesthetik,” Monatshefte für Musikgeschichte 35 (1903): 1-8.
[3] A. John-Laugnitz, “Neue Beitr?ge zur Chinesischen Musik?sthetik,” 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 32 (1905): 546-48.
[4] Egon Wellesz, “Vom Geist der Chinesischen Musik,” Musikbl?tter des Anbruch 1 (1919): 42-45.
[5] Albert Friedenthal, “Der Geh?rsinn der Chinesen,” 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 34 (1907): 848-49.
[1] Georg Capellen, “Chinesische Lyrik vom Dichterischen und Musikalischen Standpunkt,” Bl?tter für Haus-und Kirchenmusik 18 (1914): 100-103.
[2] Franz Kühnert, “Bestehen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esischer und Ungarischer Musik?” Keleti Szemle 3 (1902): 1-13.
[3] Howard Walter and Richard Wilhelm (ed), “Chinesische und Europ?sche Musik,” Chinesische Musik (Frankfurt: China Institute, 1927): 44-47.
[4] Arno Huth, “Chinesische Musik in Frankfurt,” Auftakt 7 (1927): 214.
[5] Louis Von Kohl, “T?nende Amtsembleme: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Musik,” Sinica 7 (1932): 5-11.
[1] Louis Von Kohl, “Die Grundlagen des Altchinesischen Staates und die Bedeutung der Riten und der Musik,” Baessler-Archiv 2, no.17 (1934): 53-98.
[2] K.Wulff, “‘Musik und ‘Freude im Chinesischen,” Historisk-filologiske Meddelelser 21, no.2 (Copenhagen: Levin & Munksgaard, 1935): 39.
[3] Norlind Tobias, “Beitr?ge zur Chinesischen Instrumentengeschichter,” Svensk Tidskrift f?r Musikforskning 15 (1933): 48-83.
[4] Wang Kuo Wei and Eduard Erkes (trans.), “Das Chinesische Theater vor der Tang Zeit,” Asia Major 10, part 1 (1934): 229-246.
[5] Hermann Scherchen, “Die Musik des Chinesischen Theaters,” Musica Viva 1 (1936): 46-48.
[6] Heinz Trefzger, “Die Musik in China,” Sinica 11 (1936): 171-197.
[7] Heinz Trefzger, “Das Musik-leben der Tang-Zeit (618-907),” Sinica 13 (1938): 46-82.
[1] Heinz Trefzger, “Ueber das Kin, seine Geschichte, seine Technik, seine Notation und Seine Philosophie,” Schweizerische Musikzeitung 88, no.3 (1948): 88.
[2] Werner Speiser, “Eine Komposition des Dschou Wen-Gu,” Sinica 13 (1938): 39-45.
[3] Wolfram Eberhard, “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 Toung Pao 37 (Suppl.) (Leiden: E. J. Brill, 1942).
[4] Matthias Eder, “Das Jahr im Chinesischen Volkslied,” Folklore Studies 4 (1945): 1-160.
[5] Wang Kuang Ki, “Ueber die Chinesische Musik,” Sinica 2 (1927): 136-144.
[6] Wang Kuang Ki, “Ueber die Chinesischen Notenschriften,” Sinica 3 (1928): 110-123.
[7] Wang Kuang Ki, Ueber die Chinesische Klassische Oper (1530-1860 n. Chr.) (bibl. Diss., Bonn Univ, 1934). Reprinted in Orient et Occident 1 (August 9-21; September 16-33; October 13-29, 1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