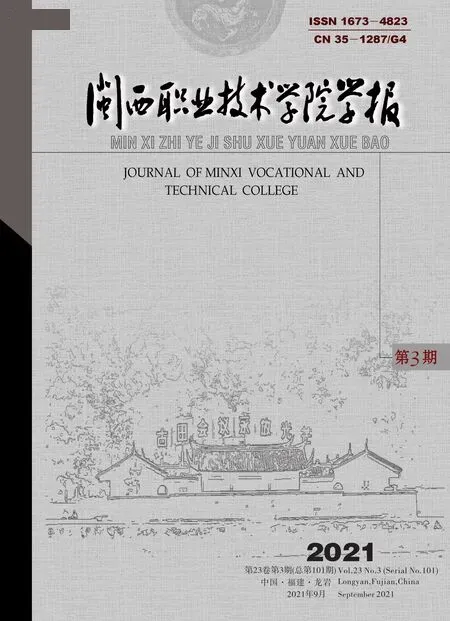蔡崇达散文文本特质探析
2021-12-07林清妹
林清妹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350007)
蔡崇达,泉州晋江人,作家,资深媒体人,中国“非虚构写作”的践行者。作为媒体人的蔡崇达,是中国新闻业的最佳特稿作者,其新闻作品曾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最佳报道奖、亚洲出版协会特别报道大奖。2014年,韩寒、刘德华、李敬泽为其作序的散文集《皮囊》上市,备受关注,十分畅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常推送这本散文集的片段。散文集前半部分写得比较凝练,《皮囊》《母亲的房子》《残疾》《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我的神明朋友》写得非常动人,是全书的精髓。虽然散文集后半部分写得比较松弛,但整体而言《皮囊》不失为一本好的散文集,得到白岩松、阿来、阎连科、谢有顺、陈希我等人较高评价和联名推荐。
《皮囊》是一部采用“非虚构写作”的散文集,蔡崇达用清淡、冷静的笔触书写生活的残酷与成长的烦恼,写亲人、朋友、小镇给予他的思考、痛与乐,借此不断反思和回望自己的成长道路。真实书写、小说质感、人文关怀、原乡情结等,形成蔡崇达散文特有的文本特质。
一、“非虚构写作”:真实书写
评论者称散文集《皮囊》是“非虚构写作”丛林里独具样貌的林木。有别于对一般散文集书写方式的评价,评论者很少用“回忆性散文”“自传体散文”,而是用“非虚构写作”对散文集《皮囊》的书写方式进行定位。“与‘纯文学’或者传统文学追求技巧、追求辞章不同,‘非虚构写作’更注重真相和感情的呈现,这是切合大众心理的关键。‘非虚构’在形式上,与1980年代的报告文学和19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小说相近。”[1]“非虚构写作”更强调散文的真实性品格,与“回忆性”或“自传体”相比,“非虚构写作”更注重作品中人物、事件、信息的真实性。散文集《皮囊》的散文都是作者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所写为“我看见的”。准确说,散文集《皮囊》的散文是在纪实与虚构文学之外的“非虚构”纯文学作品。
“非虚构”文学,其基本的伦理准则是诚实写作。目前,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基本上是纯文学作家或者媒体记者,他们对“非虚构”的概念理解可能不同,但都认同“非虚构写作”必须真诚表达。蔡崇达作为一个媒体人更注重写作的真实感,“我手写我心”的原则融进了骨子里,所以李敬泽说这是一部“认心、认人的书”[2]。
“非虚构文学以对易被忽视、遮蔽的存在的深切关注和作者亲历亲验的在场性书写,拓展写实类作品写作的时空,接通了这类文学形式与普通人生活的关联,复活了作品的生活质感和个体生命气息,保存了现实的多种真实,从而呈现出一个更为全面多样的对象世界。”[3]《皮囊》是蔡崇达真实的成长书写,他从自身真切的生命体验写阿太、父亲、母亲、文展、厚朴等人,去发现、去“看见”每一位亲人、朋友的独特之处,思考生死爱恨,所写之人和事都是从生活经验中获得的。刘德华在《皮囊》的序中写道:“打开《皮囊》,读到崇达果然文如其人的真挚,坦荡荡的自然自白成长经历,没有掩饰凡人难免的喜、怒、哀、乐、贪、嗔、痴,所以很真。”[2]蔡崇达秉承真实的准则书写成长经历,同时他还敢于解剖自我,敢于揭示那些存在于内心的幽微感受,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品里的生活质感与个体生命气息。
二、叙事策略:小说质感营造和仪式化场景描写
(一)小说质感营造
许多评论者评价《皮囊》是本有小说质感的散文集。“非虚构写作”的定位和小说质感的评价并不相悖,“非虚构”强调真实,小说质感强调叙事形式和文本的故事性。
首先,散文集《皮囊》在叙述上采用抒情退隐、冷感叙述。读完整本书会发觉作者的叙述很冷静、客观,始终克制着情感。冷感叙述和19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很类似。蔡崇达的成长环境并不理想,在散文集中他写生活的挣扎、打滚,却不大声叫嚷生活的苦痛。在《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中,他写父亲病重,他待在病房里,发现“这里的小孩脸上都有双通透的眼睛,看着你,仿佛要看进你的心里。我知道那是双痛彻后的眼睛,是被眼泪洗干净的眼睛。因为,那种眼睛我也有。和拥有这种眼睛的人说话,会有疼痛感,会觉得庸俗的玩笑是不能说的,这么薄的问题,在这么厚的目光前,多么羞愧。”[2]他用清淡的笔触书写普通人的故事,犹如细水长流,没有大肆抒发自己的情感,却传达出浓浓的亲情、友情和故土情。
其次,以叙事形式来写散文,近于小说的写法。散文集《皮囊》绝大部分篇章的叙事形式都像在讲诉一个个自己亲历的故事,如《阿小和阿小》《天才文展》《厚朴》等,强烈的故事性让人以为在看小说而不是看散文。这种叙事风格并不少见,川岛的《月夜》、许地山的《空山灵雨》都采用叙事形式写抒情散文。《中国现代散文史》也提到一些小说家如茅盾、巴金、靳以等写的抒情散文,他们把自己内心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认识等巧妙地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艺术画面,使散文具有象征意味。“鲁迅《朝花夕拾》中的许多篇目,灵活运用人物、环境的描写和记叙、议论、抒情相结合的方式,给散文借鉴小说的手法提供了良好的范例。”[4]
蔡崇达长期的新闻写作经历,锻炼了他情节提炼、场景刻画的能力。在散文集中他成功使用小说的人物塑造技巧,勾勒出的人物形象十分鲜明,文本结构完整,具有强烈的叙事性。第一篇散文《皮囊》,短短千余字塑造出一个立体的阿太。在女儿的葬礼上白发人送黑发人时阿太一声都没哭,切菜时把手指头切断阿太都没有哼一声,把年幼的不会游泳的孩子扔海里学游泳……阿太坚硬得像块石头,什么都伤不了她。阿太说的话也令人深思,“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才”[2],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有自己价值观、冷硬通透、不让灵魂被皮囊围困的老太太。
(二)仪式化场景描写
仪式化场景描写不仅是叙事策略,而且是文本意义和内涵阐发的途径。皮囊和灵魂该如何安放的主题贯穿这本散文集,并通过仪式化场景来完成哲学追问——安放好灵魂。
蔡崇达在散文集文本里描写的仪式具有厚重的精神寄托。《残疾》写接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家时的跨火苗仪式,“把包着米的金纸点燃在地上,由两个堂哥抬着他跨过那簇火苗——据说用这么个仪式,灵魂就被洗涤干净了,噩运和污秽就被阻挡在门外”[2]。跨火苗仪式寄托了渴求皮囊恢复康健、重塑洁净灵魂的良好愿望。
仪式常常与诉求表达紧密相连。《我的神明朋友》写母亲自从祈愿生了儿子以后常常去向神明祈祷,有时是倾诉,有时是讨要她丈夫康复的预言,有时甚至是撒娇和耍赖,而摆供品、点香火、投掷圣杯等仪式是每次必做的。仪式弥补了语言表达的薄弱,母亲对父亲深沉的爱体现在她一次次的求神问卜之中。父亲去世后,母亲为父亲找灵,忙碌地奔走于各个庙宇,请神明把丈夫的灵魂引回家。“你其实只是在找个方式自我安慰。”[2]作者这样对母亲说,但母亲仍坚持这么做,还让作者在庙门口喊着父亲的名字,让他“回家”……其实,母亲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安放自己灵魂的仪式。
三、温情书写:人文关怀与小镇叙事
(一)人文关怀
《皮囊》是一部直面人生的散文集,人文关怀浓郁,不仅“看见”自己,而且“看见”身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在《皮囊》中,蔡崇达把和他有关有缘的亲朋好友一个一个照亮:阿太、父亲、母亲、阿小、天才文展、神明朋友……驻足回望,深情审视,求证意义与价值,那些温情而又残酷的文字即是他对生命的理解与尊敬。”[5]他关注生命,“看见”身边人的生死爱恨,对至亲的书写感人至深。
亲情是散文最常见的母题之一,绵密真切的语言指向的是作家的永恒记忆,有温暖,也有苦痛,温情、苦情、价值观传承等都是亲情散文表达的对象。散文集《皮囊》前5篇都是亲情散文,蔡崇达深情书写自己的血脉亲情。着墨最多的是至亲,《母亲的房子》写母亲对建房子的渴望与坚持,丈夫长年卧床,家境一贫如洗,她用瘦弱的身体支撑起整个家,她的信念是盖比村里其他人家都高的房子。表面上是为了争口气,深层次是对丈夫的爱。《我的神明朋友》写母亲去庙里获得灵魂的安定。《残疾》《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写父亲面对疾病,一次次想要挣脱肉体对他的束缚恢复健康,可现实无奈,皮囊长久地折磨着他的灵魂,直至死去。这些篇章都像是作者从骨血里抠出来的,深刻、珍贵。
亲情散文因带有不同程度的传记色彩,涉及到作家的隐私生活,对于涉及到自我内心隐秘的部分,大多下笔谨慎、蜻蜓点水,甚至细心剪裁。但蔡崇达不畏惧自我的揭露,很多都是自我解剖的絮语。他写自己对父亲去世的愤怒,骂父亲为什么那么没用,跌一跤就没了……直到后来他参观大英博物馆展览时才意识到自己没能“看见”父亲,于是写了《残疾》这篇,尽可能地去寻找父亲、“看见”父亲,做一点挽留与告别,也和自己做个和解。
对朋友,在“看见”他们时,也“看见”自己隐秘的内心。他写文展,“和他说话,就如同和一个人在水里纠缠,你拉着他,想和他一起透口气,他却拉着你要一起往下坠”[2]。他写厚朴用力地打招呼,用力地介绍自己,用力地活着,“看到活得这么用力的人,我总会不舒服,仿佛对方在时时提醒我要思考如何生活”[2]。那些存在于内心的幽微感受得到显露,自我表达毫无畏惧。
蔡崇达在后记里写“想要看见更多的人”,这是对生命中所有人的尊重,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因为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一个人最终构成我们本身。每个人都需要这么一份“看见感”,也需要努力去“看见”身边人,最终“看见”自己。
(二)小镇叙事
泉州晋江的东石镇是未被现代化脚步彻底叫醒的小镇,作者生于斯、长于斯,长大后告别故土到北京打拼,但并未脱离他深爱着的这片土地。他用平实、细腻的笔触书写童年记忆、小镇记忆,“东石往事”在小镇叙事中跃然纸上,《张美丽》《阿小和阿小》《天才文展》等小镇气息浓郁。“东石往事”书写作者自己的成长历程,书写张美丽、两个阿小、文展他们的人生起落,描摹闽南小镇的轮廓和小镇特有的风物——石板路、按摩店、海鲜酒楼、渔船等。
蔡崇达对小镇进行细致观察和体悟,因此故乡也就带有他个人化的印记。在对“东石往事”的书写中,他关注到小镇在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一些“不适”。张美丽热烈追求爱情,离婚后回到小镇,开海鲜酒楼、娱乐城,却被小镇人当作反面典型,死后也不能入宗祠,成为“孤魂野鬼”。小镇保守、不够开放,当娱乐城拔地而起时,小镇人却认为现代的娱乐是罪恶的,于是不断妖魔化张美丽,逼得她自杀。儿时的玩伴文展,小镇中小学读书时取得的优秀成绩带给他满满的自信,怀抱梦想和一身的泥土味去城市读书,但城乡差异所导致的价值观差别以及过度关注自身生理缺陷,让他从自信走向自卑,长大后在城市和小镇都无法安身,既失去家乡又无法抵达远方。香港回来的阿小,穿戴时髦,肉身却安放在落后的乡镇,和小镇上带着海土味的另一个阿小形成强烈的对比。香港阿小带坏了小镇阿小,香港阿小可以回香港,而小镇阿小只能留在小镇上继续堕落。在个体的成长历程中,小镇与大都市存在差异,小镇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些慌乱、无所适从。
追望往事,作者没有明显道德、情感倾向上的批判,更多的是对故乡小镇人的“看见”,让读者产生诸多思考,或感叹、或惋惜。
四、蔡崇达散文文本特质成因
细读散文集《皮囊》,可以看出蔡崇达散文的文本特质——真实、小说质感、人文关怀、原乡情结等。作者以乡土小镇为底板,采用清淡、冷静的笔触书写生活的残酷与成长的烦恼,形成这样的叙述方式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新闻写作经历
蔡崇达虽是文坛新人,但之前的新闻写作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厚的积淀。蔡崇达大三就开始从事新闻写作,大学毕业后曾任职《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24岁担任《生活》月刊《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编,27岁任《GQ》中国版报道总监,为全球17个国家版本的《GQ》最年轻的报道总监。曾担纲央视汶川地震专题纪录片策划及撰稿工作,并与白岩松合作《岩松看美国》系列节目。在新闻工作中他写了许多特稿,如《一个人的恐怖主义》、关于药家鑫的《审判》等,新闻写作让他不断逼近更真实的本相和内心。长期的新闻写作使得他文笔凝练,注重细节描写,自觉践行“非虚构写作”,落笔诚挚,不惮于掏出深藏内心的往事解剖自我。
(二)至亲的影响
蔡崇达的亲情散文写得真切动人,《皮囊》《残疾》《母亲的房子》等是散文集中最出彩的几篇。在他笔下,阿太、母亲、父亲都是很立体很有个性的人,他在这些人身上汲取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他的写作不仅是为了“看见”身边人,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
书中的阿太是那样冷硬和超脱,镇定自若地对待身体受到的伤害、女儿的离世,她始终认为“皮囊是拿来折腾的,受苦受难都看淡,安放好灵魂才最重要”[2]。而母亲、父亲给他的精神资源更多的是一种韧劲,母亲对建房子的执念,苦苦支撑着家庭不让自己倒下,父亲身患残疾执著地想要挣脱命运给予皮囊的枷锁,对生活苦难的忍受与挣扎让作者不再害怕苦难。受家人熏陶,作者在讲述生活残酷时出奇地冷静,没有强烈的情绪,总是用清淡的笔调叙述悲痛。冷感叙述成为其散文的一大文本特征。
(三)乡土的滋养
现代人嘴上说“此心安处即是吾乡”,但真的离乡千里仍会寻找精神上的原乡。某种程度上,现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回家情结,追忆童年、故乡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对蔡崇达而言,故乡是他的出发点,是他的根。
小镇青年的成长书写带有一股浓厚的小镇气息,隐现着乡愁。在闽南渔业小镇成长的作者,闽南文化滋养着他,下笔处处体现闽南的风土人情。浓厚的宗教氛围使作者面对苦难叙述时多了一种宗教式的超脱。在厦门和泉州的对比中,作者会感动于自己故乡街头飘出的悲戚南音。泉州之于作者,不只是留存记忆的地方,这片土地像亲人一样和他血脉相连。读者通过他的书写复现各自的故乡图景或乡土影像,进而实现自身对故乡的心灵重构。从这个视角看,蔡崇达散文具有精神怀乡的文本特质。
散文集《皮囊》的最后一篇是一次圆满的精神还乡。他在《回家》里写道:“我知道那种舒服,我认识这里的每块石头,这里的每块石头也认识我;我知道这里的每个角落,怎么被岁月堆积成现在这样的光景;这里的角落也知道我,如何被时间滋长出这样的模样。”[2]他知道,这辈子他都是有家可归、有乡可还的人,不会是“孤魂野鬼”。
他与泉州是互相塑造的,“我是你的游子,你是我的故乡”,泉州文化涵养了他,让他成为有灵魂的人,使他走得更远,到大都市打拼而不怕没有根。而他的成长书写也让更多人认识泉州,塑造了带有蔡崇达个人印记的泉州模样。
五、结语
《皮囊》虽然是个人化的成长散文集,但呈现的皮囊与灵魂该如何相处、对亲人的责任和义务、对身边人的“看见”、对生死的追问、对小镇与大城市的隔膜等诸多问题,牵动读者的心,帮助读者发现自己的内心,给读者留下许多思考。散文集《皮囊》具有真实可感的人物、浓浓的人文关怀和小镇气息,不愧为一本写人、写心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