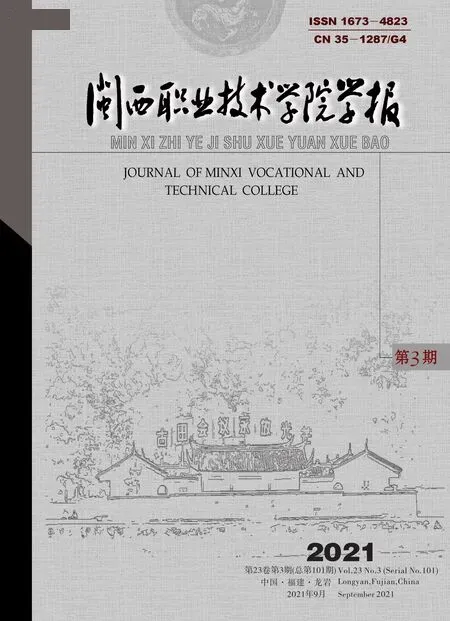项小米对客家文化的探寻和文化身份的重构
2021-12-07魏晓航
魏晓航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00)
文化是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能指系统。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关注文化的内部结构,认为文化是“某个群体共享的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对象的复合体”[1]。然而,对马修·阿诺德与约翰·弗罗而言,文化并非如泰勒所说是先验或自然决定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现象,是共同体取得认同的意识形态手段。可见,在现代多元文化互渗的语境中,对文化的追溯既要考虑泰勒所强调的对文化本质的当代性确认,也意味着在和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对话中,需要对个体身份认同危机进行反思,对文化在当代如何传承进行批判性思考。
作为闽西文化的传承者,项小米以寻找的姿态回归闽西,考察了闽西客家文化内部的复杂因子。同时,在追溯客家文化与家族史中,项小米以文化为桥梁,对个体的文化身份进行深入感知。在《英雄无语》中,项小米通过现代性视野,穿梭在客家人、城市当代知识分子和红色家族后人的三重身份中,解读客家文化的本质,探寻客家文化的精神谱系,重建“游散”现代人的文化身份。
一、客家文化元素的文本审美性建构
《英雄无语》是项小米依据家族史写就的一部长篇小说,项小米以爷爷项与年为原型,用深沉而浓烈的笔触描写了一批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浴血奋战的革命英烈,再现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段重要历史。同时,项小米在《英雄无语》中探究客家文化,探寻祖辈的情感命运。在第一章,叙事者以寻根的姿态从北京回到遥远的福建连城老家,“为的就是一件事:修坟”,在修坟中,“我”看到了祖先的两瓮白骨,产生了对爷爷为何不亲手将白骨收敛入瓮的疑问[2]。由此,怀着对爷爷身世的好奇,“我”逐渐深入闽西大山,深入触摸客家的语言、风俗,对客家文化进行追寻,客家文化由此参与小说文本的审美性建构。
(一)文化背景的呈现:语言和民俗
古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部分汉人因战乱南迁粤、闽、赣等地,居住在赣南、闽西、粤东等山区。为了区别于当地土著居民,这些外来移民自称为“客户”“客家人”。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从中原迁徙到南方,在封闭的环境中,古中原文化吸收了当地土著居民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不但在客家话中保留了大量的古音古韵,而且继承了古中原文化的习俗传统。
“文化是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3]《英雄无语》对客家具有中古色彩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民俗进行了考察,揭示隐藏在客家文化背后客家人的生存模式、思维方式与精神特质。“语言,像文化一样,是由不同年代的各种因素组合成的。”[4]在对客家文化的考证叙事中,项小米着重考证了客家方言。客家方言是中古语言的存留物,是珍贵的活化石。客家人一直保留中原古音,例如:“胡”读为“浮”,“小女孩”称之为“细妹”,眼睛称为“目”,“给我吃饭”说成“给我饭吃”。项小米在小说中详细介绍客家方言的语音、词汇,以及客家人富有文化意味的称谓。客家方言的知识性介绍是客家文化展开的文化背景,但只考证被记载的客家方言特色还不足以表现客家话的特质。项小米在书面记载的基础上,串联了具有民俗色彩的客家歌谣和日常生活中富有趣味的客家方言:“心都掏给你食了,还那样恶!我回老家去!”“月光姆,过连城,连城外,挠韭菜,韭菜心,好弯针,弯针眼,做把伞……”[2]文本中的客家方言让我们看到古中原时期的思维方式,上承古代《诗经》遗风和吸收当地畲瑶民歌的客家歌谣让我们感受到客家人明朗康健、富有创造力的生命气息。客家方言使《英雄无语》的叙事具有浓厚的历史底蕴和地域文化色彩,构造了一个具有客家民系独特思维的原生态叙事空间。
“民俗在本质上是一种带有鲜明特点的,沟通传统与现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文化现象。”[5]如果说闽西的客家方言在历史底蕴和思维方式上为小说叙事添彩加色,那么客家民俗则进一步加强了《英雄无语》叙事的地域性特征。客家人具有厚重的祖先崇拜意识,十分讲究丧葬习俗。《英雄无语》详细介绍了客家人“金斗罂”“二次葬”的丧葬习俗。丧葬习俗是客家人安放心灵、表达生命态度的载体,隆重的土葬体现客家民系对宗族根系的维护。除了介绍丧葬习俗,项小米还介绍了童养媳、闽地“蛇神”传说等,它们与丧葬习俗一起在小说中营造了具有闽西特色的文化背景,使《英雄无语》的叙事具有地方性的文化底蕴。
(二)文本叙事和主题的构建:客家精神
客家方言和习俗共同为《英雄无语》的叙事提供了具有闽西地方特色的文化背景。但客家文化不止于此,正如贾平凹所说“中国文化的积淀,是以此形成了中国国民的精神,而推广之扩大之,渗透于这个民族的性格上、政治上、经济上”[6]。在长期的迁徙中闽西客家人特有的文化源头和生存空间,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而且造就了溯本思源、爱国爱乡、崇文重教、耕读传家、吃苦耐劳、进取拼搏、团结协作、海纳百川的客家精神。
在《英雄无语》中,项小米通过考证客家方言组合而成的歌谣《迁徙诗》,挖掘客家精神丰富的文化特质。《迁徙诗》是一首记载客家人迁徙的远古传说,由于年久佚传,存在许多空缺部分和辨认不清的字迹。“楚歌哀哀,天下归汉。赐□以刘,斩根锄蔓。晦日暗月,秋雨缠绵。忽而放晴,月光带□。□用伏地……”[2]当对客家文化感兴趣的乔纳将这一首远古的歌谣带给“我”时,作为古汉语研究者和闽西客家的后代,“我”决心要还原这首歌谣的完整面貌。在考证《迁徙诗》时,“我”不断发掘其中的客家文化元素。歌谣中不仅有“月光带阑”“目汁涟涟”所包含的独特客家方言,而且有“蛇哥断路,身系两山,稚子幼妹,绑缚至前”的客家“蛇神”传说[2]。最初,对《迁徙诗》的考证仅限于客家方言和民俗方面,填补“月光带□”的空缺是“我”通过认知奶奶的客家话,得出空缺应填写“阑”——代表月光有光圈,预示明日将有风的天气现象。但随着掌握丰富的历史文献,客家精神也得以展现。客家人不仅要面对“风霜雪剑”,还要躲避“官兵趋至,火明刀暗”,他们“坠崖落涧”“咳血如溅”,却依旧相互勉励、踟蹰向前、永不屈服。最终,客家人向着“手指南天”的方向找到了他们的归属之地,在巍巍的大山下,客家人匍匐在地,在此扎根。《迁徙诗》中的迁徙壮史体现了客家人不畏艰难、永不屈服的精神品质。客家精神在《英雄无语》英雄人物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红三十四师营长三叔公,爷爷的同族兄弟,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爷爷不顾生命危险,用胆略和睿智闯过一道道关卡,历经万般艰难,将生死攸关的绝密情报送到瑞金;客家子弟在革命斗争中互相支持、团结同行。爷爷在和莫雄汇合时所用的暗号“楚虽三户,亡秦必……”未填写的即是楚,是爷爷的姓在古时被分封的地方。因楚汉之争而迁徙的客家人始终铭记着自己的根,在极其危险时以楚姓为接头暗号,可见客家人血脉情感深厚。
随着对《迁徙诗》考证的深入,文本的叙事不再局限于对客家精神和革命信念的展现。《迁徙诗》中的后半段,客家人因环境险恶捆绑幼男幼女献祭蛇神,“蛇哥断路,身系两山,稚子幼妹,绑缚至前。子哀呼地,子爷号天。飓风骤起,一忽不见”,以幼小生命换取集体生存的抉择隐喻着在集体话语面前对个体生命的漠视[2]。客家人勇敢进取,但英雄的背后也存在无语的沉默,这是历史所遗留的集体无意识。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客家人将对神灵的信仰置换成至死不渝的坚定信仰。项小米看到了这一点,随着叙事的深入,客家精神在革命斗争中充分呈现。在生死危亡之际,三叔公心中依旧挂念着家中的细妹——“细妹在干么事?他走之后阿姆会不会对她好?”但严酷的战争却不允许他有此想法,在压抑和反压抑的交锋中,对家庭的归念以及生死关头的个人想象最终汇入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中,三叔公用宝贵的生命铸就了对革命的忠诚[2]。在叙事者的探究中,《迁徙诗》所展现的客家精神和对革命的探究产生巨大的张力,穹顶的交融内部呈现多重声音。在现代性的批判视野中,文本从看似以客家文化为背景的封闭性结构中变成具有多重阐发意义的空间。《迁徙诗》所蕴含的客家精神也就和叙述者对革命的认知互相阐释,在推动文本叙事的同时丰富文本的主题建构,使文本成为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整体。
二、回溯视域下的客家文化和身份重建
如果说泰勒关注文化的内部,注重文化的本质性和普遍性,强调文化具有自然和先验的特质,那么阿诺德、弗里德曼与弗罗则更关注文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认为文化是被建构的对象,同时是使共同体获得认同感的意识形态手段。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文化不断和他者进行对比,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之中建立起自己的坐标系。而人和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正如卡西尔所言“人首先转变为‘符号’,而世界则转变为‘文化’,因此生活和历史的全部多样性都被归结为‘符号’对‘文化’的各种关系了”[7]。个体通过文化来确立自身的主体性,个体对文化坐标系的探寻也就具有确认文化身份的意义。
(一)对客家文化在当代存在的现代性反思
在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语境中,西方国家以各种手段冲击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格局,人们在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中面临如何认知自己文化的困境。此时出现的文化寻根创作潮流以寻根的回溯性方式观照地域文化或原始文明,以求对西方的文化话语进行突围解构。然而在突围解构中不同程度出现对文化价值取向与身份认同的焦虑,寻根作家往往难以克服原始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矛盾。
项小米和寻根作家同处文化变迁的时代,在对客家文化精神谱系的追踪中,以《迁徙诗》为线索重建闽西文化的当代谱系。项小米以回看方式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客家精神进行多方面的去蔽,不仅看到客家文化中积极的一面——客家人在革命中所表现的担当、勇敢、无畏,也看到了客家人在牺牲背后所隐含的个人话语被剥脱、情感荒漠化、“围屋”性格中的冷酷等。这样的精神对立集中表现在小说所塑造的爷爷身上,爷爷的性格由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组成——爷爷对党无限忠诚,在革命中“打碎门牙传递情报”,披肝沥胆、义无反顾,但对家庭和亲人却很少顾及,缺少儿女情长,看似冷酷自私。爷爷令作者迷惘困惑、爱恨交织,最终讴歌赞美。项小米解构了客家文化将自我内部合理化、神圣化的历史语境,还原了客家精神特质在革命历史时期的复杂和矛盾。
在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语境中,一些地域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中面临被改写的危机,《迁徙诗》代表的客家文化就受到东西方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双重冲击。《迁徙诗》由乔纳从闽西客家的一位老者手中带来,而对《迁徙诗》进行识别的第一语境并非在闽西的大山,而是在城市的餐馆里。流散的、符号化的城市空间取代了乡土,而以乡土地域为载体的客家文化也面临着被消散的危险。《迁徙诗》中出现的客家丧葬所用的罂,竟在美国的爱丽丝岛保存。而集中表现客家文化在当代的再生,是“我”、乔纳和申建三人对《迁徙诗》的考证。申建是“美国圣约翰大学东方学院古汉语专业博士研究生”[2],身上兼有城市化和西方化的文化印记。虽然和“我”从事同样的专业研究,但他秉持成功学的功利主义心态,将客家精神曲解成为了个人的利益和生存才走出大山的利己主义,不同于“我”真正理解客家精神的纯粹和博大。“如果他像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那样卿卿我我儿女情长,他就可能什么也干不成,不要说他干了这么多杀头掉脑袋的事,在那种险恶的环境里就是什么也不干他连三个月也待不下去。”[2]他不认可“我”行走上海、挖掘历史资料等种种寻找爷爷真实形象的寻根之路,以工具理性的思维为爷爷的精神品质盖棺定论,“我就不管爷爷是否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感情生活……只凭他当年有那样的眼光和魄力从大山里坚决地走出来,从而带给你的父亲、带给你们今天的一切这一点,你们就对该对他顶礼膜拜!”[2]而当“我”最后终于填补完《迁徙诗》的空缺,将其还原为一篇叙述客家人迁徙历史的文章后,申建却抢先发表论文,将考证成果据为己有。
尽管处于酷似德勒兹所描述的游牧文化的时代,项小米依旧以反思立场提炼出客家文化的精华,最终将冠豸山上英魂的铮铮铁骨与时代的脉搏相连接。在蛮荒的大山里,客家人以智慧和团结共同抵御自然界的灾荒和磨难,“即使他们穷得几乎无法生存也从不放弃胸中的抱负,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从大山里走出来,无论求学经商、从政从军,无不勤奋苦斗,务求出人头地、成功发达。客家人的成功,是从他们一开始迁徙就注定了的”[2]。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代,客家人纯粹自然、英勇坚韧的精神特质一脉相承。项小米在寻根之旅中以反思精神挖掘了客家文化丰富的面貌,最终提炼出客家文化具有生命力的精神特质,其回溯的背后蕴含着向前的坚定信念和对文化传承的终极关怀。
(二)个人文化身份的重建
处于文化变迁时代的现代人,往往面临如何确认身份取向的问题。“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8]而文化则是个体寻求自我主体性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项小米对客家文化的追溯实际是在精神返祖中对个体文化身份的重建。
《英雄无语》是项小米以家族人物为原型而创作的小说,其中的叙事人称项小米经过反复斟酌,最后以“我爷爷”“我奶奶”的形式呈现,在叙事人称的背后隐藏着作者的情感投射与精神的探索轨迹。项小米的身上流淌着红色基因,家族是典型的红色家族,她的爷爷项与年是中央特科成员,她的父亲项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作为红色家族的后代,她曾计划写“红色家族”的系列小说,除去关于爷爷的《英雄无语》,还有关于父亲的《红色》,以及关于自己这一代人的《粉色》。项小米的身份是多重的,她既是红色家族后代,又是身处北京的客家人。在非乡土的坐标下,漂泊无依的现代人容易产生怀乡之情,而相对稳定的乡土空间则能给现代人安全感和依赖感,乡土文化成为滋润乡土归属感的根。项小米具有很强的寻根意识,她曾坦言,把客家文化写进小说是有深意的,她是在为自己、为爷爷寻根。男一号爷爷和女一号奶奶都是客家人,也只有客家的男人和女人才能演绎出后面轰轰烈烈的故事[9]。项小米在意识到自己的根基属于客家的同时,也没有忽视自己“异乡人”的身份。项小米处在北京和福建连城的城、乡交界之中,她既不属于北京,也不属于福建连城。她的北京客居身份使客家文化具有原乡的母体象征意义,但由于没有长期在连城生活,她与客家文化之间也存在隔膜。
在三重身份的组合中,项小米对自我身份的确证叠加了对乡土作为母体的情感向往和对家族史追溯的责任意识,具有浓厚的文化寻根意义。在此基础上,项小米将个体的身份困境投射在叙事者“我”的身上。“我”在寻根之旅中,经历了一系列的精神裂变和重组,最终以客家文化为源头寻找到了个人的精神支点。
叙事者“我”以“头疼”为由,来到闽西大山寻根。“我”的老家在闽西,“我”是乔居城市中的“异乡人”。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西方的家庭背景,儿子和丈夫都在海外生活,他们与“我”对家乡的留恋不同,对国内充满着怀疑与否定。在社会身份上,“我”是一个在申建眼中不成功的古汉语研究者,临近中年还没有拿到副高职称。在当代语境中,现代人的身份复杂多重,在“我”的身上,同时集聚了文化身份确认的艰难、家庭身份情感的缺失和社会身份生存的压力。在追寻纯粹精神层面的超我中,“我”同时面对内心深处潜意识里渴望情感的本我和在社会上获得满足感、和认同感的自我。这时,寻根的历程不仅仅是对超我文化身份的确认,而且是在海德格尔称之为“拔根”的社会中对如何建立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主体性人格的思考[10]。
对个人主体性的思考在考证《迁徙诗》中逐渐深入。在对《迁徙诗》的考证中,“我”与申建、乔纳不一样,“我”拥有来自闽西的方言优势,可以辨认出其中难以辩认的字迹。“我”的客家人身份与古汉语研究者的社会身份互相促进,在精神层面得到慰藉的同时,“我”因有地域优势而在学术上得到肯定。然而,对《迁徙诗》进行考证的三个人都非纯正的客家人,乔纳是对客家语言有着极大兴趣的外国人,申建是和客家无关的外人,“我”是最靠近客家文化,但又不是土生土长的客家人。“我”和乔纳在共同寻找精神之根,客家文化对“我”和乔纳而言是远离城市的精神沃土。对于申建,他只在乎考证《迁徙诗》后所得出的成果,客家文化仅仅是满足他虚荣心和社会身份的工具。在共同考证《迁徙诗》时,“我”和申建的关系加速了对客家文化认同与对个人主体性的反思。面对申建这一具有镜像意味的人,“我”对他的感情由敏感、警惕转为好感,甚至最后发展为类似情人的关系。申建实际上填补了“我”无意识的本我欲望,在丈夫和孩子都远去重洋的时候,申建这个“浑身充满朝气和生命力,幽默、睿智,做事果断,善解人意,有钱,大方”的男人恰到好处地出现了,满足了情感方面的本我需求[2]。然而,面对申建“最小耗费原则”“成功是唯一的标准”的话语时,“我”表现出若即若离的姿态。随着对客家文化考察的深入,《迁徙诗》表现出客家文化的复杂性,并非如申建所说具有“走出大山就意味着成功”的“自私”和“利己”姿态,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内涵——在特殊历史时期,爷爷的“自私”体现了无我的博大和纯粹。然而,本我的情感层面遮蔽了“我”内心真实的看法。最后,申建剽窃“我”对《迁徙诗》的考证成果,将论文抢先在国外发表。申建的剽窃使“我”对一次次看似真心实际上是“工于心计的精心策划”幡然醒悟,而“我”也明白了“我”与申建的分歧并不仅仅是观念上的,而是所处的文化和精神根基的不同,正如容格所说“目前正在腐蚀西洋人的心灵的,乃是人们在政治上、社会上以及知识上不遗余力地追求权力,拼命扩张,贪婪获取,永不满足”[11]。在申建这类具有贪欲目的和功利性的利己主义者面前,“我”的犹疑表现出被同化的危险,而“我”最终的醒悟表现了对客家文化和个人主体性的再次确认。
最终,“我”和申建断绝关系,头痛的消失暗喻“我”最终理解了先辈,内心致敬像爷爷那样的革命者、那样纯粹的人。“在即将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里,连城除了盛产地瓜就是盛产烈士——盛产着那些最忠诚刚烈、最优秀的人。”[2]客家文化对“我”而言是精神根基,而不是成功的手段,“你爱它,出自天然,哪怕它是那样僻远、贫困、一无所有”[2]。以坚守的姿态和批判的反思性眼光去传承客家文化,在巍巍的冠豸山下,“我”寻找到了个人真正的精神沃土和存在方式。
三、结语
项小米以寻找的立场回到闽西大山,重建了客家文化的当代谱系与人的精神归属之地。客家文化在《英雄无语》中作为文化背景丰富了文本的地域性,使叙事具有地方性的文化底蕴。同时,客家文化作为叙事线索之一参与叙事,推动了叙事的发展和主题意义的建构。在全球化文化冲突的语境中,项小米以回溯性的眼光对以科技与启蒙理性为代表的现代性进行了充分的反思,对客家文化和个人主体身份的重构进行了可贵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