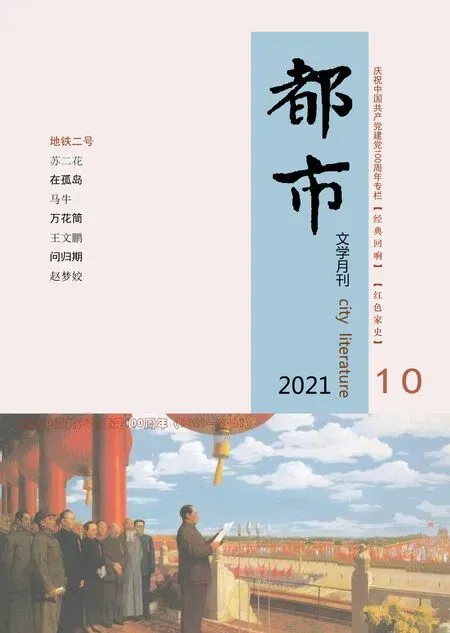《红日》映照江山图
2021-12-07刘照华
文 刘照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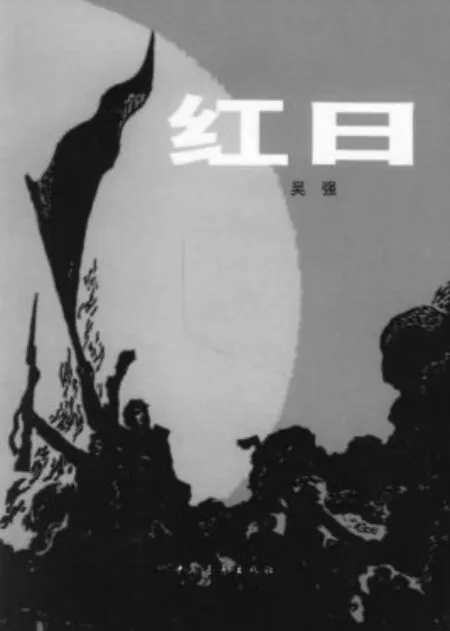
吴强创作的革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红日》,其题目颇有诗意,且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它象征着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即将一扫黑暗迎来光明,象征着人民解放军艰苦卓绝的战斗必然获取最后的胜利。而陶醉于书中的阅读者,还会从文字间流淌的气韵中获得一种鲜明的意境,如果借用画面来表达,可谓之“红日江山图”。从白热化战斗的冲锋中,从燃烧一般的誓言中,从血染沙场、前仆后继的牺牲中,传达出的是为人民打江山的信念。奋勇征战的革命军人,舍生忘死的支前百姓,他们的心里都迎着一轮红日,映照着人民的江山。
一
《红日》取材于解放战争第一年,华东解放军在苏北、山东战场与国民党军队激烈交战的史实。尽管客观上敌强我弱,但在陈毅、粟裕等指挥下,华东解放军将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构成《红日》故事主干的涟水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便具体体现了这样的作战原则,如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以诱敌深入,然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各个击破,力求全歼、速决。
据作者吴强自述,“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1947 年5 月17 日),在我们住村口头,我看到从山上抬来的张灵甫(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师长)的尸体,躺在一块门板上。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从去年(1946 年)秋末冬初,张灵甫的七十四师进攻涟水城,我军在经过苦战以后,撤出了阵地,北上山东,经过二月莱芜大捷,到七十四师的被消灭和张灵甫死于孟良崮,正好是一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后来,我有过把这个故事组织起来写成作品的想头。”然而,是否能把战斗故事写成长篇小说,这让吴强经历了长时间的选择与思量,特别是在忠于史实和发挥艺术创造力、表现力的关系问题上,他觉得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和考验。平心而论,这种意义特殊、背景复杂、头绪繁多、过程曲折的战争故事,很容易将创作者导入一种对历史事件逻辑关系的形象化叙述,即:突出史实性,牺牲文学性。而这是《红日》作者吴强所要极力避免的。
在创作《红日》之前,吴强并无大部头的创作经验,却能对文学创作有如此严肃的态度和如此高度的自觉,的确值得我们致敬。从1947 年5 月萌生创作念头,到1957 年4 月完稿、7 月出版,十年怀胎不寻常。经十年苦苦思索、打磨,吴强终于豁然开朗地解决了创作难题,找到了实现这次文学创作的路径,在确保历次战役基本情势和过程有根有据的基础上,将故事里的人物、细节合理设计、虚构,保留了较为充分的文学表达空间,让故事的骨骼上生出了文学的翅膀,富有较强的感染力。长篇小说《红日》成为正面描写大兵团作战的文学典范。
二
《红日》所反映的几场战役,是解放战争第一阶段最激烈的争锋,双方均是大兵团集结或多个部队运动配合,是场面宏大、瞬息变化的战争。小说并未将主焦点放在双方指挥、决策层面,也未将战场双方的对弈和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挺在前面,而是将参加了这三场战役的解放军某主力部队作为正面表现对象,紧紧抓住战争中活的元素——具体的人,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众多人物的形象、性格、气质、言语、行动中,塑造一支军队的魂魄,写出战争的趋势和本质。
小说中,沈振新任军长、丁元善任政委、梁波任副军长的部队,在战役中的特殊角色、特殊经历以及特殊的情结,构成戏剧性因素,他们在第二次涟水战役中,与蒋介石“心腹”、“王牌”部队——整编七十四师交战失利,遭受重要损失,心中充满复仇火焰。这种强烈愿望辗转不得施展,却又在我方运动战神来之笔的调遣下,意外地获得了柳暗花明的机会,最终痛快淋漓地消灭宿敌。这构成了小说的内在线索。小说的焦点在于这一支部队指战员接受指令、消化情绪、承受困难、打造战斗力、冲锋陷阵的层面,而所有这些,都归结于具体人物的表现。从高级指挥员到基层指战员,他们职责有别、风貌各异,而在严峻的战斗面前,都呈现了鲜明的甚至极致的一面,成为小说故事最具活力的看点。作者吴强将真实战斗过程的框架及其中的戏剧性冲突元素为我所用,在此基础上,他的创作焦点集中于典型人物的塑造。
在《红日》中,出场人物众多,并且围绕这些人物,展现了立体化的战争生活,行军、爬山、涉水、泅渡、射击、冲锋、肉搏……这些人物、事件、场景容纳在战争的故事框架之中,但它们不是简单地编排、码放,而是贯穿着统一的情绪与气韵,在构成战争生活丰富性的同时,这些元素共同服从于一个写作意图——从始至终,作者都在通过叙述、描写回答两个问题,即:这是怎样的一支军队;这是怎样的一场战争。有了这样一条贯通的气脉,小说中反映的战争与和平、爱情与友情、前方与后方、军队与人民,都自然紧密地编织起来,构成一个艺术整体。由此,小说《红日》的一切丰富都是聚合的,而其文学表达又是收放自如的。
三
《红日》重点塑造的指战员形象,有军长沈振新、副军长梁波、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班长秦守本等,就故事结构而言,位置最突出的人物,是原任四班班长、后任二排副排长、排长的杨军。
杨军是小说贯串始终且着力塑造的人物。在故事开头,第二次涟水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敌攻我守的阵地战打了两天半,敌方只见炮弹、炸弹,不见人。这时,班长杨军是全班战士的主心骨,他调整着战士们的情绪:“不要急!他们总是要来的!”“我们的刺刀、子弹,不会没事干的!有一天,我们也会有大炮!”小说通过杨军的视角,写出了战场上令人憋气的无奈的牺牲——“杨军伸头到掩蔽部门口外面望望,五班门口躺着两个战士,一个已经死了,他的头部埋在泥土里。一个受了伤,身子斜仰在塌下来的土堆上,两条腿搭在折断了的木头上,头颈倒悬在土堆子下面,杨军认出那是青年战士洪东才。”《红日》开篇就将这样的战场真实呈现出来,并且在这紧要关头塑造着杨军这个人物。
杨军看到战友们一枪不放却在掩蔽部内遭受榴弹炮袭击而牺牲,他也曾心绪纷乱,产生了带领战士们杀出去的冲动,但当敌人炮弹再次纷纷倾泻下来时,他迅速冷静下来,带领全班战士加固着工事。随后,在敌军步兵出动、攻到涟水城下,全班只剩下五人时,他的左肩楔入了一寸多长的一块炮弹片,但他顾不得包扎……当敌人步兵第七次冲锋到达近前时,他带着班里仅有的四个战斗员,迎着敌人冲了出去。
通过战场特写,最能生动、传神地反映两军锋刃相搏的情状,也最能令人信服地塑造钢铁战士的品质。小说《红日》善于以此呈现各级指战员身上的光亮,外化他们扛起壮丽河山的精神,传达他们赴汤蹈火的信念。小说开篇重点描写班长杨军组织全班反冲锋的场面,前后一长串的特写镜头里,杨军表现出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引导有方、英勇善战的品质。他既冷静,又勇猛,关键时刻能奋不顾身冲在最前,体现出优秀战斗员的刚性、韧性。
小说《红日》重视塑造像杨军这样的基层指战员形象,依托这些形象,从班、排、连这些基层作战单元描写战斗实景,展现了诸多极富冲击力、震撼力的战场特写,也自然地聚焦了战场内外许多人物关系细节,将镜头深入到军旅生活最基础、最内在的部分。这也让作者吴强丰富的经历、出色的文学才华大有用武之地,成就了小说富有写真、传奇效果的故事性,并让这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有了更多细腻的、值得咀嚼的看点。
四
小说中的杨军,经历了诸多军旅生活内容,联系起了上、下不同类型的人物,他的故事以及由他关联着的人物、事件,对于说明这支英雄部队的内在品质有着突出作用。
杨军因在涟水战役中负伤而转入后方休养,顺着他的这一经历,又延展出战场之外的更多镜头。从杨军昏迷睡梦中,交代了三年前苏国英营长率队攻城的英雄事迹,当时营长苏国英是杨军仰慕的榜样,那次苏营长受伤后也是由他背上担架的。苏国英后来成为他的团长,在涟水战役中牺牲。此处的笔墨,写出了杨军对英雄精神的传承,同时也点出了一个英雄集体的来由。
负伤休养的杨军,要求递上“我很快就要回去”的决心,并说:“我那支枪,号码是:八七三七七三,用熟了,不要分配给别人。”枪,是战士的生命,这里用枪写出了战士的心。此刻,这支枪装在杨军的心里,虽无法扣动扳机,但它比握在手里的枪更有威力,这样的战士组成的部队,锐不可当!
即便身在后方养伤,作为战斗英雄的杨军,仍然在他的部队中产生着影响。期间,杨军的继任者、四班长张华峰,原四班老战士、新任六班班长的秦守本,一起给老班长杨军写信,这一情节,仍然是对杨军“主心骨”地位的强调。而从人物之间的精神关联角度考察,小说中张华峰、秦守本二人,是先后在杨军的示范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人物塑造关系上,他们都是杨军的“影子”。
进一步考察杨军的影响力,将他引为榜样的,不仅有张华峰、秦守本等原班战士。孟良崮战役棋局已开、大军即将渡过沙河飞兵前进时,杨军伤愈归队。这一刻,特写了战友们对这位战斗英雄的敬爱与欢迎。写渡河的大木排翻转、军长沈振新落水时,再次把杨军纳入特写,他扑入水中奋力营救,与心里一直惦记他的一军之长浪里相逢。在小说故事高潮的孟良崮战役开篇之际,如此隆重地安排杨军重回战场,自然是出于对此形象的突出与渲染。杨军归队这一节,还重点借他的视角,对他回到的八连作了检阅,写出了经过莱芜大捷后,这支军队人员数量的壮大、武器装备的增强,更从他“担心落后”的心理,写出了英雄队伍的精神状态,自然地叙述了这是怎样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在小说尾声,“孟良崮高峰争夺战达到了钢铁的熔点”,火线接任二排长的杨军,最终在危难之际显身手,踏着战友牺牲的血迹奋力攀上峰顶,展开一对多的顽强战斗……胜利到来时,杨军从牺牲了的张华峰手里,拿起了红旗……从回答“这是怎样的一支军队”的角度透视,举起这胜利旗帜的,是排长杨军,更是这支铁军之魂魄。
五
军长沈振新,是《红日》中英雄部队魂魄的重要担当者。小说用不同的特写,从不同方面对他作了充分刻画。
涟水战役失利后,这位军长审问俘虏的特写,令他的形象一下子就入脑入心。他的神情和语言,如同带着锐利的锋刃,将俘虏李小甫伪装着的侥幸、傲慢、抗拒一层一层劈削而去,将其打回原形。军长的气势将对方压得粉碎,言词间坦露了一位将军骨子里的猛与刚,显露了他的血性,使得形象鲜明,个性突出。
军长的刚猛外露,体现了他与苏国英的继任者——团长刘胜的精神气质有着内在贯通。但小说着力表现的,是他的另一面——作为高级指挥员的犀利、深隽。
团长刘胜看不起知识分子出身的新任团政委陈坚,军长沈振新批评刘胜:“同志!虚心一点好!对自己要多看短处,对别人要多看到长处……骄傲自满的人,常把自己逼到独木桥上。”他看得到刘胜的明显缺点,指其毛病不绕弯子、直截了当,但内心深处,他更能看到这位在革命队伍里生活了十五年的勇士的披肝沥胆。当发现刘胜衣服后摆烧了一个铜板大的洞,便在刘胜临走时,派警卫员李尧飞跑着把自己的夹绒大衣披到刘胜身上。可见这位军长外刚内柔,有着言简情浓的坦荡与深沉。
莱芜大战在即,已无足够的练兵时间,军长沈振新说话了,这话经他的口说出,一句顶一万句:“练兵,主要在战斗里练。”“敌人的炮多得很!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有决心到敌人手里去拿。”这是对意志和信念的呼唤,这是对胆气和血性的激发,铁军的魂魄就是靠这样的“武器”拼出来的。
这是一位能在关键时刻画龙点睛的军长,他所指出的原则和方法,就是创造条件,创造经验,创造优势,创造战斗力。而这样的创造,会不断地化为这支战斗部队的内心准则和行动自觉,也就是这支部队不断强大起来的重要内因。
军一级高级指挥员,就是在这一层次上显现了特殊魅力。再看孟良崮战役中的军长特写——
当孟良崮战役进入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犯了胃病的军长沈振新靠前指挥,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来到师指挥部。他的语言在燃烧:“把所有的炮火集中!猛打!抢占山头下面那两个陡崖,站住脚,一股劲朝上攻。不许敌人还手!炮不停,枪不歇,人也不停、不歇!不要留家底子!统统统统投上去!”
在孟良崮战役的最后阶段,军长沈振新下了果断的、解渴的命令:“不管什么作战分界线,最后解决战斗的时候,只管消灭敌人!不管你的地区我的地区!”而这时刻,转瞬间又发生了新的危机,面临重大考验。千钓一发之际,军长手持话筒,与政委丁元善商量的过程不假思索,一句连一句,一边回应政委的疑问,一边提出了应对决策,当军长重新把口对到话筒上时,一道撑起千钧分量的命令便果断发出。
《红日》中,副军长梁波这个形象,与军长沈振新大体形成“双股绳”关系,加强着对一支英雄部队高级指挥层面之智慧、意志、作风的说明。他们均具有坚韧不拔、智勇双全、果敢坚定的光环。而细加品味,军长沈振新在讲大局、有谋略、守原则的同时,言语、行动间透着感性,时有率性表达;相比之下,副军长梁波细致周密,冷静果断,既胸怀大局,又处事灵活,保持着高度的理性自觉。
两位英雄的美,各有其不同凡响之处。军长沈振新性情深处有大开大合的张力,既可密不透风,又能疏可跑马,令人有情趣横生的期待、多重审美的愉悦。副军长梁波闪现着有故事男人特有的浑厚,调子里有较多相对沉稳的和弦。
六
莱芜大捷后,部队进入休整期,呈现出战争间隙的“慢板”情态,体现了与紧张战斗节奏形成鲜明反差的舒缓气氛。分别写了军长沈振新与妻子黎菁的感情生活,杨军妻子阿菊千里寻夫的家事,其中还用朦胧而热烈的笔墨,描写了女机要员姚月琴被军长魅力吸引而燃烧起的心中爱恋。对于以塑造人物形象为追求的小说而言,这和缓平铺却又淋漓尽致的叙述是重要的。
这里,小说中专门用一整章的篇幅,来写杨军与阿菊。
杨军养好伤快要回到战场时,战友们一面与他惜别,一面拿他和阿菊的话题打趣。伤员梅如福一心想在小夫妻临别前促成他们的团圆美事,当他精心谋划,与孤身的余大娘说好认阿菊为干女儿,并且当晚给阿菊和杨军布置“婚房”时,杨军的腼腆及阿菊淳朴而不失机灵的情态写得十分鲜活。最初不好意思做梅如福安排的剧中人的杨军,最终当了“新郎”入了戏,首先入的是与余大娘的“母子相认”——“恍惚间,他仿佛看到了他的慈祥的母亲。”而打扮成新娘子的阿菊,鞋子上绣着小蝴蝶,“小蝴蝶像是要飞起来似的。头发修整得很好,是黎菁给了她一个鸡蛋,教她用蛋清洗过了的,每一根发丝都清朗朗的发着亮光。”
杨军和阿菊在这特殊的待遇里,真是久违地回家了,深深体验着战友之间、战士与百姓之间的水乳交融——这必然让他更强烈地生出伟大的意志,伟大的爱,为了人民,为了江山,英勇战斗,一往无前。
小说中,“红日江山图”笔墨分布在全篇。如部队马上要开入山东老解放区作战,熟悉山东的副军长梁波讲到抗战时期当地发生的一个故事:一位青年村民冒名顶替、慷慨赴死,掩护了一位负伤的姓黄的排长。并一语道出了战争的基本面:“有这样的群众条件,仗还不好打?加上现在都分到了地,国民党来了,老百姓还不跟他们拼命?”
又如,部队在虎头崮演习时,战士叶玉明不幸牺牲,引出经常受叶玉明照顾的张大娘与战士们的交往。人民与战士的关系,如同父母与子弟,江山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人民打江山的。子弟兵的牺牲,是默默的,也是壮丽的。
再如,部队向孟良崮战场开拔前,地委书记华静表态:“打马家桥的担架队全部跟你们去!木排不够用,我们立刻动员赶做!”战场连着后方,连着百姓的奔忙。解放军与百姓同心所向。
这些情节,都在回答着:这是怎样的一支军队、这是怎样的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