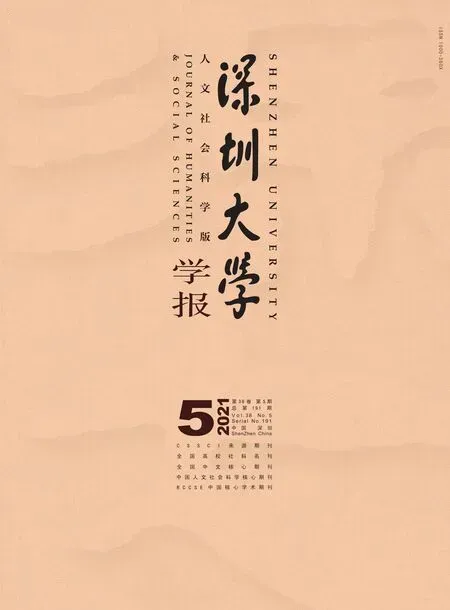中国赛博朋克文化表征及话语建构
2021-12-06江玉琴
江玉琴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
青年群体表征及其活动构成一种文化现象并成为学术研究对象,始自20世纪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青年行为表征被认为生成了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并被看作是对主流文化的抵制、反抗或协商①[1]。青年亚文化研究以往多聚焦在街头文化、消费文化,甚至青年反常行为,较少关注到科幻文学与科幻文化,没有认识到科幻文化已经成为青年文化的新领域。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极大吸引了青年群体的注意力。青年群体凭借科技创新工具实现自己超越父辈、实现自我的理想。他们的文化创造已经成为当前流行文化与青年文化中的重要表征。同时通过科幻作品、科幻文化甚至科幻游戏,青年群体正在占据话语主动权,积极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与文化模式。中国赛博朋克文化作为科幻文化与青年文化的结合体,还处于初步发展状态,但也已在逐步形成自己的话语特性。本文纵览赛博朋克小说在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科幻文学特点与青年文化意识,观照中国赛博朋克文化表征,以中国赛博朋克小说《荒潮》为聚焦点,探讨中国赛博朋克文化的话语建构。
一、赛博朋克小说成为青年亚文化的文学表征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青年亚文化的兴盛时期,其中朋克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青年亚文化主流。20世纪80年代朋克文化开始与科幻文学融合,形成颇具影响力的赛博朋克小说潮流。赛博朋克小说也由此成为青年亚文化在文学领域的突出反映。科幻作家斯特林(Bruce Sterling)宣称赛博朋克流派是20世纪80年代新生的一种新文化综合体,赛博朋克艺术捕获了“一种新的整合方式”[2],整合了过去被分离的高科技王国和现代地下世界的流行元素。赛博朋克小说作为商业市场上硬科幻小说产物,探索了结构的多元性与主体自我的不稳定性,彰显了文本的后现代性。本文认为,赛博朋克小说正是通过整合科技想象与文学叙事,呈现了被主流文化压抑的边缘青年群体想要摆脱各种社会束缚、竭力昭示自我的文化主张。
(一)作为青年反文化的朋克音乐与朋克文化
朋克音乐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天鹅绒地下乐队(the Velvet Underground)的首次登台表演为开端。20世纪70年代朋克音乐成为青年流行音乐主潮。朋克也由此成为20世纪青年运动中讨论最多、分析最多的一个词汇。经由朋克音乐发展而来的朋克文化成为20世纪70~80年代最显著的青年文化表征。但实际上朋克一词本身具有多种解释。“对一些人而言,朋克意味着反抗服从性或者反抗父母、学校、工作和社会”,“对其他一些人来说,朋克意味着控制自己的生活,无需等待别人的帮助或赞同来做自己的事情”,“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朋克是一种大声的、快速风格的音乐,极少装饰性,但里面包含有自己的用心和对音乐的忠诚”[3]。布莱肖认为,朋克音乐源于年轻人对早先20世纪50~60年代音乐与文化形式的不满与反抗。朋克一词很难有真正准确的定义。但朋克具有一些基本特性,如反叛性、非服从性、都市化、违背规则、试图获得权力,甚至从事朋克音乐的人也通常是死于年轻的[4](P6-7),这些特性往往标示出朋克音乐与其它音乐形式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朋克本身还具有政治意义,它表达了年轻人的愤怒与憎恨,彰显年轻人的直接行动力、年轻人渴望的自由。而且朋克更形成一种文化,它以音乐的形式来让青年人无需理会社会的指责,以反时尚来表达自己的独特思想状态,创造自己的DIY美学等[4](P8-9)。因此在朋克音乐与朋克文化中生成的朋克精神就呈现为个体的独一无二性,是“勇敢、自我表达、自由”,是“穿你想要穿的,说你想说的话,做你想做的音乐”[5]。
朋克文化是20世纪70年代当时英美文化危机的反映。英美经济大衰退、美国越战带来的战争创伤、政治上的水门事件丑闻等都让年轻人沉浸于激进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中,他们不愿意成为秩序和理性的囚徒。因此他们打破音乐习俗,宣扬朋克的反规则精神,这也让朋克文化甚至成为一个“激进的、荒谬的、危险的现象”[6]。年轻人借助音乐形式无视权威和资本主义,抨击主流文化是一种虚伪、浅薄和错误的文化,提出“做你自己”的口号,不跟随权威,反对商业主义。朋克文化的这些概念鼓舞了成千上万的人们跟随它,人们致力于创造自己的音乐、艺术、电影、时尚和写作,甚至产生出自由思想与行动,反抗主流文化,致力于改变世界。
(二)赛博朋克小说的兴起与新特性
20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朋克文化开启了一条新的通道。赛博朋克小说燃起年轻人的科技想象热潮。赛博朋克小说于是成为集科技想象、技术生活与青年寻求自主个性于一体的新型青年文化形式。
从技术层面看,赛博朋克的兴起离不开信息技术开拓的网络世界与赛博空间。在1980年代,赛博空间、赛博格和赛博朋克逐渐成为人们众所周知的术语,形成了一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的来源是1948年科学家维纳提出的控制论。维纳认为,控制论就是“为研究这些完全不同系统的共同特征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接近数学方法,但比数学方法更为广泛,特别是用计算机进行模拟和仿真,这显然比传统的数学方法与实验方法对复杂系统有着更为有效的作用,而且适用范围也大得多。可以说,控制论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学科群”[7]。控制论研究有机组织和机器控制、信息传播,并产生出控制论有机体:一种人类-机器混合体。而赛博空间就指向这样一种信息空间,其中信息被以这样的方式来整合以供操纵者控制、移动和介入信息的想象,人们由此被关联在一起,借用刺激物链接,产生出对操作者的反馈圈。虚拟现实应运而生,“虚拟现实表征了这个过程的最终延伸,提供一种纯粹的信息空间,由一些控制论自动化或信息建构的信息空间,提供一种人工环境的高度的生动性和整体上的感官浸入感”[8](P3)。这种技术新表征与青年朋克文化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赛博朋克文化。一方面控制论根据信息可以呈现的抽象原则糅合进大众消费产品,以此提供管理社会的方法;另一方面,这些大众消费产物又更多是象征意义的,是为了适应人类身体甚至是定义身份的一种人为制造。因此,“镶嵌在赛博文化中的东西被转变进入到商品中,以资本主义的逻辑被要求来进行不断的转换,这里并没有真正永恒的东西。同时,控制论也因它开放的多样性阐释而无法保持稳定性”[9](P19)。赛博朋克因与朋克文化的关联也具有了控制论的这种似是而非特性。
赛博朋克词语进入文学开始于科幻作家贝斯克(Bruce Bethke)在同名短篇故事(1983年收录在《惊异科幻故事集》)中的首次使用。之后在《华盛顿邮报》(1984年)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多佐伊(Gardner Dozois)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作者如斯特林(Bruce Sterling)、卡蒂根(PatCadigan)以及吉布森(William Gibson)等人的科幻故事特性,尤其是吉布森在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中也使用了这个词汇。作家们通过小说作品都致力于探讨“人性的什么方面让我们具有人类的独特性?”问题,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人们对新出现的人类与人工智能、仿生人、赛博格、计算机虚拟身体、突变与复制人等身体交互新形态的思考。赛博朋克因其中涉及的技术与资本内容而被认为是可以用“社会和文化理论来理解走向新联盟”[8](P7)的一种有用资源。因此赛博朋克小说中的“赛博”显示了它的技术想象,呈现为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万维网络与虚拟世界,而“朋克”则意味着处于边缘的人们如外来者、混杂者、心理困境者,挣扎于濒临灭绝的星球,在泥泞的道路中为未来寻求一条出路。赛博朋克就是“呈现未来的想象,是基于赛博空间观念上的延展应用,是威廉·吉布森小说《神经漫游者》中出现的世界”[9](P14)。
麦卡菲(Larry McCaffery)认为,赛博朋克小说产生的认知地图体现了人们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呈现后现代状况中强有力的但又充满麻烦的技术逻辑”,它本身也“系统性地改变了我们的基本认知,如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什么是真实、什么是人类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东西”[10](P16)。赛博朋克小说不断更新我们现有的自我与世界认知,同时也不断彰显人们对技术发展产生的社会、资本压迫等问题的批判与反抗。而且朋克文化本身就建构了一种整体美学,这种美学培育和阐释主流文化不满意的事物的意义。这也是赫伯迪克所观察到的,“朋克外表是粗俗的,以一种拒绝的姿态站立”[11]。因此赛博朋克小说与朋克音乐家们一样都拥有一种历练过的能力,即“使用技术来作为反对技术本身,从媒介产业的平庸化来控制它的形式,并重建一种危机感、紧迫感”[10](P289)。由此来看,赛博朋克文化本身具有后现代的不确定性与反抗张力。
音乐、反文化与文学共同构成了赛博朋克文化。这三者的结合刻画了赛博朋克作家身上所具有的社会语境关联性,并呈现出社会语境的亚文化特性。赛博朋克小说也因此成为了当代社会语境中无根、异化和文化疏离的隐喻,指向了都市集体中的青年亚文化形态。
二、中国赛博朋克文化表征
20世纪70~80年代兴盛的西方赛博朋克文化在20世纪末传播到中国,并在21世纪初受到青年人的大力欢迎,中国赛博朋克文化开始蓬勃发展。尤其是21世纪中国人工智能的研发极大推动了年轻人的科技热情与未来想象。21世纪以来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论文很多以“赛博朋克”为选题。赛博朋克研究充分展现了人们对赛博技术与赛博朋克小说及文化的热爱。赛博朋克文化在中国的热潮不仅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主题的热衷,还体现了青年群体在大众文化中对它的拥抱与接受。B站、豆瓣、知乎等网络平台存在大量讨论赛博朋克的帖子和视频。但青年们也普遍意识到“现在的新赛博朋克,更加偏向消费主义,注重于外观表现,而逐渐摒弃了过往赛博作品中‘反抗、反乌托邦’的朋克内核”[12],赛博朋克以技术呈现更好的视效,但其精神内核被剔除,沦为纯粹的消费品,赛博朋克俨然成为了年轻人都能讨论并热衷参与的游戏与生活。从现有的发展情况看,中国赛博朋克文化还处于生长进程中,具体呈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科技化想象:以西方科幻影视的未来世界想象中国赛博朋克城市
以豆瓣平台发表的讨论文本为观照,这一平台上赛博朋克小组核心关注的内容是赛博朋克与未来风格,具体囊括时尚、生活、文学、科幻、音乐、影视、行为、标志等自由讨论主题。中国赛博朋克文化在理解美国赛博朋克文化的同时,从中国现实认识科技未来,突出呈现都市生活的高科技与低生活,即一方面突出高科技的城市再现,另一方面挖掘底层人们生活的单一化。但有学者质疑说,“赛博朋克可以有与中国文化相通的地方,但中国必然不会有赛博朋克的基因”[13]。
从大众消费文化表征来看,中国赛博朋克城市的想象颇具典型性。首先,中国赛博朋克以嫁接与魔改的视频方式呈现科技带来的重金属视觉感受,强调中国当代科技发展产生城市快速建设中的高楼森林形象。B站视频《赛博朋克山海经》《未来之城-赛博朋克重庆》《香港魔力:赛博朋克之城》都表现出科技生活给人带来的光怪陆离的感受。这些视频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但让人感受到科技发展之下的一种阴郁、嘈杂与逃离。《香港魔力:赛博朋克之城》更能体现都市森林穿插在科技大楼之中的失去个体、单一化、流水线等意识。其次,中国赛博朋克批判科技发展带来的都市生活压力与个体异变。2017年12月8日周郎顾曲发文“宇宙中心五道口:暂时沉默的赛博朋克世界”,把北京的五道口看作是一个赛博朋克世界,是一个“北漂、拾荒者、小贩、原住民、码农和大学生又爱又恨的存在”[14]。这里作者实际上已经将赛博朋克世界看作是一个不同人群的交汇处,一个过去与现在、科技与手工、梦想与存活、精英与无产者交互的存在场所。赛博朋克成为了一种充斥着技术乐观主义与生活悲观主义的混合物,这本身也是赛博朋克宣扬的“高技术、低生活”的一种表征。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赛博朋克更呈现为一种技术乐观主义姿态。
(二)狂欢化:网络成为青年消遣与任性的场域
赛福(Stasa Sever)将假体、赛博格与赛博空间看作是三位一体,认为当今世界的我们日益依赖电子设备,这些设备已经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甚至没有这些设备,我们就会感觉迷失了自己。技术就像是我们的假体,其使得我们能够在今天的赛博空间信息世界中遨游[15]。赛博朋克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日益转变成今天的现实。很多技术如虚拟现实和网络,在当时赛博朋克文学中还被书写为是虚构性的,但现在已经成为了真实的、可以让每个人都能进入的现实。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赛博朋克,技术成为人们在信息世界的假体,那么中国赛博朋克呈现为狂欢化形态。
杜丹发现,青年人正以网络新媒介技术开辟了一个并行于实体空间的虚拟世界,青年们通过网络等各种虚拟社区进行新型涂鸦,以网络身体“替身”实现向外延展和连接,在网络中“抛弃实体空间相对单一、稳定和主流的社会审美规范,打破常规的界限,追求非常规塑造的自由,以摆脱身体极其严厉的权力控制”[16](P41)。杜丹将这种现象看作是青年文化的新话语形成和意义表达,认为年轻人以这种方式将承受的现代性压力释放出来,同时通过改造自己获得感性重生的审美实践。但虚拟身体的对抗性经由文化工业的收编与改造,演变成风格化的消费品和商业利润,消解了具体事件的讨论基础以及反讽、批判的效果,狂欢化最终导向娱乐性的物质和肉体的身体消费[16](P42-50)。笔者认为,作为技术假体的网络呈现了中国青年在赛博朋克文化中对技术的认可与自我自由的展现,赛博朋克文化由此更多呈现为狂欢化特性。张荣甚至将中国网络狂欢理解为话语狂欢,即“在互联网这一数字化空间中,参与狂欢的网民主要是使用文字、符号、图片等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戏谑和讥讽中呈现出网络狂欢的话语盛宴”[17]。众多网民在话语狂欢中构成网络共同体,形成一种风险社会中的群体归属。这恰恰与西方赛博朋克文化的个人主义与做自己的风格相背离,形成了中国赛博朋克的集体性特征。
(三)自主性:赛博朋克小说的本土创造
中国赛博朋克小说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杨平、陈楸帆、拉拉等成为中国赛博朋克小说界的典型代表。星河的《决斗在网络》(1995)和杨平的《MUD-黑客事件》(1998)可以说是中国赛博朋克作品的滥觞。这两部作品成为中国互联网大潮中的一种亚文化。但陈楸帆认为,“特殊的时代注脚反映到文本层面,可以看出对西方作品的稚嫩模仿,且着力点更偏重于‘赛博空间’的技术想象与奇观,对于更深层的‘朋克精神’却欠缺理解和表达”[18]。与美国赛博朋克小说相比较,因中国作家没有对嬉皮运动、个体主义以及药物文化的深度体认,反而导致中国赛博朋克文化并没有美国赛博文化青年的颓废与虚无,当然也就缺乏其中的朋克反抗精神内核。而之后尽管出现了大量模仿赛博朋克风格的作品,但在技术想象上都泛善可陈。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陈楸帆创作了《荒潮》,以此作为向威廉·吉布森的致敬。这里我们也能看到陈楸帆的野心,他想创造产生于中国土壤中的赛博朋克,不仅故事发生在中国,还要有中国的赛博朋克的特点和中国青年的话语建构。
陈楸帆以中国现实作为科幻发生的场域,想象人类的赛博格变异对人类主体意识发生的冲击与突破,将科技问题置于社会问题中观照,让我们看到了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身体政治与文化政治。他将吉布森张扬想象与预示性的赛博空间与赛博人回归到吉布森忽略的人的肉身与人性,让我们更严肃思考科技发展与社会正义、科技与意识的问题。陈楸帆还秉承了人本主义思想,因此技术应该以人为本仍然是他的核心。陈楸帆的这种创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开拓了中国赛博格写作的路径,建构了中国赛博朋克的话语体系,让中国的赛博朋克文化具有了中国特色。
正如陈楸帆在很多场合提到的科幻现实主义,他自己也指出,“我更愿意将‘科幻现实主义’理解成一种话语策略”,其中“真实性”是“一种逻辑自洽与思维缜密的产物”[19]。这也意味着陈楸帆不仅在赛博朋克小说的创作中致力于基于本土的想象,更以中国视角在观照现实世界中的中外技术关系、环境关系与人文关系,寻求中国科幻创作在国际科幻语境中的突破,力图找到中国科幻小说实现全球本土化的民族路径。
三、中国赛博朋克小说的话语构建:以《荒潮》为例
陈楸帆本身就是一个深受西方赛博朋克小说影响的作家。赛博朋克可以精简为两个词:“高科技、低生活”[18]。但陈楸帆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把赛博格回归到人类的生活状况,站在人的立场思考技术带来的影响,有意识地建构中国的赛博朋克话语。
(一)技术话语的发展:作为身体政治的赛博格异化
《荒潮》讲述了捡拾分类电子垃圾的打工妹小米变身为机器人小米(赛博格)的故事。这种赛博格变形是一个被动驱使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动接受的过程。技术对人施加影响这一过程得到了详细的再现。而这种技术影响过程的描述也成为探讨人之为人的本质的依凭。在这个讨论中陈楸帆将技术看作是权力话语的载体,但技术又成为拉平精英与大众之间鸿沟的媒介,因此在技术表征与技术话语中,身体政治成为讨论的聚焦点。陈楸帆洞察了身体在赛博格之中的奥秘,他如吉布森一样反思肉体与神经/精神的关系,但与吉布森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陈楸帆更在乎现实场域对人的肉体变形产生的作用,因此这使陈楸帆的赛博格小说更具现实反映与物质的可捉摸性,赛博格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而不是少数有着奇特电脑经验的人。
打工妹小米演化为赛博格小米的技术革新就是一场身体政治的博弈。小米来自于一个山区的贫穷家庭,是硅屿岛上的外来人,又是一个小女孩,是硅屿岛权力金字塔底层人中的底层。她作为女性的身体首先成为了资本权力、男性权力霸权的受体。身体是女性主义观察和评论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平衡与不平等的重要领域。赫尔姆(Rachel Holmes)认为,“身体政治使人们重新聚焦在物质实践的形式上。通过物质实践,身体被社会规范的同时也被它自身的历史和变动中的身份所构型”[20],女性的物质身体承担了父权制的压迫与剥削。实际上,女性身体被置于持续压力之下以服从规范化的社会与文化模式。这也是马瑟(Kanchan Mathur)评论的,“女性的身体是文化代码化的空间,是女性被规范化的禁令标准的空间”[21]。
《荒潮》里详细描述了小米遭遇刀仔暴力凌辱的细节与感受:“…她的双手同样被胶带牢牢反捆在身后,将两块肩胛骨向后撕扯成钝角,泪和汗混杂在一起,刺痛她的双眼,浸湿领口。她能感到身上到处火辣辣地疼,却不知道伤在何处,像是无数蚂蚁舔舐着神经末梢,带着一种凌迟般的快感。…”刀仔对小米的凌辱将这一场男人施加在女人身上的暴力再次呈现为一种性别政治。这也印证了拉克兹(Rakoczy)的观点,“暴力的施行者试图以自己的权力来驱除自己生活中的羞辱感与低人一等感,以建立自己的主导权”[22]。小米的身体还被作为拯救罗子鑫的献祭品。神婆以传统方式做法力图将罗子鑫的厄运转移到小米身上,以此达到恢复罗子鑫健康的目的,她成为了罗氏宗族厄运的替罪羊。
在这种情境下,顶级高科技装置与它的适用性可能帮助女性找到新的路径来打败父权制社会。高科技可以让女性脆弱的身体成为勇敢的钢铁战士。小米濒临死亡之际大脑与废弃高科技头套的联结激发出无尽潜力,她以脑电波指挥驱使这个巨大的钢铁躯体,生物-科技帮助小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通过神经连接,她理解了子鑫昏迷的原因,并使子鑫从无意识的昏迷中苏醒过来。同时她以强大的超能力打败了跨国公司代表斯科特,摧毁了斯科特的阴谋,赛博格小米成为超人。赛博格异化不仅转变了小米的身体,而且从精神上让小米有能力反思社会与自我。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高科技拉平了女性与男性、穷人与富人、上层与底层之间的鸿沟。
但高科技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小米无意中获得了这种权力的使用,但并不意味着她就占据了科技高地,就处于权力的顶端。占据科技高地的是陈氏宗族的族长,即使垂垂老矣,他们仍然无时无刻不在观看、掌握着硅屿岛的发展动态并指挥着硅屿岛的前行方向。而另一方面,国际高科技组织成为全球技术权力的顶层。硅屿人处于国际与本土的技术与经济网络的底端,硅屿岛以环境换发展,成为全球垃圾中转站和回收站。小米的赛博格异化是身体政治的具象表现,它反映出作者对高科技发展的技术认知,并提出一种新的人文思考,即科技可以增强或增补人类能力,但我们更要深刻认识到科技带来身体革新背后的文化政治。小米的赛博格异化是她对社会的反抗,同时赛博格异化重建了小米与世界的关系,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重建技术-人文话语并重新思考人类文化。
(二)环境话语的强化:作为一种全球技术发展主义的批判
很显然,陈楸帆有深切的现实主义关怀意识,这在《荒潮》中有浓厚的现实痕迹。他深切关怀科技理性发展之下的环境破坏,并将环境破坏归结为发展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罪恶。
《荒潮》揭示了国际环保组织的内在矛盾性。以何赵淑仪为代表的环保组织与全球知名环保公司惠睿公司的环境再生项目之间的争斗本质上是硬币的两面,最终走向的都是环保公司的股票增长,是资本的逐利。在这里,发展主义显然成为西方面向东方的一种话语策略。
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认为,发展的神话是一种历史生成的话语,就好像散漫的控制机制作为经济管理的模式,其实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西方价值本身是无可争议的正确的[23]。理维罗(De Rivero)将这种方式称之为“社会-经济隔离”,这样北半球就是富裕国家,为贫穷国家所包围。这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新殖民主义”[24],硅屿岛就是这种全球化下的产物。它本身远离发达区域,只是一个靠海吃海的海边小城,处于社会生物链的最底层。它能跻身进入全球化进程中是因为它承接了全球的电子垃圾,不惜将山清水秀的小城变成垃圾城。但即使如此,它也处于全球化的底端。这本身就呈现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导致的第一世界对于第三世界与穷人的缓慢暴力。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土地攫取方式,第一世界将高污染的工厂设置在第三世界,让第三世界成为全球发展的环境牺牲品。第三世界以土地污染和工人生病为代价,但真正获利的却是第一世界。简而言之,《荒潮》中的硅屿岛是全球发展的后果,也是西方绿色发展下第三世界的生态牺牲。
尼克森(Rob Nixon)将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生态压迫称之为“在时空之中播撒的一种被延迟的暴力,一种根本性的暴力,通常还并不被认为是暴力”[25]。这种缓慢暴力就发生在如小米这样的垃圾人身上,这些底层的人们一个月几百块钱,没有保险,在有毒的垃圾中挣扎度日。底层人成为了环境、疾病和暴力的替罪羊,而顶层的人追求财富、健康与长寿。硅屿岛上垃圾人悲惨的生活境遇间接与第一世界高科技技术和经济发展有关。本地政府意识到环境污染的危险,他们期待国际再生利用资源公司如惠睿再循环公司能帮助他们处理污染问题。但讽刺的是,斯科特代表的国际再循环公司根本不想解决任何环境问题,而是基于他自身的利益寻求被误运到垃圾岛的电子元件,这也让我们看到了环境主义与国际生态-技术公司的真面目,这种国际环境保护组织也不过是国际贸易战争或者技术战争戴上的美丽面纱而已。这样一来,环境保卫战实际上成为了对于市场股票的争夺战。这就是陈楸帆在小说《荒潮》中尖锐揭露的背后的真相。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赛博朋克小说对技术发展相生的环境关怀,对以发展之名行获利之实的环境政治的批判。
(三)情感话语的创生:人类的爱作为赛博格世界的拯救之路
相对于美国赛博朋克小说中对末世世界的悲观绝望,陈楸帆指出了未来世界的乐观路径。他认为,共情与爱将最终保留人性并维护人类在世界的存在。这个爱是父子、母女的爱、兄弟姐妹的爱、是对所有人的爱。
《荒潮》中很多人都抱有过对这个世界的仇恨。如李文,他的妹妹失踪了,他四处寻找妹妹,从地下渠道得到的一个视频中他看到了自己妹妹受到凌辱致死的苦难经历,他对硅屿岛充满着仇恨,他有意识将垃圾人召集在一起,力图与硅屿岛上的罗氏宗族展开战斗。罗氏宗族族长罗锦城也同样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敌意,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他曾移居澳大利亚,看到华裔的财富在遭遇族群危机时被瞬间吞噬;他也看到自己移居在东南亚做生意的堂兄如何在美国跨国资本的压迫下,财产被吞噬,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他拼命累积财富以增多自己的生存安全感。甚至陈开宗,因为他所爱的人小米遭遇凌辱而对未能保护小米的李文和罗氏家族充满着仇恨。但是小米以爱与共情化解了李文与陈开宗的矛盾,以爱拯救了罗子鑫,最后以大爱与陈开宗、李文一起战胜斯科特。这种爱是人道主义的爱,是爱他人、爱人类。
小米因心中有爱,所以变成赛博人的小米最终并没有变成复仇的机器怪兽,而是尽自己一切可能地帮助子鑫从昏迷中恢复;她与陈开宗并肩作战打败邪恶的斯科特,这都源自她内心有爱,爱给予她力量。在垃圾人与罗锦城率领的罗氏打手对峙时,罗锦城遭遇危险,小米建议李文救人。“可我们救的不只是命,还有硅屿人被蒙蔽的灵魂。要是我们让自己充满仇恨,那他们就赢了。我们要让他们看清楚,我们不是制造污染的垃圾,也不是寄生在他们土地上的低等动物。我们是人,跟他们一样,有喜怒哀乐,会怜悯,懂得同情,甚至可以冒着牺牲自己的危险去救他们。我们要伸出手去,看看硅屿人到底还给我们什么样的回应。”(《荒潮》)垃圾人也在小米的感召与带动下,在台风中积极救助陷入困境的所有硅屿人。这就是爱的力量。
我们可以将这种情感称之为人道主义。正如西蒙(Bart Simon)所认为的,“后人类被认为并不是与人文主义产生的巨大割裂,它形式上既没有超越也没有抛弃人文主义,而是对人的本体论的补充”[26]。人道主义聚焦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尊敬与对人的爱。爱整合了肉体的小米与赛博人小米,并让她有权力来获得社会正义。这也反映了陈楸帆对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情感认识,即当技术与社会让人变得异化而产生生命的虚无感时,爱帮助人们从中恢复过来并重新做自己的主人,同情让人类成为人类。陈楸帆以爱强调了人类在技术世界的主体性,无论技术怎样改变肉身,爱是人类存在的根本,也是赛博格世界的根本。这一点也回应了海勒所描摹的后人类的未来。海勒指出,后人类无需适应于自由人文主义,也不需要被建构为反人类。“我们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技艺,这让人类与其它生命形式,无论是生物还是人工智能,可以在地球上长期生存下去,我们共享这个星球,以及我们自己[27]。
四、结 语:科幻话语的民族认同作为中国青年文化实现创造力的一条新路径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科幻故事的创造是普遍性的,但故事创作者是生长于具体国家与民族文化中的个体。故事创作者的科学认知与人文理解也必然呈现出其所处的民族与社会的文化特性、民族独有的世界或宇宙认知。创作者们都在尝试借助民族智慧开拓科幻想象的更前沿,因此科幻话语的民族认同也必将成为青年文化实现创造力的一条新路径。
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使用高科技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赛博朋克文化极具青年亚文化的表征,在科幻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释放点。“高科技、低生活”曾一度成为赛博朋克文化的核心。但21世纪的中国赛博朋克文化正在形成自己的风格,构建自己的话语模式。中国赛博朋克小说也以陈楸帆为代表,以科技话语的发展、环境话语的强化、情感话语的创生将个体自主性与民族认同紧密结合在一起,生成特色鲜明的中国赛博朋克文化特征。陈楸帆的《荒潮》虽然并没有展示光怪离奇的赛博技术,没有如吉布森那样完全再现大脑神经的网络空间漫游与战斗,但陈楸帆创造了技术世界的现实主义观照,展现了对跨国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追求。陈楸帆提出“科幻现实主义”主张,强调技术的发展仍然立足于现实思考,人类情感的爱与共情才是最终让人类能摆脱技术发展论产生的危机,获得拯救之路。这也可以说是中国赛博朋克小说的一种探索成果。
科幻话语的民族认同并非简单地彰显民族风格,而是糅合并内化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思想,站在更宏观的全球甚至宇宙视野下对中国文化精神做出内省并真正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精神。这也是中国当代新生代科幻小说家正在尝试的路径。更为可贵的是,中国新生代的科幻小说创作已积极融入到青年文化的创造中,引领青年群体积极思考科学技术带来的技术伦理、社会责任与世界担当。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幻话语的民族认同为青年朋克文化实现创造力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即中国青年朋克文化并非亦步亦趋跟随西方模式,而是在适应中国土壤中的青年文化中开出了自己的思想之花。青年朋克文化正在成为主流文化,以创新、责任感与家国意识成就中国的青年文化新模式。
注:
①伯明翰学派早年在论文集《通过仪式进行抵抗》中就阐述了亚文化的定义和表现形态及其研究方式,认为文化是阶层、财富和权力的反映。主流文化表征自身为主导的社会文化秩序。其他文化不仅服从于这种主流秩序,同时也与之抗争、修饰、协商、抵制甚至颠覆。因此文化之间必然存在主导阶级和服从阶级的不同文化模式。他们把青年群体创造的文化形态看作是与父辈不同的文化模式,体现在对不同的活动和群体的聚焦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基于青年文化与其父辈关系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差异特性,因此称之为“青年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