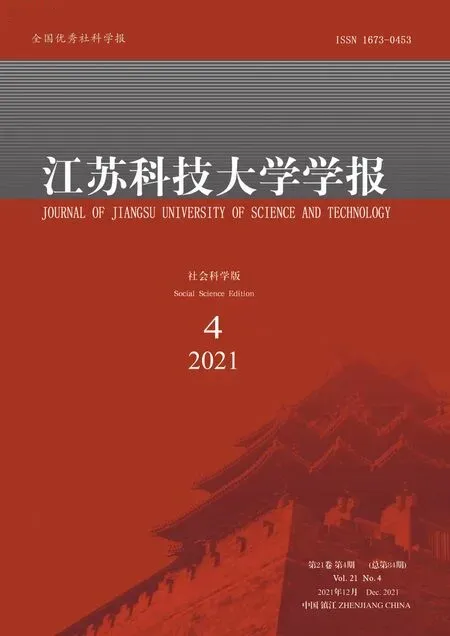杜诗天学意象与天文志关系探究
2021-12-06叶昌灏李小荣
叶昌灏,李小荣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0)
杜甫诗歌(以下简称“杜诗”)中所蕴涵的天学意象向来不为学者所重视。究其原因有二:一则是中国古代天学概念特殊,易与现代天文学混淆;二则是杜诗天学意象来源驳杂,学者难究其源。在这两重因素影响下,天学与杜诗的交叉研究久为沉寂。因此,在辨析古代天学与现代天文学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杜诗中天学意象与史书天文志的关系,可为后继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一、 古代天学与现代天文学
现代天文学概念已经有明确的自然科学内涵。《辞海》对“天文学”的解释为“研究天体和其他宇宙物质的位置、分部、运动、形态结构、化学组成、物理性质及其起源和演化的学科”。《汉语大词典》将“天文学”定义为“研究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的科学,包括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行的规律等”。《辞海》和《汉语大词典》将天文学看作一门科学技术;《辞源》则直接在天文学的条目下标注“Astronomy”,有意将天文学视作外来术语,由此可见现代普遍认同西方观念里的天文学体系。但在中国古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天文星占与历术具有深刻的民族心理意涵,它与生俱来地与政治权力挂钩,并在阴阳五行理论的推动下成为天人感应说的重要载体,尽管它也杂糅了自然科学的性质,然而究其根本,还是政府宣扬自身合法性的一种依据。因此,现代天文学的“天”与古代观念里的“天”完全无法等同,现代天文学将“天”视作没有情感的客观存在,而古代的“天”却是有自我意志的至上神。《说文解字·一部》云:“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1]《鶡冠子·度万》云:“天者,神也。”[2]同时,古代“天文学”因农业需要而产生,掌握“天”的知识,就拥有了统治的权利。冯时提出,“在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的远古社会,如果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实践逐渐了解了在多数人看来神秘莫测的天象规律,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而人一旦掌握了这种知识,他便可以通过观象授时的形式实现对氏族的统治,这便是王权的雏形。原因很简单,授时的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一年的收获,对于远古先民而言,一年的歉收将会决定整个氏族的命运。因此,天文学事实上是古代政教合一的帝王所掌握的神秘知识”[3]。于是,人们对“天”的尊崇演变为对帝王的尊崇,“天”的变化也就预示着王廷的变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史书对天象记录如此细致,因为天象是对朝野政治的反映。这一点从唐代的天文机构设置亦可见出。《唐六典·太史局》载:“太史令掌观察天文,稽定历书。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焉。”[4]太史令记录国家的兴衰,势必要涉猎天象占卜。而史书中的“史传事验”确实表现出天象对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性。如秦朝将灭,彗星四见;高祖入关,五星聚井[5]1600。又如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四星聚尾”异象导致了唐朝君臣慌忙改土运为火运,试图攘除灾异,但终究未成定论,不久之后安禄山就打着“四星聚尾”“以金代土”的旗号四处散布舆论,树立“燕”政权的合法性[6]25。
综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是对具有意志、能够改变帝王将相命运的“天”的研究,天学意象说便由此提出。“天学”是江晓原《天学真原》的核心术语,之所以取名“天学”,一方面是避免与现有的天文学概念相混淆,另一方面则为了突出天学对“天”的强调,从而反映出天学的政治属性及其背后的天人感应思维[7]65。由于古代天学带有社会属性与占卜功能,自然不可将其与讲求客观的现代天文学视作同类,现代辞典也没有出现专门界定古代天学的术语。对于偏好历史与时政书写的杜甫,如果脱离其古代天学的思想背景而去解读其诗中的天学意象,便会难窥其奥。
总之,古代天学是天人感应思维的产物,古人对天象的观测不止于考察方位和农时等技术性用途,更多的是赋予天象以社会和政治内涵,用以预测人事变化,进而逐渐发展成为政治集团发动变革的舆论工具。杜甫作为左拾遗,怀揣着回归开元盛世的政治理想,他既有朝廷士大夫的责任感,又以诗歌作为表现工具,因此天学意象的意义在其诗中便不止于表现时空状况,而是成为书写时事、表达立场的符号。而这些符号是从何而来的,又是怎样转化为诗歌话语的,正是本文亟待解决的难点。
二、 杜诗天学意象与天文志
既然杜诗天学意象的背景是天人合一,其渊源应是最具天人思维特征的文本。古代文献中对此有系统记载的一是史书,二是谶纬类书籍。谶纬之书与杜甫的关系并无文献支撑,更直接的文本源于史书。历代史书关于天文现象的记载情况较为复杂。首先,最具专业性的当属天文志、律历志;其次,是散见于各传记中的天象记录;再次,是五行志、符瑞志等偶有记载。而杜诗中常用的天学意象无论在涵义还是数量上,都与天文志较为契合。关于这一点,古代注本也有留意者。陈吁在《严中丞枉驾见过》对“何人道有少微星”一句注云:“少微星谓严,非公自谓,从来误解。按: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处士星。是则士大夫之位为少微正占,而一名处士为少微之所兼占,如奎为天子武库,又主沟渎……天星兼占甚多。隋志,天官李淳风辑,太宗御制。公引本朝书,必有根柢,非若后人止知少微星之为处士,而不知少微星之为士大夫也。”[8]2551陈吁认为杜甫对《隋书》的天文志多有涉猎。黄生《杜诗说》论《伤春五首》其三云:“天官诸书,充满腹笥,惟此题合供采用。盖叙京师失陷之事,宜以隐约出之。”[9]黄生认为杜甫对天文志所有书目均有涉猎。然二家之说皆属随笔,论证未详,因此笔者将细论杜诗天学意象与天文志之关联。
(一) 源头确立:杜诗天学意象与《史记·天官书》
自《史记·天官书》开天文志之先河,后世史书皆纷纷继踵。古代天学具有传承性且自成系统。笔者以“三台”星为例考察古代官修天文志之间的传承关系。
《史记·天官书》有云:“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5]1538此处“三能”即“三台”。裴骃在《集解》中引苏林曰:“能,音台,二字通假。”[5]1604对于三台星的涵义,江晓原在《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中的解释颇具参考价值,“这里所谓的‘三能’,又名‘三台’,或‘泰阶’,《黄帝泰阶六符经》说:‘泰阶者,天子之三阶:上阶,上星为男主,下星为女主;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士,下星为庶人。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合时);不平,则稼穑不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好兴甲兵。修宫榭,广苑囿,则上阶为之坼(崩裂)也。’也就是说,星官‘三台’六星,分为上、中、下三对,每对星中两星颜色是否一致,被认为有较大的星占学意义”[7]113。由此可知,“三台”星之色与形的变化皆有星占学意义,但《史记·天官书》仅提及三台星颜色的内涵,对此尚未深入阐释。
《汉书·天文志》因袭了《史记》的原文:“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10]《后汉书·天文志》直接以彗星犯三台星为“三公”之祸:“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见东方,长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营室及坟墓里。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长六尺;癸未,昏见,西北历昂、毕;甲申,在东井,遂历舆鬼、 柳、七星、张,光炎及三台,至轩辕中灭……炎及三台,为三公。是时,太尉杜乔及故太尉李固为梁冀所陷入,坐文书死。及至注、张为周,灭于轩辕中为后宫。其后懿献后以忧死,梁氏被诛,是其应也。”[11]此处记载与《黄帝泰阶六符经》的文本相似。《宋书·天文志》曰:“八月,星孛太微,至翼、北斗、三台。占曰:‘太微天子廷,大人恶之。’一曰:‘有徙王。翼又楚分也。’‘北斗主杀罚,三台为三公。’”[12]此处对“三台”的记载亦沿袭前说。《晋书·天文志》对“三台六星”的阐释最为系统:“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次二星曰中台,为司中,主宗室。东二星曰下台,为司禄,主兵,所以昭德塞违也。又曰三台为天阶,太一蹑以上下。一曰泰阶。上阶,上星为天子,下星为女主;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士,下星为庶人:所以和阴阳而理万物也。君臣和集,如其常度,有变则占其人。”[13]293
对比上述史书对三台星的记载可以发现,历代史书对天官的解释确实一脉相承,且后代史书在沿袭前人的同时还能够综合诸家之说,《晋书·天文志》正是典例。再将杜诗中三台意象与前引史书相对照:
猛士思灭胡,将帅望三台。(《昔游》)[8]4111
台星入朝谒,使节有吹嘘。(《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8]4725
南极一星朝北斗,五云多处是三台。(《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8]4743
及乎贞观初,尚书践台斗。(《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8]5958
尔家最近魁三象(原注曰:斗魁下两两相比为三台),时论同归尺五天(原注曰:俚语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赠韦七赞善》)[8]6011
《昔游》诗中“三台”虽不特指“三公”,亦指代台辅高位,此句意为将士们欲以战功取显要之位;《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之台星意象皆指时居相位的杜鸿渐;《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之“台斗”指宰相之位,“尚书践台斗”指王砅之祖父王珪在太宗时以侍中辅政之事。由此可见,杜诗中“台星”意象的对应者往往是辅佐皇帝的重臣,与史书中的“三台”含义相符。又如《赠韦七赞善》“尔家最近魁三象”下的“原注”云:“斗魁下两两相比为三台”,这一注解几乎与《史记·天官书》“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一句相同,若确实出于杜甫自注,则杜诗最有可能依据的天文学史书是《史记·天官书》。笔者考两句自注的依据大致有三:
其一,从传世文本的角度看,两注仍然保留在大多版本中。考杜集存世最早的可靠版本,即王洙、王琪《宋本杜工部集》“尔家最近魁三象”句下“斗魁下两两相比为三台”的注释[14],王洙并未特别说明,应是和二王本其他注释一样,保留了他们所认为的杜甫自注;《新刊校订集注杜诗》保留了“斗魁下两两相比为三台”的注释,认为是杜甫自注;《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皆引“洙曰”,依从二王本观点,认为是杜甫自注;《杜诗详注》《杜诗镜诠》《读杜心解》皆直接引之为“原注”[8]6011;《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本则引《史记·天官书》“斗魁下两两相比为三台”[15]。按此,则诸家大多以此句为杜甫自注均无异议。
其二,谢思炜曾作《〈宋本杜工部集〉注文考辨》,将二王本与以上宋元注本以及钱谦益注本进行了全面比照,找出部分纰漏。但他对此诗自注并无质疑,并得出“从整体上看,二王注本应当是杜甫自注”[16]的结论。
其三,近代出土的唐代韦氏墓志铭是重要依据。《我大唐故天平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郓曹濮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大夫检校户部尚书使持节郓州诸军事兼郓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司徒杨公(汉公)夫人越国太夫人韦氏(媛)墓志铭并序》云:“我外族与京兆杜氏俱世家于长安城南。谚有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望之比也。所居别墅,一水西注,占者以为多贵婿之象。其实姻妻之盛,他家不侔。”[17]此谚语即杜诗自注所引。关于墓志铭中的谚语出处,胡可先所著《“城南韦杜”与“杜陵野老”释证》可供参考[18]。胡可先结合《长安志图》和《关中胜迹图志》证明了俗谚必出于唐人无误,认为杜甫《赠韦七赞善》出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属杜甫自注,既赞美了韦氏家族,亦标榜了自己的杜氏家族。此论亦符合诗注与诗歌文本的逻辑关系。若“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是出于称美韦杜家族,则“斗魁下两两相比为三台”的自注就应该是对韦家显赫之实录。按《旧唐书·列传第五十八》之《韦见素传》,韦见素在肃宗即位后不久便除左仆射[19],仆射之职位列三公,可对应“三台”所指的台辅高位;又据胡可先《杜甫与唐代京兆韦氏关系述论》中的韦津墓志、《杜诗详注》、《旧唐书》等文本的互证[20],韦赞善即韦津,是韦见素的侄子,则“三台”与韦见素的身份是吻合的。由此可见,《赠韦七赞善》下的谚语与出土墓志、韦氏家境都能吻合,应为杜甫自拟。
综上所述,《赠韦七赞善》诗句下的注释很可能是杜甫从《史记·天官书》中所引,说明在杜甫的天文知识体系中,《史记·天官书》是有一定地位的。且就杜诗“三台”意象的使用看,七首诗歌都以叙事为主,“三台”意象也多用于指代身份,可初步证明杜诗对天文志之采撷乃为叙事之用。
(二) 语汇分析:杜诗天学意象与《晋书·天文志》
以上虽论证了《史记·天官书》于杜诗天文意象的渊源,但《史记》对“三台”的阐释仅仅止于对颜色变化的预测意义,而杜诗中“三台”与“三公”关联较密切,故《史记》之外的天文志也应当列入考查范围。在上述征引诗句中,“汉庭和异域,晋史坼中台”“星坼台衡地,曾为人所怜”较为相似,两句皆出自《晋书·张华传》,即“初,华所封壮武郡有桑化为柏,识者以为不祥。又华第舍及监省数有妖怪。少子韪以中台星坼,劝华逊位。华不从,曰:‘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及伦、秀将废贾后,秀使司马雅夜告华曰:‘今社稷将危,赵王欲与公共匡朝廷,为霸者之事。’华知秀等必成篡夺,乃距之。雅怒曰:‘刃将加颈,而吐言如此!’不顾而出……遂害之于前殿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13]1074。在这段史料中,“中台星”即《晋书·天文志》所云:“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杜诗“晋史坼中台”当出于此。文中作为动词的“坼”与台星联用,亦同“晋史坼中台”“星坼台衡地”。且杜诗中使用颇繁的另一典故——“丰城剑气”亦与张华相关,如“夜看丰城气,回首蛟龙池”(《咏怀二首》)[8]5763,“经过辨丰剑,意气逐吴钩”(《重送刘十弟判官》)[8]5846,“徒劳望牛斗,无计斸龙泉”(《所思》)[8]2306。可见杜甫对《晋书·张华传》的文本相当熟悉。然《晋书·张华传》恰好没有直接指明“台星”与“三公”的关系,此记载仅见《晋书·天文志》,“永康元年三月,中台星坼,太白昼见。占曰:‘台星失常,三公忧。太白昼见,为不臣。’是月,贾后杀太子,赵王伦寻废杀后,斩司空张华”[13]367。对比天文志与列传,天文志几乎为列传的精简版,惟“台星失常,三公忧”的占词乃天文志独有。以此推测,杜甫对《晋书》有所涉猎,而其所用意象、典故与天文志相合,杜诗对《晋书·天文志》的接受成为可能。
除“三台”意象外,杜诗中还有不少天学意象在用字与内蕴上与《晋书·天文志》相吻合。如将北斗意象作为叙事载体时,杜甫常将其与权力中心相联系,如“玄朔回天步,神都忆帝车”(《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8]4725,“数见铭钟鼎,真宜法斗魁”(《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8]5542(1)“法斗魁”思想有较深渊源,有可能出自汉代以来的“黄帝-北斗”的信仰,详见朱磊《中国古代的北斗信仰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92页。,“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骑麒麟翳凤凰”(《寄韩谏议》)[8]4822。“帝车”“斗魁”“北斗”皆与皇权紧密相连。《晋书·天文志》云:“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枢机,阴阳之元本也。故运乎天中,而临制四方,以建四时,而均五行也。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衡。又曰,斗为人君之象,号令之主也。又为帝车,取乎运动之义也。”[13]289
与此类似的是杜诗对北辰意象的使用。《晋书·天文志》对北极的记载为:“北极,北辰最尊者也,其纽星,天之枢也。天运无穷,三光迭耀,而极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3]290再看杜诗的用例,如“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奉送严公入朝十韵》)[8]2603,“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8]5941,“宸极祅星动,园陵杀气平”(《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8]875。显然,杜甫将“北极”“北辰”“宸极”代指皇极。
如果说北辰意象在他人诗赋中还可找到类似用例,那么老人星与“慧”“孛”的天学意象则反映出杜甫对《晋书·天文志》文本的直接化用。《晋书·天文志》对老人星的记载为:“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极,常以秋分之旦见于丙,春分之夕而没于丁。见则治平,主寿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13]306而杜诗几乎化其整句于诗中,如“南极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谁勒铭”(《覃山人隐居》)[8]5098,“今宵南极外,甘作老人星”(《泊松滋江亭》)[8]5452,“结托老人星,罗浮展衰步”(《咏怀二首》其二)[8]5768。再如杜诗对“慧”“孛”的使用。他将名词活用为动词,如“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挛”(《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8]4834,“往者胡星孛,恭惟汉网疏”(《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德叙怀斐然之作三十韵》),“旄头彗紫微,无复俎豆事”(《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8]6048。杜诗是将“慧”“孛”活用的最早用例,其义或可上溯至《左传》。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对二字的分析最为精要,他指出,首先,慧、孛各有分别,孛虽属于慧一类,但不是同一物;其次,孛字有两用,一为名词,一为动词,用作动词时指彗星之光芒,如孛星一样“蓬蓬孛孛”而过[21]。这种活用的技法在《晋书·天文志》中不乏用例。明帝太和六年十一月载:“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将星。占曰:‘为兵丧。’”[13]388恭帝元年正月载:“有星孛于太微西蕃。占曰:‘革命之征。’”[13]388且《晋书·天文志》对慧、孛的辨析相当详实:“一曰彗星,所谓扫星。本类星,末类彗,小者数寸,长或竟天。见则兵起,大水。主扫除,除旧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二曰孛星,彗之属也。偏指曰彗,芒气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恶气之所生也。内不有大乱,则外有大兵,天下合谋,暗蔽不明,有所伤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将出,彗星何惧乎!’由是言之,灾甚于彗。”[13]289
除此以外,杜诗中还有对“妖气”“祲气”的使用。如“兴王会静妖氛气,圣寿宜过一万春”(《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十二韵》其五)[8]4507,“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8]5593,“帝京氛祲满,人世别离难”(《送杨六判官使西蕃》)[8]890,“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诸将五首》其四)[8]3776。这在唐代以前的诗中出现较少,究其原因,可能是唐代云气占体系已趋于完整。这一点可从《晋书·天文志》的记载中得到证明:“妖气:一曰虹蜺,日旁气也,斗之乱精。主惑心,主内淫,主臣谋君,天子诎,后妃颛,妻不一。二曰牂云,如狗,赤色,长尾;为乱君,为兵丧”[13]388。“《周礼》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一曰祲,谓阴阳五色之气,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属,如虹而短是也。”[13]330这种分辨意识多少会影响到杜甫对意象的抉取。其他如紫微、旄头、荧惑、勾陈等意象,在杜诗中都有较为丰富的例子,而这些意象的使用皆可与《晋书·天文志》进行文本上的比对,足见天文志与杜诗关系之密切。
《史记·天官书》是天文志的开端,《晋书·天文志》是唐代集前人天学大成之史书,既然杜甫于二志皆有涉猎,结合历代天文志间的传承关系,则可将天文志作为杜诗天学意象的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杜诗对天文志的采撷都倾向于叙事方面。以杜甫天学意象诗歌的题材观之,上引30余首诗歌中,至少半数以上的主题带有纪事性质,其余大多涉及战争或时政,而古代天学所涉及者,恰多与战争、政事相关。江晓原曾以《史记·天官书》的天象占卜为统计对象,发现在242条占辞中,关于战争、灾异、王朝盛衰之占辞达161条,占总数的67%[6]191,可见天文志对这三类事项的关注。以杜诗天学意象的结构观之,其作用往往在叙事开端或转折处,这里借鉴了史书(尤其天官志)以天象异变作为事件之预叙的笔法。而对天官志中天象与记叙笔法的化用,成为杜甫在古典诗歌叙事上的新创。与汉魏乐府为代表的叙事类诗歌相比较,尽管杜诗仍然采用融合片段式情景的手法,但前者往往截取实景,后者在化用天象进入叙事之后,将虚与实的界限变得模糊,让叙事产生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使诗歌既有沉着、痛快的叙议,又不乏跌宕起伏的情感,达到浑成精警的高度。如“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挛”,看似以叙事为中心,然而笔者将“黔首”放在“胡星异变”的特殊语境,确能令人感受到作者痛惜兵燹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还可隐约联想到诗人对这场战争的理性反思,于是“感事”与“写意”在此天衣无缝地融合。这是对天文志中天象占卜的巧妙化用,天文志遂得以作为叙事性天学意象的文本来源。
三、 结语
本文从天文志与杜诗的关系入手,探究了杜诗天学意象的来源。杜诗的天学意象出处甚杂,从前人之诗文、类书中可得到不少验证,而天文志是其中较为全面的一类,故着重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天象在史书中虽然被作为一种叙事符号,但毕竟只是一种喻体,它的内涵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并为古代文人所共同认知。唐代诗人如王维、高适、李白、白居易的诗中皆有对天象的使用,但往往没有脱离喻体,还是保留了天象本身的指向,如北斗指代皇权或方位,参星指代时间等。而杜甫在对时事的书写中,有意将个人情志融入天象中,使得作为喻体的天文生发了鲜活的艺术意象。杜甫或在诗歌中使用天文意象来表达自己的反战思想及对秩序崩坏、民生涂炭的忧心,或借由自抒情感的诗歌传情言志。总之,杜诗天学意象完成了从指引人事之“天文”到表现人间情事之“人文”的转变,这就是杜甫对天学意象发展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