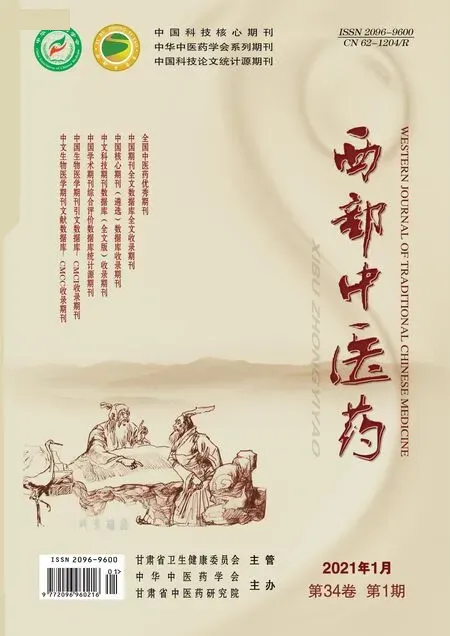陶汉华教授基于“气血水并调”理论运用小陷胸合四君子汤加减治疗肺癌经验*
2021-12-05姚鹏宇吕翠霞
姚鹏宇,刘 芳,吕翠霞
1 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辽宁 沈阳110847;2 山东中医药大学金匮教研室
陶汉华(1951—),山东莱芜人,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专家,师从刘献琳教授,从事科研、教学、临床工作40余年,擅长诊治疑难杂症。
气血水(水即津液)是人体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三者生理、病理关系密切。“气血水并调”理论是张仲景在《黄帝内经》气血津液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形成于《金匮要略》一书,最初是为诊疗“水气病”设立的方法[1]。陶汉华教授继承、阐释并发挥该理论,用于指导多种疾病的诊疗。肺癌指来源于支气管-肺的恶性肿瘤,陶汉华教授根据肺脏气血津液不归正化,痰凝、血瘀、湿聚、毒蕴等有形实邪互结于肺,积久成癌的复杂病机以及升降失司的发病前提与气血水同病的病理特点,提出了基于气血水并调理论并运用经方治疗肺癌的临床诊疗思路。
1 探源气血水
“气血水并调”理论是临床治疗大法,是在中医学关于气、血、津液等人体精微物质丰富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气血水三者密切的生理联系及相互病理关系是这一理论的前提,近年来对于气、血、津液概念内涵的探讨与“津血同源”“血不利则为水”“痰瘀同源”等学说的提出对该理论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帝内经》中对于气血津液三者的论述,为气血水并调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其内容有三:1)气血水的同源性,《黄帝内经》分别论述气、血、水三者在人体的重要作用及相互联系,明确了三者同源异流,可以相互转化的特点;2)气血水的功能联系,《黄帝内经》中明确了气血水三者的生理功能,明确了三者相互为用的特点;3)气血水的病理联系,生理的相关性决定了其病理联系,气血水三者任意一者为病,均会影响其他二者。《黄帝内经》中气血水(津液)生理特性功能及相互关系的论述,为气血水并调三元论的构建提供了条件,而基于生理调节病理,基于常态改善病态,“以常衡变”的思维方式也为该理论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可能。
张仲景《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K中曰:“少阳脉卑,少阴脉细,男子则小便不利,妇人则经水不通;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名曰血分。”提出在治气的基础上,还需利水活血,水血并治,这是“气血水并调”理论的雏形,并创立了当归芍药散等名方。《金匮要略》首次将气血水并调作为治则用于临床,这一治则的提出符合“三角理论”特点,即无论侧重于何种疾病,在针对性治疗的同时,都会有两个支持治疗,这种主次有别而兼顾整体的立法准则,也是中医整体观的体现。
历代医家均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其中《血证论》一书最为详备。唐容川“水病则累血,血病则累气”“血与水本不相离,病血者未尝不病水,病水者未尝不病血”等论述阐明了气血水同病的复杂病机特点。陶汉华教授以张仲景“气血水并调”理论为基础结合历代医家论述,将“气血水并调”理论用于肾病综合征[2]、慢性肾衰[3]、肝硬化腹水、胸腔积液、周围血管疾病淋巴回流障碍等的诊疗。
气血水并调理论是兼顾整体的思想,而明确气血水三者病理主次关系又是把握病机的关键。肺体阴用阳,通过肺气以呼吸,肺津、肺血以濡养。《类经图翼》言“(肺)呼之则满,呼之则虚,一呼一吸,消息自然,司清浊之运化,为人身之橐龠”,肺主气,司呼吸是肺的基本功能,而这一功能依赖于肺气的宣发肃降;肺为血脏,内有肺络,血行络中滋养肺体,《医碥》“咳多则肺络伤,而血出矣”;肺主津液,《金匮悬解》“肺痿之病,由于津亡而金燥也”,津伤则肺损。肺气不利津血失运,则为痰饮瘀浊。包括肺癌在内的肺系疾病,病理过程多以气病为先,渐至血、水,最终气血水同病,而初期多实、中期多虚实并见,后期多虚是其病理进展过程,多种病因及复杂病机是肺癌的病理特点。陶汉华教授提出“气血水并调”理论指导肺癌诊疗符合其病理特点,具有执简驭繁的优势。
2 明辨痰瘀毒
肺癌早期可无明显症状。当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常出现刺激性干咳、痰中带血或血痰、胸痛、发热、气促等症状。当呼吸道症状超过2 周,经治疗不能缓解,尤其是痰中带血、刺激性干咳,或原有呼吸道症状加重时,要高度警惕肺癌的可能性。组织病理学诊断是确诊肺癌和治疗的依据[4]。有文献研究[5]由于肺癌早期临床表现不明显,初诊时57%的患者已发生了远处转移,所以晚期患者的治疗是肺癌治疗的重要部分。
肺癌属中医学“肺积”“胸痛”“咳嗽”“咯血”等范畴。虚实夹杂,痰凝、血瘀、浊毒有形实邪互结于肺是肺癌的病机特点,《杂病源流犀烛》中“邪积胸中,阻塞气道,气不得通,为痰……为血,皆邪正相搏。邪既胜,正不得制之,遂结成形而有块”,肺主宣降,宣降失司,气机不利,因百病皆生于气,气病则延及水、血;“肺为贮痰之器”,气机失调则水液代谢障碍,湿盛为痰,水泛为饮,停聚于肺,郁结日久变生为痰热痼结;气为血之帅,气病及血,血液循行失常,寒则涩而不流,热则妄动外溢,或留脉中,或出脉外,变而为瘀。“毒,邪气蕴蓄不解之谓”,血瘀痰阻日久变为浊毒,日渐积聚皆如有形之窠囊,最为难除。气血水不归正化,致使痰瘀毒结于肺。
《临证指南医案》云:“(肺)为娇脏,不耐邪侵,凡六淫之气。一有所着,即能致病。其性恶寒、恶热、恶燥、恶湿、最畏火风。”外感内伤邪气着于肺系,导致宣降失司,气血水不归常化,于肺络末端阳气较微之处先发,由细小的肺络不断发展至肺脏,积微成著,发为癌变。肺癌为有形癥瘕积聚,其始病于气,病及血水,互为因果,交阻盘踞,虚实夹杂,本虚标实,其病理因素多、病机复杂,且起病隐匿,病情进展快。临床在明确气病为先的前提下,针对肺癌病机特点,当辨病邪痰瘀之主次,虚实之偏颇,病程之进展。针对其病理特点确立治气、治血、治水三法,治气包括补气、理气、行气等,宣降肺气也属调气;治水即是化痰、生津、滋液,肺气得调津液得补,而治水以治气为先;治血包括补血、活血、化瘀等,血之变动无不赖气以生化运行,亦以治气为先。针对肺癌复杂病机确立以治气为主,化痰祛瘀解毒为辅,气血水并调,邪正兼顾,补虚泻实,运用复方治疗的原则。
3 四君陷胸化裁方
小陷胸汤见于《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篇》,以黄连、半夏及瓜蒌组成,具有化痰清热,宽胸散结的功效,主治痰热互结心下证。体内外实验均显示小陷胸汤具有抗肿瘤细胞增殖效应[6]。陶汉华教授认为小陷胸汤具有明显的病位特点与黄连入中焦有关,以黄芩代替黄连,入上、中二焦,更适应肺癌的病位特点,正如李东垣“黄芩,味苦而薄……手太阴剂也。”及朱丹溪“黄芩乃上、中二焦药”的论述,黄芩味苦寒,具有燥湿清热,止血解毒,消散结聚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7]证明黄芩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对流感病毒等有一定抑制性;具有抗肿瘤作用。半夏辛温,能燥湿降逆,止呕化痰,消痞散结,《名医别录》谓其“消心腹胸膈痰热满结,咳嗽上气”,为治疗痰饮之要药,药理研究[8]亦证实半夏多糖可抑制鼠嗜铬细胞瘤细胞株PC12 细胞和神经母细胞瘤细胞系增殖并诱导其凋亡,具有抗肿瘤作用;半夏多糖还可提高小鼠结肠腺癌细胞表面MHC-Ⅱ表达,增强免疫反应。陶汉华教授提出半夏还具有消瘀止血的作用,能除积冷,暖元脏,治心腹一切痃癖冷气[9]。瓜蒌能清热涤痰,宽胸散结,润燥滑肠,因肺与大肠相表里,腑气通则肺气通;且胸为清阳之府,肺居其中,瓜蒌宽胸,胸膈清朗则肺为清虚可复。三药合用,瓜蒌宽胸散结,化痰通腑,宣畅气机以通肺痹;黄芩专入肺经,清热燥湿解毒;半夏辛温化痰散瘀,散结除痞,全方苦辛并用,寒温同调,辛开苦降以复肺宣发肃降之司,兼理痰瘀毒,除邪以扶正。《医方考》载清气化痰丸一方用以上三药加南星、茯苓、陈皮、杏仁、枳实而成,药虽增味,法无二致。
四君子汤见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人参、白术、茯苓、甘草组成,功能益气健脾,主治脾胃气虚之证。现代药理研究[10]表明四君子汤具有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生长、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方中人参为五加科植物,补益元气疗效显著,多用于骤补虚损,陶汉华教授多以桔梗科党参代替,党参补益虽缓,却有专入脾肺之能,可“培土生金”补益肺气。有文献[11]认为党参主要成分党参多糖具有抗肿瘤活性。《神农本草经》谓茯苓“主胸胁逆气”,《药性论》言“治肺痿痰壅”,有益气健脾燥湿之能。白术和气补中,陶汉华教授临证多用炒制品,《医学启源》中谓炒白术能“除湿益燥,和中益气”,且炒制后芳香醒脾,助于运化补益。甘草生者清热解毒,炙者补益中气,临证视病情择用。4 药合用补益中气,培土生金,以扶助正气。
根据肺癌痰瘀毒病机,兼顾其病理特点,以小陷胸汤与四君子汤合方加减应用,虚实兼顾,以切病机。临床加减,根据气病为先的病理特点,若气滞不舒,常用前胡、杏仁、旋复花、枳壳、桔梗等调理肺气,恢复升降;若津液不利,痰饮较盛,加重小陷胸汤药物剂量,并酌加南星、白芥子、莱菔子、苍术、青皮等化痰药,或与涤痰汤、四子降气汤(莱菔子、苏子、白芥子、葶苈子)合方;若血瘀较重,则配合丹参饮、颠倒木金散或加用丹参、当归、川芎、牡丹皮、旋覆花、茜草等活血通络之品,或与丹芍二地汤(牡丹皮、赤芍、地骨皮、生地黄)、旋覆花汤等合方;兼阴虚配合刘献琳老育阴清热法,酌取清灵润泽之品,加沙参、麦冬、玉竹、百合等清润濡养之品,而非阿胶、熟地黄等滋腻类补阴药;兼气虚则遵“培土生金”治法,加党参、黄芪、西洋参等品;若兼胸腔积液者,与控涎丹、十枣汤或葶苈大枣泻肺汤合用,可酌情加入蚤休、百部、半枝莲、白花蛇舌草、夏枯草、山慈菇、鱼腥草等清热解毒之品,或与五味消毒饮、银翘蚤休二根汤(金银花、连翘、蚤休、板蓝根、山豆根、牛蒡子、蝉蜕、荆芥、僵蚕、玄参、桔梗、甘草)等合方,陶汉华教授强调应用清热解毒类药时须注意气味,如败酱草虽有清热解毒功效,然气味秽浊,当慎用,防止苦寒败胃。
4 典型病例
案李某,女,65 岁,2013 年 6 月 28 日初诊。胸痛半年。经查右肺肺癌伴转移,已化疗6 次,5月前出现右侧胸痛,刀割性疼痛,咳嗽时明显加重。莱芜市人民医院诊断为:1)原发性支气管肺癌(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广泛期),2)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行EP 方案化疗。余无明显症状。舌淡苔薄白,脉弦。西医诊断原发性支气管肺癌(小细胞癌中央型),中医辨证本虚标实,宣降失司,痰阻血瘀,治法:扶正祛邪,宣降气机,化痰散瘀,方拟小陷胸汤加减,药物组成:瓜蒌15 g、黄芩15 g、清半夏10 g、党参15 g、茯苓15 g、炒白术10 g、桔梗15 g、前胡10 g、炒杏仁10 g、牡丹皮10 g、赤芍15 g、百部15 g。15剂,每日1剂,水煎分2次口服。9月9 日二诊,患者又住院半月,化疗2 次,现手足麻木,无胸痛,余无明显不适,舌脉如前。上方加山慈菇10 g、半枝莲10 g,8 剂,制成水丸,每次5 g,每日3 次。12 月2 日三诊,无明显不适。舌红苔黄,脉弦。黄芩15 g、瓜蒌15 g、清半夏10 g、生甘草10 g、党参15 g、炒杏仁10 g、百部15 g、前胡10 g、茯苓20 g、山慈菇10 g、半枝莲15 g、牡丹皮10 g,10 剂,制成水丸,每次 5 g,每日 3 次。2014 年 2 月28 日四诊,近日咳嗽加重,少痰,胸闷。CT 示右肺上叶中心型肺癌并淋巴结转移,阻塞性炎症。舌红苔黄,脉弦。上方去山慈菇,加浙贝母15 g、桔梗10 g、桑白皮15 g,10 剂,制成水丸,每次5 g,每日 3 次。9 月 15 日五诊,现基本无症状。CT 示第五、第八胸椎有转移。血常规显示血红蛋白8 g。舌红苔黄,脉沉细。黄芩20 g、瓜蒌15 g、清半夏10 g、炒杏仁10 g、百部15 g、半枝莲15 g、牡丹皮10 g、浙贝母15 g、桑白皮15 g、薏苡仁30 g、赤芍10 g、桔梗15 g、前胡15 g、当归15 g、党参15 g,10剂,制成水丸,每次5g,每日3次。2015年2月2日六诊,咳嗽吐白痰,余无不适,舌脉如前。上方加紫菀10g,10剂,制成水丸,每次5 g,日3次。2015年 6 月 1 日六诊,上月因咳嗽,喘憋住院 3 次,5 月11 日最近1 次住院。憋闷感活动后加重,伴右侧颈部淋巴结肿大,吐白沫,无血丝,食欲不振,脉沉细数,苔薄白。黄芩15 g、瓜蒌15 g、清半夏10 g、浙贝母15 g、半枝莲15 g、白花蛇舌草15 g、桑白皮15 g、鱼腥草15 g、牡丹皮10 g、白及10 g、百部15 g、炒杏仁10 g、党参15 g、白前15 g,8 剂,制成水丸,每次5 g,每日3次。患者药尽,未再来复诊。
按肺癌按照解剖学位置分为中央型、周围型两大类,按组织病理学分为小细胞癌和非小细胞肺癌,小细胞癌病情发展快,全身播散倾向突出,存活率低。本案患者临床诊断明确,发现已属晚期,其年高体弱,癌毒蔓延,正虚邪实,病进之时当以扶正祛邪为治则,针对气血水同病,气病为先的病理特点,痰瘀互结毒邪内蕴的复杂病机,气血水并调,以小陷胸合四君子汤加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之品,水(津液)不正化则为痰饮,血不循常则为瘀病,气血水失其常则为患,而患者病情复杂气血水三元同调,以常衡变是为正途。方中党参、白术、茯苓补气扶正,培土生金;桔梗、前胡、炒杏仁宣降并用,调畅气机;半夏、瓜蒌、黄芩消痰散结,化浊理气;牡丹皮、芍药活血祛瘀,凉血止血;百部解毒散结,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有抗癌、松弛支气管平滑肌作用,取援药之意,优其所主。该方气血水并调,以补偏救弊复常为目的,方切病机。二诊仍守调气活血化痰解毒之气血水并调治法,针对邪实程度,加大援药药味数量,以增解毒散结功效,以丸剂缓图;其后仍遵治法剂型,略更药味,大意不变。研究显示肺癌患者61~75 岁中位生存期多为13.36 月[12]。此例患者发现已属晚期,延及生命近两年,治疗颇有成效。
5 结语
肺癌是目前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复杂的病机特点。“气血水并调”理论是陶汉华教授总结发挥经典著作中气血津液等物质及其联系理论,对于肺癌的诊疗具有明显优势。陶汉华教授从气血水的运行失常论述肺癌病机,依据病机特点气血水并调,依法统方,运用小陷胸汤合四君子汤加减治疗肺癌,理清法明,方简药精,颇具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