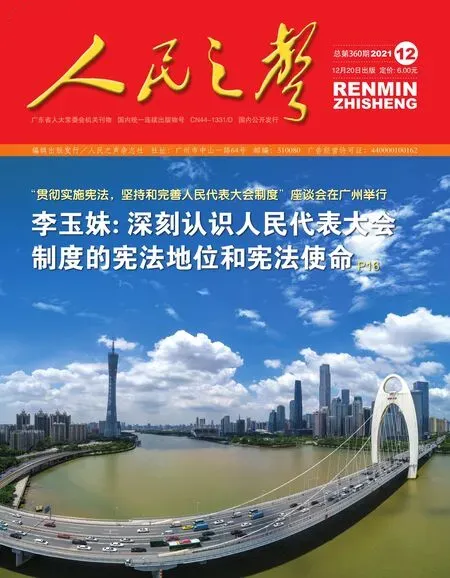新就业形态下的工会职责
2021-12-05阿计
近期,电商巨头京东集团召开了首次集体协商会,企业代表与职工代表就各项劳动权益充分商讨后,形成了两份集体合同草案,经职代会审议通过后将付诸实施。这一对大型平台具有示范意义的破冰之举,来自北京市总工会的全力督促,也来自于三个月前刚刚成立的京东集团工会的深度参与。而最近几个月以来,由工会推动的劳资双方集体协商行动,已在多个地区的快递等行业不断涌现、渐成潮流。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也重塑了劳动者结构。截至去年,依托互联网平台提供快递、外卖配送、货运、网约车等服务的从业人员已达8 400万人。然而,平台用工方式的特殊性、现行劳动法制的滞后性等因素,却导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处于收入不稳、伤害频发、社保欠缺等权益“裸奔”困境,尤其是过劳猝死、自杀抗争等极端悲剧的发生,更是印证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最近半年来,中央多个部委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已经彰显了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决心和努力。其中,推动集体协商、集体合同正是顶层设计的一个重要维度。其深层缘由就在于,除了政府监管等国家力量的干预,还必须畅通劳动者群体表达权利诉求的渠道,建构劳资双方公平的利益博弈机制。而通过集体协商达成集体合同,正是最普惠、最高效的维权路径。
在此进程中,工会所扮演的角色至为关键。个体劳动者与资本相比,当属弱势群体,并不具备对等的谈判和议价能力。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度分散、频繁流动等特点,以及平台企业更为强大的资源、技术等优势,又进一步放大了双方力量失衡的危险。这就需要工会担当起维权这一首要职责,以足以抗衡资本强势的组织形式,凝聚集体意愿,代言劳工权益,进而降低维权成本,实现公平博弈。
尤其是在现有的劳动法律框架下,新就业形态并不具备法律所规定的劳动关系的全部要素,从业者是否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身份,存在巨大争议,其与平台企业之间的权益纠纷,也难以直接适用法律所设计的保护机制。这也是一些平台规避企业责任、劳动者维权艰难的根源所在。然而,大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生活来源主要来自平台收入,却是不争的事实,因而以从业者身份加入工会组织,并不存在制度性障碍。也正因此,在法律制度供应不足、公平秩序尚未形成的情形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托工会实现权益主张,不失为一条最为现实可行的维权道路,也是工会义不容辞的职责。
新就业形态下的工会功能,并非仅仅复制一般意义上的维权模式,更在于应对诸多全新的维权难题。比如,平台用工与传统用工的显著区别是,需要对订单分配、劳动定额、奖惩制度、进入退出等设定规则,并运用算法进行管理。但在现实中,平台企业往往借助大数据等技术优势,垄断规则和算法的制订权,肆意扩张资本收益,无度压缩劳动权益。劳动者不仅对此毫无话语权,并且个体在知识等方面的劣势,也难以洞察技术复杂性背后的侵权隐蔽性,因而极易沦为规则欺凌、算法压榨的受害者,最终陷入“困在系统中”的境地。这就更加突显了工会主导维权的价值,承载着集体意志的工会组织,不仅有能力制约规则、算法等企业制度构造,也更利于引入技术支持、法律援助等专业力量,提升维权的专业水准。如此,才能为劳动者赢得平等的话语权,以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等姿态,实现合法权益的最大化。
谋求制度的公正,其意义远胜于争取个案的正义。正因此,工会不仅需要介入企业规则的设计,更应投身国家法制的改造。2006年,劳动合同立法引发空前激烈的立法博弈,正是因为工会坚守立场、全力呐喊,促使法律奠定了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基调。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总工会界别的提案,也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困境,发出了修法等一系列强烈呼吁。可以预计,工会将劳动者权益需求转化为立法诉求的努力,以及其在立法决策中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终将助推劳动法律的更新完善,进而从法制源头守住劳动者的权益底线。
资本和劳工固然存在利益冲突,但劳资双方并非死敌。维权固然是工会的天职,但其目的也并非制造劳资对立。重要的是,弱势的劳动者群体,是否享有制度的、道德的文明关怀,是否拥有通畅的、有力的代言机制。这既是实现权利公平的必需品,也是消解利益冲突的润滑剂。如此,才能确保维权行进于有序理性的航道,最终驶向劳资和谐的彼岸。而这,正是新就业形态下,工会的深层价值和时代使命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