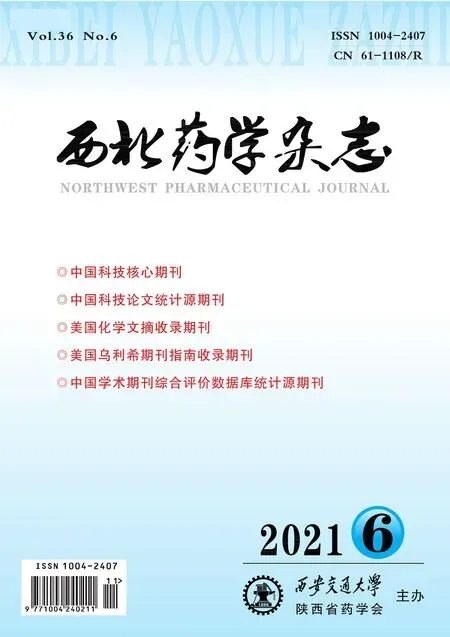基于植物药的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活性化合物研究进展
2021-12-04苟喜兰王嗣岑西安交通大学药学院西安710061
苟喜兰,魏 芬,王嗣岑(西安交通大学药学院,西安 71006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由β属单链包膜RNA病毒引起的严重呼吸道综合征,因其极强的传染性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对COVID-19的治疗,目前主要包括小分子药物、生物类药物、疫苗和植物药[1]。小分子药物主要以传统抗病毒药物如利巴韦林、瑞德西韦等为主,源于病毒基因组的相似性,小分子药物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但其生物安全性数据缺乏,在治疗过程中存在QT间期延长(QT指心室除极和复极激动时间)、慢性肾损伤等不良反应[2-3]。生物类药物以单克隆抗体和恢复者血浆抗体为代表,托珠单抗通过靶向抑制白细胞介素-6(IL-6)受体活性而阻断炎症反应,减轻患者的心血管损伤、淋巴细胞综合征等,高滴度抗体血清能明显改善患者的疾病进程,但单克隆抗体的持续使用会增加菌血症感染风险,同时高滴度抗体血浆较难满足[4-6]。疫苗是由灭活病毒诱导机体免疫系统早发性产生抗体等免疫物质进而降低疾病发生率的一种治疗方式,目前已有包括辉瑞、国药以及科兴等不同医药公司的疫苗投入市场,考虑到病毒基因组的不断变异,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有待评估。
植物药具有悠久的用药历史,衍生出了包括中医、阿育吠陀、汉方医学和韩医学在内的多个分支,其对于传染病的治疗可追溯至周朝,植物药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7]。在COVID-19疫情防治中,植物药如莲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以及清肺排毒汤、麻杏石甘汤等被应用于COVID-19的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然而,植物药成分复杂,作用机制不明确,安全性隐患制约了其进一步的应用和推广[8-9]。同时,植物药中化学物质具有结构新颖及独特药理作用等特点,为发现新的候选药物提供了巨大而宝贵的资源。因此,从植物药中筛选先导化合物,兼具有效性和安全性,对抗COVID-19创新药物的研发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于COVID-19中植物药的研究以网络药理学、分子对接、分子动力学和成药性评价等多种筛选方法与蛋白印迹、空斑实验和细胞活性测试等药理方法相结合为主,集中在物质基础的解析和治疗机制的阐释等方面[10-13],旨在寻找能有效治疗COVID-19的先导化合物。
1 以生物活性蛋白质为基础的药物筛选
蛋白质相互作用如酶-底物、受体-配体、抗原-抗体等在生物体的新陈代谢、信息交流以及生长发育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机体维持内稳态的重要条件。在COVID-19的发生发展中,新型冠状病毒与靶细胞的相互作用,是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基础,新型冠状病毒的黏附、渗透以及释放都直接影响疾病进程,是药物研发的重要靶标。
1.1以病毒抗原为靶标的药物筛选 对新型冠状病毒进行病原学解析,其主要有刺突蛋白S蛋白,衣壳蛋白E蛋白,膜蛋白M蛋白以及核蛋白N蛋白。S蛋白主要与靶细胞ACE2受体结合可进一步解析为负责识别的S1片段和负责跨膜融合的S2片段[14],是目前研究最多的病毒蛋白。芳香疗法利用药物的气味进行疾病的治疗,在印度具有漫长的应用历史。最近有一项研究以病毒S蛋白为靶点,利用分子对接的手段,对挥发油类物质进行筛选得到了如百里香酚等多种酚类小分子物质,后者具有消毒杀菌作用,由于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是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重要途径,筛选得到的化合物有望以空气清洗剂、消毒剂等多种形式用于COVID-19的预防[15]。此外,对黄酮类化合物以S蛋白为靶标进行分子对接的虚拟筛选,得到了以槲皮苷为代表的多个化合物,分子对接模型表明,其可与S蛋白的多个残基成键,推测槲皮苷类黄酮化合物可能通过预先结合S蛋白而阻碍S蛋白对靶细胞的识别而发挥抗病毒效应[16]。
1.2以病毒酶为靶点的药物筛选 新型冠状病毒是包膜的单链RNA病毒,隶属于β冠状病毒属,尽管其基因组与其他冠状病毒如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 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 CoV)享有较高同源性,但致病能力和传播速度却相距甚远,基因的变异和病毒的多样化切割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酶是参与病毒蛋白质切割的重要活性物质,通过将多蛋白进行不同位点的切割产生功能不同的非结构蛋白,后者参与病毒RNA的复制、翻译以及病毒颗粒的组装等多个过程。M蛋白酶即3 CL蛋白酶(糜蛋白样蛋白酶),主要作用于亮氨酸-谷氨酰胺(丝氨酸-丙氨酸-甘氨酸)位点,与RNA剪接翻译、加工及细胞调控等多个过程相关,在生理条件下还能对宿主蛋白进行切割,通过干扰宿主的转录翻译等促进自身增殖,是药物研发的重要靶点[14]。以M蛋白酶为靶标建模对不同数据库进行筛选,Gurung A B等[17]得到了萜类化合物bonducellpin D和caesalmin B,而Aanouz I等[18]得到了地高辛、β-桉叶油脂、藏红花素等化合物,证明M蛋白酶是筛选治疗COVID-19活性化合物的有效靶点;进一步结合分子动力学模拟,Tahir Ul Qamar M等[19]在筛选了32 297个化合物后列出了结合力较强的包括杨梅苷、迷迭香酸甲酯在内的9个活性化合物。除M蛋白酶外,RNA聚合酶也可作为药物筛选的有效靶点,Singh S等[20]利用此靶点对天然多酚类化合物进行筛选,得到了没食子酸酯、茶黄素苷等8个活性化合物。Lung J等[21]筛选得到了茶黄素,并进一步计算得到茶黄素对RNA聚合酶的键合自由能为-9.11 kcal·mol-1,提示其有望成为治疗COVID-19的先导化合物。
1.3以靶细胞受体为靶点的药物筛选 新型冠状病毒以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受体为靶点,通过自身S刺突蛋白对其特异性识别,进一步失去刺突蛋白S1片段而与靶细胞细胞膜融合,在跨膜丝氨酸蛋白酶2(TMPRSS2)跨膜蛋白的介导下进入细胞内,实现病毒体的复制与增殖。同时,由于ACE2受体在机体不同器官和组织的广泛分布,新冠病毒可引起如心脏、脾脏等多器官的功能性损伤,导致心血管损害、淋巴细胞减少症等多种严重并发症,恶化疾病进程和预后[22-23]。因此,研发ACE2与TMPRSS2的抑制剂是COVID-19治疗药物研究的有效策略。以ACE2受体为靶点,利用分子对接,对来自阿尔及利亚西北部的轮叶金鸡菊进行筛选,得到了异麝香草酚,对黑种草进行筛选,得到了对苯二酚,进一步对得到的候选化合物进行药代动力学、生物利用度等分析,发现两者均对ACE2具有较高的结合活性和稳定性,有望成为治疗COVID-19的先导化合物[24-25]。醉茄酮和醉茄素A是以TRANSS2蛋白为靶点,通过分子对接、分子动力学筛选南非醉茄而得到的2种化合物,将其与表达有TMPRSS2的人乳腺癌(MCF7)发生作用,发现醉茄酮不仅能占据TMPRSS2的催化位点,阻止病毒粒子的黏附,还可以下调TMPRSS2蛋白的表达量而正向循环抑制病毒对靶细胞的入侵[26]。
2 以类药性为基础的药物筛选
类药性是指化合物成为药物的可能性,一般用Lipinski′s于1997年提出的五原则衡量:相对分子质量≤500道尔顿,lgP(P为化合物在正丁醇和水体系中的油水分配系数)≤5,氢键供体≤5,氢键受体≤10,化合物的可旋转键数量≤10。相较同一类化合物的数据库筛选,类药性原则的使用在对化合物结构差异较大的数据库进行筛选时具有明显的优势,可有效节约时间和成本,比如直接排除某些亲水性差的化合物诸如石油醚类、鞣质类等[16-17]。在一项通过文献挖掘寻找靶向新型冠状病毒M蛋白酶的研究中,类药性的使用可直接将候选化合物从38个排除到10个,显著缩短了筛选时间[17]。此外,在对黑胡椒、丁香和姜筛选抗新型冠状病毒化合物时,类药性原则的应用以已有的化合物阿巴卡韦和羟氯喹为基准,有效避免了对某些化合物如阿魏酸的误判,同时,将3种植物中总的候选化合物种类降到20种[27],大幅度降低了后期药理活性实验的成本。
3 以代谢安全性为主的药物筛选
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直接影响药物作用的效果,化合物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absorption,distribution,metabolism,excretion,ADME)是决定其成药性的关键。ADME通常以人结肠腺癌-2细胞系(Caco2)的通透性和人肠道吸收值(HIA)对药物的体内生物利用度进行衡量。以槲皮素为例,筛选发现其对新型冠状病毒S蛋白具有潜在效应,通过ADME预测发现,口服槲皮素后体内血药浓度明显低于鼻喷雾给药后,故推荐给药方式为喷雾剂会获得更好的疗效[28]。穿心莲内酯是一种对病毒M蛋白具有潜在活性的化合物,通过ADME分析发现,其对细胞色素P450等多种代谢酶无作用,不与抗糖尿病药物、心血管疾病药物发生相互作用,有望用于患有慢性疾病的COVID-19患者的治疗[29]。ADME测试除可用于后期化合物类药性测试外,还可参与先导化合物的前期筛选。在一项以病毒蛋白酶M为靶点的虚拟筛选中,通过文献搜索建立抗病毒化合物数据库,得到115个潜在的抗病毒化合物,经ADME预测后,排除102个不符合代谢安全要求的化合物,使候选化合物数量降低到13个,极大降低了时间和精力成本,即ADME是一种有效的药物筛选方法[30]。
4 以结合稳定性为主的筛选
动力学模拟(molecular dynamics,MD)通过计算机虚拟靶标在不同构象下与目标化合物的结合状态并计算结合能,可用于判断化合物与靶标的结合方式,推测化合物-靶标/化合物-活性靶标残基的稳定性构象。通过计算候选化合物与靶标蛋白的结合能,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断结合力的强弱并对化合物的靶标效应进行预测。在对COVID-19的候选化合物进行分析时,动力学模拟可被用于判断或验证目标化合物的结合位点,如在考察地高辛与病毒E蛋白的作用机制时,其结合复合物骨架C原子的位置在20 ns时不再变化而保持稳定,且在形成复合物时E蛋白的氨基酸残基二级构象波动小于0.25 nm,可推测地高辛对病毒E蛋白具有较高的结合稳定性,且其结合方式为与Thr35形成氢键,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31]。同时,动力学模拟还可用于药物设计,利用临床有效药物寻找可能的靶标结合位点,通过结合能大小对靶标进行网络化筛选,可以得到潜在的具有药理活性的靶标官能团,为基于活性基团的药物设计提供依据;当活性靶标确定后,通过系列化合物对其进行结合能分析,可以进行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和开发。此外,密度泛函理论(DFT)以化合物的分子轨道能量受到其结合状态影响为理论基础,通过计算靶标在结合不同化合物后的分子轨道能量变化,进而对化合物的结合活性进行预测,在药物筛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5]。
5 体外药理学筛选
由于COVID-19的突发性和传播迅猛的特点,前期的研究大都以虚拟筛选和计算机辅助为主要手段,虽高效快速地得到了例如茶黄素、槲皮素等潜在先导化合物,但缺乏体内外药理实验,限制了其临床的进一步使用[21]。在后期的研究中,一些体外药理实验例如Western blot、MTT、划痕愈合实验和空斑形成实验等被广泛应用于COVID-19的药物研发[26,32]。在阐明麻杏石甘汤预防性治疗COVID-19的机制中,前期采用网络药理学方法筛选得到了105个活性化合物、83个潜在靶标和63个相关通路,进一步结合IL-6诱导的小鼠肺表皮细胞损伤程度分析和Western blot蛋白表达状况分析,推测得到了苦杏仁苷对主要靶标通路如IL-6相关的JAK-STAT等具有抑制作用,有望成为治疗COVID-19的活性化合物[33]。此外,在对连花清瘟胶囊和热毒宁注射液的临床效果进行评价时,均采用了vero E6细胞结合蛋白含量分析的方法,为其临床实验奠定了基础[32,34]。尽管体外实验相对虚拟筛选具有更高的药理学应用价值,但考虑到实验周期长、影响因素多及成本高等特点,其多用于化合物的后期药理活性验证。
6 临床实验筛选
COVID-19与非典型性肺炎、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在病原体、临床症状上的相似性为其早期经验性治疗奠定了基础,瑞德西韦、氯喹及地塞米松等先前用于其他病毒的药物直接进入了不同规模的临床试验阶段[2]。在一项涉及多地区的包含1 062个COVID-19患者的随机双盲试验中,服用瑞德西韦的患者较对照组表现出更慢的疾病进程、更短的住院时间以及更低的死亡率,推测得到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的有效性[35]。氯喹是一类具有悠久历史的抗病毒药,对其进行结构改造后的磷酸氯喹具有较低的心血管不良反应率,当其用于COVID-19患者的治疗时,患者肺部损伤明显改善,核酸检测病毒转阴率提高,住院时间显著缩短,已被纳入COVID-19临床治疗指南(第八版)。地塞米松作为一种糖皮质激素类免疫抑制剂,在抑制细胞因子风暴方面效果明显,当其应用于治疗COVID-19时,可明显降低需要体外膜肺氧合(ECMO)等机械通气患者的死亡率,被有条件地纳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重症COVID-19患者的治疗方案[36-37]。临床试验是筛选COVID-19治疗药物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但其需要以候选药物具有高度的安全有效性数据为基础,常作为药物大规模上市之前的人体安全性和有效性考察。
7 其他方法
除上述方法外,还有包括Meta分析、数据挖掘等文献计量学方法可用于快速的靶标化合物筛选,如姜黄素的抗病毒效果可通过文献计量学得到,而清肺排毒汤中的多糖被认为是有效成分则源于对多糖的药理学研究[38-39]。
COVID-19是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引起的以下呼吸道严重感染为主要症状的复杂疾病,其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年龄、慢性疾病、机体营养状态均是感染的促进因素[40-41],而心血管疾病、免疫系统损伤是常见的并发疾病[42-45],COVID-19疾病进程的复杂性要求系统性、综合性的治疗方案。植物药具有悠久的用药历史,多成分、多靶点的物质基础优势和系统性、整体性的治疗优势使其成为复杂疾病治疗的有效策略和优选方案[46]。在抗COVID-19药物的研发中,以植物药为基础进行候选药物的发掘和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植物药用于COVID-19药物研发的几种主要策略,以生物活性蛋白为靶标的药物筛选,基于化合物类药性、成药性、体内代谢安全性和化合物对靶标的结合稳定性为基础的药物筛选,以体外药理实验为基础的药物筛选和临床实验筛选等多种药物筛选手段,旨在为从植物中发掘得到高效、安全的治疗COVID-19药物提供一定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