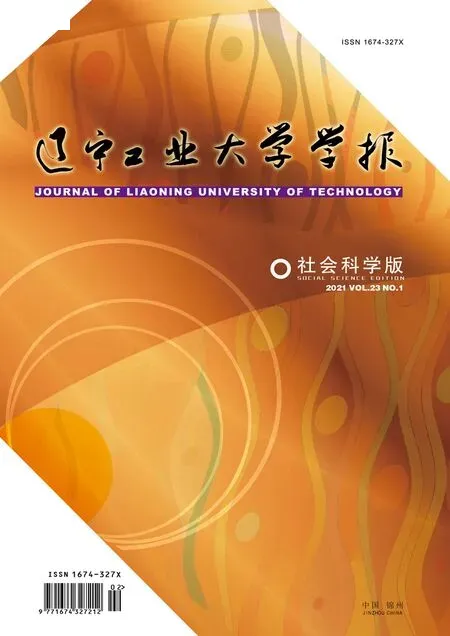《梦蕉亭杂记》点校献疑
2021-12-02邸召鑫
邸召鑫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梦蕉亭杂记》作者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又作小石,号庸庵居士,贵州贵阳人,历任河南、江苏巡抚和四川、湖广、直隶总督。《梦蕉亭杂记》记述了陈夔龙一生相伴随的历史事件(如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参与议和、签订《辛丑条约》等)和耳闻目睹的生活琐事,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清末政治有较高价值。然而,校书如扫落叶,难免扫而未净。本文以中华书局2007 年版“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中的《梦蕉亭杂记》为底本,采用陈垣提出的校勘四法以及多种训诂求义方法,对该书进行深度整理,指出某些字词的讹误及其原因,以便读者更好地阅读。本文所呈现的点校整理条目,均按其原文的顺序排列,并保持其文本面貌[1]。
一、讹文问题
1.厥后遭际时会,摧授京尹,督漕一稔,遂抚汴吴,未绾蜀符,旋移湖广,今上初元复拜北洋之命,不知者群诧官符如火,实则受恩愈重,报称愈难[2]5。
按:“摧授”不辞,系“擢授”之误。“擢,提升”。“摧”与“擢”形体相近,极易相混[3]。古代表示官职调动的词语较丰,例如“擢、拔、升、陟、晋、加”等都是表示升官。此处的“擢授”表示升官义。“擢授”在古籍中经常出现,例如《后汉书·袁绍传》:“臣以负薪之资,拔于陪隶之中,奉职宪台,擢授戎校。”《清史稿台湾资料选辑》:“十三年,调督粮道。十五年,从定贵州,遂擢授巡抚。”
2.讵五月杪,事竣还京,司吏来告,余名已列第三,迨至七月抄,竟列第一[2]7。
按:“七月抄”不辞,“抄”系“杪”之误。“木”“扌”草书写法相近,在中国古籍中,相混是普遍现象[4]89。“杪”本义为“树枝的细梢”,引申为年月或四季的末尾。另外,通过本校法,利用本书前后互证,句中一“杪”一“抄”,必有一误。“木”旁、“扌”旁在古籍中经常不别[4]89。如清李鸿章《李文忠公选集》:“前闻廷臣于冬月杪会议,嗣因先皇疾革,遂尔迁延,约今春再行议覆。”清许葭村《秋水轩尺牍》:“弟自甲午夏杪,移砚会川,以积累故,迄未少有储蓄。”
3.翼日,具奏奉旨谕允,余仍为京曹矣[2]13。
按:本句断句不当,应在“奉旨谕允”之前断句。又“谕允”不辞,系“俞允”之误,误增偏旁而误。“俞”,应诺之词。后即称允诺为“俞允”多用于君主。运用本校法前后互证,本书共出现7 处“俞允”,仅此1 处为“谕允”。例如:“覆奏上,奉旨俞允。时高阳已病,仍力疾入直,阅文忠折,拂然不悦。”[2]70“余奏请入《国史儒林传》,奉旨俞允。”[2]100“余入觐情殷,归思正切,专电枢廷,请以苏藩陈君伯平启泰,护理抚篆,以便克期交代,入京祝嘏,奉旨俞允。”[2]100前后互证并关照上下文义,可知此处当为“俞允”。又如《台案汇录丁集》卷一:“嗣准贵部院以陆路各标协营每年所报倒马过浮,恐致营弁冒销,循照广东减报之例,议将陆路各营减报倒马三百一十三匹,共节省银六千八百八十六两,除各项公务派给外,下剩朋银,赏给出洋官兵等项之用等因,折奏奉旨俞允,并单开军标两营应减报马四十五匹等因,咨会前来。”
4.而国事危如累卵,已亦身败名裂。哀哉[2]22!
按:“已”字于义不通,系“己”字之误,义为“自己”。“已”与“己”字形相近而误。据上下文可知,此处“己”是指载漪刚愎自用,笃信拳匪,假托帝王诏命诛杀大臣,不仅将国家置于危险之地,而且导致自己也身败名裂。“己”“已”“巳”三字在古籍中不别,须根据上下文而定[4]166。
5.此数日间,吾二人亦犯嫌疑,恐难动听,不如遨同荫轩(徐桐字)、文山(崇绮字),四人请起,力量较大[2]36。
按:“遨同”不辞,系“邀同”之误,义为“约别人一起”。“遨”“邀”形近而误,“敖”旁稍有变异,即易误认为“敫”旁。例如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先父乃命先兄邀同乡里绅衿赴县具禀,并请邑尊出示禁止,挨风自此渐息。”又如许啸天《清代宫廷艳史》第七十三回:“恭亲王不肯,要他把兵队退到天津去,才肯开议和局;英国公使也不答应,恭亲王无法可想,便邀同周祖培、陈孚恩联名上奏行在,说外人十分强悍。”
6.君在此少候,我立约彼等即来。先商文山,谓:与筱云虽无深交,亦无意见,可以同住[2]36。
按:“同住”不辞,系“同往”之误。据上下文义可知,此处应为同去为筱云尚书求情,当为“同往”之意。“住”“往”形体相近,在古籍整理与传抄过程中,稍不注意即易产生混淆。
7.全权告以庄王、毓贤诚有罪,总兵英年当时并无仇洋实权,不过联衔出有告示,原难辞咎,但讵能正法?至重不过斩监侯罪名[2]45。
按:“斩监侯”一词,运用本校法可知其有误,并可做出准确的校勘。本书共两处“斩监候”,一为本例所列,另一例“甲申法越之役,中丞防边失利,拿交刑部治罪,部定斩监后[候],秋后处决。”[2]8“候”与“侯”并非异体字,两处必有一误。“斩监候”在《汉语大词典》当中释义同“斩候决”[5]9045。“斩监候”是清代缓期执行的一种死刑,不同于立即执行的“斩立决”。孙家红在其著作《清代的死刑监候》中写到:“清律采取列举主义,对诸多应判死刑监候(绞监候、斩监候)的情况进行严格、细致的规定,条目繁多,内容广泛。”[6]在《大清律例·名律例》中明确规定死刑二:绞,斩。绞、斩即绞监候与斩监候。故本例“斩监侯”应改为“斩监候”。
8.后恩君洊升副都统,庚子之变,赍志以没〔殁〕[2]53。
按:“没”古同“殁”,为一组异体字,此处不烦改。校勘古籍时,文义无误的地方应尽量保持古籍原貌。
9.不得已令厂商先搭席棚,缭以五色绸绫,一切如门楼之式,以备驾到时借壮观赡[2]63。
按:“观赡”不辞,系“观瞻”之误。“贝”的繁体“貝”与“目”极为相近,稍不注意便容易致讹。运用本校法,通过本书前后互证,“迟之又久,某督入觐,面奉懿旨,谓:门楼为中外观瞻所系,急须修建。”[2]63从词义来看,“观瞻”义为瞻望;观赏;观看[5]14333。而“观赡”则于义难通。
10.丁丑春,师病没密云,学士往吊,并撰挽联云:“成一代史不可无公,岂期积蠹丛残顿惊绝笔;封万户侯何如知已,剩有素车白马为赋招魂。”措辞极其哀痛,余心折之[2]74。
按:“知已”系“知己”之误。“己”“已”字形相近所致。由上下文义可知,此处当为“知己”。他例如《萤窗清玩》第一卷:“李生谓仙曰:‘昨日之言,未知尊意决否?与其块然独居,何如知己同游之为愈也。’李祥亦极力相劝,碧仙方才允承。”
11.惟限于地势,凡细民无力居肆者,咸于肆旁设摊贸易,不下千余家,均借此谋生活,由来旧〔久〕矣[2]103。
按:“旧”字不误,不烦校改,义为长久[5]12454。“旧”作“长久”义,可参见《诗·大雅·抑》:“於乎小子,告尔旧止。”郑玄笺:“旧,久也。”宋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二:“煮面谓之汤饼,其来旧矣。”《新唐书·李岘传》:“于是吕諲、李揆、第五琦同辅政,而岘位望最旧。”
12.先保护铁路、电杆,及一马〔码〕头等处与租界联属之地[2]104。
按:“马头”无误。“马头”与“码头”为异形词,义为“船只停泊处,即码头”[5]17586例如宋梅尧臣《次韵和马都官宛溪浮桥》:“马头分朱栏,水底裁碧天。”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六回:“少刻,船拢了马头。”校勘古籍时,若原文无误则不要轻易更改古书内容,此处“马头”不烦校改。
13.苏浙文风相捋,衡以浙江一省所得之数,尚不及苏州一府[2]106。
按:“相捋”于义难通,系“相埒”之误。“相埒”义为“相等”,符合文意。“捋”与“埒”字形相近,运用本校法前后互证可知此处当为“相埒”。如本书45 页“随往者仍那相与余及翻译各员,与上次相埒。”他例如清梁章钜《枢垣记略》:“即如盐运使一官,亦系三品,外官司道并行,体制相埒,此外盐政关差,亦有外旗人员,其子弟似亦应一体回避。”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三:“隋仁寿元年造,石作幸巧,与赵州石桥相埒,长四百五十尺。”
14.大工未集,忽值国变,一切匠作,因而停止。幸南海梁文忠公鼎芬痛哭陈书,严责当事,拔给巨帑,得以乘时兴工[2]110。
按:“拔给”扞格不通,系“拨给”之误。形近所致。“拨”后接宾语多为钱款、粮食。古籍中较为多见,如《台案汇录丁集》卷四:“今乾隆六年分应赏银两,汇入乾隆六年分估饷册内请拨,准部拨给在案。”《法军侵台档案》:“窃臣前因奉旨饬调恪靖等七营北上,兵力益单,而各路增兵之请纷至迭来;比饬各战将就近添募十二营,遵旨奏请饬部每月拨给银五万两以济该新军在案。”
15.谓藏与川相为表里,一切筹兵、筹饷,责在川督。总督与边务大臣休戚相关,源源接挤,藏事自易奏效,否则无从办理云云[2]118。
按:“接挤”不辞,系“接济”之误,义为“在物质上援助”。形近所致。清蒋良骐《光绪朝东华续录选辑》:“闽省云者士枪弹,曾国荃务速运厦,速解吴鸿源营;并着左宗棠等将台军饷械源源接济。”《左文襄公奏牍》:“此间库款支绌,臣等行营饷需,全赖各省关源源接济,方敷支放;各台、局按月筹解、络绎转输,诸军得以士饱马腾者,未始非各员之力也。”
16.一切目见耳闻,离奇怪异,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不屑笔之记载,污我毫端。盖三纲五常之沦久矣[2]125。
按:“沦”即“沦斁”。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是“斁”的简化类推字,在书中出现次数较少。“沦”即“沦斁”,义为“败落”。
二、词汇问题
17.文忠公派余与濮君子潼、裕君厚筠,庵师派端君方、何君乃莹、丁君象震为随带司员,前往刑部会讯[2]9。
按:“会讯”一词,义为“会同审理案件”。“会讯”在古书中出现较多,如《台湾文献丛刊南明史料》南明史料卷三:“本年九月初三日奉总督李都御史详批:据详,孙枝秀之讦谢三宾通贼行贿,屡经该司会讯,似为明允。”明杨慎《廿一史弹词》:“刑部尚书颜颐寿于午门会讯,良与景全共指福达即寅,寅语塞,颐寿奏闻。”《福建省例》:“其必须准理者,不可轻批提省,但责成本管知府秉公研讯,或委贤明之员前往会讯。”《汉语大词典》未收“会讯”一词,但收有与其构词方式相同的“会审”,义为“会同审理”[5]7246。“审”与“讯”为同义词,故“会审”与“会讯”应均译为“会同审理案件”,应在将“会审”词义下增加“同‘会讯’”的义项。
18.维时皇上尚在勤政殿接见日相伊藤博文,宫中府中不暇传宣警跸,慈驾已回西苑[2]20。
按:“慈驾”一词,义为“太后的车驾”,亦借指太后。《汉语大词典》失收,但收有与其构词方式相同的“圣驾”,释义为“皇帝或临朝皇后的车乘。亦借指皇帝或皇后”[5]11831。如明杨铭《正统临戎录》:“铭随圣驾,不离左右,寻米面做干粮预备答应。”运用文例求义法与归纳法可知,“慈驾”借指太后。例如《皇朝通典》:“恭奉皇太后慈驾登舟巡幸山东,至泰安诣岱庙瞻礼,至曲阜诣文庙行释奠礼,回銮至良乡行郊劳礼。”又如李逸侯《宋代十八朝艳史演义》第七十八回:“李宫娥就奔告太后道:‘昭容病势十分沉重,刚才晕厥过去,请慈驾亲往一观,还须速请医生诊治。’”再如清梁鼎芬《康有为事实》:“谭以湖南人而到京,移住南海馆,与康同居合谋,谭一人潜往,见侍郎袁世凯,诈传谕旨,令袁以兵力先害北洋大臣荣中堂禄,即带兵入京,围颐和园,震惊慈驾,此尤臣子所不忍言、神人所共愤者也。”
19.丁文诚前官蜀中,改定鹾章,剔除中饱,百余万尽数归之公家[2]57。
按:“鹾章”一词,义为“管理盐务的规章制度”。《汉语大词典》失收。但有收与此构词方式相同的“鹾政”,义为“盐务”[5]17831。清昭梿《啸亭续录》:“又有鹾贾查氏,富逾王侯,交结要津,人莫敢撄,故鹾政日见疲弊”。“鹾法”义为“管理盐务的法令”[5]17831。明黄仲昭《八闽通志》:“时县之鹾法更变,帑藏空虚”。清程雨亭《整饬皖茶文牍》:“至所议仿照淮鹾章程,令茶商领照运茶一节,自系维持茶务之计。”运用同义连文法以及揣摩上下文,可知“鹾章”义为管理盐务的规章制度。
20.夙谂镇中商办救火会最得力,札令该会彻夜巡逻,以防未然[2]104。
按:“札令”一词,义为“上级对下级下达命令”,《汉语大词典》失收,但收有与其构词方式相同的“札委”,义为“旧时官府委派差使的公文”[5]5790。
根据文例如《福建省例》:“其偏僻营分并无道府同城者,即札令驻札之丞倅州县等官,会同营员点验收贮,取结报查。”《信及录》:“现已多雇剥船,即可分起赶收,不必拘定两船一起。合亟谕饬。谕到,该洋商即传知副领事、领事速即遵照,札令参逊率领九洲各趸船一齐驶到龙穴,听候收缴。”清佚名《乾隆下江南》:“当日大学士刘墉读完圣旨,立即札令扬州府地方官建立烈女祠,并于库中拨银二千两,置买产业,四时祭祀,后来显圣。”《台案汇录庚集》:“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据福康安奏:台湾剿捕逆匪,即日大功告竣,所有抚恤难民及添建城垣等事,亟须大员董率经理,请旨令徐嗣曾速渡台湾办理,现已札令该抚即行起程等语。”运用归纳法归纳可知“札令”一词,义为“上级对下级下达命令”。
21.疏上,奉硃批,饬余查明得力人员,择尤保奖[2]109。
按:“保奖”一词,义为官员向上荐举有功之人,使得到奖励擢升。《汉语大词典》失收。但收有与其构词方式相同的“保举”,义为向上级荐举有才或有功的人,使得到提拔任用[5]1396。《中国历代官称辞典》中也收有“保举”一词,义为大臣向朝廷推举人材并为其作保,称为保举[7]。“保奖”一词在古籍中出现频率较高,例如清蒋良骐《光绪朝东华续录选辑》:“五月丁未(十一日),谕:沈葆桢等奏“南路剿番攻克各社情形”一折,淮军自到台后,艰苦出力;准其择尤保奖,以示鼓励。”《清实录宣统朝政纪》:“各将弁不敢仰邀奖叙。得旨、仍著陈夔龙查明择尤保奖。勿许冒滥。”清恽毓鼎《澄斋日记》:“至国史馆总裁荣中堂、陆太宰、陆都宪处谢得保奖。”“保奖”与“保举”构词方式相同,运用联系法与归纳法可得出,“保奖”一词,义为官员向上荐举有功之人,使得到奖励擢升。
22.余于宣统己酉腊月。履直督任,所辖北洋第二、第四两镇,兵力甚强,足以建威销萌[2]122。
按:“销萌”一词,义为消除祸端,多与“建威”连用。《汉语大词典》失收。但古籍多见“销萌”例,如清谢宸荃《安溪县志》:“公用意复出于是,究其施,将使文教昭明,礼义兴起,以为畜众销萌之机,而向者卓然之劳烈,可以永措而不复设,又非独其才之过人而已。”《清实录乾隆朝实录》:“而擒首恶以儆余凶。亦可销萌于事始。此之谓化大事为小事。化有事为无事。”赵翼《廿二史劄记》:“近日英吉利国遣使入贡,乞于宁波之珠山及天津等处,僦地筑室,永为互市之地,皇上以广东既有澳门,听诸番屯泊,不得更设市于他处,所以防微销萌者,至深远矣。”运用联系法与归纳法可知,“销萌”一词,义为消除祸端,《汉语大词典》应据补。
三、余论:倒文一则
23.余谓董军前戕害日本书记官山杉彬,各使恨之切齿,万不能派往[2]94。
按:“山杉彬”文字颠倒,当为“杉山彬”之倒文。杉山彬(1862-1900),日本近代外交官,庚子事变时被杀[8]。赵尔巽《清史稿》:“时祸首已惩办,公约亦定,朝廷因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特简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赴日本道歉,所得偿款四百五十兆,日本应得三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两,惟以俄不退东三省、俄约不归公议为言。”清罗惇曧《庚子国变记》:“曰本书记杉山彬,出永定门,董福祥遣兵杀之,裂其尸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