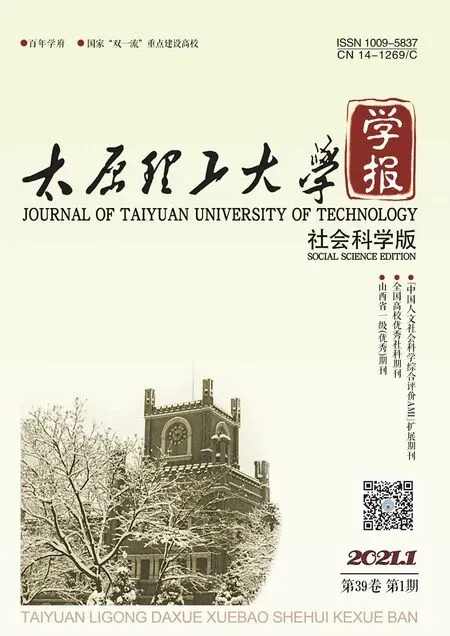论《民法典》中自甘冒险规则的司法适用
2021-12-02谭佐财
谭佐财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自甘冒险(Assumption of risk, Handeln auf eigene Gefahr),源自拉丁格言“volenti non fit injuria”(译为:自甘风险者自食其果)。通常认为,侵权法中的自甘冒险是指受害人明知或者应知存在的风险,非基于法律、职业、道德或类似义务而自愿将自己置于危险环境或场合的行为[1]。但就自甘冒险对行为人发生免责的效果还是减轻责任的效果则有截然相反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在自甘冒险被提出时,就没有适用与有过错的余地,接受风险就排除了责任[2];相反观点认为,自甘冒险虽然同意承受一定的风险,但是并不意味着希望自己的人身与财产遭受危险,要通过过失相抵或比较过失等制度进行相应的减轻甚至免除[3]。存在争议的表面原因在于规范的缺失,实则是对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范围存有不同认识。《民法典》第1176条首次在立法层面对自甘冒险规则予以明确规定后,前述问题则需要重新审视和回答。
虽然《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均未确立自甘冒险规则,但并不妨碍法院根据社会共同认知和域外司法经验发展出的法理进行裁判。通过对既有司法案例的梳理发现,审判实践对自甘冒险的适用突出存在着适用对象类型宽泛不一(典型的如篮球、足球、羽毛球运动,登山探险、垂钓、野外骑马、野泳、划船、练舞等),导致对自甘冒险适用的法律效果迥异,具体而言包括:适用自甘冒险直接免除行为人的侵权责任,且不要求行为人依照公平责任分担损失(1)曾立华与李逢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湘13民终612号。;适用自甘冒险免除行为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之后,继续适用公平责任要求行为人承担补偿责任(2)张木茂与郑汝青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粤03民终7720号。;将自甘冒险作为受害人过错的认定因素,进而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减轻行为人的侵权责任(3)刘燕、王思语、韩继英、王兆坤与冯作柱、朱彬、刘成超生命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2)川民初字第2108号。法院认为,虽然受害人的行为符合自甘冒险的特征,但自甘冒险仅仅是认定受害人过错程度的考量因素与情节,但并不能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责任,仅可以根据过错程度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责任。。除此之外,活动组织者或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其他主体也常作为责任的“兜底主体”而泛泛适用(4)周某与刘某等侵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01)萍民终字第177号。,既有研究对自甘冒险活动中的活动组织者相关问题也尚待深入讨论。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民法典》第1176条为基础,首先明确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范围,这是后续展开讨论的前提;进而解决本条与《民法典》第1173条(过失相抵规则)、第1186条(公平责任)区隔不清的问题;然后讨论活动组织者的认定及民事责任问题。由于第1176条系《民法典》新增规则,学说上也多为立法论的构建而缺乏解释论的分析[3-4],本文将以解释论的视角,全面诠释该条款的司法适用难题,以期助益于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规范适用。
二、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范围
(一)“文体活动”限缩在具有竞技性质的活动
“文体活动”是自甘冒险规则在文义上的适用范围。从字面意义上看,文体活动包括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但一般认为此处的文体活动是指风险性较高、对自身条件有一定要求、对抗性较强的文体活动[5]。这一范围似乎是确定和封闭的,没有可以扩张的空间[6]。诚然,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范围不能超出“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但并不代表“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均有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余地。换言之,“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是适用自甘冒险规则的必要不充分条件。那么在法律适用中,应当如何对“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的适用范围进行确定?
立法机关工作人员认为,《民法典》新增自甘冒险规则是为了满足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技活动的需要[5]。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为防止自甘冒险规则适用范围过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以“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限缩了“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审稿)”第954条第1款 “具有危险性的活动”的规范范围。由此可见,立法者倾向于限缩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范围。
《法学方法论》认为,若按照相对狭义理解的意义更符合“立法者的意志”,则必须作限缩解释[7]。首先,我国法上的自甘冒险规则采完全抗辩模式,具有免除责任的法律效果,不同于德国实务上采“过失相抵”路径仅发生减轻行为人责任的效果。行为人援用自甘冒险规则抗辩将会完全免除其责任,所生损害由受害人自行负担。就正义平衡而言,其适用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其次,具有竞技性质的活动同时兼具对抗性和观赏性,在活动中需要发挥勇敢拼搏的体育竞赛精神,较高风险成为竞技性文体活动的通常属性。对参与者科以较高的注意义务,将与竞赛的性质和目的相冲突,从长远来看,将妨害社会体育运动的长足发展。与之不同的是,不具有竞技性质的其他文体活动参与者有义务也有能力警惕风险的现实发生。据此,将“文体活动”的文义限缩至具有竞技性质的文体活动,竞技性质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活动本身体现竞技性,旨在挖掘和发挥人体运动的潜能,以创造优异成绩、战胜对手为目的,如此便将一般的健身、休闲、娱乐活动排除在外;(2)损害在竞技场合现实发生,如果活动具有竞技性但损害却并非在竞技的场合发生则不在此列。
需要注意的是,训练、教学等活动不属于本条规范的“文体活动”。法国法上,关于风险接受的理论只在竞技性体育运动中得到适用,在非竞技性的或即兴的运动会中、青年运动训练中(如高尔夫球课程训练),并不适用[2]。事实上,接受风险本身并不代表主观上愿意承受损害之结果,在竞技活动尚且如此,遑论在训练或教学过程中的损害。客观上,在训练和教学中的风险一般应当是可控的,提供训练、教学内容的主体应当采取严密的安全保障措施。类似活动突出健身、休闲、娱乐性质而非竞技性质,自愿接受训练和教学不应推定为认识到固有风险的存在,活动参加者应尽到自身安全防护义务和避免造成他人损害的注意义务。例如,参加学习具有一定难度系数、危险性的民族舞不属于自甘冒险(5)卞某某与平顶山市艺欣舞蹈学校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4)新民初字第1414号。,体育课上的篮球教学活动也不在此列(6)孙佳平与刘海潇等健康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7)吉0102民初3571号。。
自甘冒险的构成要件之一为所参与活动具有对抗性或者危险性。一方面,对抗性是指活动本身的固有属性而非受害者与行为人之间必然存在对抗关系,受害者与行为人之间也可能是对抗性活动中的合作关系。因此,“其他参加者”不仅包括对抗者还包括合作者。另一方面,文体活动的固有风险是公开且明显的,在该活动范围内无法完全避免风险或者能够避免但需付出巨大代价[8],换言之,当风险超出公开且明显的固有风险时,所生损害无法为自甘冒险规则所涵摄。例如在学校举办的运动会接力比赛项目中,运动员串道撞倒相邻赛道运动员,该串道风险则超出活动固有风险之外,应当根据各方过错承担责任(7)蔡学清等与昆明市盘龙区水务局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云0103民初6764号。。
进一步而言,固有风险的具体化非由受害人、活动的组织者或者活动本身所致,而是由活动参加者之间的积极对抗行为或者消极不作为所产生。《民法典》第1176条也表明竞技性文体活动中的风险和损害需由其他参加者导致。换言之,如果仅具有较高的专有风险,但损害并非来自其他参加者,则不符合适用自甘冒险规则的文义要求。如此便将垂钓溺亡、舞蹈培训受伤、滑雪摔伤等类似情形排除在自甘冒险规则适用范围之外,转而适用普通侵权规则。
(二)自甘冒险活动中受害人的范围
场外无关第三人(如行人)遭受损害,行为人、活动组织者应当根据各自过错承担责任,对此并无争议。争议焦点在于,观众能否认定为自甘冒险活动中的受害人?“肯定说”认为,观众被界外球击中受伤可基于受害人承诺而阻却行为人违法性,从而不应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9]。“否定说”认为,因运动员的错误造成在观看场地的观众损害时应当肯认运动员的过错,进而承担责任,尤其是对于危险体育项目,若参与者知道组织者未为观众提供充分的安全措施时就应当拒绝参赛,或者则应认定为参与者具有过错[10]。笔者认为,活动的参加者需符合危险的承担者和危险的制造者的双重身份属性,但观众或者其他第三人仅承担危险却并不制造危险,径行认定其对风险具有承诺或者同意之意思不妥。因此,观众或者其他第三人不应纳入自甘冒险的规制范围。观众或者第三人遭受损害的责任承担,视活动组织者或者运动员是否尽到必要的安全防护义务而不同:若已经尽到必要的防护义务,观众自行脱离防护的保护范围而遭受损害,则按照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无法向其主张权利;若未尽到基本的防护和注意义务,例如观众被“一个理性的参赛者,即体育界的理性人所不会犯的判断错误所伤”(8)Wilks v.Cheltenham Homeguard Motorcycle & Light Car Club(1971) 1 WLR 674(A).,运动员、活动组织者、观众则均有过错,应当按照各自过错(过失相抵)确定责任。
概言之,自甘冒险活动中的受害人仅指该风险活动的直接参加人,不宜将观众或者其他第三人纳入其中。
综上所述,自甘冒险规则的完全抗辩效果赋予限缩适用范围的正当性。一方面,自甘冒险规则的适用领域应当限定在具有一定风险的竞技性文体活动中,不仅要求活动本身具有竞技性,而且损害发生在竞技过程中并由其他参加者所导致,由此排除了自甘冒险规则中的训练、教学和其他健身、娱乐、休闲活动的适用空间;另一方面,自甘冒险规则对观众或场外第三人并不适用。
三、自甘冒险规则与相关规则的适用关系
(一)自甘冒险规则与过失相抵规则
德国实务上,早期认为自甘冒险是默示合意免除责任,后将其解释为受害人允诺而具有阻却违法性,最近则改采“过失相抵”标准[11]。英国普通法上,自甘冒险是完全抗辩,一旦成立,原告将得不到任何补偿。基于结果公平的理念,英国在许多原本适用该抗辩的场合转而适用共同过失(过失相抵)抗辩[12]。国内有学者借鉴德国、英国等实务经验,主张自甘冒险规则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失相抵规则即可解决实践中的情形[13]。此种观点也同样体现在司法实践中。但笔者认为,在自甘冒险规则已被立法确认的背景下,需要更加警惕过失相抵规则对其之侵蚀,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法定的援用自甘冒险抗辩的情形相当狭窄,只有在符合自甘冒险的严格适用条件时方得以适用,因此不会造成自甘冒险的泛滥适用而对受害人形成不公平的后果。必须要承认的是,“要么全部承担责任,要么不承担责任”(all-or-nothing)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减轻行为人的责任比完全免除其责任更为公平,正因为如此,《欧洲侵权法原则》第7:101条第3款则明确“在特殊情形下,责任可予以减轻而非免除”[14]。但是,该特殊情况可均被过失相抵规则或者过错责任原则所涵摄,不能成为自甘冒险抗辩不应存在的理由。
第二,虽然在运动员获取高额报酬和社会荣誉并且有完善的体育保险的职业体育竞技活动中适用自甘冒险一般不会导致显失公平,但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职业运动员之间发生人身损害并诉至法院的几乎没有,主要都是业余爱好者之间发生的纠纷(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让毫无保障的体育活动参与者(受害者)自行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风险,确有违背公平和朴素法正义基本价值之嫌[15]。但是,经由解释论的发展,可以通过对风险的分散形成受害人损失救济或者弥补体系。职业运动员通常能通过体育保险、雇主责任等方式分散风险,而业余竞技活动参与者亦可通过由受益人承担公平责任、活动组织者承担相应责任等方式分散风险。简言之,即便适用自甘冒险规则,尚有较大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对受害人损失进行填补。
第三,在自甘冒险领域直接以过失相抵作为承担责任的标准也难以囊括实践中存在的所有情形。过失相抵规则责任划分逻辑在于原则上由行为人承担全部责任,在此基础上根据受害人的过错程度相应地减少行为人的责任,受害人无过错或者过错无法证明时,行为人将承担全部责任;也即,过失相抵规则要求受害人存在过错时方能减轻或者免除行为人责任。依照《民法典》第1176条的规定,作为行为人的其他参加人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方才满足承担侵权责任的过错前提,同样地,受害人作为参加人也需要满足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方可认定为具有过错。但受害人自愿参与文体活动的行为本身却无法认定为其存在过错,如此形成的责任分配对行为人过于苛刻。
基于此,在自甘冒险纠纷中一律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将产生行为人承担过重责任的后果,这与自甘冒险基本法理和精神相悖。所以,自甘冒险作为独立的抗辩事由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过失相抵规则无法完全替代。虽如此,由于自甘冒险规则适用范围狭窄,过失相抵规则仍将在自甘冒险规则无法触及的场合发挥重要作用。
有学者将一般的自甘冒险分为现象意义和规范意义两种类型,“明知危险而仍然冒险”的现象就属于现象意义上的自甘冒险,而规范意义上的自甘冒险是法律明确的一种独立的抗辩事由[4]。《民法典》直接规范的自甘冒险属于规范意义上的自甘冒险,但尚存在大量现象意义的自甘冒险。这些类型的自甘冒险被域外经验、司法实践、大众认知所接受。DCFR的自甘冒险规则中虽明确主要适用领域是参与武术活动或者其他危险的运动,但却也明确表示“并不限于此”[2]。在行为人满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前提下,行为人仅以受害人“明知危险而仍然冒险”的行为存在过错要求减轻其侵权责任。例如,搭乘醉酒司机驾驶的车辆造成损害。
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即便受害人的行为符合现象意义的自甘冒险,但若无法证明行为人存在过错,则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无法成立。《民法典》过失相抵规则相较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过失相抵规则在措辞上发生的轻微变化表明“过失相抵”的抗辩不仅适用于过错侵权案件,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也一般地适用于无过错责任侵权案件[6]。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下,“明知危险而仍然冒险”达到重大过失的程度时,才可以减轻行为人的部分侵权责任。
(二)自甘冒险规则与公平责任
《民法典》第1186条(公平责任)与自甘冒险在以往司法实践中关系微妙、适用混乱,主要存在“对立说”和“统一说”两种观点(9)“对立说”观点,例如郎同星等与陈硕等健康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6)鲁15民终1747号;“统一说”观点,例如张明与肖高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14)信中法民终字第225号。。在自甘冒险过往司法实践经验中,法院多基于对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由行为人进行损失的分担,而由受害人自行承担全部损失的案例较为少见[15]。《民法典》第1186条将《侵权责任法》第24条中的“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修改为“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系对《侵权责任法》第24条泛化适用而常被诟病的回应,表明公平责任的适用更加严格。而此处的“法律的规定”既包括法律规定适用公平责任的情形,也包括法律规定不适用公平责任的情形。《民法典》第1176条明确规定自甘冒险活动中受害人不得向其他参加人主张侵权责任,这就排除了公平责任的适用。申言之,在《民法典》体系下,我国法上的自甘冒险采完全抗辩模式,原则上将不再有公平责任的适用空间,这将极大地改变原有司法裁判习惯。
一般而言,由其他参加者直接致损所产生的责任主要涉及受害者、其他参加者、活动组织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但存在活动受益人时,则涉及四方关系。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活动受益人可能会与活动组织者身份重合。为了缓和自甘冒险的完全免责效果,受益人在风险活动中分担损失具有合理性,这也符合“受其利者蒙其害”蕴含的利益与风险同在的精神,归根结底体现的是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民法基本原则[16]。
要求受益人公平分担损失本就已经超出了一般法律责任的构成条件,若继续扩大受益人的认定范围,将会不当地侵蚀社会的公平原则。因此,对受益人应当严格认定,不可过于宽松。申言之,在自甘冒险活动中受益人的认定应当考虑受益内容与危险行为之间是否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并且受益人通过参加人的危险活动获取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利益。由于受益人与受害人分担损失是以财产的平衡为正当性基础,故获取精神利益或者其他利益不能认定为“受益人”。
四、活动组织者的法律责任
(一)活动组织者的认定
《民法典》第1176条第2款规定活动组织者的责任认定适用《民法典》第1198—1201条的规定,但《民法典》中仅第1198条对“组织者”这一责任主体做出了规定,并且该条表明组织者与经营者、管理者系并列关系。那么,是否可以据此得出第1176条第2款的活动组织者仅指第1198条的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的结论?其实不然。群众性活动是面向社会公众组织的活动,但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却并不限于此,具有封闭性的学校等教育机构亦是活动组织者的主要认定对象(10)周慧蓉与四川省宜宾军分区幼儿园健康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7)川15民终770号。。这一点在立法过程中也能得到印证,“侵权责任编草案(二审稿)”规定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该审议稿第973条的规定,在“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进一步明确了活动组织者为学校等教育机构时应当适用学校等教育机构在学生受到人身损害时的相关责任规定。因此,活动组织者不仅存在于群众性活动中,其他面向特定群体的封闭式活动仍然得以适用。
首先,活动组织者的认定需要谨慎把握,从严认定。就司法实践经验而言,在行为人和受害人均无过错时,活动组织者通常无法免除其责任(11)陈硕与郞同星等健康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5)临民一初字第1674号;李蓓、王慈枫等与王兴江、岳良荣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2019)苏05民终4857号。,因此活动组织者可能承担的责任是严苛的,不宜对其宽泛认定。借鉴司法实践经验,笔者认为,活动组织者需要满足组织行为的特征。主观上,活动组织者需具有组织活动、管理人员、控制风险的意思;客观上,活动组织者需有组织活动、管理人员、控制风险的客观行为。例如在“李某某等与刘某某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中,二审法院推翻了一审法院认定的“李某某是此次户外活动的发帖人,由其制定出行日期、路线、经费,召集人员汇合并安排车辆,其一系列行为均具有组织行为的特征,应认定其为组织者”,二审法院从主观上无组织、管理的意思且客观上无组织、管理的行为而认定其身份应为活动召集人而非活动组织者[17]。在司法裁判时不可将本不具有活动组织者属性特征的主体认定为活动组织者,从而使其承担较重的赔偿或补偿责任。概言之,《民法典》第1176条第2款所规定的“活动组织者”不可作为责任承担的“兜底主体”。
其次,在不符合活动组织者主体条件时,公共场所、教育机构等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的责任并非直接免除。一般而言,只有较为正式的文体活动中存在活动组织者,实践中存在较多非正式的文体活动导致损害(自发组织的竞赛或者其他文体活动),则缺乏活动组织者责任主体。而《民法典》第1176条第2款可能使人产生如下误解:在受害人自甘冒险活动中,仅符合活动组织者的特征时,才能依照第1198—1201条(在公共场所、教育机构等遭受损害的责任)要求其承担责任,否则不承担责任。其实,活动组织者是适用《民法典》第1198—1201条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虽然缺乏活动组织者时无法经由第1176条第2款适用第1198—1201条的规定,但却可以直接适用第1198—1201条的规定。例如,课后或者放学后学生自发进行篮球运动,学校自然不符合活动组织者的责任构成,无法适用《民法典》第1176条。但学校的安全教育、提示、安全保障的责任并不会因其自甘冒险活动而免除,《民法典》第1198—1201条的规定得径行适用(12)洪某某与庐江县金林小学、庐江县志成学校等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5)合少民终字第52号。。
(二)活动组织者的责任
首先,活动组织者侵权责任构成的特殊性。由于活动组织者具有更强的风险控制能力和代价,受害人自愿承担风险时并不免除活动组织者的注意义务[18]。因此,活动组织者无法援用受害人自甘冒险作为抗辩事由,即便受害人的行为符合自甘冒险的构成,活动组织者应否承担责任仍需结合其过错进行认定。《民法典》第1176条第2款为引致性规范,虽然活动组织者的责任在法律规定上应当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198条(安全保障义务)、第1199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遭受人身损害)、第1120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遭受人身损害)、第1201条(第三人侵犯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责任),但自甘冒险情形下组织者的责任与非自甘冒险情形下组织者的责任应当区别对待[3],在自甘冒险的情形下,受害人已经意识到了固有危险的存在,如果仍强调活动组织者完全依照有关安全保障义务、学校责任的条款来承担相应责任,会与自甘冒险的立法初衷和规范目的相悖,不利于鼓励活动组织者积极开展体育运动[19]。因此,在具体进行法律适用时,需要对《民法典》第1198—1201条过错要件严格认定、对免责条件从宽认定,不宜变相加重活动组织者的责任。
其次,活动组织者通常不享有对其他参加者的追偿权。相较于《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40条,《民法典》第1198条、第1201条新增对直接侵权人的追偿权。在自甘冒险活动中,其他参加者即为《民法典》第1198条、第1201条所指的“第三人”(直接侵权人)。从文义来看,活动组织者或者公共场所、教育机构等经营者、管理者对行为人享有追偿权。但追偿权的规范对象是构成侵权责任的行为人而非任意第三人,换言之,如果第三人尚不构成侵权责任,则活动组织者向该第三人行使追偿权缺乏法律根据。反之,第三人构成侵权责任时,活动组织者对该第三人是否享有追偿权须视损害是否落入安全保障义务保护范围而有所不同。若在此范围,则应当承担自己责任;否则方生补充责任,从而向侵权人进行追偿[20]。
五、证明责任
(一)向行为人主张权利的证明责任
受害人向行为人主张侵权责任,需要证明符合侵权责任请求权之构成,而后行为人方有援用受害人自甘冒险抗辩之余地。一般而言,受害人需就行为人实施了不法行为、行为人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损害事实客观存在、不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果关系需符合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构成要件,仅具有事实上的关联而不具有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无法认定为侵权(13)郭峰与张维霖、天津市滨海新区远航室内运动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津0117民初2553号。。体育违法行为主要指直接从事体育运动及与之相关的人员或机构,在体育项目训练或比赛中,所实施的不具有阻却违法性因素的犯规行为、暴力行为及直接违反法令的行为等体育致害行为。难点在于,受害人对行为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举证较为困难,较多案件以受害人未能证明此项待证事实而导致败诉(14)梁宝坤与刘祖福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1)南市民一终字第1379号。但也有法院不当地要求被告就损害后果与运动行为没有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参见王瑛等与王虎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0)安少民终字第24号。。故意较容易判断,但重大过失是介于故意和一般过失中间的过错形态,常被立法和理论研究所忽略。有必要对自甘冒险活动中行为人存在重大过失的认定进行讨论。
过失的本质在于注意的欠缺,亦即注意义务之违反,是以意思与预见或防止可能性及社会共同生活的确保为过失损害赔偿责任赋予正当性基础。重大过失(具体轻过失,culpa lata)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属于有认识的过失,且行为人知道行为的危险性和非正当性;行为人客观上制造了巨大的风险(体现为危险转换为损害的盖然性、损害的可能规模),行为人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该过错侵权的发生[21]。在日常生活中被禁止的特定行为在运动中常常是被允许的,甚至在犯规的情况下,也不能必然能推导出有重大过失。这是因为,运动规则不仅不能被等同于法律规则,运动规则经常为其他目的服务,而非仅仅是保护运动员[2]。并非如部分学者所言,仅在遵守运动规则情况下方能阻却违法[22]。虽然如此,但是对运动规则不同程度、不同内容的违反可以成为法律规则违反与否的衡量因素。申言之,竞技性活动通常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可能通过约定、惯例或行业规范形成)进行,行为人对运动规则的反复持续违反、严重违反、恶意违反均可能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进而无法适用自甘冒险规则。总之,在自甘冒险活动中,风险绝非侵权责任的“挡箭牌”,恶意犯规、明显超出犯规的合理范围或者在文体活动中的暴力活动应当被认定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二)向活动组织者主张权利的证明责任
向活动组织者主张侵权责任的举证责任需要按照《民法典》第1198条—1201条的举证规则进行分配。一般而言,受害人需就活动组织者未尽到管理、充分的安全提示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但证明责任的基本理论表明,如果将所有的证明责任均让原告承担,那么事实上任何一个诉讼从一开始就会变得毫无希望。这就等同于使法律取决于义务人的善意,将会发生法的不安全性(Rechtsunsicherheit),这种法的不安全性等同于缺乏任何法律保护,被告通过任意的否认便可使得原告的胜诉成为不可能[23]。因此,对于某些专业性较强的事项之证明需要由经营者、管理者或者活动组织者承担。但是,在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等教育机构遭受人身损害时需要实现举证责任倒置或者采严格责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