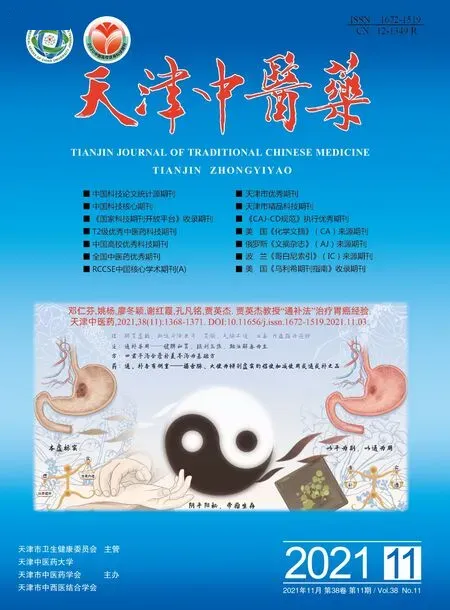张德超老中医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经验
2021-12-02张荣春周宇
张荣春,周宇
(1.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南京 210009;2.江苏省中医院,南京 210029)
张德超老中医,少承家学,后深造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并蒙获中医泰斗岳美中教授亲授,于中医经典著作研习,孜勤不倦。张老从医60余年,临证经验丰富,擅长肝胆病、脾胃病、老年病及疑难杂症,专著有《医道求真录》等。现将其临证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的经验,作初步整理,供阅者参考。
1 慢性病毒性肝炎的病机分析
传统认为,慢性肝炎的湿热疫毒大多留恋气分,只有化燥后才能深入血分;病位由肝入脾,日久伤肾[1]。张老认为慢性病毒性肝炎的病机错综复杂,以湿热疫毒为致病因素;脾胃湿热挟疫毒瘀滞肝络为本病的主导病机;由实致虚、脾肝及肾为其病机发展;湿热疫毒久羁,可因热伤阴血、湿伤阳气,病久及肾而致肝肾阴虚或脾肾阳虚。临床表现出正虚邪实、虚实夹杂、迁延难愈的慢性病程。
肝硬化是慢性肝炎的转归。肝炎病毒长期慢性刺激肝脏,使肝窦内肝星状细胞的活化,胶原等肝组织内细胞外基质成分代谢失衡,生成大于降解,促使肝脏细胞外基质沉积与组织结构重构,形成肝纤维化,进一步发展为肝硬化。张老认为,慢性肝炎久病,湿热疫毒之邪消耗正气,导致正虚瘀结而形成癥积痼疾。肝炎后肝硬化主导病机为气滞、血瘀、痰凝水停及正气亏虚。根据肝硬化的临床表现和病变特点,代偿期多属癥积,为气滞血瘀痰凝而成,主要涉及肝、脾;失代偿期肝硬化腹水,多属鼓胀,为癥积既久,水瘀交阻而成,主要涉及肝、脾、肾。
2 慢性病毒性肝炎的治疗思路
慢性肝炎治宜清热解毒化湿,疏肝利胆化瘀。临证时应处理好气血、脏腑、邪正之间的关系。
2.1 气血关系 因肝脏本身存在体用关系,即肝以阴血为体,而以疏泄为用。如一贯煎用治肝阴不足、肝气郁滞之肝病,其中以生地黄、麦冬等补肝肾之阴,以养肝体,金铃子疏肝理气,以遂肝用,即体现这一原则。郁不解则血难通,血不行则气必滞。张老临证用方降酶退黄时常考虑到湿热蕴于血分,而加入牡丹皮、丹参、赤芍等活血化瘀药及皂角刺、王不留行、丝瓜络等活血通络药。
2.2 脏腑关系 脏腑之间的生理功能常互相联系,而病理变化亦常互相影响。是以临证治病组方遣药时亦须注意及此。如治慢性肝炎肝脾失调证,症见胁肋胀痛,脘痞食少,便溏,脉弦者,常用加味逍遥散,调和肝脾,即守“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旨。治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于应用方中常选用茯苓、白术(常用量为30 g),实脾土以制水,守治肝病防传脾之法,亦即所谓“发于机先”,令其不传之意。又如张老曾治清华大学一名男性研究生,苦于乙型肝炎肝功能反复异常,曾用多种保肝降酶之药乏效。详审证情,每于咽喉疼痛时即加重其发作。依其肺金与肝木相互制约关系,遂于清肝降酶方中加桑叶、杏仁、瓜蒌、贝母、射干、山豆根等药,清金以制木,竟获效机。用药体现肝失疏泄、脾失健运、肺失治节的脏腑病理联系。
2.3 邪正关系 正气虚则毒邪难去,毒邪不去则正气难扶。湿热瘀毒交结,久必耗伤肝阴,损及脾气,表现为正虚毒结的虚实夹杂证。临床上应以清热利湿解毒为基本原则,且“祛邪务尽”。注意湿热伤阴状态,用药必须做到养阴而不滋腻,清化而不苦寒。
概言之,慢性肝炎治疗不单纯针对病毒,要重视整体机能的调整,宜气血并理、脏腑同调、邪正兼治。
3 慢性病毒性肝炎的主辅用方
清代徐灵胎在《兰台轨范》中曰:“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如东汉时期张仲景论治百合病中高度针对心肺阴虚内热这一主导病机的主方是百合地黄汤,辅方有百合知母汤、滑石代赭汤、百合鸡子黄汤等。主病主方有别于一病一方的专病专方,也异于一方可治多病的通治方。
张老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的主方是茵陈蒿汤加味:茵陈 30 g,山栀子 15 g,大黄(后下)6 g,金钱草 15 g,六一散(布包)15 g,车前子(布包)、车前草各 15 g,黄芩 10 g,虎杖 15 g,茯苓 10 g,乃针对慢性肝炎湿热疫毒瘀滞肝络的主导病机与清热解毒化湿、疏肝利胆化瘀的治法而设。辅方有:针对肝血不足、湿热留连兼痰热的当归贝母苦参丸加味[2];慢性肝炎、肝硬化既有脾虚气滞之腹胀,又有湿热水聚之腹水,则用中满分消丸进退[3];重症肝炎、血氨升高之肝昏迷患者,联系《温病条辨》“脾郁发黄,黄极则诸窍为闭,秽浊塞窍者死”之理论,用逐秽凉血解毒之吴又可桃仁承气汤合犀角地黄汤[4]。
对于临床上病毒性肝炎“无症可辨”现象,张老运用《素问·至真要大论》“有者求之,无者求之”思维方法,结合实验室理化检测的异常结果,辨析病机,拟定相关经验方,如慢性活动性肝炎肝功能异常而无明显症状者,用自拟“垂黄降酶汤”;非活动性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携带者,用自拟“养肝解毒丸”。
4 肝炎后肝硬化的治疗策略
肝硬化的治疗在于阻止或逆转肝纤维化,改善患者的肝脏功能与结构,延缓肝硬化及其失代偿期的发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与延长其生存期[5-6]。肝硬化代偿期,病邪尚浅,多以邪实为主,兼有正虚,治宜攻补兼施,根据不同个体的证候表现及邪正盛衰的具体情况,治以疏肝理气、清热利湿、活血化瘀,及健脾、养肝、益肾,并注重软坚散结;肝硬化失代偿期,病程日久,体质虚弱,本虚标实,以虚为主,治宜扶正为要,补益肝脾肾,兼顾祛邪、行气、利水、祛瘀、化痰。高热神昏者,通腑泄热解毒,凉营开窍。张老总结肝硬化治疗原则为“四宜四不宜”:宜柔肝,不宜伐肝;宜调气,不宜破气;宜养血,不宜耗血;宜健脾,不宜伐脾。肝郁脾虚证,常用逍遥散、柴芍六君汤;水湿内停时,合苍牛防己汤、胃苓汤;湿热蕴结者,合茵陈蒿汤、中满分消丸;瘀血阻络者,合膈下逐瘀汤、大黄虫丸;脾肾阳虚者,用方附子理中汤、济生肾气丸;肝肾阴虚者,用方一贯煎;软坚散结,合鳖甲煎丸。介绍几个张老的经验方。
采用SPSS 18.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垂黄降酶汤。主治:慢性活动性肝炎,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升高,或无明显症状者。组成:垂盆草 30 g,田基黄 15 g,黄芩 15 g,黄郁金 15 g,丹参、沙参各15 g,赤芍15 g,牡丹皮8 g,猪苓、茯苓各15 g,山豆根 15 g,蒲公英 30 g,焦三仙各 15 g,鸡内金(杵)6 g。水煎服。慢性肝炎日久见肝阴虚者,合一贯煎。功用:清热化湿散瘀,养肝健脾降酶。
2)养肝解毒丸。主治:非活动性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组成:生黄芪150 g,重楼150 g,黄芩100 g,丹参100 g,北沙参100 g,女贞子100 g,猪苓150 g,太子参150 g,桑寄生100 g,紫花地丁150 g,金银花150 g,炙甘草 60 g,紫草 150 g,虎杖 200 g,板蓝根150 g,夏枯草150 g,白花蛇舌草200 g。共研细粉,以垂盆草200 g,田基黄100 g,煎浓汁加蜜适量为丸。每服10 g,每日2~3次,开水下。功用:养肝扶正,清热解毒。有抗病毒,调整免疫作用。
3)复肝散。主治:肝炎后肝硬变,肝腹水,低蛋白血症,见神疲乏力者。组成:人参30 g,紫河车30 g,炮穿山甲30 g。血瘀甚而腹壁青筋显露者,加参三七30 g。共研为散。每服2 g,每日3次。一方用红参30 g,田三七30 g,紫河车30 g。研粉,制胶囊。每服3 g,每日3次,开水下。功用:益气扶正,化瘀软坚。有升白蛋白作用。
5 典型病案
5.1 病案1 慢性活动性肝炎(肝阴不足,湿热疫毒留连)。患者男性,29岁,1994年4月20日诊。患者罹乙型肝炎3年余。以肝功能反复升高,曾辗转于数家医院诊治,诊断为慢性活动性肝炎,服用联苯双酯、护肝片等药。以其降酶疗效不理想,而来商治。肝功能检查:血清总胆红素(TBIL)48 μmol/L,麝香草酚浊度试验(TTT)6.8 mol/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175 U/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138 U/L,白蛋白球蛋白之比(A/G)47/34。乙型肝炎检测:HBsAg(+),乙型肝炎 E 抗原(HBeAg)(+),核心抗体(抗HBc)(+)。B超示:肝区光点密集,脾稍大,脂肪肝(轻度)。诊得胁肋隐痛,脘胀,纳谷差,肢体乏力,口苦而干,脉象弦细而数。审察证候,揆度病机,证由肝阴不足,湿热疫毒留连为患。治以滋阴养肝、清热化湿解毒。方用垂黄降酶汤合一贯煎:垂盆草30 g,田基黄 15 g,黄芩 15 g,黄郁金 15 g,鬼箭羽15 g,丹参、沙参各 15 g,赤芍 15 g,牡丹皮 8 g,猪苓、茯苓各15 g,女贞子 15 g,熟地黄 15 g,枸杞子10 g,麦冬 10 g,当归 10 g,川楝子 6 g,功劳叶 15 g,制黄精15 g,炙鳖甲(杵,先煎)15 g。煎服,每日1剂。服16剂后,胁肋隐痛、腹胀诸症均减,纳谷亦香,精神亦较前好转。脉象弦细而数,舌苔黄薄。查肝功能:ALT 135 U/L,AST 97 U/L,均下降。患者之精神负担亦较宽松,情绪转佳,复以前方随证略事加减,以胁痛减而去川楝子,并加太子参、褚实子益气阴而养肝。16剂后再诊,前症皆明显好转,但仍不耐劳累,遂以前方加生黄芪15 g,服用40余剂,复查肝功能 3 次均转正常,HbsAg(+),抗 HBe(+),抗HBc(+)。遂以原方小其制,续服2月,并参以饮食调养善后。观察数年,未见肝功能异常。
按语:本案慢性活动性肝炎,虽曾经中西药治疗,而效不显。推究其源,盖由湿热疫毒之邪留连日久、肝阴受损所致。阴愈伤则邪难解,邪愈盛则阴越伤,形成病理之恶性循环。故方以垂盆草、田基黄、鸡骨草、黄芩清热利湿解毒,以降酶降浊,合一贯煎,并加功劳叶、制黄精、炙鳖甲,养阴柔肝疏肝,鬼箭羽、丹参活血疏肝络,以改善肝细胞营养。祛邪与扶正兼顾,治标与治本同施,如是则肝阴得养,湿热毒邪得清,故其获效乃佳。
5.2 病案2 慢性乙型肝炎(湿热蕴毒,瘀滞肝胆)。患者男性,22岁。1993年9月18日初诊,目黄、身黄、小便黄1月余。患者8年前被诊为乙型肝炎。现身目黄色鲜明,小便黄赤,脘部隐痛,口干喜饮,四肢无力,全身皮肤瘙痒,饮食尚可,大便溏而不爽。舌质红,苔薄黄,脉象弦数。查肝功能:TBIL 109.8 μmol/L,TTT 12.8 U/L,ALT>200 U/L,γ-谷氨酰转肽酶(GGT)136 U/L,A/G 45/41。乙型肝炎五项示“大三阳”。尿常规:胆红素(++)。辨证为湿热蕴毒,瘀滞肝胆,胆汁外溢。治以清利湿热,解毒祛瘀。方用茵陈蒿汤加味:茵陈30 g,山栀子15 g,大黄(后下)6 g,金钱草 15 g,六一散(布包)15 g,车前子(布包)、车前草各 15 g,黄芩 10 g,虎杖 15 g,茯苓 10 g。煎服,每日1剂。服方7剂后,仍感乏力、大便已畅但偏溏,遂减大黄,加白术、猪苓、泽泻各10 g,纳食不香加焦山楂、炒麦芽、六神曲各15 g。服至28剂,目黄身黄已退,小便转清,余症亦退,舌质红,苔薄黄腻,脉滑。复查肝功能基本正常。转进清化解毒之剂(白花蛇舌草15 g,蚤休15 g,石见穿15 g,夏枯草15 g,白英 15 g,龙葵 15 g,土茯苓 15 g,猪苓 15 g),以清余邪,服用近1个月,自觉无明显不适,腻苔得退,复查肝功能已转正常。
按语:茵陈蒿汤为治湿热黄疸之经典名方。仲景在《伤寒论》236条云:“阳明病……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饮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在《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中强调“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以及“脾色必黄,瘀热以行”两方面,明确了黄疸的病因是湿邪,病机是“瘀热在里”。“瘀”,积血也,乃血病,实非气郁之“郁”也。诚如唐容川《金匮要略浅注补正》所说:“瘀热以行,一个瘀字,便见黄皆发于血分也,凡气分之热不得称瘀……脾为太阴湿土,主统血,热陷血分,脾湿遏郁乃发黄……故必血分湿热乃发黄也。”由此可见,黄疸之成,由湿热蕴结脾胃,土壅日久则木实,肝胆疏泄不利,导致血行不畅,邪热瘀结肝胆,胆汁不寻常道使然。张老受其启迪,每与清热解毒、活血祛瘀之虎杖或赤芍等味同用,治疗肝炎、胆红素血症,证属湿热瘀结之黄疸,热邪偏盛者,其效尤佳。
5.3 病案3 肝炎后肝硬化(肝肾阴虚,脾虚水困)。
患者男性,47岁。1992年1月13日诊。患乙型肝炎3年余。近半年来因腹胀明显,曾在某院诊断为肝炎后肝硬化,用西药保肝药等治疗,未见明显好转,而来就诊。刻诊:腹部胀大,食后脘腹胀甚,纳谷欠馨,大便偏溏,小便短少,胁肋作痛,口干,咽干,牙龈出血,头昏目眩,手足心热,腰膝酸软,神疲乏力,面色苍黄。舌质红,苔少,脉弦细数。查肝功能:AST 62 U/L,碱性磷酸酶(AKP)17 U/L,GGT 110 U/L,白蛋白(ALB)28 g/L,球蛋白(GLB)30 g/L。乙型肝炎五项:HBsAg(+),抗乙肝核心抗原(HBcAg)(+),抗 HBeAg(+)。B 超示:肝硬化,脾肿大(肋下78 mm),腹水(液性暗区25 mm)。证属肝肾阴虚,脾虚水困。治以滋养肝肾,实土制水。方用一贯煎合苍牛防己汤(方药中验方)加味。处方:生地 10 g,北沙参 15 g,丹参 15 g,枸杞子 10 g,麦冬10 g,当归10 g,川楝子 6 g,苍术、白术各 15 g,川牛膝、怀牛膝各15 g,防己15 g,大腹皮15 g。7剂,每日1剂,煎服。并辅以乌鱼与大蒜瓣煮汤食疗(《本经逢原》记载鳢鱼治水肿腹大之方法)。复诊,齿衄未作,口咽干燥减轻,仍腹胀、胁痛,加厚朴10 g,香附10 g,郁金10 g,服至30剂,腹胀胁痛诸症消失,纳可,大便成形,精神亦渐转佳。复查肝功已恢复正常,B超未见液性暗区。考虑毒邪渐清,而正气亏虚,免疫功能低下,转以复肝散(自拟方:红参30 g,田三七粉30 g,紫河车100 g,共研粉,每服3 g,每日3次)养肝益气、活血化瘀,合乌鸡白凤丸补气养血,以善其后。
按语:本案肝硬化腹水,证由肝病延久,肝肾阴虚,木失条达,木邪乘土,脾气虚败,不能制水,而致水湿之邪困阻中焦所致。是以肝脾肾之正虚为本,水邪之恣肆为标,证属本虚标实,治疗颇为棘手。若徒滋阴则碍脾湿,徒治水则伤肝肾之阴,故方选一贯煎以滋肝肾之阴而遂木之条达之性;合以苍牛防己汤健运脾土而制水邪之泛滥。肝脾肾三脏同调,标本虚实兼冶。善后之复肝散,功能益气扶正,活血化瘀,实为治本之图。方中应用紫河车、乌鸡血肉有情之品意在调整肝脏功能、提升白蛋白。
6 小结
张老根据慢性病毒性肝炎的病因病机和缠绵难愈、易于反复的特点,强调扶正解毒以调整免疫功能、清除或抑制病毒而治本;久病在血分者尤多,治疗本病以活血化瘀为要;观察整个病程中存在着肝郁脾虚的病机机转,临证紧抓肝脾虚实补泻。主病主方、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合理运用中医药治疗,以致改善临床症状,减少抗病毒药物(核苷类似物)耐药率,提高抗病毒疗效,减轻肝细胞炎症坏死及肝纤维化,减少和防止肝脏失代偿、肝硬化等并发症的发生,是慢性病毒性肝炎的治疗目标。
张老提出的慢性病毒性肝炎的“血分湿热毒瘀与由脾入肝伤肾”的病机观,突破了“湿热疫毒由气化燥入血与由肝伤脾及肾”的传统观念;“气血并理、脏腑同调、邪正兼治”的治疗观,也有别于气血分治、脏腑偏治、解毒唯上的常规治法;主方结合辅方的处方观及自拟“垂黄降酶汤”“养肝解毒丸”“复肝散”等验方,显示出常法与变法的用方特色。张老对于肝炎后肝硬化代偿期、失代偿期分别从“气血痰虚”“气血水虚”的治疗策略与“四宜四不宜”的治疗原则,均具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