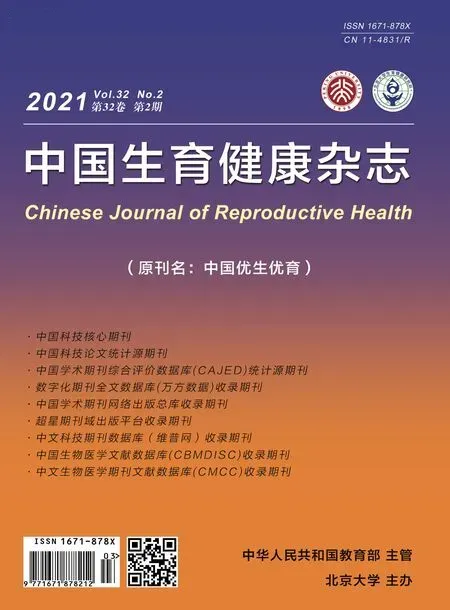环境内分泌干扰物-双酚A与女性生殖健康关系的研究进展
2021-12-02王璐鹿群王斌
王璐 鹿群 王斌
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人类健康与环境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然而,研究表明[1],天然物及合成物(如水、空气、食物、消费品等)中的化学物质-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EDCs) 可通过触发不同的分子通路,干扰人体内源激素的合成、分泌、运输、结合及代谢过程,导致机体生殖、神经、免疫等系统内分泌功能受损,影响机体稳态及自我调控能力,从而对生物体或其子代健康造成潜在危害。已有近800种EDCs被发现是全球范围内肥胖、代谢紊乱、不孕、内分泌疾病、糖尿病和激素依赖性癌症等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1-2]。目前,对EDCs的相关研究已成为生殖医学、环境卫生学、生物学等领域的热点。通常,EDCs要么是持久性的,在组织中堆积(如有机氯化合物);要么是非持久性的,在体内快速代谢和排泄,如双酚A(bisphenol A,BPA)、邻苯二甲酸盐等[1]。近年来,有关非持久性EDCs与人类生殖健康关系的文献报道逐渐增多,本文现就其中研究较多的双酚A对女性生殖健康影响的相关内容进行综述。
一、BPA简介
BPA是一种苯酚,其分子式为(CH3)2C(C6H4OH)2或 C15H16O2,化学名称为4,4 ′ -二羟基-2,2-二苯基丙烷[3]。19世纪90年代,BPA首次被用于雌激素合成;20世纪30年代,研究发现BPA在雌性大鼠生殖系统内具有雌激素功效[3]。随后,作为聚合物(如聚碳酸酯和环氧树脂)的单体、阻燃剂合成的前驱体、聚氯乙烯聚合末端的抗氧剂和缓蚀剂,BPA被广泛用于许多日用品和医疗耗材中(如重复使用的塑料瓶、奶瓶、食品和饮料罐的内部涂层、医疗设备、商品收据、牙科密封剂等)。如同其他化学物质,BPA随温度和pH值的变化可迁移到食物、空气等中,人们主要通过饮食(超过90%)、吸入灰尘、牙科手术和皮肤接触等(低于5%)途径暴露于BPA[4]。BPA的预期生物半衰期约为6 h,可以葡萄糖醛酸苷或硫酸盐结合物的形式从尿液排出体外[3]。尽管如此,BPA还是会经历结合-解离循环,在组织中积累很长一段时间,导致部分BPA的排泄延迟。BPA暴露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不易被察觉且具有慢性毒性效应,几乎所有成人和儿童的尿液、孕妇血清、母乳、滤泡和羊水、脐带血和胎盘组织中均可检测到BPA[1-5]。人类对BPA的可接受剂量为≤50 μg /kg/d[6]。欧洲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指出[6],目前的BPA暴露水平可能对人群并无风险。然而,有科学家却认为,这一BPA水平可能已经对成人健康造成危害,且由于胎儿药物代谢系统尚未成熟,即使是微量暴露,也可能使之更容易受到BPA的不良影响;甚至有时低剂量比高剂量造成的影响更明显[7-8]。
二、BPA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
由于很难用常规方法对人体BPA等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进行筛查和检测,以往很多学者主要是通过动物实验及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对其与女性生殖健康关系进行分析探讨,结果虽不尽相同,但很多研究提示,BPA与不孕症、自然流产、早产,多囊卵巢综合征及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疾病有关[9-27]。
1. BPA与不孕症:研究显示[9-12],BPA与不孕症密切相关。Caserta等[9]对不孕症妇女与有生育能力妇女不同EDCs暴露量开展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不孕症妇女的血清BPA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而其他EDCs暴露量在两者间没有差异。故认为高BPA暴露可能与女性不孕症的发生有关;且与其他化学暴露物相比,BPA与女性不孕症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其中吸入和(或)吸收的BPA可能是通过干扰排卵和干扰减数分裂、诱导卵母细胞染色体畸变等途径影响卵母细胞质量,进而影响女性生殖系统功能[6-7]。Mok-Lin等[10]对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性的研究发现,较高的尿总BPA与卵巢低反应(每个周期的获卵量减少、E2水平低)呈显著相关。Ehrlich等[11]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较高的尿BPA与卵母细胞成熟度下降、卵母细胞受精率下降均相关;且与第五天囊胚形成率减少有关;尿BPA较高的女性胚胎种植失败率较高。Bloom等[12]的研究亦显示,女性较高的血清BPA与血清总雌二醇(estradiol,E2)、甚至每个成熟卵泡的较低E2水平呈负相关。与前两个研究[9-11]不同的是,Bloom等[12]并未发现BPA与每个周期的获卵数有关。以上研究提示血清和尿液中较高的BPA水平可能与E2水平降低及卵母细胞成熟度下降、卵巢反应差和胚胎着床率下降相关。
2.BPA与复发性自然流产(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RSA):有关BPA暴露与RSA关系的研究报道很少。Sugiura等[13]对日本同一地区45例连续3至11次RSA女性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RSA组血清总BPA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进一步分析了其中13个妇女流产的胚胎核型,发现胚胎异常的女性有更高BPA的趋势。在随后成功怀孕至分娩的流产患者中,血清BPA呈下降趋势,但并不显著。虽然该项研究的样本量很小,但研究结果提示RSA与BPA暴露之间存在关联。BPA暴露是否引起减数分裂过程中卵母细胞染色体畸变增加,从而导致RSA的发生尚需更多研究证实。
3.BPA与早产:Cantonwine等[14]收集了60例墨西哥妇女怀孕后期的尿液样本,对其尿样中BPA与妊娠时间(孕周)关系的分析结果显示,尽管受试者分类样本量很小(N=12),但总BPA升高与早产(< 37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为了增加样本量,研究者将37周分娩的病例也列入早产组再次分析,结果发现二者间亦存在相关的趋势;提示BPA暴露与早产有关。但此结果在其他学者[15]的相关研究中却并未被验证,研究结果均显示BPA暴露与妊娠期长短无关。由于样本量小且相关研究报道很少,因此,BPA与早产是否有关尚待更多研究证实。
4.BPA与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PCOS):近年来,许多研究[16-23]将成人女性的BPA暴露与PCOS的发生联系在一起。研究发现[16],与非PCOS女性相比,PCOS女性的总血清BPA暴露量明显增高。无论对照组还是PCOS患者组,较高的血清BPA与总睾酮(testosterone,T)、游离睾酮、促黄体激素、雄烯二酮和硫酸脱氢表雄酮浓度升高间存在显著正相关[16-21]。随后,Tarantino等[22]研究发现,绝经前PCOS女性的总血清BPA显著高于对照组。血清BPA高于0.45 μg / L的PCOS女性T浓度也增加。近期Leyla等[23]对土耳其112名青春期PCOS患者研究亦发现了类似成年女性的结果。进一步将该研究结果与以往结果比较发现[16-18],BPA与高雄激素血症的相关性在青春期女性似乎比成年女性群体更强,故认为BPA可能在青春期PCOS发病机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雄激素升高是PCOS的主要特征,且与BPA增加有关,故BPA、PCOS及雄激素间的关联无法归因于任一因素。一方面,BPA可通过调节甾体激素生成关键酶的表达,刺激卵巢泡膜细胞促进雄激素的合成,并抑制T分解代谢,从而导致T浓度的增加[6-7]。另一方面,高浓度的T亦可能下调参与血液循环中BPA代谢和清除的关键酶——尿苷二磷酸-葡萄糖醛酸转移酶的活性,使BPA水平进一步增高[17]。因此,目前尚不清楚是BPA通过使雄激素水平增高、导致PCOS发生,还是PCOS患者自身较高的T反过来导致BPA浓度增加。因此,通过观察动物和人体产前BPA暴露与女性PCOS发生间的关系,来确定子宫内或早期发育阶段暴露于BPA在PCOS发病中起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5.BPA与子宫内膜异位症:Itoh等[24]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病变程度与BPA关系进行了研究,提示较高的尿总BPA与重度子宫内膜异位症呈正相关,但通过尿肌酐调整后再次分析,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与BPA无关。与之不同的是,Cobellis等[25]对58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血清BPA总量显著高于对照组,高BPA暴露的妇女患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风险明显增高,故认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与BPA暴露有关。小鼠实验模型的研究支持了该结果,小鼠宫内暴露于BPA会产生类似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成年子宫表型[14],为上述文献提供了依据[19]。
6.BPA与子宫内膜病变:成年女性的子宫内膜病变与BPA暴露的关系目前尚不明确。Hiroi等[26]对子宫内膜病变患者(包括单纯、复杂、不典型子宫内膜增生及子宫内膜癌)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显示,与单纯子宫内膜增生患者相比,复杂子宫内膜增生患者的血清BPA显着降低;同时,子宫内膜癌患者的血清BPA也显著低于单纯子宫内膜增生的患者和对照组。说明BPA与子宫内膜增生和子宫内膜癌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但对其间为何存在这种负相关关系尚无法解释。
三、BPA对女性生殖系统影响的作用机制
人类接触BPA的敏感窗口期包括配子、胚胎形成和胎儿发育期、婴儿期、童年和青春期及妊娠期,许多不良围产期、儿童期和成人健康结局与其在这些时期的BPA暴露有关[8]。机体稳定的内源性激素含量是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及免疫系统发挥正常功能所必须的。BPA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触发多种作用机制,干扰内源性激素的动态平衡,对女性生殖系统造成负面影响[6-7,9-11,15,27-30]。
1. 受体介导途径:BPA通过干扰激素反应通路,导致一系列生殖功能障碍(如卵巢功能紊乱、PCOS、子宫内膜异位症等)[6]。一方面,BPA的分子结构特征使其具有“弱”雌激素效应,可与两种核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亚型(ERα和ERβ)结合,形成受体-配体复合物,再通过与雌激素反应元件特异性结合,激活环磷酸腺苷等一系列激素依赖性信号通路,活化受体-配体复合物,调控有关细胞生长和发育的靶基因表达[6]。另一方面,BPA具有抗雌激素作用,通过与内源性E2竞争,阻断雌激素反应[7]。此外,BPA可与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AR)结合,并作为雄激素拮抗剂阻断内源性雄激素的作用,进而影响激素信号在靶细胞、组织和器官的传递,产生相应的生物学效应[6]。BPA亦可与其它受体如孕烷X受体(pregnane X receptor,PXR)、芳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AhR)、甲状腺受体等结合发挥激动或拮抗作用,造成机体生殖系统等功能失调[6-7]。
2.非受体介导途径:BPA可通过干扰内源性激素及其受体的合成、代谢和运输等非受体介导途径,或干扰激素合成和代谢过程中涉及的酶途径,对激素的生物利用度进行调节,从而影响内分泌功能[6]。雄激素通过芳香化酶作用产生雌激素,雌/雄激素的相对平衡对维持机体正常生殖功能具有重要作用。BPA可通过干扰芳香化酶的活性来破坏雌/雄激素的平衡状态,导致生殖系统功能紊乱而致病。BPA也可通过作用于性激素结合球蛋白、血浆激素结合蛋白,干扰内源性激素的活性而发挥作用。此外,BPA还可通过抑制类固醇激素相关酶的活性(如调节女性生殖组织中的类固醇生成酶等),延长内源性激素半衰期或通过增加17-α羟化酶、胆固醇侧链裂解酶等关键细胞色素P450甾体生成酶的表达影响卵巢类固醇的生成,进而破坏卵泡内环境,影响卵母细胞的成熟,导致不孕[6-7]。
3.下丘脑-垂体-卵巢轴:BPA对生殖内分泌系统的影响可发生在大脑水平,通过间接或直接影响下丘脑-垂体-卵巢轴(hypothalamic-pituitary-ovary,HPO)干扰性腺和配子的功能,降低生育能力[27-29]。Fernández等[27]研究发现,暴露于500 μg /kg/d BPA的大鼠,其HPO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最终停止排卵而不孕。其潜在的机制可能与神经激肽B和/或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onadotropin release hormone,GnRH)有关。神经激肽B被广泛认为是青春期HPO轴的基本激活因子,亦可促进下丘脑合成GnRH[29]。研究表明[29],BPA可通过抑制神经激肽B的合成,阻断下丘脑GnRH的释放,间接引起HPO轴功能失调;或者BPA可通过作用于下丘脑,降低 GnRH的分泌,直接影响HPO轴的功能,进而减少卵巢类固醇的生成,抑制排卵而导致不孕[29]。然而,BPA通过神经激肽B和GnRH对HPO轴产生的生物学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在各环节对女性生育能力的相对重要性目前仍不清楚。研究者推测,BPA通过HPO轴影响女性生殖的主要靶点可能是下丘脑和垂体,而不是卵巢本身[29]。
4.基因表达和表观遗传学修饰:研究证实,BPA可通过直接影响生殖系统发育相关基因(如ER、AR等基因)的表达,干扰激素反应途径或类固醇生成,进而影响女性生殖功能[9,30]。例如,Caserta等[9]对111名18~40岁原发性不孕症女性的研究表明,BPA暴露水平与ERα和ERβ、AR、PXR、AhR基因表达量呈正相关。
BPA亦可通过影响生殖系统发育相关基因表观遗传学修饰(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乙酰化和微小RNA等),改变表观基因组的表达影响女性生殖系统的功能[9,30]。Hanna等[30]对瑞典女性IVF患者的横断面研究发现,全血中较高的血清BPA与TSP50基因启动子区137位CG二核苷酸的低甲基化显著相关,提示BPA通过对TSP50基因的甲基化修饰上调了其表达水平。但TSP50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最终如何对女性生殖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目前尚不清楚。
5.卵母细胞发育和卵巢功能:流行病学研究表明[10-11],尿BPA的浓度与卵母细胞发育异常有关。卵母细胞发育始于胎儿期原始生殖细胞减数分裂、卵泡的形成,生育期卵母细胞的生长和减数分裂的恢复等关键阶段。对啮齿、灵长类动物及人类胎儿卵母细胞的体外研究发现,这些阶段很容易受到BPA的影响,致使卵泡形成及生长受损、纺锤体和染色体异常、胚胎发育异常,包括卵母细胞和胚胎的表观遗传变异,最终导致胚胎种植失败[6-7]。
卵巢被认为是EDCs作用的主要靶器官之一。研究表明[11,15],始基卵泡、窦前卵泡和窦卵泡(即激素反应性卵泡)暴露于BPA中,会诱导减数分裂畸变(如染色体非整倍体增加),卵泡破坏,降低窦前卵泡计数及卵母细胞存活率,卵巢储备功能下降,最终导致不孕。
四、未来研究的启示和展望
过去几十年里,关于BPA等EDCs与人类生殖关系的相关研究报道虽迅速增加,但人类暴露于BPA后对生殖健康不良影响的直接数据依然有限。
由于BPA与女性生殖健康间的关系涉及众多学科领域、受多种混杂因素干扰,需要通过大规模、多种族(民族)、跨学科、多地点的长期研究来完成,且化合物生物半衰期短,故在缺乏密集和频繁暴露样本的情况下,其影响很难通过单一而短时的研究来确定。为了在这一领域获得更多专一和更好的研究结果,建议对BPA与女性生殖健康相关性的研究应尝试[1,3,6,29]:(1)采用同一方法,收集不同社会、经济、地域等不同样本,提高结果的普遍性和实用性;(2)获得不同群体的多个尿样,以更好地显示持续接触对不同群体的影响;(3)分别评价混合物及个别化学品的作用,筛选适于研究EDCs与不良生殖健康结局关系的有效标记物;(4)同时关注女性和男性的暴露,交叉研究数据的融合可用来增加探测环境暴露微妙影响;(5)确保充分控制混杂物,包括其他化学品的接触;(6)纳入不断发展的“组学”技术(如基因组学、表观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等),以加强暴露组的暴露评估(即终生暴露程度的总和),并提供基于生物学的个人风险评估;(7)进一步通过人体研究阐明BPA暴露对女性生殖健康的影响及其影响的生理机制。
不同研究对BPA与女性生殖健康关系的结果虽不尽一致,但新的科学和临床数据越来越多地表明,接触BPA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生育能力,尤其是对发育期和敏感人群有重大影响。国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将BPA称为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化学物质”,且在奶瓶和吸管杯中禁止使用BPA。由于人一生中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EDCs接触,因此,对于每一个女性个体来说要提倡生活方式改变,如通过减少使用含有BPA等EDCs的个人护理产品、生活用品等,有效降低这些化学物质在体内的含量。对社会群体来说,应高度重视整个地球的环境保护,更好地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致力于对此方面的深入研究,提高个体保健和人口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