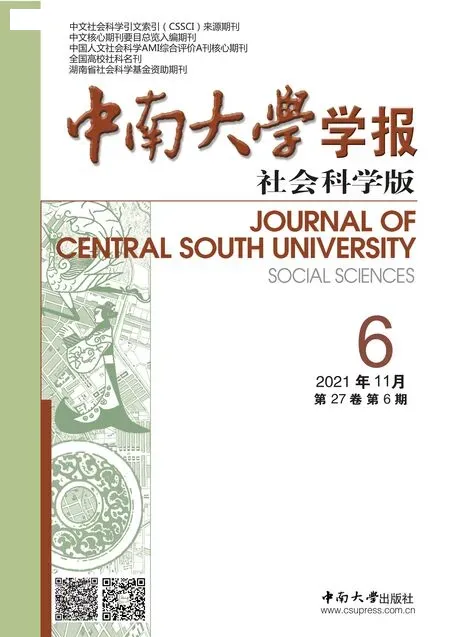康德论“道德狂热”
2021-11-30费尚军
费尚军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江西南昌,330031)
一、人性“妄想”与“道德狂热”
哲学家们一直秉持着人兽之别的古老信条,并从中区别出人性的价值和意义。在赫拉克利特关于兽性、人性与神性的叙述中,就指明了人性的弱点和局限性,但也让我们明确了人类追求卓越和完善理想的必要和可能。对柏拉图而言,在二元世界图像中也对应着二元人性的理解。当灵魂寄居于肉体之中而产生本能的负累时,“由于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它通常使用快乐作诱饵进行捕捉,使人相信它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2](341)。人类普遍受到欲望的驱使,甚至在本能欲求的满足中变得疯狂。因此,我们必须克制欲望的生长和盲动,从追求所谓的快乐转向追求善,“我们必须试着用三种最高的事物——畏惧心、法律、真正的谈话——来检查和制裁它们”[3](540),从而以理性去控制那未受约束的欲望,避免陷入无止境的悲哀。显然,柏拉图也是在确认人性的本能属性及其扩张限度的同时,诉诸人类理性,通过外在的强制和内生性的理性自觉,使人性得到教化、灵魂得到改善。康德表现出对古希腊道德哲学的某种拒斥而努力建构其批判哲学,在对人性的二重属性的殊分中去区别人之善恶的根基与意义。一方面,“人就他属于感官世界而言是一个有需求的存在者,在这个范围内,他的理性当然有一个不可拒绝的感性方面的任务,要照顾到自己的利益”[4](84)。一个人属于感觉的世界,如同动物的生命一样,自然有其本能的欲求和需要。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作为感觉的生命存在,因为人具有理性。如果这种理性的作用,只是为了像动物的本能一样照顾自身的需要、利益和为自己服务的话,“那么他具有理性就根本没有将他在价值方面提高到超出单纯动物性之上;这样理性就会只是自然用来装备人以达到它给动物所规定的同一个目的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而并不给他规定一个更高的目的”[4](84)。人按照自然对他做出的这种安排,固然需要理性来照顾他的需要,但是,说人具有理性,是因为理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即什么就自身而言是善的或恶的。这却是纯粹的理性、不受感性利益影响的理性所独自做出的判断,并且要把这一种评判与对感性利益或福祸的判断区分开来,使之成为后一种评判的至上条件。
康德强调了道德上的善恶评判作为纯粹的理性所做出的判断,不仅不受任何感性利益和需要的影响,也是一个人应当享有幸福的至上条件。人虽然作为自然存在者具有某种“动物性”,但同时作为自由的存在者,因其具有“自由的本性”而在为善避恶中提高自身的价值,并使之超越于动物性之上。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在对人性二重性的区分中去明确善恶,以及由此断定人性的自然本能和冲动所具有的善恶意义。因为善与恶的概念,只能是就人作为自由的存在者所具有的自由选择的意志规定根据而言的。康德认为,要廓清哲学家们在道德原则方面一切失误的起因,首先,需要追问最初何以区分出善恶概念,是先有善恶概念而后有道德的法则,还是与之相反。如果我们马虎假定各种原则,尤其是断定意志只有经验性的规定根据,并且从某一对象的欲求中来区分所谓的善,那么,“善或恶的标准就只有可能建立在对象与我们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的一致之中了”[4](86)。正是这种次序上的颠倒,人们努力在幸福中,或是在完善中,或是在道德情感以及上帝与神的意志中,来搜寻特定满意的对象,当作法则而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然而,绝对的善与恶,并不是对象对于人的感觉状态,抑或根据对象给人带来的快乐或痛苦区分出来,而只是对于人的意志或行动的支配性规则而言。其次,善和恶的概念必定不是先于道德法则的,而是在道德法则之后或凭借道德法则才得以被规定的。无需考虑欲望的可能对象,而仅仅凭借准则的纯粹立法形式来直接规定意志,这意志就是绝对的圆满的善,并且是一切善行的至上条件。由此,也就需要在肯定意志行为包含“法则”精神而具有“道德性”的同时,区分出那只是“符合”法则而徒具“合法性”的行为,因而行为的客观规定根据必然要求一种切实作用于主体的主观性的动机与力量。最后,如果说道德法则自为地和直接地成为意志的规定根据是全部道德性的本质所在,那么我们既不能寻求任何舍弃道德法则的其他动机而导致“伪善”,也不能让其他动机(如利益动机)一起与道德法则起作用而陷入危险。要让道德法则促动意志,也就需要阐明其作为意志规定根据或动机对人类欲求能力的作用。这也体现在作为受道德法则支配的自由意志上,不但不需要感性冲动的协作,甚至要全部加以拒绝,抑制和防范凡是对法则有对抗或违背的一切性好冲动。由此,就通过自身立法理性而产生对本性冲动的一种道德强制,也就是义务。
如果说一切先于道德法则而呈现为意志对象的东西都将排除在意志的决定根据之外,而把准则普遍化的实践的立法形式本身作为自在的善和绝对的善的唯一根据,那么在康德看来,基于人性而首先容易产生的一种“妄想”或错觉就是,当发现我们本性作为感性的存在者对于所欲望的事物,不论是希望还是恐惧,总是不由自主地抢先呈现于我们面前。这种受本能决定的自我,虽然完全不适用于普遍的立法,却仿佛造就了我们“整个的自我”致力于首先提出它的要求,并且使自我真以为是首位的要求。正是这样一种嗜好,使我们将选择上的主观规定根据作为一般意志的客观规定根据,并自认为具有立法性,进而“冒充”为一项无条件的实践原则,这也就是一种“自负”(自大)。与此同时,如果说道德价值必然只在于行为出于义务而发生,即纯粹只是为了法则之故而发生,那么义务的观念的客观要求,就是行为必须与法则相一致。而主观的要求,则体现为行为的准则对法则的敬重,且作为决定意志的唯一方式。然而,出于爱人之故抑或出于同情的好意对他人行善,以及因社会秩序之故而主持正义,在对这些确乎“美好”事情的确认中,“我们自以为能够仿佛像一个见习生那样凭借高傲的想象而置义务的观念于不顾”[4](112),好像可以不受任何命令所驱迫,完全由自己愉悦的心情决定而做着自己想做且无需遵奉任何命令的事情。但是,康德认为,这也是由于错误估量我们作为被造物的卑微地位,“妄想”推倒道德法则的尊严,并对之加以自大的拒绝。还存在着另一种人性的“妄想”,就是我们也幻想着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主体,能够达到与道德法则完满的契合一致,完全摆脱来自感性的欲望和冲动,从而达到一个神圣性的道德理想。不用敬重道德法则和对义务服从,就能宛若神明,“我们就能像那超越于一切依赖性之上的神性一样自发地、仿佛是通过一种成为我们的本性而永远不会动摇的意志与纯粹德性法则之间的协调一致”[4](112)。实际上,人作为被造物所能处的道德状态,就是要不断与本能冲动作斗争。倘若“妄想”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能够在意志本性上拥有一种完全纯洁的神圣性,就完全是“道德上的狂热和自大的膨胀”[4](116)。它使人们的心灵置于这样一种幻想之中,在抛却义务和对道德法则敬重的同时,不再听其检束而感到谦卑,却能蒙受高贵和崇高的美名。
二、有限性的“忘却”与“道德狂热”的根由
正如康德所言:“如果最广泛意义上的狂热就是按照原理来进行的对人类理性界限的跨越,那么道德狂热就是对人类的实践的纯粹理性所建立的界限的这种跨越。”[4](117)如果说我们要遏制或尽可能预防在对上帝的爱这方面的宗教狂热,那么同样也要遏制或预防那感染着许多人头脑的单纯的道德狂热。康德认为,一般言情小说家或情感教育家,有时甚至是最严肃的哲学家,都曾被诱入道德狂热的境地。当人们让善行脱离义务的管束,热衷于虚幻的道德完满性而陷入狂热之中,就会无视自己的界限而沉溺于自爱和自负之中,失却了法则义务为其所设立的谦卑限制,也就没有了自知之明。同时,也产生了这样一种轻浮的、粗俗和幻想的思维方式,就是自以为自己的心灵有一种自愿的驯服,似乎他们的心灵既不需要鞭策,也不需要管束,甚至一个命令也是不必要的。实际上,康德的学说基于人的理性和自由来为道德奠基,迎合了时代的需要。他强调人为自身立法而张扬人的自由和主体性,以及对道德原则的确证,与他对道德主体作为有限存在者的弱点和局限性的认识深度契合。在他看来,脱离义务观念而为人们所幻想的完满境界终将彻底损害人类的道德。究其根由,在于完全无视道德主体的有限性。可以说,正是人们“忘却”了这种“有限性”给人类的道德追求及其所能达到的等级设立的界限,成为产生“道德狂热”的最重要的根源。康德认为,人类的实践的纯粹理性所建立的界限,就在于禁止把正确的行为的根据建立在任何别的东西之上,而只能建立在道德法则本身之中,并由此产生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因此,我们也就要把义务观念认作是人生一切道德性的至上的生活原则。正是这种义务观念,既中止和抑阻一切傲慢和虚荣的自爱,也消除和打倒一切自负(狂妄自大)。
对大多数启蒙道德哲学家而言,也许一个重要的理论事实就是,不是首先去考察“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考察一个“像人这样如此软弱和不完美的生灵”,将会提出和接受道德上赞许或非难的原则[1](94)。“在人身上一切善都是有缺陷的。”[4](105)对康德而言,首先,人作为道德主体的有限性体现在人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尽管人们是在与自己的第二重世界(理智世界)及最高使命的关系中来看待自己的本质的,但是同时也意识到,作为感性世界中的存有,人也有着与此相结合的病理学上的感触性和依赖性。因为人既然作为被造物,就他为完全满足自己的状况所需要的东西而言,也就并非是完全独立自足的,而是始终依赖着为得到完全满足所必需的东西,由此,也就不能超脱诸种欲望和性好。这些东西基于身体的原因,不会自发地与具有完全不同来源的道德法则相符合,有限存在者的理性并不必然按其本性就符合客观法则。而所有的性好一起构成的“自私”,要么表现为一种对自身过度钟爱的“自私”,要么是一种对自己感到满意的“自负”。如果说后者需要“完全消除”,那么前者自然地存在并先于道德法则而活动于我们的内心之中,只能加以“限制”,使之与道德法则不相违背。其次,即使是对道德法则表示的敬重而言,由于其并不能被赋予那超越感性冲动的至高的存在者,也就预示了敬重主体所具有的感觉性(即有限性)。“向着道德性的动机观念只有针对有限的理性行为者,例如我们自身这些处于野兽和诸神之间的人来说,才是合适的。”[5](177)动机、兴趣和准则的概念,都是以有限存在者的本性的某种限制性为前提条件的,由于假定了有限者有某种内在的障碍与其作对,也就不得不依赖于某种驱遣动力。最后,尽管被造物始终有必要将准则的意向建立在道德的强迫之上,但是即使法则自动进入内心,赢得的也往往是“不情愿的尊敬”。基于性好的情感、意志和准则,亦常常与之相抵制。“人还不够神圣,他们虽然承认道德法则的威望本身,也可能会一时感到违背它的愉快。”[6](392)同时,服从法则之所以是“命令”,也在于其要求人们去做的,往往是他们不乐意去做的,“因为一个要人们应当乐意做某件事的命令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当我们已经自发地知道我们有责任做什么时,如果我们此外还意识到自己乐意这样做,对此下一个命令就会完全是不必要的了”[4](114)。假如理性被造物有朝一日能做到完全乐意地去执行一切道德法则,那么就意味着在他心里甚至连诱惑其偏离法则的某种欲望的可能性都没有。然而可惜的是,世间没有一个被造物能达到这样一种道德志向的境界。
倘若“忘却”道德主体的有限性,那么也会对“至善”在实践上如何可能陷入某种谬误和“狂热”。在康德看来,至善概念既包含 “至上的善”(德行),也包含实现“完满的善”所要求的幸福。然而,对这两个要素的关系及其联结的实践可能性的解释,却一直陷入某种错误而未能成功。当人们把对幸福的欲求看作德行准则的动机,进而确立为最高的原则时,也就把从个人爱好而来的准则普遍化,并偷换成为“法则”。这贬低了他们的至善及期待的幸福,只是通过个人理智而达到的对性好的控制和节制所能达到的界限。这样的幸福是可怜的。当把德行的准则看作必须是对幸福起作用的原因时,因为把对个人幸福的欲求排除在意志的规定根据之外,这似乎正确选择了他们的至上的实践原则。但是,又“妄想”在今生此世,人们通过严格遵守道德律而达到至善,甚至陷入“道德的狂热”。因为他们不仅把人的道德能力张扬到超越其本性的一切限制的高度,而且在否认幸福作为至善要素的同时,使之所设想的理想人格能“宛如神祇”,“通过意识到自己人格的杰出性而完全独立于自然(在他的满足方面)”[4](174)。在康德看来,这种幻想着的玄妙境界,既是自欺,也是错误地估计了人的本性及道德使命的结果。他认为,实现至善是一个通过道德法则来规定意志的必然目标,必须要实现心灵与道德法则的完全契合。然而,要做到意志与道德法则完美匹配,非神圣性不可,但在感官世界中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其存有的任何时刻都不能达到这样一种完满性。由于这样一个目标在实践上是必然的要求,所以这只能在一个无限的进程当中得以实现。如果不能确立这一正确的实践原理,那么道德法则就会被完全夺去它的神圣性而流于放纵,或者我们便会热衷于通过使命与期望来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从而企图希望获得意志的完全的神圣性,“迷失在狂热的、与自我认识完全相矛盾的神智学的梦呓之中”[4](168)。因此,基于道德主体的有限性,需要某种无限持续的生存和人格的前提来持续这无限的进程,才能实现与道德法则的完全切合。而灵魂不朽的悬设,就是由这样一个实践必要条件而来。同时,道德法则是自由的法则,但却没有丝毫的根据说道德和人生幸福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这也体现了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至善的可能性上的“无能”。“这个存在者正因此而不能通过他的意志而成为这个自然的原因,也不能出于自己的力量使自然就涉及他的幸福而言与他的实践原理完全相一致。”[4](171)所以,至善在尘世中的可能,就唯有假定存在着一个具有与道德意向相符合的最高主体才可以,这也就是上帝实存的悬设。可以说,正是由于道德主体的这种彻底的有限性,使之成为一种道德上的“需要”。从道德法则给予我们的目标以及随之而来的实践意图的要求来说,就是“信仰”。
三、“狂热”抑制与“崇高”使命
作为伦理学的创立者,亚里士多德着力标举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在于对善恶观念的辨认。“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7](9),人类通过成就德性以彰显自身的卓越和高贵。与亚里士多德把德性设定为某种适度而获得道德赞许的原理不同,康德明确反对从遵从某些准则的程度中去寻求德性与恶习的区别。康德认为,唯有先奠定道德法则,而后才能区分绝对的善恶。德性就是遵从法则和义务而行动的意志和力量,唯有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感性的情感和欲望的对象,才是真正的道德动机。因此,人类所能达到的道德等级层次,就是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而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所能达到的“最大的道德完善”,就是“尽自己的义务,确切地说是出自义务而尽义务”[6](405)。法则不仅是行为客观有效的决定根据,也应是行为主观意志的决定原则抑或动机。对康德而言,正是出于法则义务及其产生的敬重,让人们能够在自明谦卑的同时,也追求着崇高,并得以正确地防范各种形式的“道德狂热”。因为敬重感所起的作用,既能够让我们防范把任何基于性好的感性情感“冒充”为普遍法则,或“偷换”成理性情感的狂热,从而让我们在与追求物欲和快意生活目的的比照中,保持和尊重人性自身的尊严和价值,也能够让我们避免因脱离人类本性的有限性而完全痴迷于某种完美的道德境界和理想的人格范型。就道德法则及其产生的敬重感对于“狂热”的抑制作用而言,也首先体现在其“否定性”的贬抑作用上。要真正实现法则的“精神”,避免只是遵守“条文”要求行为的客观法则,必须同时成为作用于主体欲求而规定意志的主观动机。由于有限存在者的一切感性冲动,都是建立在某种快乐或不快乐的情感基础上的,对其产生作用的也不外乎是“情感”,“道德律通过把爱好和使爱好成为至上实践条件的这种偏好、也就是把自爱排除在任何参与至上立法的活动之外,而能够对情感发生作用”[4](102)。它不仅中止或限制了自爱的自私,更是彻底击毁和瓦解了将自爱的主观条件颁布为法则的“自负”。由此对主体的感性施加了影响,并产生了一种促进道德法则去影响意志的“独特”的情感,也就是敬重感。一方面,从起源来说,敬重感不同于基于性好而产生的“病理学”的情感,它只是通过理智根据起作用的“道德情感”。另一方面,敬重感也不只是因为限制或中止了自爱和自负而具有消极否定的作用。由于排除来自感性欲望的冲动,在去除前进中的阻力的同时,唤起人们对法则的敬重而确认理性的界限,也就使人谦卑并抑制狂热,从而具有积极肯定性的作用。
道德法则的概念褫夺了自爱的影响和自大的妄想。正是通过道德原则的纯粹性,以及其与有限存在者局限的适合性,“使人类的一切善行都服从某种摆在他们眼前的、不容许他们在道德上所梦想的完善性之下狂热起来的义务的管教,并对自大和自矜这两种喜欢弄错自己的界限的东西建立起了谦卑(即自知)的限制”[4](118)。对超越了任何感性冲动的至高存在者而言,自然无需有因为对于感性冲动的贬损,而使之谦卑并产生敬重之情。因为有限存在者具有感性的冲动,道德法则旨在抑制这些冲动,击毁自大,并使之成为支配意志的主宰,从而从理性出发,产生对于意志影响的敬重之情,在防阻本能冲动和抑制狂热的同时,也使人们获得了对于人格价值和自身尊严的理解。这是因为,敬重的对象只限于人格,而决不能用于物件。然而,凡“人”也未必就是敬重的对象,世人的财富、地位和权势,虽能引发人的无限钦慕之情,但是“我的精神并不鞠躬”[4](105),内心的敬重却仍阙如。只有向我们显现“法则”的范例,尽管其本身也不尽完美,却使我们去除心中的自大和傲慢,才成为我们敬重的对象。因此,一方面,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之情,这种情感之不快,会使你去找作为榜样实范的过失或瑕疵,以减轻这种敬重使我们谦卑的负担。同时,我们之所以把道德法则贬低为性好,抑或把它看作是保护自己利益的箴言或规范,其实都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另一方面,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这种不快其实又是如此之微小,一旦人们摆脱自大、放下自负,且允许敬重对实践产生影响,或者说在实践上达到敬重,那就不只是理解了法则的威严。同时,心灵由于看到这神圣的法则高居于自己那脆弱的本性之上,也就深信自己因此被提高。如果说要限制某一种对活动产生的障碍和阻力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对活动的一种促进,那么,“在感性方面对道德上的自重的资格的贬低、亦即使之变得谦卑,就是在智性方面对法则本身的道德上的、即实践的尊重的提升”[4](108)。它既不允许人们听任性好及其满足的摆布,也将使人们抛却将纯然的功绩及期待作为获得赞许和赢得尊重的条件。由此,人类的价值尤其是道德的价值在何处生根?唯有坚定地根植于法则自身和对法则的敬重之中。这既是唯一使心灵得到道德教化的方法,也是人生道德唯一的实践方式。
如果说康德的理性批判在理论领域里“把我们理智的野心限制于经验秩序的限度之内”,那么其实践理性批判所确立的道德法则和义务观念,“把我们的生命从斤斤计较得失的‘实用’水平,提高到无上命令的更高水平上去。无上命令使人谦卑,而同时又使人骄傲;它暴露了我们的局限性,但它又能让我们通向我们所追求的崇高使命”[8](38)。显然,康德对“道德狂热”的斥责,在反对人类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过度自负和自大的同时,并没有贬损人类对道德价值和崇高精神的追求。在他看来,义务和敬重感既让我们在与性好傲然断绝一切亲缘关系的意志决定中找到了人类唯一能够给自己奠定价值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也让我们找到了人类本性中彰显高贵和崇高的根源,以及其可能的获得方式。正如康德所言:“反抗一个强大但却不义的敌人的能力和深思熟虑的决心是勇气,就我们心中的道德意向的敌人而言是德性[道德上的勇气]。”[6](393)因此,就作为人之所能及的目标而言,也应首先使人自己有德性,而这也是“必须来获得的东西”。作为一种遵从自己义务时的准则力量,“其方式是通过对我们心中的纯粹理性法则之尊严的沉思,但同时也通过练习来振奋道德的动机”[6](410)。通过德行训练,使人服从于自己所特有的、由理性所给予的实践法则或命令,也在超越感性而与理智世界的关联中,获得独立而实现自由的自律抑或人格条件。凭借人格,使有限的存在者成为自在的目的本身,正是在超越感性实存的道德努力中,意识到人性自身的某种崇高性。这样的生活境界,不仅与追求物欲和生命快意毫不相干,而且在对自身的检省中避免自身人格和尊严的丧失。在这样的目的王国中,不仅因自由的自律而获得自尊,而且因尊重他人的独立人格而获得互尊。显然,这样一种道德理想追求不仅赋予作为个体的人生以崇高价值和意义,而且是一个生活世界某种“应然”的伦理秩序。对追求个人良善和社会之善来说,具有积极的范导意义,对痴迷于物欲和工具化陷阱的现代性社会症候,也不啻为一副清醒剂。尽管由于人性的有限性及其完善的需要而最终乞灵于神学,也同样以“一种值得冒险的信仰”[2](128)来激励人们对于道德的信心,但是康德对“道德狂热”的斥责于现实生活世界的肯定性意义在于为人类道德生活设立了一条明确的“准线”,即通过确立实践法则的界限,来防范和避免人们陷入各种形式的狂热。对心灵的健全而言,要避免陷入狂热成为徒有激情而失去理智和判断力的“幻想家”[9](96);对当下社会而言,要警惕任何背离人类本性呼声的道德“玄想”和逾越“准线”的狂热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