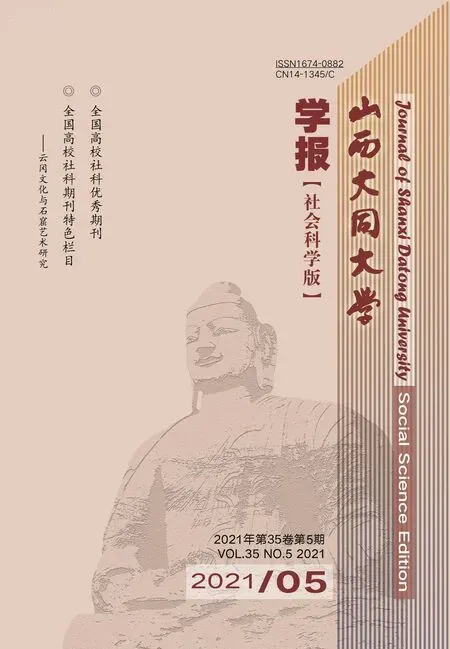多中心治理视角下抗击新冠疫情的“中国之治”
2021-11-30徐子钧
徐子钧,王 英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09)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中心位置。在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卓有成效。中国抗疫的成功实践,为世界提供了一套重大传染性疾病和应急治理的“中国方案”,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体系是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一、多中心治理理论
治理(governance)是政治学、公共管理领域中的重要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起流行于西方学术界。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国家治理”写入官方政治文件,治理理论因此也受到国内思想界、学术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并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一)治理理论的缘起 当代语境下的“治理”概念来自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1989年,世界银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从危机走向可持续增长》(Sub-Saharan Africa: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Growth:A Long-term Perspective Study)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治理危机”(governance crisis)。报告认为,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圭那亚、加纳、利比里亚、圣多美尼和普林西比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经济衰退,从中等收入国家滑向低收入国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公共机构的失败”(the failure of public institutions)。解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治理危机和经济衰败,需要私营部门的主动性和市场机制与“善治”(good governance)相辅相成,即“有效的公共服务、可靠的司法系统和对公众负责的行政机构”。[1]
1992年世界银行发表题为“治理与发展”(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的年度报告,进一步阐发了他们的治理理论。年度报告指出,治理是一个国家在管理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行使权力的方式,“善治”是健全的经济政策的重要补充。世界银行认为,“善治”包含四个方面:改善公共部门管理、问责机制、发展的法律框架和信息透明度。政府的作用在于制定保障市场有效运行的规则,纠正“市场失灵”,提供社会公共物品。[2]
(二)治理理论的内涵 在世界银行提出“治理”理念之后,“治理热”风靡全球,西方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对“治理”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
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指出,治理是某些领域内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管理机制。罗西瑙区分了“治理”与“统治”这两个概念。在主体上,统治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正式机构,治理的主体不一定是政府,也包括非官方和非正式的机构。在实现方式上,统治主要通过政府的强制力和正式机制,而治理则包括非政府机制。[3](P5)罗茨(R.Rhodes)认为,治理是以新的过程、新的方法在新的条件下来“统治”社会。在《新治理:没有政府的管理》这一著作中,罗茨提出了治理的6种含义。其中,“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包括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等多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互动。[4]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在1992年发布的报告《我们的全球之家》(Our Global Neighborhood)中,将治理定义为:个人和公共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5]进一步阐明了治理的意义与指向,有利于准确把握其实质,以便全球对此达成共识。
中国学者针对治理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俞可平认为,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社会秩序、满足公共的需要。[6](P23)杨光斌认为,治理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治理的主体未必是政府、治理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是上下互动的权力运作、治理意味着管理手段多元化。[7](P25)中国学者都强调治理的公共性、运作的多元与协调。
从中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治理概念的阐述中可以看到,参与主体的不同是治理区别于“统治”的一个显著特征。传统意义上的统治一般被认为是单纯的政府行为,普通民众几乎不能或很少能参与到统治过程中。而参与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包含政府、公共部门、民间机构和公民个人等,治理的过程也是多主体之间的持续合作与互动。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建构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Vincent Ostrom)在治理理论和米切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多中心”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理论。奥斯特罗姆夫妇基于大量的调研案例认为,公共事务的管理应当避免单一的集权制或分权制,同时应当摆脱政府或市场的“单中心”治理模式。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之下,有许多互相独立的决策中心。他们尊重其他决策中心的存在,互相签订合约、开展共同合作,利用冲突解决机制化解决策中心间的纠纷。[8](P12)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是通过多样化的制度设立,在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加强协同合作。多中心治理为公民提供了多种选择;减少了针对公共产品的“搭便车”行为;能有效利用特定区域的信息做出合理的决策,增强决策的民主性和有效性。[9]奥斯特罗姆夫妇在前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相关学说,最终建构起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对国际社会治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二、中国抗疫斗争中的多中心治理
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其治理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动员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有效使用的能力。资源的有效使用既包括常规状态下公共资源的有效使用,也包括紧急状态下政府有效动员各种资源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10]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后蔓延至国内多个地区,这是对我国应急管理和国家治理的一次重大考验。在抗击疫情这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面前,没有任何部门能单打独斗。全社会投入,并重视协同与分类,多方合力编制严密的防控网,[11]促成抗疫取得显著成效,使多中心治理落到实处。
(一)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精准施策是取得抗疫胜利的根本保障 抗疫斗争中,全国各地党委、政府、社会、市场等各方力量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取得抗疫斗争胜利的根本保障。疫情发生后,中共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作出重要指示,要求遏制疫情蔓延势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大年初一召开了常委会,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成立了中央应对新冠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共召开了21次有关抗击疫情的会议,研究、决策和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中央还向湖北武汉派出了指导组,连续3个月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督促湖北武汉落实好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同时指导抗击疫情。
党的最高决策者始终密切关注疫情,不仅亲自指挥抗疫还亲赴一线督导。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打赢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12]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北武汉,考察定点医院患者救治工作和社区一线的防控情况,提出要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和武汉保卫战。[13]
在党中央的部署和指挥下,各级党组织闻令而动,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党支部建立在患者救治和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共产党员冲锋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各地援助湖北的医务工作者向党员看齐,涌现出一批无私无畏、甘于奉献的抗疫先锋队。在社区防控工作中,也到处可以看到共产党员的身影。在北京海淀,540个区级单位的党组织与644个社区和村党支部对接,6万多名党员干部下沉到社区一线,参与社区联防联控。2月2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号召全国党员自愿捐款,支持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捐款,全体党员积极响应。据统计,全国党员自愿捐款金额达83.6亿元。各级党组织服从指挥,落实中央部署,全体共产党员积极主动参与,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二)各级政府加强统筹、协调联动是抗击疫情的主导力量 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是治理效能发挥的重要前提。其中,各级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2020年1月21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32个部门共同参与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成立。在联防联控机制中,多部门分工明确、协调配合,每日汇总各地感染者数据,通过国家卫健委向全社会公布,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国家各部委的负责人介绍疫情防控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2021年2月,联防联控机制共印发文件通知92篇,内容涉及卫生防护、隔离观察、核酸检测、患者救治、环境消杀、物资供应、复工复产、药物和疫苗研制等多个方面,为各地疫情防控工作起到了引领和指导作用,成效显著。
湖北武汉告急后,各级政府迅速集结人员、物资等驰援湖北武汉。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派出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多名医护人员奔赴湖北武汉。1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按照“一省包一市”或“两省包一市”的原则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以外的各市、自治州和县级市。支援省份在前方设指挥部,统筹各项支援工作;援鄂医疗队整建制接管感染病区,全力救治新冠肺炎患者。江苏省派出2813名医务人员和300多名工作人员支援湖北,13个地级市分别组队前往。山东省派出的援鄂队伍由副省长亲自带队,支援的物资从口罩、蔬菜、水饺到取暖设备和洗衣机,一应俱全。“散装式江苏硬核”和“搬家式山东援助”,体现了政府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对口支援这一中国特色的地区间合作机制,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2020年4月,当湖北疫情得到控制后,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各地政府出台了严格落实境外入境人员集中隔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学校复课等一系列政策。2020年底,当河北、辽宁、黑龙江等省局部地区出现疫情后,政府倡导民众就地过年。2021年春节,一些地方政府还通过发放“红包”、消费券、手机流量等方式,让不能返乡过年的群众得到多方关爱。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安定了民心,同时有助于防疫。
(三)社会力量是抗疫斗争的有力支撑 在抗疫斗争中,企业、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于2020年1月23和25日分别决定,按照“小汤山模式”建设火神山和雷神山定点医院。在接到任务后,中央企业中建三局组织了4万多名现场施工人员,昼夜不停施工,仅用时10余天就将这两座医院建成。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全国多家企业紧急转产。广汽、五菱、比亚迪等汽车企业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口罩产品。全国防护服的产能从1月23日的3万件到2月27日的31.7万件,[14]仅用时一个月。
公益组织和民间志愿者通过物资募捐和人力支持参与疫情防控。中国红十字会共接受社会捐款捐物20多亿元,湖北省慈善总会共接收捐赠资金60多亿元。[15]民间公益组织“蓝天救援队”,出动人员一万多人次,转运防疫物资2380万件。武汉顺丰速运的快递员汪勇,以志愿者的身份主动联系共享单车和网约车企业,解决医务工作者上下班出行难题;联系餐饮企业和便利店,为医务人员送盒饭,被称赞为“生命的摆渡人”。活跃在武汉和其他地区的志愿者成为抗疫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不仅亲身参与抗疫工作,而且用志愿者精神感染整个社会,凝心聚力、共克时艰。
(四)抗疫斗争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
从2020年1月23日凌晨武汉“封城”,到4月8日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湖北、武汉人民渡过了抗役斗争中最艰难的76天。在封闭或隔离期间,广大群众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居家隔离、减少外出活动,不少居民也主动加入到社区防控志愿者的队伍中。截止到2021年2月1日,96万余名密切接触者接受了医学集中隔离观察,大大延缓了疫情的传播速度。在疫情初期,海外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积极为国内抗疫筹集物资;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时,境外归国人员接受核酸检测和自费隔离观察;在2021年春节之际,许多人响应政府号召“就地过年”。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降低了疫情传播的风险。在抗役斗争中,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的第一责任人,在保护了自己的同时,也保护了他人。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全国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得到增强,无论是主动作为的志愿者,还是其他普通群众,无不与疫情作斗争,共同成为多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抗疫“中国之治”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了多中心治理理论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争中,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地区之间相互协调,共同汇聚起了强大的抗疫中国力量,形成了抗击新冠疫情的“中国之治”,并在实践中发展了多中心治理理论。
(一)重视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威 西方的多中心治理和治理多元化,强调弱化政治权力,甚至去除政治权威。[16]此次疫情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存在防控措施不力,疫情持续蔓延,至今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政府未能发挥主导作用,政策缺乏权威性是西方抗疫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党和政府能有效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积极出台抗击疫情的各项政策,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都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终取得了抗击新冠疫情的胜利。这表明,在多中心治理中,治理主体多元并不意味着弱化政治权力、去除政治权威,有效运用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才能更好发挥治理效能。多中心治理理论在中国抗疫实践中得到验证,并得到发展,强调运用权威对于治理的重要性切合中国国情,极大地提高了治理成效。
(二)将执政党作为主体纳入多中心治理 在西方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公共部门、司法系统、企业、市场、社会力量和公民等,很少重视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在治理中的作用。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所在。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统领全局、果断决策、力挽狂澜,在数月内抗疫局面就有了显著改变,其执政能力经受住了疫情的检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调动了社会各界资源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将党组织的优势转化为了国家治理效能。这表明一个强大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能够将多中心治理的主体更加有效地组织、联系起来,更好发挥多中心治理的“合力”。
结语
在一年多的抗击新冠疫情斗争中,中国所取得的成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之治”。实践证明,中国将政治权力与权威运用、渗透到治理中,重视发挥执政党的作用,不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而且发展和完善了多中心治理理论。“中国之治”的成效也验证了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可行性。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有效性将会得到进一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