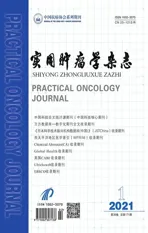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肺癌脑转移的研究新进展
2021-11-30鲍瑜朱立建综述钱江审校
鲍瑜 朱立建 综述 钱江 审校
约30%~43%的肺癌患者在病程中会发生脑转移[1],不同病理类型的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脑转移发生率约为6%~12%[2],存活2年以上的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的脑转移发生率高达60%~80%[1]。目前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已成为肺癌脑转移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传统治疗干预基础上,积极探索联合应用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成为重要研究方向之一[3]。当前治疗肺癌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包括单克隆抗体、以内皮细胞为靶点的抗血管生成剂、内源性血管生成抑制剂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Vascular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VEGFR-TKI)[4-5]。本文就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肺癌脑转移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1 肺癌脑转移的血管生成机制
肺癌脑转移的发生过程复杂,癌细胞进入脑循环后,停留在血流缓慢的毛细血管床,和内皮细胞相互作用并以黏附分子作为媒介穿过内皮细胞,进一步与局部细胞外基质、脑实质细胞相互作用,同时脑组织通过血管内皮因子、血管扩张和血管生成模拟机制帮助转移瘤转移增殖[6]。在上述过程中,血管生成与脑转移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其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pidermal growth factor,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ascular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是肺癌脑转移灶中血管生成的重要信号通路,由VEGF-VEGFR信号通路诱导生成的肿瘤新生血管,通透性差,不仅为肿瘤细胞的迁移和扩散提供条件,而且引起瘤周水肿,后者导致局部缺氧和酸中毒,进一步诱导VEGF过表达,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研究发现肺癌脑转移灶中VEGF呈高表达,与预后不良有关[6],而抑制VEGF-VEGFR信号通路可产生显著的抗肿瘤效应[7]。
2 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肺癌脑转移
2.1 单克隆抗体
2.1.1 贝伐珠单抗(Bevacizumab) 贝伐珠单抗是重组人单克隆IgG抗体,与VEGF特异性结合,阻断其与VEGFR结合,从而抑制肿瘤新生血管生成。研究证实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对晚期非鳞NSCLC患者是安全、有效的[8-10],并不会增加脑出血的发生风险[11]。
BRAIN研究中晚期非鳞NSCLC伴无症状脑转移患者接受贝伐珠单抗联合紫杉醇和卡铂一线治疗,6个月无进展生存率为56.5%,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为6.7个月,中位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为16.0个月,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为62.7%,其中颅内病灶ORR为61.2%,最常见3级以上不良反应为中性粒细胞减少(43.3%)和血小板下降(11.8%)[12]。Stefanou等[13]发现贝伐珠单抗、培美曲塞联合卡铂一线治疗晚期非鳞NSCLC伴症状性脑转移,ORR为66.7%,中位PFS和OS分别为8.2个月和14.0个月,无颅内出血患者,也无治疗相关死亡患者。Tian等[14]研究将晚期肺腺癌伴脑转移(症状性或无症状)患者分为贝伐珠单抗、培美曲塞联合卡铂或顺铂一线治疗组(B+PP组)和培美曲塞联合卡铂或顺铂一线治疗(PP组),结果显示,B+PP组与PP组间中位OS、ORR和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中位OS:33.4个月vs.21.0个月,P=0.460;ORR:53.8%vs.44.4%,P=0.445;DCR:88.5%vs.88.5%,P=0.420),与PP组相比,B+PP组的中位PFS、颅内PFS明显延长(9.2个月vs.8.2个月,P=0.029;24.3个月vs.10.9个月,P=0.008),两组间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7%vs.4.4%,P=0.970),B+PP组未出现血栓和出血,也无治疗相关死亡患者。Gubens等[15]的荟萃分析显示贝伐珠单抗联合培美曲塞二线治疗晚期肺癌伴脑转移,中位PFS和OS分别为7.2个月和14.8个月,未发生脑出血事件。Wang等[16]回顾性研究提示慢性心血管病是贝伐珠单抗治疗晚期肺癌脑转移出现神经毒性反应的独立风险因素(HR=16.6,P=0.004)。以上研究提示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治疗晚期肺癌伴脑转移具有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未增加脑出血风险。
日本一项研究纳入8例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驱动基因阳性晚期肺癌伴脑转移患者一线接受贝伐珠单抗联合厄洛替尼治疗,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7例,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1例,2年生存率为62.5%,4例患者疾病控制超过1年[17]。Yang等[18]回顾性研究发现,贝伐珠单抗、吉非替尼联合全脑放疗(Whole brain radiotherapy,WBRT)组的DCR较吉非替尼联合WBRT组、单纯WBRT组明显提高(96.1%vs.83.1%vs.60.0%,P<0.05),贝伐珠单抗、吉非替尼联合WBRT组的总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率(48.6%和29.8%)分别较吉非替尼联合WBRT组(36.7%和29.6%)、单纯WBRT组(9.8%和14.6%)明显升高(P<0.05),三组间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Jiang等[19]研究发现,贝伐珠单抗联合EGFR-TKI组的ORR、颅内病灶ORR、PFS以及颅内病灶PFS较EGFR-TKI组明显提高(74.6%vs.57.1%,P=0.019;66.1%vs.41.6%,P=0.001;14.4个月vs.9.0个月,P<0.001;14.0个月vs.8.2个月,P<0.001),且OS明显延长(29.6个月vs.21.7个月,P<0.001),多因素分析提示联合贝伐珠单抗与PFS、颅内病灶PFS以及OS延长相关,联合治疗组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4.7%,未发生脑出血以及咳血事件。国内专家共识也推荐EGFR敏感突变的晚期非鳞NSCLC患者(含无症状脑转移患者),可一线选择厄洛替尼联合贝伐珠单抗[3]。
早在REBECA研究中就发现贝伐珠单抗联合WBRT治疗实体瘤伴脑转移具有一定的疗效[20]。潘绵顺等[21]研究发现,对于肺腺癌伴脑转移,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SRT)联合贝伐珠单抗的近期肿瘤缓解率和瘤周水肿控制率较传统治疗组(SRT联合激素和甘露醇)更有优势。因此,贝伐珠单抗联合放疗有望成为肺癌伴脑转移的新的治疗策略。
2.1.2 雷莫芦单抗(Ramucirumab) 雷莫芦单抗是一种完全人源化的IgG抗体,高亲和力选择性结合VEGFR-2的胞外域,特异性阻断VEGFR-2和其配体结合,进而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和肿瘤生长。REVEL研究证实了多西他赛联合雷莫芦单抗二线治疗铂类药物一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肺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22]。日本的RAMNITA研究旨在评价雷莫芦单抗联合多西他赛治疗既往化疗失败的NSCLC伴脑转移(除外脑膜转移)的疗效和安全性,主要终点为PFS,次要终点为OS、颅内病灶PFS、ORR以及安全性,研究结果值得期待[23]。
2.2 内源性血管生成抑制剂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恩度(Recombinant human endostatin)通过抑制VEGF的表达及蛋白水解酶的活性,特异性抑制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并诱导其凋亡,发挥抗肿瘤血管生成作用。Ⅲ期临床试验表明恩度联合长春瑞滨和顺铂可作为初治晚期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24]。吴竞等[25]观察恩度、多西他赛、顺铂联合WBRT治疗NSCLC脑转移,分为研究组(恩度、多西他赛、顺铂联合WBRT)和对照组(多西他赛、顺铂联合WBRT),结果显示,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近期有效率(79.2%vs.66.7%)和局部控制率(95.8%vs.85.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研究组较对照组的中位PFS(12个月vs.8个月,P<0.05)以及中位OS(14个月vs.12个月,P<0.05)均有所延长,全组患者3~4级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发生率为15.6%和6.7%。Jiang等[26]的一项Ⅱ期临床试验将肺癌脑转移患者随机分为恩度联合WBRT组和单纯WBRT组,结果显示,恩度联合WBRT组与单纯WBRT组的ORR无统计学差异(90%vs.75%,P=0.07),进一步分析在VEGFR-2阳性或KDR基因扩增的患者中,恩度联合WBRT组较单纯WBRT组的ORR明显提高(93%vs.67.7%,P=0.012;94.4%vs.47.3%,P=0.002),其次,总体患者或VEGFR-2阳性或KDR基因扩增的患者中,恩度联合WBRT组较单纯WBRT组的水肿指数(Edema index,EI)均明显下降(P<0.05),两组间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5),两组间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未发生出血或神经毒性,研究提示恩度联合放疗较单纯放疗可减轻脑水肿,并可提高VEGFR-2阳性或KDR基因扩增患者的近期疗效,但并未延长OS。
2.3 以内皮细胞为靶点的抗血管生成剂
沙利度胺(Thalidomide)是一种免疫调节剂及抗血管生成剂,通过阻断VEGF的表达,从而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RTOG 0118研究纳入176例实体瘤伴脑转移患者(其中肺癌109例),随机分为WBRT联合沙利度胺组和单纯WBRT组,结果显示,两组的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6个月vs.3.6个月,P=0.88),联合治疗组与单纯WBRT组的3个月神经系统进展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3.1%vs.18.7%,P=0.097),联合治疗组3~4级毒性反应发生率较单纯WBRT组升高(46.4%vs.11.9%,P<0.0001),48%的患者因沙利度胺的毒性反应而中断治疗,提示沙利度胺联合WBRT并无OS的获益,且毒性反应发生率较高[27]。刘建刚等[28]的研究将肺癌脑转移患者分为实验组(WBRT联合沙利度胺)和观察组(单纯WBRT),结果显示,实验组ORR高于观察组(71.4%vs.42.9%,P<0.05),但实验组与观察组DC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2.9%vs.82.1%,P>0.05),实验组PFS较观察组有明显延长(8.2 个月vs.5.9 个月,P<0.05),实验组骨髓抑制和乏力的发生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未见严重不良事件。因此,沙利度胺联合放疗治疗肺癌脑转移的疗效和生存获益有争议,联合治疗较单纯放疗的毒性反应明显增加,既往多项研究发现沙利度胺联合化疗治疗晚期肺癌较单纯化疗并未提高疗效和生存期[29-30],因此还需进一步探讨。
2.4 VEGFR-TKI
2.4.1 阿帕替尼(Apatinib) 阿帕替尼是一种小分子TKI,可靶向抑制VEGFR-2酪氨酸激酶的活性,阻断VEGF与其受体结合后的信号转导通路,从而强效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发挥抗肿瘤作用。诸多研究证实阿帕替尼治疗晚期肺癌具有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31-33]。张智显等[34]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将常规治疗失败的肺癌脑转移患者分为实验组(伽马刀、阿帕替尼联合替莫唑胺)和对照组(伽马刀联合替莫唑胺),实验组PFS、OS较对照组明显延长(9.6个月vs.7.8个月,P<0.05;13.6个月vs.10.8个月,P<0.05),实验组ORR和DCR较对照组明显提高(84%vs.64%,P<0.05;52%vs.40%,P<0.05),实验组3~4级的高血压、蛋白尿、出血、皮肤黏膜炎发生率高于对照组,而其他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张智显等[35]进一步回顾性分析发现阿帕替尼联合替莫唑安序贯WBRT二线治疗SCLC脑转移,较单药拓扑替康在PFS、OS、ORR和DCR均具有明显优势。Xu等[36]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探讨阿帕替尼单药、阿帕替尼联合化疗或EGFR-TKI治疗复发性肺癌伴脑转移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显示,与阿帕替尼单药相比,阿帕替尼联合治疗具有明显的PFS(11.77个月vs.2.27个月,P<0.05)和OS(24.03个月vs.6.07个月,P<0.05)获益,主要不良反应多为1~2级,包括高血压、手足综合征等,提示阿帕替尼可作为肺癌伴脑转移的潜在治疗选择。
2.4.2 安罗替尼(Anlotinib) 安罗替尼也是一种小分子TKI,主要通过抑制VEGFR 2~3、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FGFR)1~4、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PDGFR)、c-Kit等多个靶点,具有抗肿瘤血管生成和抑制肿瘤生长的双重作用。ALTER0303研究证实安罗替尼三线治疗晚期肺癌的疗效与安全性[37]。对ALTER-0303研究中肺癌脑转移亚组人群进行分析发现,安罗替尼组较安慰剂组PFS明显延长(4.17个月vs.1.30个月,HR=0.29,P<0.01),OS有获益的趋势(8.57 个月vs.4.55个月,HR=0.72,P=0.171),患者的颅内ORR和DCR分别为14.3%和85.7%,多因素分析显示,接受安罗替尼治疗与更长的颅内进展时间(Time to brain progression,TTBP)有关(HR=0.11,P=0.001),安罗替尼组较安慰剂组有较高的神经毒性(18.4%vs.8.4%,P=0.007)和精神症状(49.3%vs.35.7%,P=0.008)发生率,但与梗死或脑出血无关,提示安罗替尼对肺癌脑转移有潜在的疗效[38]。黄行志等[39]的研究显示,与单纯放疗比较,安罗替尼联合放疗的ORR和DCR(60.0%vs.35.0%,P<0.05;90.0%vs.55.0%,P<0.05,)明显提高,1年和2年生存率也明显提高(90.0%vs.60.0%,P<0.05;75.0%vs.40.0%,P<0.05)。目前国内一项前瞻性多中心Ⅱ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该研究旨在探索立体定向放射外科(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SRS)联合安罗替尼治疗肺癌伴局限性脑转移(<5个病灶)的疗效以及安全性,研究结果值得期待[40]。
2.4.3 其他VEGFR-TKI 其他VEGFR-TKI还包括索拉非尼(Sorafenib)、西地尼布(Cediranib)、凡德替尼(Vandetanib)、尼达尼布(Nintedanib)、呋喹替尼(Fruquintinib)和瑞格非尼(Regorafenib)等。MISSION研究证实索拉非尼虽延长复发进展晚期肺癌的PFS,但无OS获益[41]。BR29研究提示西地尼布联合紫杉醇和卡铂较单纯化疗一线治疗晚期NSCLC并未表现出更好的OS获益,反而增加毒性反应[42]。LURET研究提示凡德替尼可提高RET重排阳性的晚期NSCLC患者的中位PFS(6.5个月)和OS(13.5个月)[43-44],Subbiah等[45]报道1例凡德替尼联合依维莫司治疗伴脑转移RET重排阳性的晚期NSCLC的病例,颅内外病灶均得到良好控制。SENECA研究证实了尼达尼布联合多西他赛二线治疗晚期非鳞细胞肺癌的疗效[46]。Ⅱ期临床试验提示呋喹替尼较安慰剂能显著提高二线化疗失败晚期NSCLC的PFS和6个月生存率[47]。也有初步研究发现瑞格非尼治疗早期肺癌具有良好的疗效[48]。目前尚未见到上述VEGFR-TKI在肺癌脑转移中的相关研究,但期待有所突破。
3 小结与展望
随着对肺癌或肺癌脑转移的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和新药的问世,肺癌脑转移治疗迎来新的局面。临床研究提示抗血管生成治疗在肺癌脑转移的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包括单克隆抗体、泛靶点抗血管药物和小分子TKI,均显示出一定的疗效与良好的安全性,且与化疗、放疗以及EGFR-TKI表现出协同抗肿瘤作用。未来,抗血管生成药物的介入时机,与传统治疗的合理搭配,优势人群的筛选,不良反应的全程管理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