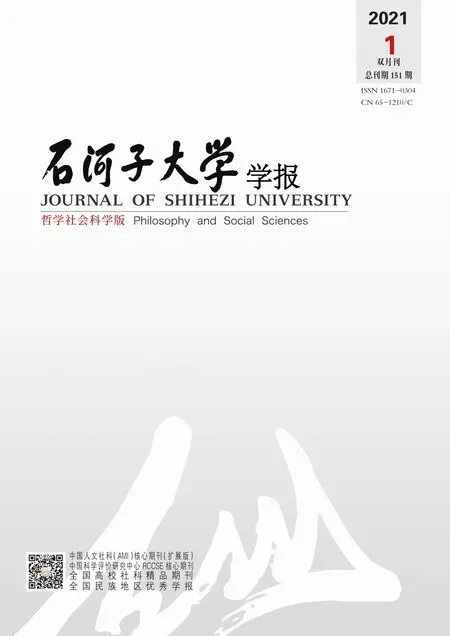玉门关早年移徙新证
——从小方盘汉简T14N3的释读说起
2021-11-30张俊民
张俊民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 兰州730000)
小方盘遗址,位于东经93°51'50.47″、北纬40°21'12.68″。自斯坦因中亚探险之后,与之有关的活动没有终止过。小方盘遗址,斯坦因考察编号T1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号D25。目前是敦煌市旅游的热门打卡地之一。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夏鼐曾在此工作过,除了一般常见的障城之外(边长八丈),还在东、北、南三面发现了边长约卅丈的外围坞墙遗迹,并掘获汉简七十余枚①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35-261页。。伴随着敦煌卷子的发现与研究,很多学者将小方盘遗址与汉代的玉门关联系起来②有关汉代玉门关位置问题,王蕾在《汉唐时期的玉门关与东迁》一文对之有比较详细梳理,参见《西域研究》2020年第2期第96-108页。。但在1979年小方盘城遗址西侧11公里的马圈湾遗址发掘之后,因为此处出土了较多出入关记录文书,吴礽骧提出了玉门关在马圈湾以西的观点,小方盘遗址是玉门都尉府所在地①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67页。。1998年小方盘遗址维修过程中,再次出土简牍380余枚,使玉门关之辨再起。经2014年“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之助,小方盘遗址俨然就是玉门关了,以至于重点介绍此次所获简牍的书也以“约定俗成”命名为《玉门关汉简》②张德芳、石明秀:《玉门关汉简》,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玉门关似乎已经定谳!
在梳理已有研究的过程中,感觉有一条简文不得不再次提出来说一说。为何说再次?因为这条简大家都曾注意过,新图版与释文是我们感觉意犹未尽的主要原因。新的简牍简号是T14N3,《敦煌汉简》编号敦·2438,《疏》编号435。最新的简牍释文作:
谓天降衣以次为驾当舍传舍诣行在所
较早的《疏》作:
疏*435③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简称《疏》。
《敦煌汉简》的释文作:
夜(?)以传行从事如律令
敦·2438④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简称《敦》。
《敦煌汉简校释》作:⑤白军鹏:《敦煌汉简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41页。简称《校释》。
我们述列上述释文,旨在说明简牍释文的变化,也就是人们对简文的理解与认识随时间的不同是变化的,尤其是史语所新版的图版与释文。将它们放在一起,就会发现本简上残,文字上、下二栏书,上栏仅存二字,一字可释为“长”,一字不识;下栏文字三行,字迹的清楚度从右向左递减,右行最清晰,左行最模糊。释文的准确性以右行为最高,从来没有异议;中间行疑问在“降衣”(原来的造字)与“为”字(原来“马”字),至今总算得到解决;左行史语所仍持存疑态度的三个字,《校释》补充作“夜以”“信”。
今案:现有释文校以图版,“天降衣”二字,可从;“夜”字不能成立,字形有点“厩”的形状,可释作“厩”;“以”“信”二字,作为传信文书暂从。之所以暂从,本简的两个“以”字字形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对本简文字的检讨,最完整的是夏鼐之《新获之敦煌汉简》⑥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35-261页。,惜早年释文较多残缺,尚处在简牍文书研究的初期,虽考虑到本简涉及的时间与敦煌、玉门关设立的时间问题,但因“天降衣”二字的缺释,仍可以再检讨。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一书不仅注意到本简的纪年时间,可以藉助它简找到旁证进行大致比附,还对本简的文书性质进行了定性,“据简文,此例为传一类通信证……且此传由都尉府颁发,知持有者身份地位当较高。”⑦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第6页。
因为“天降衣”二字的确定,涉及到“天降衣”县的位置问题,其中会引出玉门关的位置问题,当然还有敦煌郡设立的问题。这就是本简的重要性所在,仅仅是这条不完整的传文书,竟然会涉及汉代敦煌郡、玉门关的设置时间问题,还有天降衣县的位置问题。这些问题,恰是西北史地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且也是一直令人困惑的问题。
河西四郡的设立时间,因为《史记》与《汉书》、《汉书》的《纪》与《传》的出入,众说纷纭。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之后,先后参与讨论的学者有张维华、劳干、张春树、周振鹤、王宗维、吴礽骧、李并成等。纷纭的诸说,敦煌郡晚于酒泉郡是无疑的,至于能晚到哪一年争议较大。敦煌郡早者设立时间是元鼎六年(前111),晚者到后元元年(前88)。
正因为本简涉及到这么多的问题,也许“天降衣”的补释能对这些问题认识有所帮助。这就是我们再次关注本简的原因所在。
为了更好地进行检讨,我们将前述诸家的释文进行再融合,作:
首先,本简的时间问题。本简没有出现专门记录时间的用词,根据同在小方盘遗址出土的其他汉简可以旁证推演。依据是同在小方盘遗址出土的玉门都尉“护众”,具体简文如:
简2.大始三年闰月辛酉朔己卯玉门都尉护众谓千人尚尉丞无署就
…… 敦·1922A①敦煌汉简的简号,基本是统一的。即敦·1922A在《校释》、《敦》都可以检索到,页码不需赘注。
本简松木,左侧残而仅存笔迹。斯坦因掘获汉简之一。已有的释文,诸家无异议。其中的玉门都尉护众,虽然没有前面的“酒泉”二字界定,但作为“玉门都尉护众”,将其与“酒泉玉门都尉护众”视作一个人是可以成立。即护众曾在太始三年任玉门都尉,则简1的时间应该在太始三年(前94)前后。西北汉简中“太”多作“大”形。注意这个时间距离敦煌郡设立的后元元年(前88)很近。敦煌郡设立之后,玉门都尉与酒泉郡的关系如何?也许都尉护众正好是在这个过渡交接期。
纪年时间虽有旁证,但如何理解简2还是有出入的。或作“大始三年闰月辛酉朔己卯,玉门都尉护众谓千人尚、尉丞无署就”②饶宗颐,李均明:《敦煌汉简编年考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第3页。,或参考《中国简牍集成》句读作“大始三年闰月辛酉朔己卯,玉门都尉护众谓千人尚、尉丞无署,就”③白军鹏:《敦煌汉简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75页。。
如此理解,则是都尉护众向其下属尚、无署转达指令。有可能将“无署”作人名理解。“无署”是不是人名呢?如果不是人名,不就是说“都尉护众”的下属“千人”“尉丞”缺少具体的署所(办公场地)。如此一来就会出现都尉的文书或指令,仅有一人署名,没有一般联署的丞出现。如:
简3.八月戊辰朔戊子居延都尉谊丞直谓居延甲渠障候箕山隧长冯利不在署第
十一隧候移书验问案致言会月十八日书以十九日食坐到案甲渠候EPT51:189A④此类EPT简号见张德芳主编《居延新简校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下同。
简4.延都尉德库守丞常乐兼行丞事谓甲渠塞候写移书到如大守府
书律令/掾定守卒史奉亲 EPT51:190A
上述二简是一种情况,而都尉单独直接下文者也有,且与简4是一个人或一个时期。如:
若根据简5、简6的文书格式,则简2是都尉护众给千人尚的指令,其中提到“尉丞”的状况如何。尉丞应该是都尉之丞,悬泉置汉简之“鼓令册”对“丞”的区别是明显的。郡太守府之丞称“守丞”,候官之丞称“候丞”,县府之丞称“县丞”⑤牛路军,张俊民:《悬泉汉简所见鼓与鼓令》,《.敦煌研究》,2009年第50-54页。。
其次,简1属于传文书的性质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其与悬泉置汉简所见的传文书格式是不同的。悬泉置汉简比较完整的传文书格式如:
简7.使乌孙长罗侯惠遣斥候恭
上书诣
行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 (第一栏)
甘露二年二月甲戌敦煌骑司马充行大守事库令
贺兼行丞事谓敦煌以次为当舍传舍如律令(第二栏) ⅤT1311③:315⑥此类简号见悬泉置汉简,权以录文为是。下同。
简8.危须王遣副使赵疏□□□□□……
奉献橐它言事诣
行在所以令为驾一封传 …… (第一栏)
……敦煌大守快长史布施丞汉德谓
敦煌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第二栏)
ⅠT0310③:13
简9.建平四年五月壬子御史中丞臣宪承
制 诏侍御史曰敦煌玉门都尉忠之官为驾一乘传载从者 (第一栏)
御史大夫延下长安承书以次为驾
当舍传舍如律令 六月丙戌过西 (第二栏)
ⅠT0112②:18
简10.甘露二年三月丙午使主客郎中臣超承
制 诏侍御史曰顷都内令霸副候忠使送大月氏诸国客与斥候张寿侯尊俱
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 (第一栏)
御属臣弘行御史大夫事下扶风厩承
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第二栏)
ⅤT1411②:35
简11.甘露三年十月辛亥
丞相属王彭护乌孙公主及将军贵人从者道上
传车马为驾二封轺传有请诏 (第一栏)
御史大夫万年下谓成以次为驾当
舍传舍如律令 (第二栏) ⅤT1412③:100
简12.初元四年十一月乙亥朔庚子
酒泉大守卒史廉□众……
以令为驾一封轺传 (第一栏)
酒泉大守贤□□□王□禄福厩以次为驾
当舍传舍 (第二栏) ⅤT1410③:26
以上所列六简,其中前简7、简8是敦煌郡发往长安的传文书,简9是长安发往敦煌的传文书,最后一简简12是酒泉郡发出的传文书,在悬泉置出土可视作是酒泉郡发给敦煌郡传文书。
由长安发出的完整传文书可以由以下数项组成,即①传文书的签发时间“年+月+日”、②传文书签发机构“官名+人名”、③传文书签发程序(承制诏侍御史曰,七字,其中“承”在一行尾,“制”字转行提格)、④持传人的“身份+人名+办理某事”、⑤用传规格与人数、⑥传文书编号、⑦传文书具体下发人员“官名+人名”、⑧首起第一站(持传人的出发地)、⑨传文书后附规定(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⑩持传人途经悬泉置时间。
所列数项,案之以简9则⑦传文书具体下发人员“官名+人名”之后在简牍的第二栏,其上为第一栏;第⑩持传人途经悬泉置时间,是不一定存在的。
由敦煌郡颁发的去往长安的传文书(我们重点以有“诣行在所”为主),可见首起是上述的②传文书签发机构“官名+人名”、④持传人的“身份+人名+办理某事”、⑤用传规格与人数、⑦传文书具体下发人员“官名+人名”、⑧首起第一站(持传人的出发地)、⑨传文书后附规定(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⑩持传人途经悬泉置时间等等。以简7、简8为例,可见“诣行在所”是在第一栏,且分书两行。因为“行在所”,指的是皇帝所在。因此之故,西北汉简中多以提格处理,且在第一栏书写。《后汉书·光武帝纪》引蔡邕《独断》称“天子以四海为家,故谓所居为行在所”①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页。。
这种传文书格式的差异,可能是时间不同造成的,与文书格式的演变有一定联系。酒泉玉门都尉护众的时间比较早,在武帝之时;悬泉置汉简的时间相对晚一个时间段,多在宣帝之后。在西北汉简中我们曾注意到文书格式简的存在,且这类格式简多出现在宣帝之时。盖宣帝之时,伴随着边塞生活的相对稳定,众多文书管理的需要,才出现了行政文书格式的统一与规范②张俊民:《简牍文书格式初探》载于《简牍学报》15期,1993年,第43-59页;张俊民:《悬泉汉简所见文书格式简》,《简帛研究(2009)》,2011年,第120-141页。。
简1之传文书与敦煌颁发传文书相类,虽然第一栏的文字不完整,但通过第二栏的文字类比我们会发现,酒泉玉门都尉府颁发的传文书“诣行在所”是在第二栏,且没有提格;传文书之⑧首起第一站(持传人的出发地)是“谓天降衣”。“谓天降衣”作为简1传文书的首起地,类似简7、简8之“谓敦煌”,简9之“下长安”、简10之“下扶风厩”、简11之“下渭成”。简12是酒泉郡颁发的传文书,首起是“禄福厩”。
我们将这些文书作类比,旨在检讨酒泉玉门都尉府所发传文书的第一站是“天降衣”。因此之故,“天降衣”的位置对于我们认识玉门都尉府所在至关重要。假若玉门都尉府在今天的小方盘遗址③因夏鼐在《新获之敦煌汉简》中有“敦煌未建郡以前,玉门关即已在敦煌西之小方盘城”,后世之人多视小方盘遗址为玉门关。文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43页。,其颁发的传文书首起第一站是“天降衣”,两者关系如何,持传人如何去往行在所呢?如果简1的玉门都尉府不在小方盘遗址,简1出土在小方盘遗址又当如何理解呢?这是简牍释文补充“天降衣”之后出现的问题,也是将会引起的连锁反应。
复次,天降衣的位置问题。“天降衣”,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无疑应该是酒泉郡的天降衣县。有关天降衣县的位置,目前的说法并不统一。关于酒泉郡县置十一所名称的研究,最大的分歧也集中在此。
《汉书》颜注作“音衣。此地有天降衣阪,故以名”①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614页。。《中国历史地图集》以高亢之地为“阪”,将天降衣县大致标在祁连山中,约是《汉书地理志汇释》所指的肃北县东北与肃南县“交界一带”②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凉州刺史部”,上海:上海地图学社,1975年,将“天降衣”标在骟马城偏西南25公里的山前台地上,没有具体地点;周振鹤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62页。。
悬泉置汉简里程简提到酒泉郡有县置十一所,具体名称阙佚③悬泉置汉简简ⅡT0214①:130A。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8年第1期,第62-69页;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2-107页。,其中是不是有“天降衣”县名尚存争议。贾小军将天降衣县归入十一所之内,位在玉门东骟马河西侧骟马城,后汉更名延寿县④贾小军:《汉代酒泉郡驿置道里新考》,《敦煌研究》,2020年第1期,第122页。;李并成认为,天降衣县位在昌马盆地中央、玉门市北柳沟村乡,与后汉延寿县无关⑤李并成:《汉酒泉郡十一置考》,《敦煌研究》,2014年,第115-120页;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另外,吴礽骧将天降衣县放在嘉峪关双井子木兰城一带,即后汉更名的延寿县⑥吴礽骧:《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简帛研究(2001)》,第348页。初世宾在《汉简长安至河西的驿道》一文,将天降衣作为玉门与禄福之间的驿站,且与玉门、禄福之间均间隔一站⑦初世宾:《汉简长安至河西的驿道》,《简帛研究(2005)》,2008年,第114页。。
因为简1传文书所记的“天降衣”原则上应该是汉代的驿路上,祁连山北侧台地上的位置显然是不合理的。
汉代的玉门关一般说是小方盘遗址,东边的玉门县附近有没有玉门都尉?因为从小方盘遗址发出的传文书第一站天降衣与小方盘城之间距离太远了。300公里之外,姑以415米为1汉里,七、八百汉里的距离,足见简1所记玉门都尉府所在地一定不在今天的小方盘城。这一问题,与西汉玉门关之西移是不是有关系呢?
按照《史》《汉》二书的记载,元封四年(前107)王恢伐楼兰,还封浩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汉书·地理志》记酒泉设郡在太初元年(前104)。如是则先有列亭障至玉门,后有酒泉郡。此玉门因在酒泉郡之前,可能不是一般所言的玉门县。而《史记》在此条的注,《集解》“韦昭曰:‘玉门关在龙勒界。’《索隐》韦昭云:‘玉门,县名,在酒泉。又有玉关,在龙勒也。’”⑧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172页。韦昭已莫知所衷。这个“玉门”位置在哪里,恐今天已经难以辨明。但是如果考虑到玉门都尉府派人去长安的传文书,出发的第一站是天降衣,则无疑应该在天降衣的西侧比较合理。
天降衣县在哪里?从现有的诸家检讨来看,在骟马城比较合理。因为这里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此地最早的遗存是骟马文化遗址,有汉代的城址,也有明代的城池。从距离来看,基本上处在嘉峪关与赤金镇之间的中间点。“天降衣县位在昌马盆地中央,玉门市北柳沟村乡”的说法,立足点是骟马城是东汉的延寿县,史书没有记录“天降衣县”改延寿县的线索⑨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如果将天降衣县放在骟马城就有天降衣改延寿的嫌疑。但是,这个地点如此重要,东汉在此能设县,西汉为何不能呢?且前、后汉的出入就在天降衣与延寿二县,虽然没有文字记录二县的更名,为什么就不是呢?天降衣县在骟马城,则玉门都尉府在其西,西到何地?是不是玉门县所在?还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之“玉门”?赤金峡或赤金镇所在,汉长城在其北约40公里。若在玉门县以西,其首站应该是玉门而不是天降衣。但无论在何处,一定不会在今天的小方盘遗址附近。
一般而言“列亭障”,应该与汉塞也就是汉长城的修筑有关。此玉门在何地?尚缺乏明确认识。酒泉玉门都尉府也许就是管辖玉门附近汉塞的管理机构,此时的玉门都尉府距离汉代的驿道最近的驿站点应该就是天降衣县(置)。
先有酒泉郡,再有敦煌郡,这一点虽有争议,估计是可以成立的,即敦煌郡设立时间没有酒泉郡早。敦煌郡与玉门关还与李广利伐大宛,皇帝使使者遮玉门关之事有瓜葛,也是西汉玉门关东西迁徙说的依据之一。
李广利首伐大宛,在太初元年(前104),也就是酒泉郡设立之年。《史记·大宛列传》记:
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关,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175页。。
玉门关在敦煌东,不是与太始三年(前94)前后称酒泉玉门都尉相符吗?既然不能入关,就屯兵敦煌。既是屯兵敦煌,贰师将军复伐大宛,兵出敦煌,大胜而归,还到玉门关时,“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②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178页。。出入关是标志,首次未入关屯敦煌,在玉门关外;二次发关外,得胜而回入玉门关。如是就很好地解决了贰师将军不得入玉门关而屯敦煌的问题。
从这个时间来看,酒泉郡刚设立,敦煌郡还没有设立。敦煌郡设立之前的敦煌在哪里?是今天一般所言的敦煌吗?或者是敦煌郡治之所在的敦煌绿洲吗?
《史记》123卷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③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162页。。
张守节《正义》称“初,月氏居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自是之后,“以东”“以西”无有疑问。但祁连山不管是现在的祁连山也好,还是天山也罢,应该都是山,且山体的走向大体都是东西向。敦煌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地点怎能与山脉相对应来说明?正如“正义”所谓“敦煌以东”好理解,作为东西向的山“祁连以西”又当是何处?如果祁连山是一个大体东西走向的山脉,是不是应该与一个东西走向的参照物,不应该是一般所言的点或面。与祁连山相对的“敦煌”为何?恐应劭所谓“敦者,大也。煌者,盛也”绝非一个点,而是一个广阔的地域。这个地域是指今天的敦煌绿洲区?还是河西走廊之北山?还是戈壁滩?还是指今天的疏勒河?
伴随着西汉对西域的经营,尤其是贰师将军伐大宛,敦煌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汉塞由敦煌修至盐泽,敦煌郡设立。界东西的玉门关西移,玉门都尉府也在敦煌郡设立不久之后,向西转移,归敦煌郡管辖。如果按照《汉书·地理志》后元元年(前88年)设敦煌郡,西移之后的玉门都尉府保留太始三年(前94)的公文档案也是合理④最能体现档案文书存放地点的移徙是马圈湾遗址出土的王莽末年所谓的王骏“莫府档案”,天凤年间征战焉耆失利后,“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西域都护李崇等退兵入塞,很多档案文书被带到马圈湾遗址保留下来而被后人发现。相关研究参见孙占宇《敦煌汉简王莽征伐西域战争史料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5-110页;后晓荣、苗润洁《关于马圈湾汉简涉及西域战争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05-111页。。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认为简1酒泉玉门都尉府应该距离天降衣县(置)最近,这样酒泉玉门都尉府颁发的“诣行在所”传文书,才能首站是天降衣;敦煌郡设立之前的玉门都尉在今天玉门附近,当然玉门关也应该在今天的玉门附近;因此之故,贰师将军首伐大宛兵败,不得入玉门关,而屯敦煌;敦煌郡设立(前94)后,管理东西交往的玉门关也随着玉门都尉府西移;玉门都尉府转移到了今天小方盘遗址,原来酒泉郡玉门都尉府使用的公文档案也随衙署搬迁,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小方盘遗址出土的汉简有酒泉玉门都尉府的公文;作为初创之时的机构,都尉府下属人员还没有得到合理安排,也就有简2玉门都尉护众对千人尚所言的“尉丞无署就”。
因为玉门关是一个时空很大的问题,有汉唐之变,文献繁杂,论者颇众。本文仅以小方盘汉简为据,藉助传文书的格式就其中出现的地名“天降衣”,探讨其所反映的问题。时间大致集中在汉武帝时期,汉宣帝之后的玉门关不在讨论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