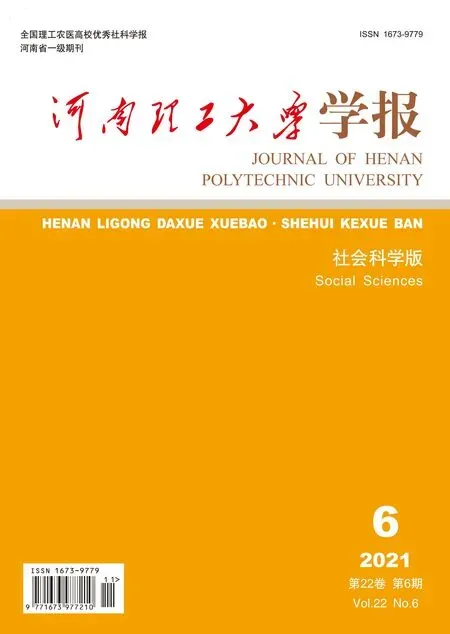主体改造的现代性困境
——基于延安文学医疗卫生叙事的一种考察
2021-11-30林继鹤
林继鹤,赵 洁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延安文学是一种以“人的改造”为导向的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曾指出,文艺工作的服务对象是以工农兵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其目的在于普及和提高工农兵的群体知识水平,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1]。这从侧面对延安文学首要承载的任务做出了规定,即延安文学要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文化启蒙和主体改造。在延安文学众多叙事主题中,延安文学有关医疗卫生的叙事,因其对人体治疗与修复的直观反映,成为考察此时期“人的改造”的一个重要面向。
作为这一时期的政治改造活动之一,延安乡村卫生改造运动因其自身依托的现代科学精神,不仅对人体直接进行医疗卫生层面的干预和治疗,而且还参与推动了民众卫生意识的现代性转型。从这个角度上看,延安文学的医疗卫生叙述与过往的“疾病叙事”区隔开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医疗卫生叙事”[2],其延续了“五四”文学一以贯之的将人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对人进行现代性改造的精神主旨,成为整个现代文学关于“人的改造”的话语谱系中重要的一环。但是,与此同时,在四十年代革命与救亡局势的制约下,政治任务成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政策主张限制了民众的主体性改造,此前强调人的主体自由的启蒙,转而服膺于社会变革的政治需要。作为个体的人过多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产生勾连,甚至演变成为国家话语空间对民间话语空间的压制。在这种启蒙与政治颉颃的处境面前,延安文学陷入了有关人的主体改造的现代性困境。
一、乡村卫生改造与医学话语启蒙
自晚清时期中国真正走上现代性转型开始,有关国民身体的叙事始终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联系在一起。从早期抽食鸦片、面黄体弱的“东亚病夫”,到后来无所事事、麻木旁观的精神看客,这些身体形象的呈现构成了对近代中国国族形象的隐喻。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的身体形象和国家形象紧密相连,与“政治局势、文化思潮、社会形态、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纠葛成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3]。因而,从很早开始,寻求国家变革的近代知识分子就明确了“完善自我即所以完善社会、国家”[4]的层级逻辑观念,进而将改革的目光聚焦在了国民个体的启蒙与改造上。梁启超“新民”“新人”概念的提出及其“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5]的论述即是这方面的最直接体现。到了延安时期,在政治革命与抗日救亡运动齐头并进的紧迫局势下,实现国民改造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顺利转化显得尤为迫切。这一阶段文学中大量出现的改造叙事,都表现出在民族危亡面前尽快通过主体的启蒙和改造以促成现代化转型的紧张与焦虑。其中,乡村卫生运动因为直接涉及对人体的启蒙和改造,成为延安文学反映现代性改造过程中焦虑情绪的直观内容。
丁玲于194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正是这种焦虑下的产物。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因为生病被送到霞村休养,目睹了同样因病返乡治疗的贞贞在乡亲们闲言碎语的压力下重又离乡出走。在丁玲的叙述中,“我”与贞贞是作为延安时期疾病观念的靶向投射而存在的。在病理概念上,虽然这两人都是病患,但闭塞山村环境背后所附着的老旧卫生观念与权力趋向,使得乡民们对疾病的处置方式体现出一种悬殊的差距:“我”是经政治部介绍来此休养的干部,身份上的权力着色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身体上的缺陷,因而受到全村的友好对待;而贞贞是被日军糟蹋过的女人,这层经历在疾病的晕染下带上了更多的歧视色彩。这恰好解释了在丁玲笔下,贞贞形象的蜕变何以如此惨烈:在“我”初见到贞贞时,这时的她还是个“脸色红润,声音清晰,不显得拘束,也不觉得粗野”,“一点有病的样子也没有”的健康人[6]224;而当“我”即将离开霞村时,贞贞却变得“像一个被困的野兽”“把脸藏在一头纷乱的头发里,望得见两颗狰狰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表现出一副残酷的样子[6]228。在霞村充满流言与保守顽固的乡里空间内部,乡民们这种将疾病与道德、权力挂钩的落后思维方式使人变为“非人”,这在解放区“明朗的天”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思维方式的普遍存在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问题”[7],显示出蒙昧的民众主体意识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巨大的矛盾。
寻求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医疗卫生观念,已经不单单是个人身体与精神健康的问题,更关乎整个民族国家集体的健康[8]。在这个意义上,延安时期开展的乡村卫生运动凭借对民间卫生观念的改革,促成了民间主体的启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与弥合了国民意识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差距。
葛洛的《卫生组长》是对这一卫生启蒙的直接反映。小说主人公卫生组长“我”所在的村子,社区环境脏乱芜杂,“村子里到处都是牲口粪,满年四季不打扫。人们天天不洗手,不洗脸,吃着不干净的东西”[9]2553。现代意义上的卫生理念在四十年代的延安乡村仍旧是一个相对陌生的知识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卫生运动在施行过程中所遇见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拉锯就成为意料之中的事情。在卫生组长的工作过程中,其碰见的最大阻碍,就是这种信奉着老一套的村民们的历史惯性。“不干不净,吃了不害病。”“我们生来没听过讲卫生,不也平平稳稳活了几十岁?”[9]2553在村民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面前,卫生组长“我”只有通过一遍又一遍地对现代细菌理论的宣传以及对环境卫生与健康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强调,才换取了村民们在行为上的改变。这个过程中,现代医学话语开始撼动传统观念的稳固地位,新的卫生理念的进入促使乡村世界对身体、疾病、卫生观念和行为展开新的界定与启蒙,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新的身体观和卫生观。
在一定程度上,《卫生组长》表现了卫生宣传对民众卫生意识提供的启发和引导,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单凭这种宣传无法确保民众会发自内心地对这种改革行为进行接纳。从一开始,卫生组长的妻子和母亲就不服膺他的“卫生话术”。与葛洛的《卫生组长》相比,欧阳山清楚地看到了这层想象背后的逻辑漏洞,并在他的《黑女儿和他的牛》中透露出,真正促使民众发生现代主体转型的,是疾病给人们的生产、生命所带来的威胁。欧阳山的《黑女儿和他的牛》塑造了白黑女儿这样一个“死牛人”的形象,但凡是他自己认定的主张,无论别人怎么劝说也不会改变。即使是在牛瘟爆发、村里组织打疫苗的时候,白黑女儿也不为所动。“牛生病不生病,是跟着人的运气走的。”[10]427以白黑女儿为代表的社会大众在现代医学理论面前,表现出来的大多是这样一副顽固抵触、毫无说理可能的姿态。但等到自家的牛染上瘟疫,一头接着一头倒下时,白黑女儿这才开始对自身进行反思,“怨不怨我的错呢”[10]429,并且主动向医生寻求帮助。虽然最后延安来的兽医并未救活白黑女儿家的牛,但白黑女儿在见证了其他养牛户的牛“起死回生”后打心底里信任现代医学,开始自发地四处为它做宣传。这种转变反映出在疾病威胁面前,本土传统中人们对疾病、医疗的基本观念有所改变,不再盲从过去的迷信观念,而是自主地对现代科学知识进行辨择。
在欧阳山的另一部中篇《高干大》中,欧阳山延续了这一种叙事模式:乡村卫生运动联合起经济生产使主体启蒙发挥出了最大效能。小说中的任家沟刚经历过改革,土地革命和经济合作社的设立使得村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有关疾病的恐惧并没有因此消散,整个乡村世界在疾病面前仍旧毫无招架之力。“咱们这里,七八十里寻不出一个医生,请了巫神、神官来,花了钱没顶事。”[11]147一旦村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染上疾病,往往就会因为医疗基础设施的匮乏而失去生命。这种由疾病带来的生命威胁切实影响到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创设医药合作社、寻求现代医疗救治的呼声取代了无用的降神仪式。过去在乡村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民俗医疗体系面对现代医学话语的启蒙逐渐走向失效和崩溃。而这种医药合作社,实际上是一种由国家出面的“公医制度”。“国家根据保障并增进全民健康的责任经营医药事业,或将全部医药事业作为公有,借以有系统有组织地普遍施行医疗、保健、预防等工作。”[12]医药合作社的设立,大大改变了任家沟村民的身体、生命意识。装神弄鬼的巫神对于病痛的祛除起不了任何有用的功效。比起虚无缥缈的神佛,村民们更加信任被从领区被聘请过来的现代医生。这样一种有组织的医疗救治形式,反过来促进了本土社会关于身体、生命观念的启蒙。
借助对“卫生宣传”与医学实践的叙事,延安文学在打击传统的蒙昧医疗观念的同时,确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与卫生理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民间主体身体、生命意识的现代化改造,塑造出了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同样健康的现代化个体。
二、反巫神斗争与政治话语规训
通过引入“卫生现代性”的方式,乡村卫生运动推动了民众卫生意识的启蒙,进而从身体、生命的层面促成了民众主体的现代性转变。以乡村卫生运动为代表的现代医疗体系是弥合国民意识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差距的良好载体,其在一定程度上对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起到了舒缓作用。但是,对焦虑的舒缓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充满民族危难与国家危亡的四十年代,革命与救亡任务的存在时刻强化着这种焦虑。“讲卫生也是干革命”[9]2554,在巨大的变革焦虑下,《卫生组长》一语道破乡村卫生运动与政治革命之间的隐性联系:相较于启蒙,为政治服务才是开展乡村卫生运动的最终目的。在这种政治挂帅的运动形势趋导下,乡村卫生运动对民众主体开展的医学启蒙自然而然成为一种有限度的启蒙。
这种背景下,丁玲《在医院中》就成为理所当然的批判对象。小说中,年轻的产科医生陆萍被派遣到延安的一个乡村医院工作。工作期间,陆萍目睹了医院运作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乱象:院子里的注射针是弯的,做手术的橡皮手套也是破的,“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6]242,整个医院人浮于事,工作的重心根本不在病人的救治上。上海来的医生对乡村医疗卫生弊病的发现,《在医院中》实际上是对“五四”文学叙事模式的再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陆萍想要在医院进行的专业化改造是一种延续启蒙的尝试。但是,陆萍的行为并未获得院方领导的信任与支持,反而招来了对其政治身份的敷衍与猜忌。怀着苦闷抑郁的心情,陆萍最终离开了医院。黄子平在《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一文中,将《在医院中》描述成“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的环境,却终于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13],无疑触及了这篇小说最为核心的矛盾,即寻求启蒙的个体与强大的政治惯性之间相互颉颃的张力。这篇小说及其作者后来的遭遇表明,在政治惯性面前,启蒙成为一种难以掌控的变动性因素而需要加以控制。
在上述医学与革命相联结的情况面前,民众的主体性改造陷入了启蒙与政治的困境:一方面,乡村卫生运动极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人想象自身与世界的方式”[3];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重塑过程始终伴随着身体的国家化趋势。
作为乡村卫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巫神斗争旨在以批判改造的形式反对封建迷信,同时也因其明显的政治参与特征,成为实现民众身体国家化的主要方式和渠道。在葛洛的《卫生组长》中,这种身体的国家化以民间与官方两个相互对立的话语场形式出现。卫生组长“我”的妻子在一次外出中染上伤寒,针对如何治疗的问题,“我”与母亲和丈母娘产生了意见上的分歧。母亲和丈母娘希望“按旧的路数”请巫神过来驱邪,而“我”因为在村里宣称卫生工作的关系,极力反对巫神高金锁的参与,并主张向现代医学寻求帮助。面对“我”的坚持,母亲和丈母娘甚至用“看你有没有孝心,就在这一回”[9]2559这样的传统孝道观念来寻求“我”的妥协。双方在巫神面前所采取的截然相反的矛盾态度,代表了政治官方话语与传统民间话语之间的激烈对抗。在过去缺乏基础卫生设施的乡村,巫神因为承担了民间社会的医疗职能而具有特别的权威[14]。巫神文化作为一种民间独有的话语形式深深地镶嵌在民间意识里。但在具体的行医过程中,巫神的治疗行为常常掺杂神鬼精怪的内容,这不仅有悖于现代卫生理念,而且以一种顽固的地方性势力对民族国家政权的建设造成了阻碍。因而,乡村卫生运动中的反巫神斗争是一种将个体医疗行为纳入由政权主导的话语体的实践。借助这种话语实践与舆论造势,政治话语将现代国家关于健康的观念,渗透到每一个民众的固定思维中去,让民众认可这种国家观念,进而达成使国家力量更深、更广地渗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的目的[15]。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对生命主体掌控的范围和领域不再仅仅满足于公共卫生空间,而且更为深切地进入了以家庭为代表的私人空间。在这双重空间的话语压制下,个人的身体成为国家在民族生存复兴的话语下支配和干预的对象。
如果说《卫生组长》中的反巫神斗争以争夺话语主导权的温和方式,隐性暗示了革命境况下民众主体的国家化趋势,那么在欧阳山的《高干大》中,这种斗争形式联系上经济生产演变得愈发激烈,直接突显出革命情景下政治社会化的国家权力在场。与《卫生组长》不同,《高干大》中本应承担巫神改造任务的人,“合作社医生李向华只象影子一样一晃不见了,反巫神的担子放在高干大肩上”[16]。从医卫人员到政治干部,这一执行者的转变直观地显示出反巫神斗争的政治本质:改造巫神已经不仅仅是一项医疗卫生任务,更是一项“革命的既定任务”[17]。与之相对应,在实际斗争过程中,对巫神的批判也不再局限于医疗卫生内容。豹子沟的巫神郝四儿是《高干大》中最主要的巫神形象,小说除却对他在医疗过程中装神弄鬼、大搞封建迷信的批判外,还对他的“二流子”身份进行了驳斥。所谓的“二流子”,实际上是对陕北农村不务正业、不事生产、搬弄是非、为非作歹的各色人员的统称[18],这是一种从经济生产角度发展出来的道德考量。由合作社组织的春耕大会上,以郝四儿为代表的巫神们因为逃避劳动遭到了来自群众的集体批判。“对着咧,叫他们也说一说!说一说他们为什么不生产!”[11]243过去巫神惹人歆羡的生活水准,在大生产运动面前成为不劳而获的斗争典型。这反映出政权引导下的反巫神斗争,其目的不仅在于用现代卫生理念取代落后的医疗模式,还在于以一种观念改造的方式将所有人纳入到整个社会的生产机制内。在延安时期发展生产的大背景下,改造巫神与改造二流子之间获得了内在的一致性:现代国家政权以社会改造的方式夺取了对民间身体的医疗/治理权力,通过国家权力与广大民众身体的联结,国家政权渗透到民间世界,对民众身体进行了控制,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国家对民众主体的征用与驯服。
三、结 语
“延安时期,文学追求的目标不仅是承继‘五四’所开拓的现代性,更是为了契合民族国家的革命事业。”[19]在文化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双重任务面前,延安文学中的医疗卫生叙事在内容上呈现出来的“人的改造”主题以及现代医学理念,为延安时期现代健康个体的塑造提供了支持。但是同时,由于延安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过于浓重的政治图解色彩,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叙事表现出与政治意识之间密切的关联。因而,在表现人的主体启蒙过程时,虽然延安文学想要极力刻画出民众主体的成长与优化,但最终还是难免落入对政体国家与主体性压制的叙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