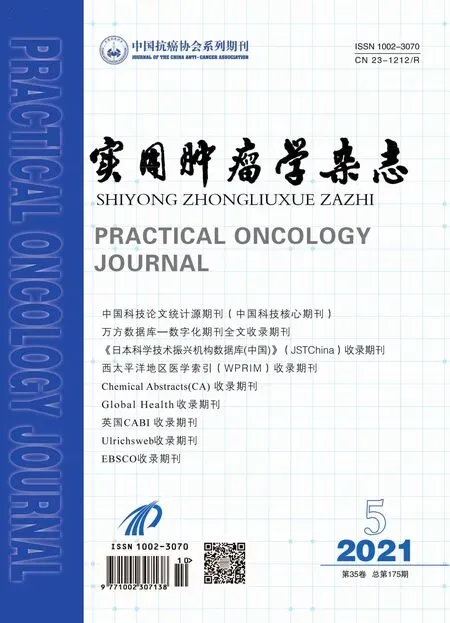肠道微生物影响结直肠癌化疗疗效的研究现状
2021-11-30韩淑玲姚洋刘超综述张艳桥审校
韩淑玲 姚洋 刘超 综述 张艳桥 审校
近年来,肠道微生物在结直肠癌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受到关注。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物通过诱导炎症信号通路、基因突变及表观遗传失调[1]等多种机制促进癌变,亦可通过影响代谢、免疫调节、细菌易位、酶降解、菌群多样性减少和生态变异等关键机制影响化疗药物的效率,调节宿主对药物的反应,从而提高疗效或介导毒副反应[2]。肠道微生物有望成为提高抗癌疗效的一个新的杠杆[3]。
1 肠道微生物与结直肠癌化疗药物相互作用
根据NCCN指南推荐,结直肠癌术后辅助化疗推荐氟尿嘧啶(Fluoropyrimidines)单药或以氟尿嘧啶为基础的联合化疗;以氟尿嘧啶为基础联合奥沙利铂或伊立替康互为结直肠癌的一、二线治疗方案,同时,根据原发肿瘤部位及RAS基因状态,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或西妥昔单抗;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或错配修复缺陷(dMMR)患者,可行免疫治疗。
1.1 氟尿嘧啶
氟尿嘧啶是一种抗代谢药物,在细胞内先转变为5-氟-2-脱氧尿嘧啶核苷酸,后者抑制胸腺嘧啶核苷酸合成酶,阻断脱氧尿嘧啶核苷酸转变为脱氧胸腺嘧啶核苷酸,从而抑制DNA的生物合成。此外,它还可以通过阻止尿嘧啶和乳清酸掺入RNA,达到抑制RNA合成的作用,影响蛋白质的生物合成。研究证实,在维生素B6、B12、核糖核酸代谢介导下,以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双歧杆菌属(Bifidobacterium)及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属为代表的肠道微生物参与调节氟尿嘧啶发挥作用。维生素B6调节细菌中的一碳代谢(OCM),进而调节核糖核苷酸通量,以介导宿主对5-氟尿嘧啶(5-FU)的反应[4]。维生素B12是塑造微生物群落的决定性因素[5]。此外,肠道微生物可作为5-FU诱导细胞死亡的调节器,通过核苷二磷酸激酶NKD-1的调节效应[4],细菌脱氧核苷酸池中的干扰可增强5-FU诱导的宿主细胞自噬和细胞死亡从而增强治疗效果。由此可见,肠道微生物影响氟尿嘧啶转化及代谢,进一步影响氟尿嘧啶治疗效果。
1.2 铂类
铂类化疗药包括奥沙利铂、顺铂、卡铂和洛铂[6],通过作用于细胞DNA,与DNA形成Pt-DNA化合物从而导致肿瘤细胞的凋亡。Iida[7-8]等发现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等益生菌能够刺激免疫细胞分泌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ROS可增强肿瘤细胞的DNA损伤,阻断肿瘤细胞的DNA修复和转录,导致细胞死亡,进而增强铂类的疗效。同时,益生菌对奥沙利铂引起的肠道毒性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9]。但也有研究证明顺铂与DNA结合,形成阻碍复制的交联,引起肠道共生菌变化,进而导致肠黏膜的完整性破坏,阻碍化疗的继续进行,并可能导致菌血症,危及生命。通过粪球灌胃来恢复肠道微生物群,可以促进顺铂引起的肠道损伤愈合,改善整体状态。这揭示了粪菌移植可以成为一种治疗化疗相关肠损伤的全新干预措施[10]。
1.3 伊立替康
伊立替康(CPT-11)是一种喜树碱半合成衍生物,主要作用于细胞周期的S期,通过抑制拓扑异构酶I干扰DNA复制和细胞分裂。在体内组织中被羧酸酯酶代谢为SN-38,伊立替康及SN-38通过抑制人体细胞DNA复制所必须的拓扑异构酶I,诱导DNA单链损伤,阻断DNA复制而产生细胞毒性,进而发挥抗肿瘤作用。但因其水溶性很低,极易引起严重的腹泻[11]。回顾现有肠道微生物与伊立替康相关研究,一项在黑暗刺鼠体内进行的研究表明,在单剂量伊立替康给药后,16srRNA测序分析粪便样本结果显示,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和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即β-葡萄糖醛酸酶产生菌)显著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数量显著减少[12-13]。另外一项研究显示,强化伊立替康剂量治疗,梭状芽孢杆菌簇XI和肠杆菌增加,这两种细菌都有机会感染病原体,增加感染风险。伊立替康联合5-Fu方案也可升高梭状芽孢杆菌簇XI和肠杆菌,但其升高程度低于单用伊立替康方案[14]。由此可见,伊立替康可改变肠道微生物组成。
1.4 靶向治疗药物
化疗联合靶向药物已成为晚期结直肠癌治疗的趋势所在,目前临床中应用最广的两种靶向药物分别是贝伐珠单抗和西妥昔单抗。贝伐珠单抗是通过特异性结合并阻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发挥对肿瘤血管的多种作用。西妥昔单抗是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IgG1型单克隆抗体,与癌细胞表面的EGFR特异性结合,阻断细胞内信号转导途径,从而抑制癌细胞增殖,诱导癌细胞凋亡。肠道微生物与靶向药物之间亦存在相关性,第一:化疗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的晚期结直肠癌患者,腐质霉属(Humicola)、红酵母属(Rhodotorula)、巨孢菌属(Magnusiomyces)的丰度降低,念珠菌(Candida spp)、银耳亚纲(Tremellomycetes)、双齿科(Dipodascaceae)、酵母菌纲(Saccharomycetales)、马拉色菌目(Malassezia)和香菇菌属(Lentinula)的丰度增加[15]。第二:肠道微生物与西妥治疗后引起的皮疹相关,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梭菌属(Clostridium)、梭杆菌属(Fusobacterium)、毛螺菌科(Lacetospiraceae)、瘤胃菌科(Rumen bacteria)、拟杆菌属(Bacteroides spp)为皮疹组差异菌属,相比于无皮疹组,皮疹组肠道微生物群α-多样性及β-多样性更高,且两组在菌群结构上差异较大,两组存在特异性菌群[16]。可见,靶向药物的应用改变肠道微生物的丰度,反之,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及某些特异性菌群与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密切相关。
1.5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
ICI现已被广泛应用于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使癌症的治疗方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现有数据支持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表达[17]、肿瘤突变负荷(TMB)[18-19]、致癌突变(Oncogenic mutation)[19]和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TILs)的存在[20]可作为生物标记物预测ICI治疗疗效的指标,肠道微生物群可能是与治疗反应性相关的额外因素。换句话说,肠道微生物可预测ICI在抗癌免疫反应中的作用程度[21-22]。一方面,肠道微生物通过将免疫细胞招募到粘膜、促进肠道相关淋巴组织成熟和刺激保护性上皮细胞的功能而具有免疫激活作用,增强T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的浸润,提高ICI的疗效[23]。另一方面,抗CTLA-4药物激活局部淋巴细胞,促进上皮屏障的恶化,从而改变肠道菌群,有利于类杆菌(Bacteroides)的富集,而类杆菌又可能在激活抗原提呈细胞(包括树突状细胞)中发挥作用,从而增强抗肿瘤T细胞的反应。抗PD-L1药物似乎与微生物群发挥协同作用,进而增强树突状细胞抗原提呈功能,从而增强T细胞反应[24-25]。相反,在使用抗生素或无细菌治疗的患者中ICI失去其治疗效果[23]。
此外,在临床前肿瘤模型及临床肿瘤患者中均可发现与抗癌免疫反应相关的菌种,如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脆弱类杆(Bacteroides fragilis)、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spp)、泰氏拟杆菌(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和普氏杆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在肿瘤学之外领域,它们也被证明具有促进健康的作用[8,26]。
2 小结与展望
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通过多种机制参与调节化疗药物、靶向药物及ICI作用,进而改变药物对癌症治疗的疗效和毒性。相应的这些治疗药物可对肠道微生物群产生影响,导致微生物群落失调,介导毒性反应,继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可见,肠道微生物有可能成为探索癌症治疗个体差异的重要贡献者,开启个性化癌症治疗的新兴领域,为结直肠癌患者带来更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