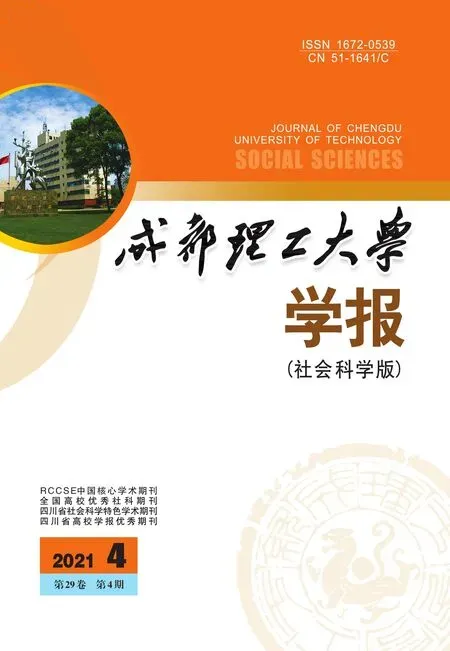枪支崇拜之“新虚构”探析
——《科伦拜恩的保龄》中的“集体恐惧”
2021-11-29何柏骏
何柏骏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207)
美国社会长期饱受枪支问题侵扰,2020年美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枪击事件,仅在7月4日和5日的独立日假期就发生411起枪击案[1]。1999年4月20日,科罗拉多州丹佛郊区科伦拜恩高中发生严重校园枪击案,惨剧造成两名枪手在内13人死亡,24人受伤,该事件震惊全美。2002年上映的美国纪录片《科伦拜恩的保龄》(以下简称《科》),以此事件为起点,试图探寻校园枪击案——这一美国社会“梦魇”背后的根源问题。有别于传统纪录片,《科》的特点在于它被归类为一种调查性记录片,或称作“新虚构”纪录片,其主要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部分具有后现代特色的纪录片,“这种虚构有一个非常重要而千万不可忽视的前提:基于对特定生活现实非常有理由的重新解读,即有根据地去怀疑和批判当下公认的相关真实,努力重新定义并构建已经或正在被放弃的那种可能是更为可信的真实”[2]。作为一部以真实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为线索的纪录片,《科》中的探索和调查基于大量的实地体验、真人采访和真实材料追溯。也就是说,此片的叙事是基于部分已发生的现实,但又质疑其真实性,从而尝试探索更多的、被忽略的现实。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也为本文讨论和挖掘美国枪支问题间接提供了现实参考依据以及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关于校园枪击案的诱因,《科》中的媒体和所谓的专家们给出了多种解释。例如,是“嗜枪如命”的美国步枪协会还是当时千夫所指的玛丽莲·曼森代表的重金属亚文化音乐,抑或是暴力电影、电子游戏的过错,或家庭的破碎导致问题孩童的增多,还是如标题谕指的两名酿下惨剧的男孩在案发当天早上参加的保龄球课程?然而,所有这些推断有一个共同特点,也是其缺陷,即仅将关注点放在青少年身上,而非聚焦“正题”——枪支,因为随着调查的进展,以上推测便难以立足。因为,如片中所示,德国亚文化音乐同样流行,加拿大年轻人也是暴力电影的拥趸,电子游戏主要来自日本,英国离婚率是美国的两倍,但这些国家的枪支问题并非如美国一般突出,那么对美国枪文化的探讨或许还得从更深层次原因入手。
事实上,《科》中追问的关键话题是:为何普通美国人能获得枪支,又为何渴望拥有枪支。前半句问题可以在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和美国相对自由、宽松的枪支弹药产业找到部分解释,但后半句关于对枪支的需求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目前,国内有关美国枪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宪法制度和历史、美国步枪协会(NRA)、美国枪支经济等几个方面,也就是说,基本属于考察第一类问题,较少触及第二类问题;而既有文献对纪录片《科》的讨论偏重于导演的创作艺术,少有挖掘片中的枪支主题,对其的深入解析或许也是对此片以及美国枪文化论域的一种丰富。美国人对枪支的热衷是一个较为艰深且待探讨的问题,在《科》中,一种笼罩在美国民众之中的 “集体恐惧”是美国枪支崇拜的一大症候。结合此电影纪录片文本,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析这一症结。
一、“恐惧论”与“集体恐惧”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出“自然状态”, 其认为人和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处于一种战争状态[3]94,并进一步指出,“由于人民这样疑惧,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3]93。霍氏将“疑惧”视为这种紧张、对立状态的动机和缘由,认为“当人们具有对象将造成伤害的看法时,嫌恶就称为畏惧”[3]39,而对其中“嫌恶”发生在当意向避离某种事物时;而“意向”则进一步解释为“人体运动的微小开端”[3]36。与此同时,霍氏还将恐惧分成两类,一是身体的恐惧(bodily fear),二是精神的恐惧(spiritual fear)[4]。枪械,作为杀伤性武器,一方面具有物理上的破坏力,能给予身体上的物理威慑;另一方面,枪械以其杀伤力,心理上也能予以施压。在《科》中,导演在采访好莱坞影星、前NRA主席查尔顿·海斯顿时,后者大方表示自己家中有枪,而且时刻上膛,尽管自己从未被侵犯过。对和他拥有相似想法和行为的人而言,拥有枪支即代表安全感的获得从而克服恐惧。但这种恐惧的缓解是和可能增加给其他人的恐惧共生的,因为一方持有枪支必然会对潜在的第二方造成威胁。为了尽可能单方面地克服这类“二元性”的精神恐惧,美国的男性、女性都成为了枪支崇拜者,同时,他们作为个体,所需消除的恐惧也有多元表征。正如帕梅拉·哈格(Pamela Haag)指出,美国迈进20世纪现代社会后,枪支产业在广告宣传中将枪支与男性(及其他美国“普通民众”)品格、愿望和优点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枪支经历了由19世纪的“男性工具”到“男性标志”的转变过程[5]。这样一种转变带来的效果就是将枪支与男性气质挂钩,即枪支是缓解男性对阴柔气质的恐惧。此外,如片中手持步枪在镜头前摆出造型的模特女郎那样,枪支也不再属于男性的专利,而当女性拥枪被精心地包装成一种时尚时,对枪支的离弃和排斥会产生对脱离时尚的疑惧。片中,密歇根州的一位女民兵坦露道,警察对她来说仅仅是拥有枪支而已,那么自己拥有枪支便可以第一时间保护自己和家人,在其说话时一旁就站着她年幼的女儿,也就是说,在部分女性眼中,枪支能消除对家的威胁的恐惧。
片中,在导演麦克·摩尔和一位枪击案受害学生父亲对导致美国枪支问题困惑不解时,穿插了一个从恐惧的视角出发,简要回顾美国历史的动画片段:从五月花号开始,清教徒们的一大初衷是为躲避旧世界的迫害前往新世界,不安和恐惧是他们冒险的重要动机;接着面对北美土著印第安人时,殖民者因为恐慌而对其诉诸暴力、种族屠杀;再到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后,由于黑人自由的逐步获得,白人出于对黑人的恐惧成立了宣扬白人至上的Ku Klux Klan(三K党),试图以白色恐怖来抵御黑色恐怖。再后来,到现代社会,美国白人“抱团”入住单一人种社区,紧锁房门,纷纷购置枪支和子弹。
对于“恐惧”,学者科瑞·罗宾(Corey Robin)提到,很少有人注意到《圣经》中人物经历的第一种情感不是羞耻而是恐惧,就在亚当偷吃禁果后在上帝面前坦言,他感到害怕,因为他赤身露体[6]1。这一说法可以有两层解释,一是这属于亚当的个人恐惧,二是鉴于《圣经》在西方精神世界的元典性地位,话语中多了塑造“集体无意识”的意味,即西方人的恐惧更像是与生俱来的。如果说亚当的恐惧只属于他自己,那么这种恐惧仅为个人恐惧,好比有人害怕坐飞机或轮船,但这只与个体心理、体验相关,几乎不对他人造成更大影响。科瑞·罗宾接着阐释了政治恐惧,即一种对集体安乐现状的损害,这种政治恐惧是由社会团体的冲突和社会内部矛盾引发[6]3。这实则是一种集体恐惧,即一个社会中的某一群体共同所有的恐惧,它可以视为集体中个体身上恐惧的集合,对个体而言,可理解为“成集体之恐惧”;同时它也是集体中每一个体所感受到的外部对于所处大集体安乐现状威胁的恐惧,即一种“为集体而恐惧”。
二、“恐惧”的历史和政治劝说
《科》中颇有戏剧性的一组镜头是:科伦拜恩枪击案当天上午,在科索沃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出兵空袭塞尔维亚,电视画面里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发表全国讲话并声称攻打时尽可能减少无辜人员的伤亡,话音刚落,电视记者便播报有医院和学校受到炮弹袭击,而仅仅过了一个小时,克林顿就宣布了本土科伦拜恩枪击案的发生。导演对于这样“巧合”的安排似乎在提醒人们注意个中的联系,有学者认为,通过采访、纪录片片段和个人反馈,该片试图将国内的枪支暴力和国际暴力联系起来[7]。另外,此片通过实地探查发现,每个月离案发地不远的空军基地会收到来自国防部的火箭头,每次运输都会经过学校,不过都发生在半夜。同样,科伦拜恩高中不少学生的父母就工作于离学校不远的武器工厂。这些事实探讨了美国社会中暴力或攻击性存在的又一方面,即国家政治层面。
学者基钦斯(James T. Kitchens)和鲍威尔(Larry Powell)提出“美国政治的四个支柱”即恐惧(fear)、自恋(narcissism)、消费主义(consumerism)和宗教信仰(religiosity)[8]1,其中第一个支柱便是恐惧。说起美国的恐惧,不得不提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四大自由”(The Four Freedoms),其中第四项就是“免除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罗斯福的话应验或者预设了美国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将经历的恐惧。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德国和日本给美国制造了自南北战争以来最大的威胁[8]9;二战之后,冷战拉开序幕;到了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渗透进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美国笼罩在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之中。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间,诸如《海滨》(OntheBeach) 和《失效安全》(FailSafe)等关于核交战的书籍和电影十分受欢迎[8]9。后来,美国又陷入越南战争的恐惧泥潭,一大理由是“政治中的‘多米诺理论’,即一个地区的关键国家落入共产主义阵营,那么其他的国家也会重蹈覆辙”[8]10。美苏对抗给美国社会带去的恐惧持续到1991年,直到苏联——美国人眼中的“他者”崩塌。到了21世纪,“911”事件的余震很长一段时间也未消退。2005年,在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四年后,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认为次年将会有第二次相似的袭击发生,45%的美国成年人袒露,对潜在的恐怖袭击的恐惧使他们倍感压力[8]12。关于国家层面的恐惧,影片讲述科伦拜恩校园枪击案前,穿插了美国在20世纪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一系列国际战争和冲突的视频资料。比如,1953年美国废除伊朗首相摩萨台并另立国王进行统治;1954美国推翻危地马拉民选总统,造成二十万平民罹难;1963—1975 美军在东南亚杀害近四百万人;1973年美国在智利发动政变,民选总统阿叶德遇刺;1977年美国支持萨尔瓦多军事领袖,战争造成七万萨国人遇害;1980年代美国中情局援助训练本·拉登党羽以对付苏联;1989美国入侵巴拿马;1990美国入侵科威特;1998 美国误炸苏丹药厂,然后到1999年科伦拜恩枪击案的同天空袭塞尔维亚。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的美国本土几乎未受战争硝烟的侵袭,那么政治、国家层面的恐惧又是如何传递给大众,从而去影响美国民众趋于认同他们这一集体所经历的来自外部的威胁呢?
“政治语篇的主要语用功能是参与国家事务,进而影响社会和改造社会。劝说指采用一定的策略,通过信息符号的传递, 影响他人的观念、行为, 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9]83。 政治语篇与劝说行为的功能相融合时,便催生了政治劝说话语,以此达到出于政治考量的劝说效力。总统通过电视对全美民众的发言属于官方话语,其目的和受众与国家重大事务相关,考察美国总统的全国发言或许有助于廓清此问题。《科》中再现了比尔·克林顿总统针对塞尔维亚空袭事件的讲话,后者在全国观众前对敌方的描述为“machinery of oppression”,即压迫机器。这一修辞层面的隐喻将一个国家和政权比作压迫机器,有两层意思:一是它具有压迫性,即使人屈服的,而压迫的对立面就是反抗;二是它是机器,机器是冰冷、机械死板的。除了《科》中提到的,在1998年伊拉克战争背景下的公开讲话中,克林顿对萨达姆·侯赛因政府的表述是“predators of the 21stcentury”[10]。 “predator”(可译作“捕食者”)根据韦氏词典解释,其本义指“一种主要通过杀死或吃掉其他生物体来获取食物的生物体”[11],这一喻体所指涉的意象具有暴力、残忍、极具攻击性等特征。此外,话语中的“21stcentury”并未到来,但已将对方视作新世纪的一大威胁。隐喻通过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认知另一领域的经验。另外,隐喻能够提供认知的新视角,赋予政治概念以新的意义[9]19。对敌方的形容,赋予其新的易于大众理解的意义,此举趋于契合美国的外交价值观,通过此话语劝说对美方的“先发制人”进行辩护。
另外,“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发表全国讲话宣称:“每个地区的每个国家,现在必须决定,要么支持我们,要么支持恐怖分子。”[12]修辞即劝说,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出了劝说的三种模式:一是人品诉诸,即展示说话者的品格;二是理性诉诸,关乎语篇中的逻辑论证;三是情感诉诸,表示说话者和语篇对听众和读者的影响[13]。小布什发言的立场很明确,即其他国家必须采取立场,这一表达实则为“情感诉诸”的劝说策略,即对受众情感的激起。 基钦斯和鲍威尔认为,布什将这次战争(反恐)定义为一种情绪(emotion),因此,美国人是与恐惧为战——“War on Terror”[8]14。再比如,在小布什的公开发言措辞中“evil”(邪恶)一词的出现频次较高,他先是称恐怖组织为“evil-doers”(恶人)[14];之后,在2002年,他首创“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一词称呼伊朗、伊拉克、朝鲜三国[15]。而“Axis”(轴心)一词最早是用于指称二战时期的法西斯阵营,这一表达从侧面触发了美国社会的恐惧联想。“evil”作名词主要表示痛苦、不幸和灾难等意思,可以看出,小布什的政治劝说是带有强烈的情绪、心理导向的,且在描述政治上的对立势力时常与带有负面情绪的词语进行关联以此营造充满威胁的话语进行恐惧劝说。在《科》中,就在小布什说完带有“evil-doer”那句话后,画面中马上配上了一张因恐惧而失声惊叫的成年女性的脸。
作为一种政治语篇,领导人在政府层面的话语对于社会和民意的影响应该是显然存在的,而克林顿和小布什总统的政治语篇实则是将其“为集体而恐惧”对民众进行劝说,使后者作为集体中的一员去共情这一恐惧,民间的不安全感和戒备心便会随之波动。
三、媒体话语权力:一种“恐惧规训”
“权力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力,即某行为体促使其他行为体做其原本不会去做的事情(其代价为前者可以接受)。权力也可以视为对结果进行控制的能力”[16]。在此基础上,学者王华生认为,话语具有对其他人意志和行为以及事态发展结果的控制能力,不同的媒介形态由于其自身的性质特征会抑制或强化某些话语的传播,从而形成话语权力[17]。也就是说,电视、报刊等媒介以其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也就拥有了自身的话语权力。提及话语权力理论,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观是分散、去中心和多角度的。在讨论拥有“训练”这一主要功能的规训权力时,其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18]。对此,学者何卫华认为,福柯排斥认为权力停留于宏观结构或统治阶级手中的观点,进而提出了“微型权力”,并称其为“规训权力”,这种权力不是个人的特权,而是一种机制,其通过策略和实践运作的[19]。据此观点,和政府、国家机构相比,那么普通大众媒体可以视为“规训社会”中的规训体制,它在相对微观的层面对观众进行“恐惧”训练,使其身体置身、习惯于这样规范化的训练中。
与一国总统公开讲话这类官方话语权力有所不同,至少从影响频率上讲,报刊、电视等媒体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更为贴近,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此外,美国媒体产业庞大且成熟。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在传播学中提出的“涵化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电视观众有关社会现实的观念更接近于电视所表述的符号现实,而非客观现实”[20]。也就是说,电视观众倾向于认为电视上目睹的就是现实中的实际情况。《科》中的媒体、企业、政客们毫无缘由地就对美国民众进行恐吓。比如,曾困扰美国人的“千年虫危机”(Y2K Scare),使成千上万的相关行业人员在千禧年到来前倍感恐慌,很多人担心电脑只工作到1999年12月31日,但实际上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万圣节苹果里的刀片恶作剧引发了巨大恐慌,在媒体的大肆报道下,人们由于害怕纷纷取消赠送糖果;还有电视节目用大大的标题警告人们电梯的危险等。不妨再看看和枪支、暴力相关的媒体话语。学者巴里·格拉斯勒(Barry Glassner)指出,1990年至1998年间,美国凶杀率下降了20%,但此期间电视新闻对于凶杀案的报道却增加了600%[21]。《科》的导演迈克·摩尔采访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颇为流行的犯罪类电视节目《警察》(Cops)的制作人迪克·赫兰(Dick Herlan),探讨为何这类节目都是以白人警察抓捕黑人或拉丁裔为题材。后者的回答是:愤怒、仇恨、暴力等内容更卖座,而容忍、谅解、接受这类题材收视率差。为呈现美国电视暴力报道的偏向性和选择性问题,片中剪辑了大量新闻报道,它们的一大特点在于:报道的高频核心关键词为“黑人”“男性”“嫌犯”等。那么,如片中指出,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塑造了“黑人-罪犯”这一刻板印象,白人对黑人的恐惧被放大,甚至被利用,黑人在刑事案件中可能成为替罪羊。比如,在纪录片中,密歇根州检察官解释道,在密歇根的郊区,也就是白人聚集区,拥有更多枪支,青少年也就更有可能获得枪支;1989年波士顿律师查尔斯·史都华杀妻后栽赃给黑人,警方一度信以为真,直到最后才真相大白。
围绕犯罪和暴力问题,上述例证试图说明,电视等媒体作为一种话语权力机制,它的策略主要通过提供具有选择性和侧重性的产品,其对美国受众的规训就是通过一套程式化同时服务于大多数人情感倾向的议题设置的训练,以此达到支配、控制、甚至造就人的行为。此处的议题表现为集中报道引发公众恐慌的群体性事件、刻画如黑人族裔的群体形象并渲染白人对黑人的恐惧心理。从接受规训的角度说,规训的受训者以个体为单位,直达其身体,“恐惧”也就得以被规训为生理机能。对一定数量的个体的有效规训的集合就会产生群体的规训,最终个体的“恐惧”也就上升为集体的恐惧,即“成集体之恐惧”,比如媒体规训下的白人群体出于对黑人群体的恐惧,促使前者通过普遍拥有枪支来缓解这一焦虑。
四、结语
《科》通过导演本人在邻国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做实地探访揭示:此市某街区接连好几户家庭都没有锁门的习惯,而美国的情况却大相径庭。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对此有过相似论述:“一个人外出时他会要带上武器并设法结伴而行,就寝时,他会要把门闩上;甚至就在屋子里,也要把箱子锁上。他做这一切时,自己清楚有法律和警察惩办使其免遭伤害的一切行为”[3]95。由于不安和疑惧,片中的部分美国人用三层锁对家进行全面防护,这种戒备既是物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也如文本所探讨的“恐惧”,拥有身体和精神两种维度。从此部“新虚构”记录片出发,以美国人的“集体恐惧”入手,阐释恐惧的哲学概念,并通过对照美国历史和领导人的政治话语以及美国媒介的权力规训,剖析了“集体恐惧”——这一美国枪支崇拜的症结,不失为探究扑朔迷离的美国枪支“成瘾”问题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