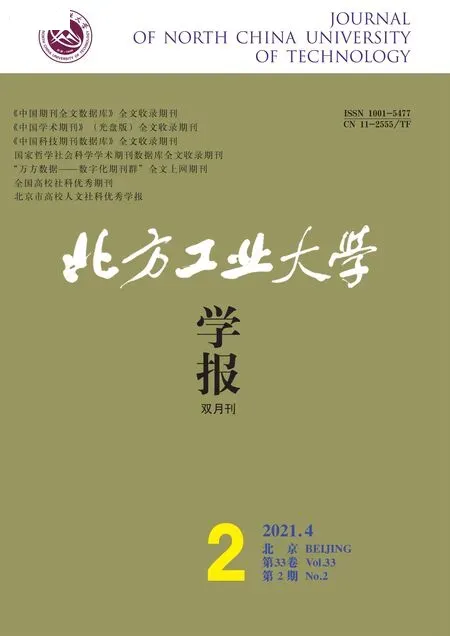中日传统戏剧中的“狂者形象”
——以《牡丹亭》与《松风》为中心
2021-11-28温彬
温 彬
(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560-0043,大阪,日本)
在东亚文艺史的长河中,一直延续着一种对于“狂”与“狂人”的探讨。而在中国文学与戏曲作品中,自“楚狂”接舆之后,狂人的艺术形象便更是层出不穷、千变万化。他们可以是滑稽的,例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也可以是正气凛然的,例如《四声猿·狂鼓史渔阳三弄》中的祢衡或者《疯僧扫秦》中的风波和尚;同样其也可以是深刻而灵性的,例如民间传说中的济公以及《红楼梦》中的跛道与癞僧。
同样,狂人的形象在日本文艺史中也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狂在日语中叫做“物狂(ものぐるい)”,日本能乐大师世阿弥曾在其著作《风姿花传》中将其作为能乐“九体”,即九种重要的模仿形象之一,并认为其是最富情趣的人体类型;同时,世阿弥认为“狂体”分为被附身而狂与因强烈的思念而狂两类,由此与狂相关联的能乐作品也大致被分为了两类;第一类是被神鬼附体之狂人(《歌占》《弱法師》《卒都婆小町》之类);第二类则是因事而导致情感爆发失控之狂人,例如被情人抛弃的男女、丢失了子女的母亲之类(《樱川》《松风》之类)。
总体而言,在中日两国的传统演剧中,都确实存在着对“狂”的强烈意识,这点体现在两国的诸多戏剧作品中。例如明代传奇《牡丹亭》里《玩真》一折中的柳梦梅则与能乐作品《松风》中的主角松风便是如此。柳梦梅因为对所拾得画中杜丽娘形象的强烈爱慕而产生癫狂之意,直将画中肖像当做是真人,要“早晚玩之、拜之、叫之、赞之”;而另一方面,《松风》的主人公松风因为对死去的情人在原行平的强烈思念而陷入狂乱的状态,将远处的松树错认为是在原行平而对其倾诉衷肠。由此可见,两部作品的共通性在于,主人公都因为强烈的爱意而陷入一种“狂”的状态,从而产生了二人“执幻为真”的举动。但更重要的是,即便行为举止一样,但由于中日两国的文化土壤之别,二人之“狂”的背后却是有着同样深刻却又完全不同的意蕴。
1 柳梦梅形象与晚明狂禅思想
《玩真》一出出自汤显祖名作《牡丹亭》第二十六出,但实际于情节上与其直接联系的则是第二十四出《拾画》。柳梦梅在赶赴长安取试途中受了寒疾,幸遇到书生陈最良搭救,将其携至梅花观中调理痊愈。柳于梅花观里春怀郁闷,遂在老道姑的指点下去观后一座废弃花园消遣散步。柳于假山处拾得一副画,并将画中女子(实为杜丽娘)误认作观音,要带回馆中供奉赏玩。而仔细观察之后,柳梦梅终于明白此画为“人间女子行乐图”,且为画中女子天人难辨之美貌所倾倒,甚至于产生了将画中人认作真人的幻觉:
【啼莺序】他青梅在手诗细哦,逗春心一点蹉跎。小生待画饼充饥,小姐似望梅止渴。
小姐,小姐,未曾开半点幺荷,含笑处朱唇淡抹,韵情多。如愁欲语,只少口气儿呵。
小娘子画似崔徽,诗如苏蕙,行书逼真卫夫人。小子虽则典雅,怎到得这小娘子!蓦地相逢,不免步韵一首。(题介)“丹青妙处却天然,不是天仙即地仙。欲傍蟾宫人近远,恰些春在柳梅边”
【簇御林】他能绰斡,会写作。秀入江山人唱和。待小生狠狠叫他几声:“美人!美人!
姐姐!姐姐!”向真真啼血你知么?叫的你喷嚏似天花唾。动凌波,盈盈欲下——不见影儿那。咳,俺孤单在此,少不得将小娘子画像,早晚玩之、拜之、叫之、赞之。[1]
整个《玩真》一出中,柳梦梅的心理状态从疑惑,到惊愕,终于到上引【啼莺序】时发展到了爱慕。但其真正的情感爆发则是在【簇御林】一曲中。此时的柳梦梅已经陷入了一种虚实难分、半醒半狂的状态,直将画中的美人当做了真人,不但觉得她“动凌波,盈盈欲下”,如画中走出来一般,更是要“拜之,叫之”,呼唤画中人。对此,《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记》中评论道:
人知梦是幻境,不知画境尤幻。梦则无影之形,画则无形之影;丽娘梦里觅欢,春卿画中索配,自是千古一对痴人。然不以为幻,幻便成真。[2]
“不以为幻,幻便成真”可谓是对柳梦梅此时形象的真实写照。另外,关于整部传奇中柳梦梅的形象,吴吴山三妇还提到:
此记奇,不在丽娘,反在柳生。天下情痴女子,如丽娘之梦而死者不乏,但不复活耳。若柳生者,卧丽娘于纸上,而玩之,叫之,拜之,既与情鬼魂交,以为有精有血而不疑,又谋诸石姑,开棺负尸而不骇;及走淮扬道上,苦认翁妇,吃尽痛棒而不悔,斯洵奇也。[3]
吴吴山三妇对柳梦梅的评价在于“奇”。而正如上记引文所述,吴吴山三妇所谓的柳梦梅之奇,主要表现在三点:首先是“卧丽娘于纸上,而玩之,叫之,拜之”,即上述《玩真》一出;其次是“谋诸石姑,开棺负尸而不骇”,即第三十五出《回生》。此一出中,柳梦梅冒着触律斩首的危险,联合石道姑掘开杜丽娘的坟墓,使其起死回生;最后是“苦认翁妇,吃尽痛棒而不悔”,即第五十三出《硬拷》。此一出中,柳梦梅前往丞相府拜访“岳父”杜宝,却被吊起来痛打,但其依旧不屈不挠。
纵观整部传奇,为吴吴山所称道的柳梦梅的种种奇行实际上与盛行于晚明的狂禅思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对狂禅思想的理解也成为我们打开柳梦梅这个形象所蕴含之秘密的锁匙。
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王阳明去世之后,其学散四海。而其中以其弟子王龙溪与王艮为中心的“左派王学”大行其道,尤其是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于晚明文人圈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受禅影响极深,从而成就了一种“禅儒互释”的学风,比如王心斋所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与洪州禅法所言的“平常心即是道”即有着共通性;而作为王龙溪思想重要命题之一的“立无念为宗”,其语则直接引用自《六祖坛经》。此派学人及受其影响者甚众,从而掀起了晚明狂禅风潮。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提到: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中略),泰州(王艮)以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4]
而黄氏所提及的颜山农,其门下弟子罗汝芳更是于当时名扬海内,汤显祖则曾是其门下学生;而与汤显祖交好的袁宏道、屠隆、以及其所倾慕的李贽等人也是狂禅思潮下的代表人物。如此看来,汤显祖受到狂禅影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唐宋以来的禅者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主观意识的膨胀。《古尊宿语录·卷四·镇州临济(义玄)慧照禅师语录》中写道:
如今学者不得。病在甚处?病在不自信处。你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狥一切境转。被他万境回换。不得自由。你若能歇得念念驰求心。便与祖佛不别。[5]
临济玄义认为,当时人学禅之弊病在于总是向外求解脱,最终为外境所缚而不得,所以想要求解脱,就只能求于自心。只要相信自己的本心,那么由此本心而发的一切行为,以及听到看到的一切都将是佛性的体现。说到底是要对内树立本心,对外扫除境界,从而达到一种与物浑然而通透无碍的境地。而这种思想也在晚明狂禅中深有体现。汤显祖的老师罗汝芳就曾经提到:“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学者直须源头清洁,若其初志气在心性上透彻安顿,则天机以发嗜欲,嗜欲莫非天机也。”[6]只要确立了本心(源头清洁),由此而发之物则皆为“天机”,这与临济玄义的“立处皆真”有着共通之处。对此,颜茂猷《说铃》则评价得最为中肯:
佛家悟道,则其心愈粗。所以然者,彼主扫除一切、直寻上去。扫除一切、则人情物理、俱不体贴、礼仪周旋,俱嫌曲局。直寻上去、则悟透其高、不胜自喜。奔轶绝尘、下视无物、故往往入其中者,未得其大悲大喜、无人无我、而飘思之气已生、傲睨之根已熟悉。一切狂禅、从是而起。[7]
对内“直寻上去”,对外“扫除一切”,直寻上去,就实现了自我的真性;破除一切,则就扫除了外部世界固有的是非标准,如此一来,对外部事物的一切标准皆由己心出,内外之别被打破,从而也就达到了临济玄义的“立处皆真”之境界。
由此看来,《玩真》一出中柳梦梅的形象则可谓是这种思想的具象化体现。《牡丹亭题词》中“梦中之情何必非真?”一语,可见其对于世间虚实的判断不在世俗之目光,而在己之“真情”。同理,于柳梦梅而言,画中之情也并非定是幻的。但正如吴吴山三妇所言:“不以为幻,幻便成真”,画是真是幻于柳梦梅而言并不重要,其早已“直寻上去”,以情做了主宰,由此情出发而扫除了外境(画)的真幻之别,只要情是真的,那么这画中女子于柳梦梅而言也必然真实不虚。归根结底,其以一片真情为本,并以之观照于外境,则外境也只能是其真情之体现,正因如此,其才能“卧丽娘于纸上,而玩之,叫之,拜之,既与鬼魂交,以为有精血而不疑”,从而也就达成了一种通透无碍而立处皆真的境界。世人以画与梦为幻,柳梦梅反而行之,以情立本,从而实现了自身与外部关系的再措定,这正是对颜茂猷所谓“扫除一切、直寻上去”的狂禅的“狂”之特征的最佳体现。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柳梦梅这个人物形象的内面中,确实带有狂禅之“狂”的特质,而正是其这种“狂”的内在特质,造就了上文提及吴吴山三妇所称道的种种外在的奇行。《玩真》一出已如上述,而吴吴山三妇所提到的“开棺负尸”、“吃尽棍棒而不悔”的奇行也是同样。柳梦梅对外部世界的意识是以“情”为前提展开的,所以其行为也都是以“情”为基础。正因如此,他才能不惧开棺负尸可能会带来的杀身之祸,也不惧棍棒所带来的体肤之痛,常人不敢做不愿做的事,他却能做得泰然自若,这都是因为其一切行为的主导只在于“情”。由此可见,柳梦梅的种种奇行,与其内在的狂禅之狂的特质是表里一体的。
2 《松风》中的狂乱与《六祖坛经》
无独有偶,日本能乐作家世阿弥的作品《松风》中也出现过类似的、人物执幻为真的狂乱情节。女主人公松风因为过度思念其去世的情郎在原行平,以至于将山上一颗松树当成行平而对其倾诉衷肠。全剧梗概大致如下:
游僧行至须磨浦,看到海边一颗松树似有人凭吊追悼的痕迹,从当地人口中得知这就是松风与村雨两位渔人的旧迹。夜晚游僧借宿一盐屋之中,遇见松风与村雨二人的魂魄。原来当年贵公子在原行平蛰居须磨三年,与她二人交好,返回都城之时,留下衣冠作为念物,和“卿若盼郎如松立,郎必归来探卿卿”的誓言,二人执念不灭,松风身着行平留下的念物起舞,俨然行平仍在世,屡约来相逢。清晨僧侣梦醒,唯听耳畔响起松风奏响的声音。
整部剧中充斥着一种生者必灭,会者常离的无常体验,例如松风村雨二人在汲潮时说到:“汲潮车,轮转浮世,万般皆空”“度浮世之业,行渔人扁舟。艰辛如梦世,似真亦似幻,汲潮轮空转,渔人泪濡衫。”“水无白日清,人无万年荣,荒野草尖露水命,人无万年荣。”[8]
诸如此类对于无常的感叹在全剧中并不少见(在世阿弥其他作品中也不少见),而于结尾处,世阿弥又将一切归结于一种涅槃式的寂灭:
言罢遁去无踪影,唯有潮起又潮落的海浪声。
声声拍打须磨浦,阵阵山风送来了关外雄鸡的报鸣晨。
听罢村雨闻松风,岂知今朝梦醒,妄尽情空[9]。
此处刻意营造出了一种静谧幽远的氛围,象征着此岸浮世的一切,无论是松风与行平的爱恋,抑或是松风的执念,都终究归结于彼岸永恒的虚无之中;而联接这两个世界的正是松风的狂乱:
仕手(松风) 冥途上,三濑川里泪涌涛急
满腔执念孽生深渊
哎呀呀,真是喜出望外!
你看那里不是行平他吗?正在召唤我松风。
且让我前往相会
连(村雨) 心存执念生邪相,不忘婆娑才坠此中
你看那是松树也,哪里会是行平他!
好不可怜!
仕手(松风) 休把胡言乱语讲
那怎会是松树,正是我那行平![10]
而正如前田妙子所言,《松风》的主题并不在于描写松风与行平的恋爱,其执幻为真之狂乱只是对梦幻泡影般无常现世的讽刺。致使松风狂乱的正是对行平的强烈思慕及其对行平诺言的执著,当松风明白了其所坚信为永恒不变的爱的诺言在无常的现世中只不过是梦幻泡影般的虚无缥缈时,由此导致的不安,与坚定,憧憬与绝望,多种对立情绪的激烈碰撞最终导致其陷入了一种虚实难辨的狂乱状态,而这就是前田所言的“中世情感的动因”。[11]
但世阿弥并非只是停留在对世事无常的感叹上,其深厚的禅学修为为这种狂乱提供了一个终极指归——即归于一种“本来无一物”的禅宗式的“无”的境地中。这既是此剧结尾处的“今朝梦醒,妄尽情空”,而这也是世阿弥作品中经常会出现的结尾。世阿弥自身与禅宗关系颇深,其与岐阳方秀等临济宗五山派禅僧一直有着密切的往来,自身也于晚年出家,皈依于曹洞宗补严寺门下。而其能乐理论书(伝書)中也对禅宗典籍以及禅师法语多有引用。《风姿花传》之后,“无”这个概念在其能乐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其经常会提到“无心之心”“无文之文”“离见之见”之类的概念。对此,日本能乐研究者天野文雄认为,世阿弥所言之“无”可以以《六祖坛经》中所谓“无念”“无住”“无相”之“无”来解释。即世阿弥之“无”与曹溪禅“之”无都实现了对二元对立的超越《六祖坛经》:“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12]因而从无的观点去看的话,世间万物都是平等一如的。而这点在其作品《山姥》中也有体现:
见得正邪一如之时,无非色即是空。
佛法即世法,烦恼即菩提。
佛陀即众生,众生即山姥。[13]
由此可见,世阿弥继承了曹溪禅的思想,认为平等一如才是世间万物的实相,而松风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真幻不分的狂乱,根本原因即在于其未能认清万物平等无分别之理,从而迷失于其对行平的执念。这正如松风发狂时村雨所感叹的一般:“心存执念生邪相,不忘婆娑才坠此中”。松风之狂起于松风之迷,松风之迷则起于其对行平的执念。归根结底,松风未能看清其与行平的恋情,以及行平所留下的承诺的虚幻性,而以为真实不虚。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当松风的企盼被无常的现世摧毁时,疑惑不安与绝望终将其推入了狂乱的深渊。《六祖坛经》说:“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14]此处之念即是因执着于境界而其的妄念,也是松风对于行平的执念。松风的狂乱可以说是对曹溪禅迷失论的具象化诠释,其正是因为心为外境所染,失去了“菩提本心”,才最终导致其落入了虚实难分的错乱状态。
前田妙子认为,能乐的狂乱之美需要通过对纯粹之“无”的把握来理解。世阿弥并没有将松风的狂乱作为剧的结尾,而是引导其走向了“本来无一物”的涅槃式寂灭。这象征着现世的无常与幻灭,也寓意松风因顿悟而从执念中解放了出来。结尾处二人对僧人说:“由于对此世的执念而现身于您的梦中,还请您给予我二人超度!”二人最终看清了自身对行平执念的虚幻性,而请求僧人予以超度。纵观松风由执入迷,由迷入狂,再由狂入悟的过程,可谓是对禅宗迷失论与顿悟论的最好体现。而不仅仅是《松风》,另一部作品《安达原》(又名黑冢)中也有类似的观念:
于生死中轮回 徘徊于五道六道之间
只在一心的迷失[15]
缠缚由心,生死轮回于六道,只在于一心之迷失,由此更可见世阿弥受禅宗影响之深刻。
3 汤显祖与世阿弥的时代背景与禅宗思想
综上可见,《牡丹亭·玩真》与《松风》中的执幻为真之狂都与禅宗思想有关,但很明显的是,这两种狂背后所蕴含的作者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汤显祖笔下的柳梦梅之狂,强调自作主宰,打破世俗标准的桎梏,体现了一种“随所作主,立处皆真”的无碍精神;而松风之狂则充满对现世无常的绝望与无力感,可见世阿弥与汤显祖对于“狂”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同样以禅宗思想作为基础,但完全衍生出了两种相反的狂者形象,其背后的意味则需要具体放在两国当时的社会与文化状况中去加以讨论。
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品经济和手工工场的发达程度可谓达到了空前的状态;社会的繁荣带了思想的转变,社会风气也随之“由俭入奢”,竞奢风气更是弥漫经济发达的都市地区:
流风愈趋逾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甚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16]
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松动也减弱了对思想的实际控制,人文思潮得以抬头。这主要也表现在对于人欲的肯定。于此,泰州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即是道”的口号,而李贽则谈道:“夫私者人之心也,人比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此类观念衍生到文学上,则产生了一股“主情论”思潮,除了对“情”的肯定之外,晚明白话小说与戏曲中也多有露骨的情欲描写,如《金瓶梅》《绣榻野史》等,而汤显祖的作品也不例外。
晚明的文学充斥对人以及人性的肯定,这其中也不乏禅宗的影响,马祖道一的洪州宗倡始“平常心是道”及五家禅的兴盛以来,强调本心的随缘任运,从而打破了戒律、教义等神圣权威,甚至发展到了“饮酒食肉不碍菩提,行盗行淫无妨般若”一般恣情纵欲的地步,诸僧所提倡的正是本心的绝对自由,做到“不与物拘,脱透自在”的境地。而这种态度也从根本上对狂禅思潮以及汤显祖的情欲观念产生了影响。“佛初出时指天指地,而赵州欲以啖狗子,此虽狂禅滥觞,义有攸在。”[17]可见晚明狂禅思潮的根源,还是在于洪州宗马祖道一一脉。
而《松风》作者世阿弥所处的社会状况则与晚明大不相同。其所处的室町时代以及之前的镰仓时代被称为“中世”,这正是日本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伴随着中世文艺理念展开的,是旧有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崩坏以及旧贵族(公家)的衰落。1192年,日本武将源赖朝于东日本开设镰仓幕府,武士阶层从此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相应的,旧王朝的贵族公卿阶层以及其所缔造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秩序也走向了瓦解。长期的战乱与旧有身份的丧失所带来的挫败与幻灭最终引导出了一种生者必灭、会者定离的世界观,而其在文艺中的表现则为对世事无常的无奈。不仅仅是物语文学,这种观念也体现于随笔文学与和歌之中。吉田兼好《徒然草》:“倘仇野之露没有消时,鸟部山之烟也无起时,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人世无常,倒正是很妙的事罢。“对此前田妙子评论道:“无论是于社会,亦或是历史而言,交织着人类深刻苦难体验的中世时代,其文艺思想源自于一种由挫折感出发而流向虚无的美学体验。”[18]而如上文所言,世阿弥的能乐谣曲的词章中也多有对世事无常的喟叹。禅宗的传入则将这种对无常的体验引向了一个终极归宿——即对于无常背后的寂灭(无)之体认,并从无的角度出发重新观照世界,最终达到身心脱落的涅槃境界。
而另一方面,禅宗在传入日本后与其本土原有的无常观有机结合,使日本禅宗更加适应当下环境的同时,也产生了其自身独有的精神体验。因此,以现世的厌弃与无常为基调的日本禅宗,比起洪州宗所强调的随缘任运与事事无碍,则更偏向于曹溪慧能的“无念”理念。松风正是因为不解此岸的虚妄无常,才导致自己妄想自缠,如蚕作茧,而只有去除妄念,才能得以解脱。于中世人而言,要从现世的苦难体验中解脱,只能寄托于无,而曹溪禅法的无念,正为其提供了精神上的归宿,世阿弥笔下的《松风》,正是承载了这样的一种意义;一切执念只不过是世人作茧自缚的痴迷荒唐,只有认识到自身执念的虚幻,才能顿悟菩提,解脱自在。
由此可见,汤显祖笔下的狂所接受的更多是来自洪州禅随缘任运而事事无碍的影响,而世阿弥之狂则更加偏向于南宗禅初期的无念观,二人对“狂”的意识之别,正是来源于早期南宗禅于洪州禅的真妄观之别。孙昌武认为:
但在早期南宗禅看来,在现实的人身上,妄心与净心仍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即是说,未见性的众生还是有妄心,转妄成净还要经见性的过程。这样,其基本立场仍主现实的众生心是虚妄的,尚有待去发现,悟得那不变的,永恒的清净真性……但马祖道一却发展出新的禅思想……人们不需要转妄成净去悟得自身本具的佛性,因为妄净一如,二者本来就没有什么区别。[19]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世阿弥与汤显祖笔下的狂者形象,其内面都同样具有强烈的禅宗色彩,且都以禅宗的净妄观为基础,展开了对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讨论。但是,鉴于两国的文化及时代背景之不同,即便是同样对待禅宗,二者的接受方式也取向也有着非常显著的不同。世阿弥与汤显祖笔下的狂者形象,其虽然都植根于禅的思想,但正因为对其接受的方式与取向的不同,从而使同根而生的两国戏剧文化各自结出了不同的果实。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异同,才构成了东亚戏剧文化的共通性与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