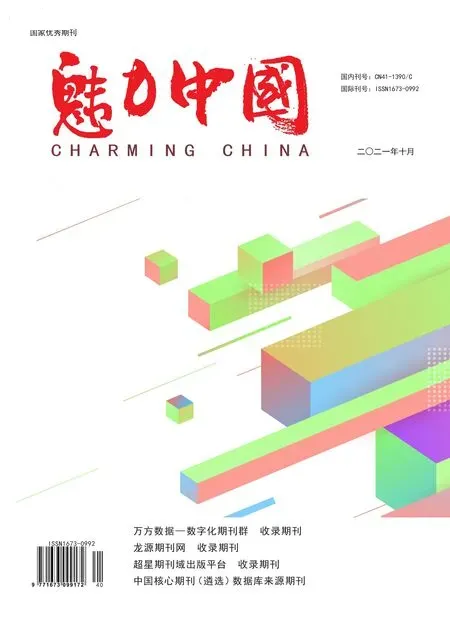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史铁生《那个星期天》的写作启示
2021-11-28许俊莹
许俊莹
(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学生作文总希望写点不一样的东西,如果真有不平常的经历,写点与众不同的东西的确容易吸引眼球——追新猎奇乃人之本性,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很不幸,绝大多数学生的人生履历中并没有多少新鲜的东西,一日复一日,无外乎上课——放学——上课,你如此,我如此,人人如此,有些同学觉得这有什么好写的呢?于是学生面对作文,忍不住慨叹:经历太简单,无米下锅,没啥好写呀。
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看看史铁生《那个星期天》吧。这篇课文的内容极其简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那个星期天,母亲原本答应带我出去玩的,我对此十分期待,可是,母亲忙于家务,没能带出去,我很失望。
事情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但文章却写得忧郁、感伤、令人唏嘘不已。为什么?因为事件虽然很简单,但作者内在情感却异常丰富充沛,跌宕起伏,从简简单单的事件中,我们读出了小男孩的期望、失望、遗憾,以及忙于家务疏忽了孩子的母亲的辛酸、无奈、心疼。
学生写记叙文,常常以为要写事,而且事情本身要吸引人,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但很不幸,学生本身阅历有限,寄希望于素材出奇出新常常令他们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
其实,学生写记叙文不妨向小说学习学习。严格说来,记叙文只是一个文类概念,本就包含以描写、叙述为主要写作方法的小说。很多文学作品本就很难说属于小说还是散文。比如,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把它视为记录名人言行故事的散文,恐怕也没什么不妥吧?《那个星期天》的作者史铁生的另一篇散文《我与地坛》最初发表时,刊物其实是把这篇散文放在小说一栏刊登的。
小说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1)生活故事化的展示阶段;(2)人物性格化的展示阶段;(3)以人物内心世界审美化为主要特征的多元化展示阶段。[1]学生希望所写事情本身跌宕起伏、吸引读者,实际上暗合了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实,写故事未见得比写内心更有力,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不得不从看得见的行动世界中掉过头,去关注看不见的内心生活”。[2]
如果拿小说类比,史铁生散文《那个星期天》则处于第三阶段,即以人物内心世界审美化为主要特征。当然,这三个阶段也绝非截然分裂。事实上,在人物内心世界审美化展示过程中,人物性格亦得以展示。比如,《那个星期天》中当“我”听说母亲要带“我”出去玩时,“我”是那样欢欣雀跃,急不可耐。“我跑出去,站在街门口”,为了“挨”时光,“我踏着一块块方砖跳”“我看着天看着云彩走”“我蹲在院子的地上,用树枝拨弄着一个蚁穴,爬着去找更多的蚁穴”“我坐在草丛里翻看一本画报”,那本画报其实早已“看了多少回”。当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时,“我”缠着妈妈,“走吧,您不是说买菜回来就走吗?”“母亲不是答应过了吗?”“整个上午我就跟在母亲腿底下:去吗?去吧,去吧,怎么还不走啊?”走吧……我就这样念念叨叨地追在母亲的腿底下,看她做完一件事又去做一件事。”当母亲推说下午去,让“我”“睡醒午觉再去”,“我”却“把午觉睡过了头”时,作者写到,“但这次怨我,怨我自己”,为了防止再次因自己失误错过出去玩的机会,在母亲洗衣服时,“我蹲在她身边,看着她洗,我一声不吭,盼着”“我想我再不离开半步,再不把觉睡过头”“我想衣服一洗完,我就马上拉起她就走,决不许她再耽搁”孩子对出去玩的热切盼望,孩子的天性在缠妈妈、盼妈妈的心态、动作中表露无余。孩子终究是孩子啊。
可是,孩子也是立体的人,复杂的人。“我”在贪玩的同时,又那么懂事。你看,妈妈说等一会儿再走,“我”便跑出去,站在街门口,藏一会儿,跳房子,看天看云彩,看蚁穴,看画报。当妈妈让“我”睡午觉时,“我”便乖乖去睡午觉,睡醒了,耽误了时间,虽然懊恼,也只是自责“怨我自己,我把午觉睡过了头”,幼小的“我”是懂事的,但当“我”一再的等待换来的是无休无止的家务,是“盆里的衣服和盆外的衣服”,以及时间不可逆转的流逝时,“我看着太阳,看着光线,我一声不吭”。读到这里,读者的心也忍不住一颤,为孩子的懂事,为孩子的失望,为孩子的落寞。
是的,在看似平淡无奇,没有多少波澜起伏的日常琐事中,我们触摸到了那个懂事又贪玩,贪玩又懂事的孩子的心灵。
那个母亲呢?作者虽是以儿童视角写的这一篇散文,但文中的母亲依然丰满、真实。首先,可以肯定,这是一位忙碌的母亲,买菜、洗衣,忙于家务。但是,就像读者丝毫不会质疑母亲的忙一样,读者也丝毫不会质疑母亲对孩子的爱。文章写到,当“母亲发现男孩儿蹲在那儿一动不动”,“不出声地流泪”时,母亲“惊惶地甩了甩手上的水,把我拉过去拉进她的怀里”,母亲“一边亲吻着我一边不停地说:‘噢,对不起,噢,对不起……’”。
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都不简单,都有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包括一个小小的男孩子,也包括一位平凡的母亲。任何人的性格都是复杂的二重组合[3],而且这二重组合——比如,男孩的懂事与贪玩,母亲的忙家务与爱孩子,它们各自的分量是多少,比例如何分配,在不同的孩子、母亲身上是不同的,具体的。
没有人是天使,也没有人是恶魔。哪怕是一篇小小的散文,从中我们也可以读出人的复杂性,在这复杂性中激发出我们对人的同情、共情。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史铁生《那个星期天》给我们的启示是:写好作文,不一定非得有动人心魄、跌宕起伏、与众不同的故事情节,那些看似平常,但引起了我们喜怒哀乐情感的日常琐事也可以写,重要的是,在简要描述事件的过程中,要能生动细致地写出事件刺激下人物的内心世界,不简化,不省略。“简化的蛀虫一直以来就在啃噬着人类的生活”。[4]就在我们细腻而生动地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过程中,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特征最终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
2020 年某小学五年级期末考试作文是《倾诉》。要求学生向朋友、长辈等倾诉心声。某学生的考场作文是这样写的:你们有没有想对别人说一些烦恼的事儿呢?你们没有,我有呀。
就比如说,为什么别人考试就可以考上八九十分呢?我为什么就是不能呢?写作文也写不出来。我为什么这么笨呢?
这次这个作文我是想了又想才写出来了。我现在头还恍恍惚惚的。我就是怕我又考个四五十分。这次作文真是太难了,我只能写在这里了。
全文一共只有142字,“为什么别人考试就可以考上八九十分呢?”“我为什么就是不能呢?”“我为什么这么笨呢?”隔着文字,我们都能体会到作者的“难”。可是,作者却欲言又止,说了“难”——这样的“说”是非常概况,非常笼统的,作者并没有告诉读者,“难”在哪里?我是怎么个笨法?我有多么想考个好成绩怕自己“又考个四五十分”?我怕考坏了,具体怎么个“怕”法?
对照史铁生《那个星期天》,我们可以给《倾诉》的小作者开一剂良药:把自己内心的担忧、吐槽,细致、生动地呈现出来,这就是作文啊,这就是文学啊。
或许这个小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不敢在文中吐露心声:或许,他太懒惰了,想表达的东西很多,但很多字不会写;或许,他的家里比较特殊,他怕说出来,会让别人笑话;或许,他觉得自己实在太笨了,付出了很多,但还是进步很小……总之,想倾诉的多是些“负面”的,“不堪”的,不好意思拿到台面的东西。殊不知,正如现实生活中人无完人一样,文学作品(包括散文,也包括小学生作文)中的人物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文学不必美化(当然,也不必要丑化)人物,如实地倾诉自己委屈,让笔下的自己接近生活中真实的自己,恰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缩短审美关照时的心理距离,而产生心理对位的效应,即读者会不由自主地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平衡比较,把作品中的人物作为自己的替代,人物的内心冲突(即性格冲突)不知不觉地激起读者的内心冲突,从而成为读者心灵的象征”。[5]
文学和历史不同。历史只记录已发生的事,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怎样的事件。文学则不同,不仅要记录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怎样的事件,更要记录这样的事件是如何发生,怎样发生,当事人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人物具有怎样的性格。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和作者一起经历选择的艰难,失败的沮丧以及成功的喜悦。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写好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学生写作缺乏素材,无米下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