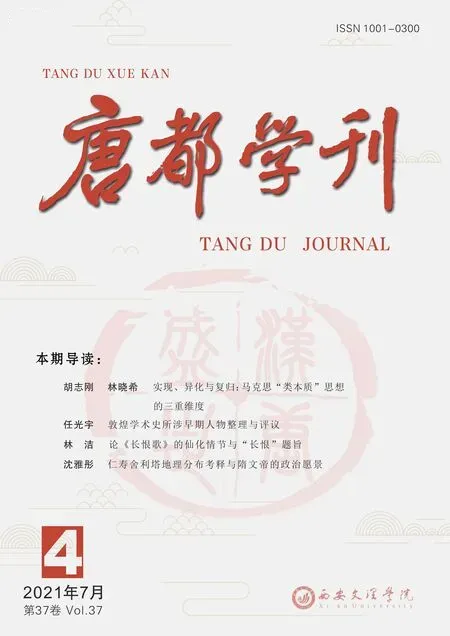近代早期的日欧贸易研究综述(16-17世纪)
2021-11-28张兰星
张兰星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 610068)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日本历史被一些学者称为“切支丹世纪”(1)切支丹是日语汉字,意为基督教。切支丹世纪又称切支丹时代,英语称Christian Century,中文亦可翻译为基督教世纪。。《剑桥日本史》对此解释道:“16世纪4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基督教在日本布道长达一个世纪,这段时期可称为切支丹世纪。”[1]这一称呼反映出当时的日本并没有与世隔绝。因为“切支丹”即指基督教,而基督教来自欧洲。如果仅从日本国内历史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称当时的日本为“室町幕府末期”“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期”或“德川幕府初期”。但如果将日本纳入世界的发展来看,16—17世纪的日欧已经发生关系。仅从基督教的传播来讲,日本切支丹世纪始于1549年沙忽略抵日传教,终于1614年德川家康禁教。不过,欧洲人在日本活动的准确时间应该从1542年葡萄牙人登陆种子岛算起,以1640年日本锁国结束。由此看来,西欧传教士在日传教的时间其实不到百年,双方的其他活动(以贸易为主)倒是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因此,用“切支丹世纪”来概述16—17世纪的日欧关系或时代特征,并不十分严谨。
16—17世纪,四个欧洲国家开展了对日贸易活动,他们分别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葡人最先抵日,日葡贸易的时间最长,贸易量最大,意义最重要。16世纪的葡人几乎垄断了日本外贸。西班牙人也较早(16世纪中后期)登陆日本,但他们几乎没有开展商贸活动。17世纪初,新教徒荷兰、英国人相继到来,他们都在平户建立了商馆。相比身为天主教徒的西、葡人,德川将军则更欢迎新教徒的英、荷人,因为他们不传教,不会对幕府统治造成威胁。这从侧面说明日本统治者不反对商贸交流,相反,他们很难容忍意识形态的“入侵”(传教活动)。到了1639年,家光将军(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决定消除天主教对日本的影响,下令驱逐全部西(班牙)、葡人。在此之前,英国人因经营不善,早早退出日本(1624)。荷兰人则坚持下来,成为最后的“赢家”。
一、国外日葡贸易的研究
(一)西方学者的研究
1542年,葡人首抵日本(2)对于欧洲人首抵日本的历史事件,东西方有共识,也有争议。大多学者赞同葡人初登种子岛意味着欧洲人首抵日本,但登陆的具体时间一直存在分歧。日本史学界以《铁炮记》的记载为准,认为葡人首登日本的时间为天文十二年(1543)秋。西方史学界的相关记载要多一些,加尔凡的《发现世界》、若昂·罗德里格兹(Joao Rodriguez,1558—1633年)的《日本教会史》、迪奥哥·多·库托的《亚洲志》认为欧洲人“发现”日本的年代为1542年。本人认为,日本方面的史料过于单一,且少有同时代文献佐证其准确性。而西方则有较多史料证明葡人的登陆时间,因此1542之说较为稳妥。。1640年,所有葡人被德川将军驱逐。日葡贸易的时间长、数量大、影响深远,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丰富(由于西班牙几乎没有开展对日贸易,相关记载也少,本文便不再详述日西的交流)。
英国史学家博克舍(1904—2000)专门研究近代早期欧洲人的海外扩张活动。他的四本专著为西方学者研究日葡贸易奠定了基础。博克舍的首部相关专著为《远东的葡萄牙贵族,1550—1770年》。该书视野宽广,不但介绍了葡人在澳门、日本的活动,还记载了他们在印度、东南亚的活动。博克舍从地理大发现角度,分析了葡人选择对日经商,而非对日武力征服的原因。他认为:“当葡人到达印度、摩鹿加和中国之时,其兴趣已经不是地理发现了,他们逐步向贸易者的角色转变。其实,这并不令人意外。当远东国家(中国和日本)能够提供足够的港口和商品之时,葡人的宗教热情和贸易激情都能够得到满足。他们没有必要与风暴进行无谓的搏斗,更无须寻找新大陆了。”[2]对于博克舍本人来说,该书尚处于相关研究的起步阶段。
博克舍的第二本相关专著为《日本基督教世纪,1549—1650年》,较上一本著作而言,该书的论述更深入和全面。首先,他采用横纵结合的方式,分析、论述了16—17世纪日欧的交流交往史。博克舍诠释了“基督教世纪”这一概念。从西方学者的观点来看,这一时期的日本历史由于有欧洲人参与,特别是耶稣会在日本开展了传教活动,故被称为“基督教世纪”。其实,该称呼有些“西化”,并没有准确概括日本当时的情况。博克舍也谈到:“在基督教世纪,日本发生了三件大事:丰臣秀吉统一全国;德川家康建立新幕府;日本进行了短暂的对外扩张,并与欧洲和东南亚建立起商贸关系。”[3]
博克舍的第三本相关专著《澳门来的巨船》是研究澳门历史、葡属亚洲史的重要史料。该书最重要的部分是“日本航线编年史”(Part I: The annual Japan voyages)。博克舍以编年的方式记载了1555-1640年葡人在澳门、马尼拉和日本开展的各种活动。该部分占据全书大半篇幅,该书剩余的二、三部分也以航海日志和书信为主。所以整本书更像史料汇编,而非史论专著[4]。
《日本封建社会的葡萄牙商人与耶稣会,1543—1640年》是博克舍较为成熟的代表作。准确地说,这是一本收录其相关研究精华的论文集。其中有总结,也有补充。在论文《“德乌斯号”巨船事件》(“TheAffairoftheMadredeDeus”)中,博克舍大胆地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民族特性与商贸活动之关系。他认为:“日、葡两国的地理位置及气候相似;两个民族都有类似阶级。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葡萄牙,商人的地位都不高。葡国贵族(fidalgo)与日本武士都代表中上阶级,是社会主流。”[5]I-43在论文《300年前的日葡商贸之旅,1630-1639年》(“PortugueseCommercialVoyagestoJapanThreeHundredYearsAgo, 1630-1639”)中,博克舍从现代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葡商向日本人贷款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导致日葡贸易衰落的重要原因[5]III-66-69。其论文《葡萄牙对日本的影响,1542-1640年》(“SomeAspectsofPortugueseInfluenceinJapan, 1542-1640”),从宏观角度分析了16—17世纪的日葡关系。博克舍曾大胆猜测:“如果1640年的日本没有闭关,如果日本一直与众多欧洲国家保持平等的商贸关系,如果日本能对基督教持宽容态度,那么佩里叩关时,日本将是何等情况?可能佩里会告诉其后人,日本人是我们(西方人)在亚洲必须面临的可怕对手,他们虽然地处东方,但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5]V-62
在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史学界,除了博克舍的研究,其它相关成果并不多。直到20世纪末,此领域的研究才逐渐兴起。尽管还没有出现直接相关的专著,但众多学者已经间接提到或谈到日葡贸易,很多人还尝试从新角度去理解日欧早期的商贸交流。
对于日葡的首次接触,德尔·玛指出,葡萄牙没有动用武力征服日本,而是以文明的方式(贸易)与日本开展交流,其原因是葡人不具备武力征服的条件[6]。虽然印度果阿驻扎有葡军,但日本太过遥远,发动远征无疑是劳师动众。对于此问题,亨舍尔认为葡人做出了明智选择。因为他们尚不清楚金银岛(日本)居民的文明程度。若贸然探索或征服,估计欲速不达。实际上,日本拥有强悍的士兵及先进的文明,且经历过战争磨砺(蒙古人曾试图征服日本,但被驱逐)[7]。正如美国学者维留斯指出:“在大西洋,葡人是探险者;在印度洋,他们是征服者;在远东,则是贸易者。”[8]
对于日葡贸易的过程或细节,学者们各抒己见。穆斯特博格将日葡贸易的过程划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1542—1600年诸侯(大名)与葡人的“无政府贸易”;第二阶段为1600—1615年“中央政府”(德川幕府)与葡人的“自由贸易”(3)此处的“自由贸易”非现代经济学中的自由贸易,“自由”是针对商人的活动而言。当时的日本禁止基督教传播,但欧洲商人可以在日本自由经商。;第三阶段为1615—1639年“中央政府”与葡人的“限制”贸易(秀中、家光统治时期)(4)所谓“限制”主要是指葡商的活动受到幕府监控和制约,其目的是杜绝传教士潜入日本。参见:外山卯三郎:《南蛮船貿易史》,東光出版株式会社1943年版,第362-366页。。这是西方学者首次对日葡贸易进行阶段划分,在相关研究中可谓一次突破。
对于教商关系,斯齐诺卡尔等人分析了传教士与葡商的关系以及双方的角色互换,他们认为:“一开始,耶稣会传教士的能耐大于葡商;后来,葡商在日本的地位和作用超越了耶稣会”。他还分析了在日耶稣会开展的商贸活动:“在日耶稣会参与贸易是个特例,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到大名们的斗争中。他们帮助一些大名的同时,也削弱了另一些大名。这种情况在九州特别明显,耶稣会很难进行‘单纯’的传教活动。”[9]布鲁斯(包乐史)从日本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探讨了17世纪日葡贸易的衰落原因。他认为,德川将军对宗教的态度决定了日本的贸易对象。将军考虑到,如果接纳新教徒荷兰人,既可避免传教,也可获得商品[10]。葡人虽然是做生意的好手,但他们无法割断与天主教的关系。葡人被日本驱逐,是迟早的事。穆多齐指出,葡商一直没有断绝与耶稣会的关系,从而影响到日葡贸易的正常开展。1637年,日葡关系变得紧张。当年的日本爆发了岛原起义,这是一次带有基督教性质的农民起义。无论葡商是否参与其中,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11]。
对于日葡贸易产生的影响,西方学者更多从世界历史的发展入手,阐述了日葡贸易在世界经济和世界交通中扮演的角色。艾利瑟夫认为:“葡萄牙在远东开展的生丝、白银贸易并非孤立的经济活动,而是南中国海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12]诺伊罗弗茨曾感叹:“葡人在世界范围的贸易活动,促使他们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据点。他们对中、日贸易的开发意味着世界贸易网络的初步形成。”[13]纽威特认为,澳门——长崎贸易是世界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现”日本之前,葡人在印度和马六甲建立了据点。澳门据点兴起后不久,日本长崎也被开发成贸易港。日本是葡人在亚洲打通的最后一个经济要塞,这样整个亚洲便被联系起来。另外,西班牙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建立了基地,这里与美洲大陆常有往来,西班牙船又将亚洲和美洲联通。1580年西葡合并后,亚洲各国的商品通过澳门、马尼拉被运到美洲。再加上日趋成熟的欧洲、非洲航线,世界主要地区的交通和贸易被“织成”网络[14]。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
日本史学界探讨16—17世纪的日葡贸易集中于两个时期。相关研究的初潮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明治维新取得初步成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较大发展,日本学者开始思考、研究大和民族变强的原因。这一时期,日本史学界未出现相关专著,众多学者只是在著作中零星提及有关内容。不过,还是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日欧早期的接触似乎与日本崛起有关系。
大森金五郎讨论了16世纪中期的长崎港,他将长崎与其他港口进行了对比,分析了各港之优劣。他认为堺(市)曾经是繁华的商业之地,但它离海岸较远,装卸货物有所不便。即便德川时代的堺再次繁荣,但其发展速度和规模已经赶不上长崎和平户了[15]。井口丑二等人重点介绍了长崎港之兴起。据其考证,长崎原是个叫“深江浦”的渔村。1558—1569年,葡船只是偶经此港。1568年,西欧传教士首次考察了长崎。他们认为这里不靠外海,港湾深度适合船只停靠,港口周围被高山环抱,无风波之扰,地形颇似里斯本,是一个不错的良港[16]。而且这里是基督教大名大村纯忠的领地,无论是经商还是传教,长崎都属最佳选择。高岛诚一高度评价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日本人在海外的活动。他说道:“那时的日本人不但到东南亚等地经商,还参与其他海外活动。比如原田孙七郎担任了吕宋经略,山田长政在暹罗朝廷身居要职,伊达政宗到欧洲进行了探访,岛津家久曾试图征服琉球。这些活动反映了日本人的壮志雄心和探险精神。”[17]对于16世纪的日欧贸易及交流,渡边修二郎甚至用“史无前例的繁盛”[18]来形容。
总体上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学者重在关注日本人从贸易中获取了什么,从交流中学到了什么,其描述和讨论的主角是日本人。这为日本史学界的相关研究确立了方向,即日欧的首次交流对日本历史产生了怎样影响、具有怎样意义。日本学者的视野更集中于本国历史的变迁,而非世界交通或贸易的发展,他们的研究重点与西方学者有所不同。
二战后,早期日欧交流的研究在日本再次兴起。该时期的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些学者着重研究耶稣会的对日传教活动,因其资料丰富,成果也就多(5)有关耶稣会在日布道的日语专著有:山本秀煌:《日本基督教史》上巻,洛陽堂1918年版;高瀬弘一郎:《キリシタンの世紀:ザビエル渡日から「鎖国」まで》,岩波書店2013年版;五野井隆史:《日本キリシタン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2002年版;吉永正春:《九州のキリシタン大名》,海鳥社2004年版。;另一些学者在有限的条件下(主要是指史料),开始研究近代早期的日欧贸易。该领域的成果虽少,意义却大。
外山卯三郎从宏观、微观角度分析了日葡贸易的全过程,他为日本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外山氏认为日葡贸易可分四阶段:(1)葡国走私商与诸侯(大名)的贸易(1542—1555年);(2)葡国官商与诸侯的贸易(1555—1587年);(3)日本统一政权与葡国官商的“自由”贸易(1587—1604年);(4)统一政权与葡国官商的“限制”贸易(1604—1639年)。外山氏基本概括了日葡贸易各阶段之特点,较之奥斯卡·穆斯特博格的分段法,外山氏更注重日葡贸易的细节变化[19]。高濑弘一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欧洲传教士在日本的活动,但他仍然没有忽略当时的日欧贸易,其专著《キリシタン時代の貿易と外交》以及《キリシタン時代の研究》(日语キリシタン指基督教)是相关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两本著作以日本人为中心,探讨了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以及他们对外贸的态度和反应[20]。另外,学者木下勇太郎分析了日葡早期的走私贸易,认为战国末期(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前)的日葡贸易最为“自由”。当时的葡船能在任何港口停靠,各大名也可以自由竞争,以招徕葡船去其领地停靠(贸易)[21]。吉永正春详细介绍并分析了葡船停泊过的港口。尽管葡人能够自由选择港口(博多、山川、鹿儿岛、堺等地),但他们还是想寻找一处相对安全、稳定的停靠点,这是葡商和传教士共同面临、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2]。
还有日本学者出版了相关的英文著作,竹越与三郎是其中代表。竹越氏继承了日本学者的一贯思路,其视野仍放在日本人一方。他认为,日欧贸易能够持续开展,与德川家康的个人意志有很大关系(17世纪初)。一方面,德川家康厌恶耶稣会传教,一直想根除其影响(驱逐所有葡人);另一方面,他又想依靠葡商发展外贸(葡商必然与传教士有联系)[23]。家康统治时期,禁教与通商就这样“博弈式”地维持着。竹越氏认为,在日本历史中,像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样重视外贸的统治者并不多。他们比很多日本人都看得更远,并对外来文化持宽容态度。只可惜其外交策略和远见卓识没有被后人继承。
总的来说,二战后日本的相关研究更加丰富。学者们对材料的挖掘更深入,对问题的分析更透彻,对观点的提炼也更新颖。尽管如此,日本学者仍然将目光局限于本国历史范畴,重在关注日本发生的变化,忽视了日葡贸易对其他国家、地区产生的影响,也忽略了日本在世界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二、国外日兰、日英贸易的研究
16世纪,抵日活动的欧洲人仅有天主教徒的西、葡人,但到了17 世纪初,新教徒荷、英人先后登陆日本。1600年,荷兰探险船首次造访日本。1609年,平户迎来了第一艘荷兰商船。1613年,英国船首次抵日,并取得德川幕府准许贸易的朱印状。这样看来,17世纪初的日本便形成欧洲四国同时对日开展贸易的局面。就西欧各国在日本的贸易份额来看,葡萄牙占主导地位,其贸易量最大。西班牙人对日本市场不感兴趣,他们更热衷于在日传教,双方几乎没有贸易互动。英、荷虽同为新教国家,但两国很难共享利益,他们在日本展开了商业竞争。日英之间的贸易量一直不大,由于种种原因,英国人于1624年败兴退出日本市场。最初,日兰贸易量也不大,但荷兰人坚持到最后,在日本锁国前夕,荷兰对日贸易量超过葡日贸易量。在日本锁国后,他们仍然留在出岛(长崎港附近的人工岛)开展商贸活动。
日兰关系的重点在于荷兰人的成功。古德曼指出,荷兰人正确认识到,搞好与幕府的关系是保证贸易成功的关键,而要想取得幕府的信任和赏识,就必须做到态度“端正”和服从将军。巴达维亚总督曾告诫东印度公司员工:“你们不要在日本制造麻烦,必须适应形势,耐心等待机会。幕府不能容忍对抗,你们应该尽量谦恭,我们的角色就是可怜的商人。在这个国家,越是这样,就越能得到尊重。这是维持日兰关系的宝贵经验。”[24]道齐认为:“在日荷兰人从不传教,他们坚持按日本的传统习俗办事。”[25]荷兰人深知基督教在日本不受欢迎,而且发现传教已威胁到幕府统治。登陆日本之初,荷兰人就坚持“只经商,不传教”原则。这恰好反映了新旧教的不同之处,新教教义鼓励资本家追求商业利润,而天主教却恰好相反。岩生成一更是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具备现代株式会社(股份公司)性质,公司受荷兰政府保护和支持,在亚洲享有各项垄断权,而西、葡几乎没有这样的公司。”[26]荷兰人在日本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公司制度的成功。普拉卡奇还指出,荷兰人能够成功插足远东市场,必须感谢他们的“老师”——葡萄牙人,正是葡人构建的贸易网络成就了荷兰的成功[27]26。简森认为,荷兰人善于利用舆论攻击葡人。他指出:“荷兰人经常诋毁天主徒。荷兰虽不能在贸易上压倒葡萄牙,但经常制造不利西葡的言论。他们宣扬耶稣会企图教化所有日本人,颠覆日本政权,要将日本再次卷入内战。”[28]这些舆论攻势看似薄弱,但对葡人却是致命的,因为德川将军最担心意识形态对其政权的威胁。
17世纪初,继荷兰人之后,新教徒英国人抵日,他们仅为贸易而来。英国商馆只在日本经营了10年(1613—1623)便被迫关闭,其失败原因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相比其他欧洲人,英国人最初颇具优势,他们得到白人武士、英国领航员威廉·亚当斯(其日文名为三浦安针)的大力协助,德川家康也因此偏袒英国人。另外,英国人信仰新教,不在日本传教,这令家康放心。奇怪的是,在如此明显的优势之下,英国人却没有把握住机会,并在很短时间就退出了日本。
巴塞特认为,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面临几个难题:英、葡一直在印度争夺据点和统治权。双方均为此耗费了巨大的人、物、财力;在其他亚洲地区,双方也展开了激烈竞争。特别在东南亚,英、荷双方都竭尽全力,争夺香料贸易权;(英)东印度公司最初的资金有限,如果要长期资助远东的平户,似乎不太可能。巴塞特认为,正是(英)东印度公司的不成熟,造成了平户商馆的最终关闭[29]。为了保全印度利益,英国人只能放弃日本。迈克尔·库珀认为,英国人选择了错误的贸易商品是其败走日本的主要原因。正如当时英国指挥官约翰·萨利斯指出:“我们带来的主要商品是毛织物,……日本人之所以不感兴趣,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日本大部分地区比英国温暖)。另外,日本的丝制品工艺高超,确实好看。如果要让日本人购买毛织物,除非我们以身作则。”[30]424提莫也质疑英国人坚持卖毛织物的策略:“就连平户的英国人都很少穿冬装,这里显然更适合穿丝绸做成的夏装。所以,毛织物根本没有市场。如果日本人在冬天作战,毛织物尚有作用。但战国时代已过,而且日本并非长年寒冷。这种商品在第一年可能有人买,但以后便无人问津了。”[31]相原良一则认为,英国人无法打开中国市场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如果中、英无法建立直接的商贸关系,平户商馆就基本失去了存在意义[32]。总的来说,近代早期日英交流的资料较少,成果不多,估计与其持续时间短有关系。
三、国内相关研究及趋向
相比西方和日本,中文学术圈对16—17世纪日欧贸易的研究相对较少。首先,相关的中文译著就不多。苏布拉马尼拉姆的《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亚洲政治的重组”一章提到了日葡两国早期的交流,但其重点在基督教对日本的影响,谈到贸易的地方不多(6)参见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何吉贤译,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年版。。速水融、宫本又郎合著的《日本经济史1:经济社会的成立,17—18世纪》介绍了德川幕府的外贸政策,参考价值较高的章节为“德川幕府的限银政策”。17世纪初的限银政策是幕府控制外贸、把握贸易主动权的重要举措。书中指出,限银并非限制日本白银被运出,而是限制日本精炼银的生产和输出。德川幕府新铸的银币最初不受欢迎,因此许多商人私下交易精炼银。从禁运精炼银到广泛使用银币,德川幕府大概用了30年时间。总体来说,限银政策取得了成效。17世纪30年代,精炼银的输出明显减少[33]。特恩布尔在其《最后的武士》中谈到了欧洲火枪对日本政治、军事的影响。火枪最初也是日欧贸易的商品之一,但后来日本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学会了制造、使用火枪。火枪在日本的应用超过了其作为商品本身的意义,甚至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火枪传入日本前,骑兵仍然是取胜关键,但自从织田信长使用轮流齐射(7)“轮流齐射”指火枪步兵部署为两排或者三排,前排步兵射击的时候,后排抓紧时间装载弹药,而且要尽量缩短动作重复的时间,这样步兵就能够专心装弹。日本人采用的二段或三段射击法,欧洲在1594年才出现,并在17世纪30年代才开始广泛使用。Geoffre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40.战术后,日本乃至世界的战争模式都发生了革命性改变(8)有关火枪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请参见张兰星《“切支丹时代”欧洲火枪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载于《史林》2010年第2期,第158-161页。。
其次,中文学术圈尚无学者专门从事早期日欧贸易的研究,更没有相关专著。郑彭年的《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提到了日欧的早期交流,因此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显得弥足珍贵。但其重点在文化,而非经贸。季羡林的《糖史》并非研究日欧贸易的专著,但却出乎意料地提到了相关内容。糖历来是中日贸易的重要商品。《糖史》介绍了中国明代的制糖术、日本人吃糖用糖的习惯以及中国糖的出口情况。季羡林认为:“荷兰不产糖,日本输入糖(荷兰船运来),必是中国之产,其理自明,无待论证。”[34]高淑娟、冯斌的《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以封建末期贸易政策为中心》提及了葡、荷、英三国的对日贸易,日文资料颇丰,只是其论述侧重于中日比较。若要重点研究耶稣会在日本的传教活动,李小白的《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是价值较高的参考资料。就日欧贸易而言,该书可以提供丰富的背景材料。还有一些论著零散提及了日欧贸易,比如黄启臣的《澳门历史》、费成康的《澳门四百年》、戚印平的《远东耶稣会史研究》等。
近年来国内期刊刊出了一些相关论文,虽数量不多,但有关研究已然起步。李小白、顾卫民讨论了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长崎及澳门之间的贸易活动。李小白在其论文中指出,耶稣会不但公开买卖生丝,还私下开展走私贸易(交易黄金等商品),并将这种交易称为“隐匿贸易”[35]。顾卫民描述了耶稣会士参与贸易的方式,探讨了耶稣会内部对此事的不同看法[36]。张廷茂在《17世纪30年代澳门——长崎的贸易危机》一文中提到,17世纪葡商在日本(向日商)不理智地大量贷款,是造成日葡贸易衰落的主要原因[37]。澳门文化局主办的《文化杂志》也刊载了一些相关论文。戚印平在《文化杂志》上发表了3篇有关日欧贸易的论文:《加比丹·莫尔制度与早期澳门的若干问题》(2004年)、《加比丹·莫尔及澳日定期商船贸易的若干问题》(2005年)、《加比丹·莫尔及澳日贸易与耶稣会士的特殊关系》(2005年)。三篇论文均与加比丹·莫尔(大船长)有关,文中引用的资料颇多。可以看出,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近代早期日欧的商贸交流。相关论文还有赖泽冰、汤开建的《明代的澳门与长崎——以1608年澳门日本朱印船事件和1610年长崎葡萄牙黑船事件为例》[38],李德霞的《近世日本与西班牙的贸易》[39],赵曼婷的《日本锁国体制的透气窗——出岛》等[40]。
当下,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基本涉及宏观领域,国外的相关研究已进入微观领域。从20世纪中后期起,国外期刊陆续刊出了一些有关日欧贸易的单篇论文。这些学者从某种商品或某类交易入手,探讨了16—17世纪的日欧贸易,这逐渐成为一种研究趋势,即学者们将相关问题细化了。比如,布朗则认为,日本之所以购买大量黄金,是出于铸币需要。在所有的金属货币中,黄金的价格最稳定[41]。小叶田淳认为,日欧的黄金交易将整个亚洲卷入了金银“游戏”。除了中国,其他亚洲地区的黄金也被运往日本,导致远东各国均出现金银兑换市场[42]。阿特威尔曾说:“16—17世纪,日本和美洲白银不但促进了明朝丝织业和陶瓷业的发展,还将中国卷入世界贸易圈。如果没有白银被运进中国,恐怕明朝将面临财政困难。”[27]44库伯对日葡生丝贸易的数量及运作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他认为,澳门据点的繁荣与生丝交易息息相关,澳门政府的税收基本来自对日生丝贸易[30]428。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领域的研究尚有较大的发掘空间,其未来的趋向有三:第一,相关研究可以更加细化、微观化和多元化,日欧贸易中的很多内容可以单独提出来进行研究。一些日本学者已经开始探讨南蛮饮食对日本的影响。至今仍受日本人欢迎的油炸食品天妇罗其实源自葡萄牙[43]。而且日本人最初只吃野鹿、野兔、野猪肉(9)据竹越与三郎记载:“日本人本来不养猪。欧洲人将猪带入日本后,他们才开始制作腌肉。”参见:Yosaburo Takekoshi,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Japan, Vol.1,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315. 学者郑彭年认为:“日本人要食野猪肉,但不养猪。”参见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学者李小白记载道:“也正是从这时开始(16世纪),日本人知道有香烟,还知道可以食猪肉和牛肉。”参见李小白《信仰·利益·权力——基督教布教与日本的选择》,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综合以上史料,本人暂且认为,在欧人到来(日本)前,日本人只食用野猪肉。接触了西方文化后,日本才开始养猪,食用家猪肉。由于猪肉自古是人类的主要肉食,所以就日本人是否食猪肉以及何时开始食猪肉,是可以且值得研究的题目。,不杀牛、马等家畜,这是当时日本的风俗。但随着南蛮船的到来,欧洲的食肉习惯传到日本,日本人也开始吃牛肉了。还有,16—17世纪的日语受外来语的影响较大。比如パン(面包)、カステラ(蛋糕)、ボロ(球)、ラシヤ(呢绒)、カネキン(细棉布)、ジエバン(汗衫)、ボタン(纽扣)、タバコ(香烟)等假名就是从葡语转化而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跨学科问题。若仔细寻找,深入挖掘,诸如此类的选题还有很多。
第二,对16—17世纪的日欧贸易作延续研究。17世纪初,葡、西、荷及英人都在日本开展贸易,但在1640年日本锁国后,并非所有欧洲人都断绝了与日本的关系。新教徒荷兰人成为唯一获准留下的欧洲人,日兰双方的贸易活动及“和谐”关系持续了近300年。这样看来,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始终与欧洲保持着贸易联系,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重视(10)中文学术圈对17—19世纪的日兰贸易缺乏研究,但对兰学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涉及日兰交流、兰学传播的专著有郑彭年的《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赵德宇的《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立——中日西学比较研究》、宋德宣的《日本文化结构演变论》等。相比专著,相关论文更多,比如有冯玮的《概论20世纪以前日本“西学的基本历程”》《日本“西学”的初创时代:南蛮学时代》;赵德宇的《试论南蛮文化》《试论兰学形成的社会基础》《西方科学初传日本及其历史影响》;刘小珊的《兰学·洋学——日本人实理实用精神的启蒙》;刘天纯的《论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分歧及其特点》等。相关硕博论文有王兵的《兰学的传播发展及其对明治维新的影响》(硕士论文)及刘维龙的《兰学对日本近代科学的影响及对日本近代化进程的作用》(硕士论文)。不难看出,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兰学、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化史的研究。系统分析日兰贸易,详细介绍荷兰商馆的专著或论文却很少见。关于日兰贸易的外语专著有:Grant. K. Goodman, Japan and The Dutch 1600-1853, London: Curzon Press, 2002;Drs. Dirk J. Barreveld, The Dutch Discovery of Japan: The True Story Behind James Clavell’s Famous Novel Shogun, San Jose: Writers Club Press, 2001;C. 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Hutchinson, 1977;石田千尋:《日蘭貿易の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館2004年版;鈴木康子:《近世日蘭貿易史の研究》,思文閣2004年版。。
第三,以日欧贸易为基础进行比较研究。日本近代之崛起一直是史学界热论的话题。近代日本(20世纪前)与西方进行过两次意义重大的交流。第一次是16—17世纪(切支丹世纪)的日欧商贸交往。第二次为19世纪的明治维新(11)也有学者认为日西(方)经历了三次重要交流:(1)16—17世纪切支丹时代,日欧在宗教、商贸方面的交流;(2)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吸收和效仿;(3)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重新崛起的过程。三次日西(欧)交流均伴随着日本社会的重大变革及快速成长,任何一次碰撞都不容忽视。参见:Michael Cooper, “Japan and the West, 1543-1640,” Ainslie T. Embree and Garol Gluck, Asia in Western and World History: A Guide for Teaching,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p. 443.。史学界对明治维新有较多、较深入的研究,但对16—17世纪的日欧接触少有探讨。如果将两次交流交往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日本现代化的进程,或者说更加透彻地分析近代日本成为强国的原因,其历史和现实意义非同寻常。除了宏观对比,还可以开展一些微观比较。比如,我们可以将日英、日兰的初期交流进行对比。两国均为新教、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又都是海上强国,还都在平户建立了商馆,但为什么荷兰成功、英国失败。当然,这些只是笔者不甚成熟的思路,诚望诸多学者参与到相关研究和讨论中,这不仅是对笔者的帮助,也能促进日本史、世界史、东西交流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