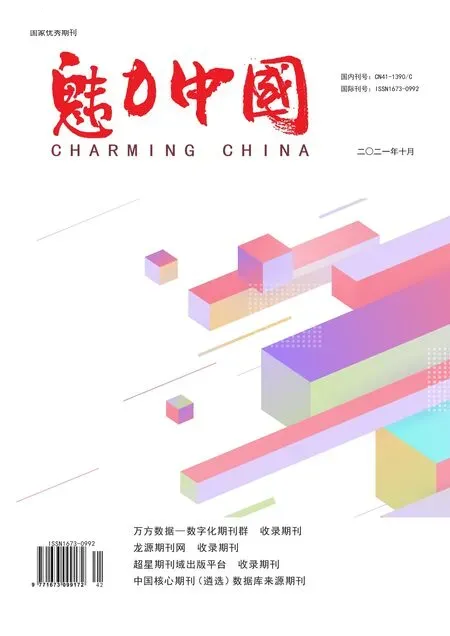老子“有生于无”思想之我见
2021-11-27何苗
何苗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有生于无”出自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自有对《老子》思想研究始,“有生于无”中展现出的宇宙生成理论就备受关注。但“有”是什么,“无”是什么,“有”和“无”到底是什么关系等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而随着帛书和楚简的出土,本就没有定论的问题更加混乱。今试从文本和思想两个角度对“有生于无”的思想加以分析,经典之所以富有魅力,就在于其中的可诠释性。
一、文本分析
王弼注第四十章原文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河上公章句、传世本中的《老子》原文与王弼注中没有区别,不过在“天下万物”四字上,部分注家,如王夫之注中《老子》此句原文是“天下之物”[2],但在“有生于无”四字上没有异议。所以一直以来,“有生于无”就成为了老子定义“有无”关系的一个重要依据。也因为“生于”二字展现出了上下层级的含义,所以“无”在后世注家的解释中,就具有了高于“有”且具有本体意味的形而上的本质。但是,随着湖北郭店楚简的出土,“有生于无”的说法突然被推翻了。
在先出土的马王堆帛书中,“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一句在乙本中作“天下之物生于有,有□于无”。可以看到,在马王堆帛书中,虽然“有”与“无”中间脱了一字,但是从“于”字仍然可以看出,“无”是高于“有”的,这也从侧面论证了学者通常所认可的有无关系。
随后出土的湖北郭店楚简则是彻底将这一关系推翻。在楚简中这一句的原文是:“天下之物生于又,生于无。”[3]可以明显看到,在这里出现了与以往所有版本都不同的情况。在这句话中,“天下之物”既是“生于有”,也是“生于无”。很显然“有”与“无”不再是上下关系,而是平行共存的。这一发现令学界震惊,随即引发了学者们的强烈争论。
争论的主题在于“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就是原文,抑或是“生于无”前脱略了一个“有”字,即“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后一种说法显然是考虑到了通用版本的说法。而这一争论也带来了关于“有无”关系的再次思考。
二、思想辨析
对文本的不同态度,自然决定了对“有无”关系的不同界定。郭店楚简的出现,使得学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分为了两个派别:一是或否认“生于有,生于无”即是完整的文本,或承认原文即“生于有,生于无”,但总的来说这一派支持“有生于无”,所以对“有无”关系的界定是“有无为本”。二是肯定郭店楚简的准确性,认为应尊重文本,重新理清“有无”关系,所以这一派支持“有无相生”的说法。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老子思想研究中,因为有学者将“无”等同于“道”,所以关于“道”、“有”、“无”三者间的关系也有非常复杂的争议。但本文只限于探究“有生于无”一句中的“有无”关系,暂不考虑“道”与“有”、“无”的关系。
(一)以无为本
“以无为本”来源于王弼注。关于“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一句,王弼注的解释是:“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在这里,王弼根据“有生于无”一句,分析出“有”与“无”之间的关系是“以无为本”,也就是“无”作为“有”的依据而存在。这一观点在第三十八章的注中有着更清晰的表现:“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4]王弼认为“有”与“无”是本末关系。一切“有”都必须依据“无”才得以存在,没有“无”那么“有”也就不存在了。他并没有解释“有”和“无”分别指代什么,只是说明了“有无”之间的关系。
河上公对此句的解释是:“(天下)万物皆从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于有也。天地神明,蜎飞蠕动,皆从道生,道无形,故言生于无也。”[5]河上公将原文中的“生于有”之“有”解释为天地,天地是有形的,被称为有;“有生于无”之“无”指代的则是“道”,道是无形的,被称为“无”。所以河上公的理解是将“道”,即“无”,作为最高的根本,是万事万物所生的依据。通过“无”与“道”的互通,将“无”的地位提升至“道”的层面,自河上公始。后来许多学者也都受到这一注解的影响,将“无”与“道”等同起来。
作为明末清初胡湘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夫之对此的理解是:“物虽未形,已是有气。天地万物从一气而生,一气从道而生。”[6]即他对“有”的解释是“气”。因为王夫之作为胡湘学派代表,其哲学思想自然继承了胡湘学派创始人周敦颐的气论。所以他认为“有”就是构成万物形体的“气”。其将“无”解释为“道”与河上公是相同的,但是王船山的“道”又有高于河上公的一点。作为宋明理学的后来者,尽管王船山反对程朱理学,但不可否认他也继承了程朱关于形上形下的划分结构:“气”是形下的“有”,“道”是形上的“无”。这一解释也就将王弼的“以无为本”与河上公的“道”本论都涵括了进来。
此三者代表了自有对《老子》的注疏以来主流的观点。但湖北郭店楚简的出土,就成了对《老子》思想研究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此前对于老子思想研究的学者们在大方向上基本都是这一主流观点的话,那么自楚简出土始现代研究者就出现了两大派别。其一仍是支持传统主流的解释,这一派主要以刘笑敢、廖明春为代表。其二提出尊重文本,重新考察“有无”关系的新看法,这一派主要是当代的一些学者,他们在对传统思想的反思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刘笑敢先生发现如果按照郭店楚简的文本,那么万物既“生于有”又“生于无”,于是万物就有了两个来源。他并不赞同:“这样读没有任何旁证,道理上也很难讲通,且与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说法有冲突。”[7]所以刘笑敢认为作为老子思想中的绝对核心、绝对本体的“道”,当然是唯一且绝对的。
廖名春教授也持同样的立场,他认为在“生于无”的“生”字前很有可能脱略了一个“有”字,或者按李若晖的解释:“‘生于亡’上当有‘有’字,只不过这无须用脱漏重文来解释,而只要将上句末的‘有’字重读即可。”[8]并进一步将这句话解释为:“天下万物由已有之物而形成,而最初的已有之物是由无形的大道而产生。”[9]同样,廖名春也认为“无”指的就是“道”。
以上几种解释都或多或少有不同,但不论是哪种解释,不论是从“道”还是“气”还是“无”来理解,其中心思想都在于否定“有”具有与“无”同等的地位——作为万物之源。
(二)有无相生
其实对于“有无”关系的争论并非郭店楚简出土之后才有的。即使第四十章的文本是“有生于无”,但在第二章中也有“有无相生”的命题。所以也有学者提出过质疑,并猜测“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一句是《淮南子》误入。[10]但在当时,这只是根据《老子》文本中存在的“有无”关系矛盾作出的一种假设,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而郭店楚简的出现则是将这一确凿证据摆在了学界面前。于是一大批持尊重文本原文的学者开始对传统的“以无为本”进行重新审视,并相继提出在《老子》文本中想要表达的其实是“有无相生”的思想。
张祥龙教授考察了“以无为本”理论的发展,思考为什么后来会将“有”和“无”的关系分出高下呢?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黄老学和法家出于政治目的,为了赋予君主以一个绝对超越和控制臣民的地位,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肯定‘无’的更高级的实体地位,以保证形名之学统一于道。”[11]而这一解释也就影响了魏晋到现在的理论。他进一步提出“有无相生”才是《老子》文本中应有之义,即“有”和“无”独立时两者都没有实际意义,也不能指代任何存在。只有“有无”共同存在时,才真正具有了内涵。在这里“无”代表的是否定和潜伏,是将一切外加于无的东西否定掉,然后才能呈现出其中潜伏的真;“有”则是在“有无”共生时使双方具有了本身的含义。
聂中庆教授则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寻求答案。他提到“模糊思维”的概念,这是“自然界普遍联系之无限性及主体认识之有限性的产物”。[12]也就是说,老子在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时,所使用的都是一种否定的描述,因为主体认知能力的有限,在表达时只能通过类比、比喻以及说明其不是xx 的方式。
何石彬教授考察了“道”与“有”“无”之间的关系,发现“以无为本”的思想很大程度上与把“道”与“无”等同起来解释“有生于无”的方法有关。所以他重新对“道”进行了分析,认为“老子道论是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思维模式下展开的,老子的“道”并不是一个与主体隔绝无关的纯客观概念”。[13]老子对“道”的体悟与表达都是与个体相关联的。何石彬与聂中庆的观点是类似的,即老子所采取的表达方式多是以否定的形式,作为否定形式的“无”并没有实质的含义。“无”字起到的作用是说明道本体的无规定性和不可直接言说性。这种否定式的命题,在后来的理解中却将“无”与“道”等同了起来,从否定转向了肯定。可以说这种转换是对老子思想的一种扭曲。从逻辑上来说,当我们说一个东西非A 的时候仅仅代表着这个东西不被包含在A 所处的范围之内,但对他究竟所处于哪个位置,并没有加以确定。
由上可见,之所以产生“有无”关系究竟是并生还是本末的争论,首先是传世本中,尤其是王弼注本中出现的两处似乎矛盾的“有无”关系定义——第二章的“有无相生”与第四十章的“有生于无”。这一点在郭店楚简未出土前就已经提出来了,但对“无”的概念化理解,将“无”上升到“道”的层面,以“无”作为万物存在的依据作为主流的理解占据了上风,并且当时也找不到除第二章以外的其他证据证明“有无相生”的关系,所以未能引起大范围的讨论。
郭店楚简的出土,则是将这一问题再次摆在了学界面前。这一次持“有无相生”观点的学者因为有了楚简作为强有力的证据,也更加丰富了对老子思想的阐释。
三、结论
总而言之,对郭店楚简“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文本的不同理解,大致有两个派别,且郭店楚简的出土加剧了两种观点之间的碰撞。就笔者而言,“以无为本”与“有无相生”或许并非是对立的关系。
如前所述老子之“无”是一种否定式的描述,所以老子的“无”并不是一个事实概念,并不是真的有一个形而上的“无”作为本体而存在。而是无差别,是混沌一体。当我们称一件事物为A 时,我们就是在将这个事物定义为A。与此同时,我们也就否定了其是非A。A 和非A 之间是决然两分的,正是这些区别分出了A 与非A。老子说“无”,其实就是要将这种定义给去掉。因为这些定义都是人“强为之名”,只有将这些人为外加附属的定义剥离开,才能看到最真的事物。这是否定式的境界概念,即通过否定掉不属于事物自身的外在属性、定义,达到的混沌境界。
老子深刻意识到我们现实的世界是感性的经验世界,服从逻辑规律。但老子之“道”,不是通过经验感知到的,而是直接的精神体悟,所以他无法通过符合逻辑规律的语言对“道”加以描述,只能用“无”等一系列否定概念言“道”,即“道”不可以用人的语言概念定义。更重要的是,“无”的这种无差别状态,并不意味着无物存在,而是万物都在,但又无差别。
在解释清楚“无”所表达的无差别性后,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以无为本”和“有无相生”不是对立关系。“以无为本”是从境界论的层面理解,是以“道”观之。站在“道”混沌境界的视角看待世间万物,人与刍狗都不过是万物,都是无差别的,这是“无”。这是需要直觉体悟到的,无法通过感性经验的总结获得。“有无相生”则是落实到了现实的感性世界,此时的“有无”是一对共生范畴,“有”是感性认知上的存在,“无”是感性认知上的不存在。正是因为有了“无”的反衬,才使人意识到“有”的存在。这是经验世界的产物,所以是“有无相生”。
所以,“以无为本”中的“无”所展现的无差别境界状态,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有”。即万物“有”且“无”,意思是万物存有,但又处于无差别的状态。这样一来,其实“以无为本”与“有无相生”并非是不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