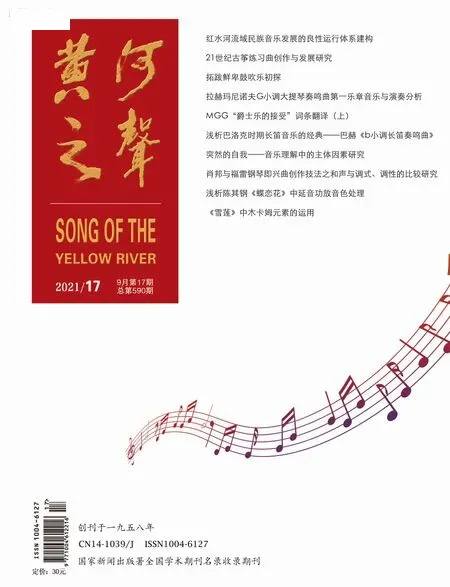米约《世界之创造》中的爵士乐风格研究
2021-11-27张娅
张 娅
一、《世界之创造》的创作阶段及其爵士乐风格溯源
达律斯·米约(1892年-1974年),是20世纪法国“六人团”的成员之一,也是作品颇丰的著名作曲家。在20世纪的法国乐坛,也属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在求学时期,他就与法国著名作曲家萨蒂等人有过交集。同时,他也注意博采众长,同时具有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乃至音乐教师等多种不同的身份。这种融会贯通,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米约一生共创作了400余部音乐作品,其中包括交响乐、室内乐、钢琴音乐、芭蕾舞、歌剧与戏剧配乐,甚至电影配乐等等,因此也有了“作曲机器”的名号,其作品在20世纪音乐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米约作品数量的高产,与他的四方游历不无关系。他曾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四处旅行,像其代表作《屋顶上的公牛》中,就集桑巴、探戈之大成,可以说他的巴西工作经历功不可没。本文所要重点阐述的《世界之创造》同样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米约是一位善于博采众长的作曲家,所以其数量繁多的作品中,除了有新古典主义的基底外,也常常杂糅着彼时各种音乐风格与主义之风。例如在此时交杂着表现主义、原始主义等等,可谓应接不暇。但这种多元的音乐风格,也常常在米约的创作中得到体现。例如,其代表作品《屋顶上的公牛》是他在巴西工作两年之所得,其中吸取了美洲的探戈、桑巴等曲风。《世界之创造》同样如此,该作是米约于20世纪20年代应邀创作的芭蕾音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
笔者认为,《世界之创造》的创作,乃至其中突出的爵士乐风格,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感性认知阶段。1920年6月,米约在伦敦受邀指挥《屋顶上的公牛》时,首次听到了爵士乐。在指挥之余,米约在泰晤士河以北的哈默史密斯舞厅,谛听到了来自美国的爵士乐队——比利·阿诺德的演奏,由此了解到了萨克斯管、长号与打击乐之间配合的精妙。在此之后,他曾在回忆录里称“这种新的音乐对音色的使用极其微妙”,由此种下了创作爵士乐的火种。
第二个阶段是此后的1922年,米约访问纽约,并在黑人聚集的哈莱姆区接收了大量一手的爵士乐现场演出,为创作《世界之创造》打下了基础。尤其是,欣赏了素有“爵士乐之王”之称的保罗·怀特的表演,并在波士顿助手的引导下,遇到了将灵歌带入大雅之堂的著名作曲家亨利·伯利,这些机缘为米约创作爵士乐打下了理论基础。同时,他也产生了融自己的创作风格与爵士乐于一炉的想法,而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第三个阶段则是在1923年,米约受瑞典芭蕾舞剧院经理马雷之邀请,创作一部芭蕾舞音乐,此作即为《世界之创造》,也是米约在爵士乐方面的具体实践。此作的形式与内容较为驳杂。其创作的原始文本,源自法国诗人布莱斯·桑德拉斯所著的《黑人选集》(1887-1961年),此书涉及到了创世故事与非洲神话;与此同时,桑德拉斯也正是《世界之创造》的脚本作者,他大刀阔斧地缩减了原作中的神话故事,并注重在舞台间营造复古、原始感。在此基础上,米约则赋予了整部舞剧以与时俱进的“骨血”,以黑人最擅长的爵士乐,加深了整部作品的神话图腾之感。在谈及《世界之创造》中的爵士乐氛围时,米约曾如此说道,“音乐与我原来听到的全然不同,在打击乐衬托下,旋律互相交织着;节奏型纵横交错地进行,形成一种具有强大脉冲动力的织体”,此外米约也明确表示,“为《世界之创造》创作音乐至少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把我以前用功学的那些爵士音乐用一些进去”。由此也可看出,在经历了前两个阶段的积累后,《世界之创造》成为了米约创作爵士乐作品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需要提及的是,《世界之创造》在法国的初期演出并不理想。直至作曲家鲍里斯·德·施略泽看完后,才给出了相对中肯的评价,并逐渐在音乐圈中掀起波澜。
提及古典音乐融入爵士乐,许多人会先想起格什温和他创作的代表作《蓝色狂想曲》。事实上,米约创作的《世界之创造》首演是在1923年,甚至比《蓝色狂想曲》还要早。而从作品溯源深入其文本,也会深刻地发现:米约的《世界之创造》,的确在爵士乐的根基上开枝散叶,呈现出鲜明的风格特点。
二、从爵士乐角度分析《世界之创造》的创作特点
《世界之创造》共分六个章节,整体时常约为15分钟左右。从结构上分别为“序曲”,以及第一部分“创世前的混沌”、第二部分“黑暗缓慢地消散,树木、植物、昆虫、鸟兽被创造出来”、第三部分“创造人类之舞——男人和女人被创造了出来”、第四部分“男人和女人的欲望”,以及第五部分“男人与女人的亲吻”。从风格特质俯瞰,是运用20世纪先锋技术来处理非洲神话文本的一部佳作。
从作品的细节处理上看,序曲首先奏出绵长的布鲁斯旋律,为整部作品的爵士乐风格打下了底子。此后,第一部分“创世前的混沌”聚焦于非洲传说中的三位创世之神——恩科瓦、梅勃勒与恩咋没,演绎出创造生灵的景观。第二部分“黑暗缓慢地消散,树木、植物、昆虫、鸟兽被创造出来”正如题名,期间填有众赞歌与赋格主题。第三部分“创造人类之舞——男人和女人被创造了出来”出现了整部作品的核心,即最早的男人与女人塞科美与姆邦维,两人有节奏地从舞台生灵中脱颖而出,由此传递出人类进化的深意。第四部分“男人和女人的欲望”,是一段塞科美与姆邦维的热烈舞蹈,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其他人类也从“生灵”中逐步跳脱出来,致使热烈的情绪逐渐攀至顶峰。第五部分“男人与女人的亲吻”中,创世之神与一众生灵均从舞台上撤下,唯独留下塞科美与姆邦维在舞台上逐步靠近,直至拥吻在一起。
从整体的创作思路上分析,米约曾谈到,“在我的芭蕾舞配乐《世界之创造》中,我想用交响性来处理我的主题,并且用我一部分爵士乐编制来表达、陈述其中的忧郁风格。”从中既可看出爵士乐在整部作品中提纲挈领的作用,也渗透出米约对乐队编制的理解;同时,米约在《世界之创造》中也注意运用切分节奏来制造舞蹈的戏剧性。接下来,笔者将通过乐队编制、配器原则、主题构建与曲体结构几个方面具体分析这部作品折射出的爵士乐风格。
首先,从乐队编制方面,该曲在传统管弦乐队的编制模式下又有所不同,其中木管乐器包括长笛(其中一位兼吹短笛)、单簧管、双簧管、巴松管,以及萨克斯管;铜管乐器包括小号、圆号与长号;弦乐器包括小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之所以制定如此的乐队编制,并非是米约“空穴来风”,一方面是他考虑到芭蕾舞演出的实际成本,并综合了主题、节奏、和声与器乐演奏的效果而定;另一方面,参考了黑人作曲家马切奥·平卡德的歌剧《莉莎》的结果,这也是一部具有爵士乐风格的歌剧。《莉莎》的乐队编制,即包括长笛、单簧管、中音萨克斯管等在内的木管乐器,长号等铜管乐器,以及弦乐、钢琴等,《世界之创造》与之采用了相似的配器策略。与此同时,这种乐队编制的定性,显然也与米约于1922年造访的哈莱姆区中的黑人爵士乐队相仿,但17人的编制显然有了扩增——这也是考虑到管弦乐呈现所做的综合考量。而从器乐选择上,米约选择了在爵士乐独奏中占据主势的单簧管、小号与长号,同时也选择了彼时在20世纪20年代已在爵士乐中普遍使用的萨克斯管。
其次,从具体的配器原则上,米约追求的是爵士乐、室内乐的音响层次。所以在具体的器乐配比上,米约也下足了功夫。例如,考虑到爵士乐的效果,米约严格控制了弦乐器的数量,中提琴被萨克斯管取代,并在整部作品中占据了引导位置。这种爵士乐曲风的影响贯穿该曲的配器原则。再如,乐队中的大提琴被低音提琴取代,同时引入了爵士乐中常见的钢琴。因循于爵士乐的配乐大原则,主题的呈现也与传统管弦乐队不同,小提琴仅仅在第三部分“创造人类之舞——男人和女人被创造出来”中担任了一次主的陈述工作,其功能与钢琴类似。与此同时,大提琴也仅在第一部分“创世前的混沌”的主题中担任陈述。米约的这种选择并不代表弦乐变得不重要,而只是一种功能的位移——在《世界之创造》中,弦乐更多的并非充当主题陈述,而是作为背景铺垫而存在。笔者认为,米约的这种考量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增加弦乐的数量会使大家的注意力分散,而从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舞台上的表演。这种刻意削弱弦乐器的做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毫无先例。例如莫扎特的《降B大调第十小夜曲》、又名为“大帕蒂塔”,该作品就是由成对的双簧管、单簧管、巴塞特单簧管、巴松管,以及四支圆号和一把低音大提琴构成,在此中突出了管乐的整体作用。同样的例子还包括德沃夏克的《D小调小夜曲》,同样也是以管乐为主,弦乐在其中主要起到了背景或者说拖底的作用。
再次,从主题旋律的构建上,《世界之创造》主要依附于爵士乐与布鲁斯音乐。但这不代表《世界之创造》的每一行每一句都写有爵士乐,只是说它占据了重要位置。而布鲁斯音乐可谓贯穿整部作品。例如在第一部分“创世前的混沌”伊始,即由中音萨克斯管在d小调上奏响了忧郁的布鲁斯主题。而在第二部分,忧郁的新布鲁斯主题改为双簧管演奏,并变得更加抒情。此后的第三部分“创造人类之舞——男人和女人被创造了出来”以人类如何从已创造的生物中独立为切入点,并在双簧管独奏后,小提琴奏出了上文提及的第二部分中的布鲁斯主题;并在先锋音乐的包裹中,亚当和夏娃开始互相注视,形成了芭蕾舞中的重要段落。此后在第四部分“男人和女人的欲望”,在讲述亚当和夏娃诞生之后,人类队伍得以继续繁衍后,单簧管独奏出了全曲欢快的布鲁斯段落。第五部分“男人与女人的亲吻”中,故事的重心回到“回顾”,此前的几个布鲁斯主题便得到了相继回顾。而在乐曲的结尾处,又停在了布鲁斯的第七级之上,米约通过此举成功地给整部作品留白,引出观众对内容的无限遐想。
最后,从曲式上看,米约的《世界之创造》也充分借鉴了彼时爵士乐的一些结构范例。在此,米约充分使用了循环曲式的一些特点,用主题的碎片化来形成主题与主题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点,显然是米约从爵士乐的“riff”——也就是两小节或四小节的简短乐句这一概念沿袭而来的。米约这种循环技法与“riff”的结合是非常巧妙的。在循环技法的牵引下,米约通过主题以完整或者碎片化的形态、和声或者其他主题的融入,来形成类似于爵士乐中的“riff”效果。这一点在第一部分的赋格主题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了非洲三位立体主义形象的神仙,即恩扎梅、恩柯瓦与梅博乐通过施展法术,创造世界的初始情况。在钢琴的陈述结束后,低音提琴嗡嗡奏响了这一部分最重要的赋格主题,随后,米约即采用了类似爵士乐“riff”的技巧将这一主题在长号、萨克斯管与小号之间来会穿梭,为整部作品的爵士乐曲风奠定了坚实的结构基础。
结 语
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通常将《蓝色狂想曲》看作是最早将爵士乐与交响乐相融合的范例之作。正如上文所示,实际上米约创作的《世界之创造》更早、也同样称得上是掷地有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音乐佳品。故从历史地位上看,米约的《世界之创造》,是一部可与《蓝色狂想曲》相较的优秀作品。但从两部作品的知名度来说,米约的受关注度还是远远被低谷了。
以上,笔者从该作与爵士乐的溯源;并深入该作的音乐文本,尝试从配器、曲式等方面对全曲的爵士乐风格加以阐述。一方面,是通过作品分析还原米约的爵士乐创作技法,另一方面,也想从中捋出一条线索,为打开米约丰富的作品库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从中既可一窥米约所处的20世纪初期丰富的创作风潮,也能感受到他作为音乐史洪流中的一员猛将,在其中存留下的浓重阴影。
由此引申开去,笔者也发现,米约的该作研究、乃至作曲家本人的研究在国内还是相对较少,尤其是缺乏针对其代表作的深入分析与研究,而从这一角度来看,《世界之创造》还具有相当大的讨论与研究价值。其对交响性与爵士乐的融合,对舞剧音乐的探索,乃至对20世纪先锋音乐的启示等方面,也值得给予更多的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