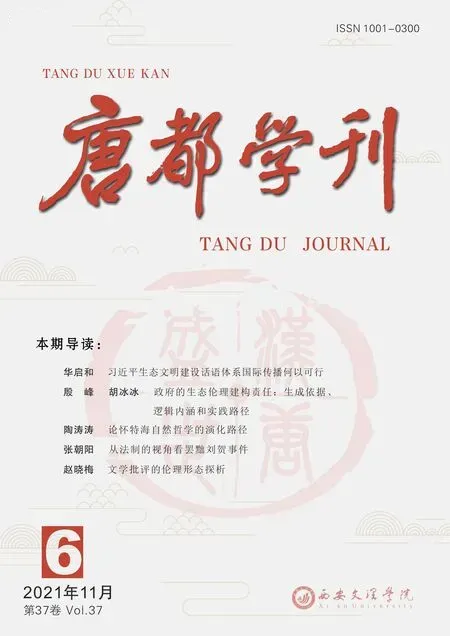从法制的视角看罢黜刘贺事件
2021-11-26张朝阳
张朝阳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只当了27天皇帝的刘贺为什么被罢黜?随着近年来海昏侯墓考古重大发现,这个经典问题又浮出水面。是刘贺作恶多端,自取其咎?还是他不懂政治,激怒霍光?抑或是更复杂的帝系继承纠纷之反映?看法可谓众说纷纭(1)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此处仅举三例:廖伯源《汉昌邑王废黜考》,载于《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2000年第8期;吕宗力《西汉继体之君正当性论证杂议——以霍光废刘贺为例》,载于《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王子今《“宗庙”与刘贺政治浮沉》,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各家主张固然都有其道理,但大都是在推测罢黜事件的动机而忽视了两个细节问题:其一,霍光没有采取宫廷政变这种常见手段,而是通过一系列严肃的程序,公开、和平地完成了对短命皇帝刘贺的罢黜;其二,霍光将自己的行动定性为维护汉制度。这两个特点使得刘贺之被罢黜非常独特,不同于常见的宫廷政变而具有一定的法制色彩,值得我们深究。
一、罢黜之程序与正当性依据
罢黜刘贺的过程,史书记载极其详备。从程序的角度看,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严格、规范、和平。根据《汉书》记载,霍光有意废黜刘贺时,首先派人与丞相杨敞商议,这显然是因为丞相是百官之首。得到丞相的认同后,霍光召集大臣在汉王朝的权力中心——未央宫进行集体决议:“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2)参见《汉书》卷68《霍光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37-2938页。以下关于罢黜事件的引文,如无特殊说明,皆出自此文献。惊愕的百官还是一致通过了罢黜动议。之后,由丞相带头联名36位大臣上书皇太后,又由皇太后召见刘贺,当众宣布罢免决议:“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光与群臣连名奏王,……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当废。……皇太后诏曰:‘可。’”最后,霍光从刘贺身上解下玉玺,交给太后,又“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事件情节固然充满了紧张和软硬胁迫的意味,如群臣商议时,霍光的亲信田延年“离席按剑曰”,又如太后召见刘贺时“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但整个过程并没有使用武力,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从动议到决议再到执行,环环相扣,严密而有条不紊。
这些特征与吕后死后,大臣铲除诸吕时混乱与血腥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汉廷群臣先是在宫内大开杀戒并且族灭吕氏,之后,傀儡少帝也没有幸免。《史记》记载道:“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1]520-521这一系列行为可谓斩尽杀绝。相形之下,霍光的举措称得上文质彬彬,像是一套规范的弹劾流程——正是通过正常的机制,汉朝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群臣罢免皇帝。
抛开对动机的猜测,就说辞而言,罢免刘贺的正当性依据在哪里?我们分析群臣上书文辞的细节可以看出,杨敞、霍光等人先罗列了刘贺在短时间内犯下的1 127宗罪,然后将其归纳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这总结包括了道德、礼和“汉制度”三个方面,而以“乱汉制度”结尾,可见“制度”是重中之重。文本没有解释被破坏的“汉制度”到底是什么,但既然明确说过了道德和礼仪两方面,则该“制度”很可能和法制有关;似乎可以对应文本中提到的“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缚嘉系狱”等细节。
事实上,汉律对淫乱有严格的禁止。《二年律令·杂律》有如下规定:“复兄弟、孝(季)父、柏(伯)父之妻、御婢,皆黥为城旦舂。复男弟兄子、孝(季)父、柏(伯)父子之妻、御婢,皆完为城旦。”[2]这里规定:如果与兄弟、叔父、伯父的妻子或与兄弟、叔父、伯父有过性关系的婢女发生性关系,犯事者要被“完为城旦”,服劳役刑。刘贺继承了昭帝的帝位,等同于子。与昭帝宫女发生性关系,应该比杂律所见这一条还要性质严重。所以刘贺作贼心虚,特意“诏掖庭令敢泄言要(腰)斩”,以腰斩来恐吓潜在的走漏消息者,这种恐吓行为自然是罪上加罪。更甚者,刘贺随意抓捕、治罪夏侯胜等谏议大臣。即便皇帝有这个权力,但滥用权力显然践踏和危害了法制。
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杨敞等人的“议”,进一步指向了刑法之上的最高准则——“孝”:
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仓议,皆曰: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诗》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属,莫大不孝。
汉朝号称以孝治天下,而“五辟之属,莫大不孝”,似乎将刘贺的罪过定性为“不孝”。可见,除了律令之外,“汉制度”还应该具有更深刻、更高阶的含义——治国之道(例如孝道)。这一推断契合汉宣帝“汉家自有制度”的论断。在回应太子(元帝)“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的批评时,汉宣帝说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3]277表面上,这段话侧重于刑的一面,但这是语境所致:为了纠正太子忽视刑的错误倾向,宣帝特意强调了霸道。但宣帝所理解的汉制度显然不局限于刑,还包括了德教,是儒家王道和法家霸道的糅合。可见汉制度涵括但不局限于具体的律令,可理解为以某种治国之道为核心的法制体系。
如果破坏汉代法制是罢黜刘贺的一大原因,那么我们可以推导出:汉代法制本身构成罢黜动议的合法性来源。换言之,根据汉代法制,群臣认为有理由罢黜刘贺;刘贺的皇帝意志不能违背汉代法制(3)这里仅就说辞本身的逻辑而言,不牵扯到话语背后的政治权谋等因素。同理,我们看到,除汉制度外,德和礼也是罢黜的合法性来源。。这个推论契合赋予霍光行动决心的故事——“伊尹放太甲”(4)关于伊尹故事之不同版本,参见岳宗伟《〈古本竹书纪年〉校正〈史记〉举例》,载于《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之寓意。霍光曾咨询亲信田延年是否有罢黜天子之先例,得到的回答是伊尹放太甲这样的古老传说[3]2937。这个传说在《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孟子·万章上》《史记·殷本纪》等文献均有记载,但《竹书纪年》将这个事件描述为血腥的宫廷斗争,最终太甲杀死伊尹夺回王位。 故事虽存在如此迥异的版本,但它所传达的理念却赋予了霍光行动的决心,这个理念是什么呢? 《孟子》曾说:“大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4]309由于太甲颠覆了汤所确立的“典刑”,伊尹将他流放。朱熹注解说“典刑,常法也”[4]309,显然这个故事强调天子需要遵守既有法律。既然刘贺破坏了汉代法制,那么罢黜他也就顺理成章了。
事实上,尊重法律并非霍光为了打击刘贺而随意祭出的法器。辅政之初,霍光在正式场合已表现出对法制的尊重。史载:“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3]2933政自己出的霍光,在紧急情况下想收取玉玺,却被“尚符玺郎”拒绝。“尚符玺郎”是什么?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又有尚符玺郎”[3]85,可见是专门保管天子符玺的郎官。这样的低级官吏如何敢按剑怒对辅政大臣? 《后汉官》对尚符玺郎的选择标准说到“当得明法律郎”(5)参见范晔《后汉书·百官三》注引,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99页。,可推知该郎官通晓法律,是法律赋予他不畏权臣的胆魄。该事例一方面表明了霍光能尊重法制,止于当止之时;另一方面也说明普通官吏也敢于坚持法制原则,不被权势所屈。他们共同遵守了法律制度,维系了法的公信,成为一时之美谈。
二、汉代皇帝意志与法律规定之张力
汉代精英曾多次争议皇帝意志与法律之关系。总体而言,自战国变法起,中国古典法律迅速发展,各类律令不断编纂与公布,而法律知识也由垄断而逐渐普及。例如,睡虎地秦简不但包含各类律令还包括问答类文本,显然很注重在官吏中普法(6)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这批珍贵的法律文本出土于一个普通地方官吏墓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律知识的扩散。。 秦汉时代兴起专门传授法律知识的律令学,说明了法律在知识阶层中相对普及(7)参见邢义田《秦汉的律令学:兼论曹魏律博士的出现》,收入《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2011年版。。毫无疑问,法律的力量在当时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君主权力削弱了贵族力量之钳制,随着秦制不断壮大成为皇权,而权力与生俱来的无限扩张欲,使得皇权不断向绝对集权、绝对专制方向发展(8)是否可以称之为君主专制,有争议,但君权不断扩张是史实。相关研究和争议,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载于《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载于《文史哲》2009年第1期;白彤东《中国是如何成为专制国家的》,载于《文史哲》2016年第5期。。因此不可避免地,法律与皇权、法制与圣意两种力量、两种趋势在西汉产生了激烈争锋。
根据现有史料,第一次争锋发生在张释之与汉文帝之间。汉王朝以“约法三章”起家 ,法律和约定颇受时人重视。汉初行黄老之道,与民休养生息的同时亦尊重法制(9)详见后文对黄老法律思想的分析。。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分析《史记·张释之列传》所载张释之史实。张释之曾担任守卫皇宫的公车令。有一次太子去朝见文帝,没有按规定在司马门下车。张释之追上去,阻止其入内,并且弹劾他“不下公门不敬”,直到皇太后出面向文帝求情才平息此事。
张释之不但讲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便对文帝本人,也多次据理力争,迫使文帝遵从法律而改变旨意。升迁为廷尉不久,张释之面临了一场考验:是严格遵照法律处理案件还是遵从皇帝一时的好恶?《张释之列传》记录了法制史上精彩的一幕。一日,文帝外出巡视,车队纵贯长安城外横跨渭水的大桥。突然有人从桥下跑出,正好惊到了御马,吓到了文帝。文帝派人抓住闯入者,交给张释之治罪。张释之查明该人是附近乡民,遇到天子出巡,躲到桥下避让。乡民误以为队伍已经走远,从桥下走出,不想冲撞御马。尔后,张释之回复文帝:“一人犯跸,当罚金”,按法律罚钱结案。文帝大为不满,认为若非御马性格温良,自己肯定就被受惊之马摔伤了,你张释之怎么就只判罚钱?面对文帝的质疑,张释之说出一番彪炳史册的法制道理:“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1]3333在张释之看来,法是天子与整个天下共同遵守的规则,这种规则具有强烈的公开属性,必须认真履行、共同遵守以取信于天下。如果受天子个人好恶之影响产生偏差,就会使法律失信于民,后果严重。张释之进一步强调说:“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1]3333廷尉是天下的公平所在,对法律负有责任。执法如果有倾向性的偏差,就会对法制产生破坏,使得民众无所适从,欲守法而不能。这样,就不能由于顾忌文帝的感受而扭曲法律的准绳。汉文帝思考良久,承认说“廷尉当是也”!这表明张释之对君主意志与法律规定的解读得到了汉文帝的认可。由此可以推导出,这个解读在当时成为官方的认识。也正是这个原因,张释之得以多次据法驳议天子的指令(10)详见《史记·张释之列传》。
第二次可考的争锋发生在武帝时代的杜周与佚名客人之间。根据《汉书·杜周传》,杜周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廷尉。有人指责他审理案件时,一味逢迎武帝的好恶,武帝希望死刑就死刑,希望赦免就赦免,丝毫不顾及法律条文的规定。杜周辩解说:“三尺安出哉? 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3]2659所谓“三尺”就是指法律,因为秦汉时代的律令,一般书写在长约三尺的竹木简上(11)这是传统的解释,但出土法律简牍形制颇为多样,并不一定遵循“三尺”之制。。仔细品味,我们发现杜周从法源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他的理解中,无论是“律”还是“令”皆为君主的意志。因此,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是法的来源。同理,君主最新的意志就是最新的立法成果,如果和之前的法规有冲突,当以最新之立法为准则。因此,一切执法皆应根据君主当时当下的需要。在君主意志即法律的前提下,杜周的辩解在逻辑上也算自圆其说。
但是,从汉代法律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三尺安出哉”并非绝对的史实。首先,按杜周“前主所是著为律”的说法,汉律之初始内容应该是高祖的意志,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高祖约法三章,很快就被《九章律》所替代。《汉书·刑法志》记载:“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12)《汉书》卷23《刑法志》,第1096页。对比汉初《二年律令》与睡虎地秦律,《汉书》记载是有根据的。由此可知,汉律的内容在源头上承袭了秦法,又由丞相萧何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了修改。没有证据表明汉高祖在这个生成过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次,这一说法不符合张释之时代的法制理念和实践。张释之多次根据既有法律否定汉文帝的意愿,而佚名客人对杜周的质疑就是基于汉初的认识——君主意志不能代替既有法律。最后,即使武帝本人也不愿公开宣扬自己的意志高于既有法律。《汉书》记载,武帝外甥昭平君杀人,有人建议赦免,但武帝表态说要尊重既有法令:“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3]2852(13)杜周为何说 “三尺安出哉”呢?考虑到武帝时代兴起的一系列集权举措,杜周显然企图运用自己的权力去建构新的话语,为武帝不断集权进行理论背书,但武帝本人至少在姿态上仍然表示尊重既有法律。武帝并不认为法令是自己的意志,而将其归于先帝所造,认为自己不可以因私情而违背先帝之法。即便这仅仅是一种姿态,也无疑否定了杜周的“三尺安出哉”。
三、黄老、法家与儒家对君权的态度
汉初对法制的尊重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古典思想对君权的态度有关。汉初行黄老之道,《经法·道法》开篇即言:“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6]2这里将“法”理解为由“道”所派生出的规范,是衡量一切是非曲直的准绳。“执道者”不敢违犯和废除既有法律。“执道者”显然是掌握了“道”的君主,借助道的力量来实现统治。君主遵循“道”,自然要遵循“道”所派生的“法”,从中可推导出:君主的个人意志需要服从法的规范(14)美国法制史学家裴文睿(Peerenboom)认为,这可称为中国古典的自然法理念。见R.P.Peerenboom,Law and Morality in Ancient China: The Silk Manuscripts of Huang-Lao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76-84.。也正是基于这个认识,《经法·君正》又说:“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6]71法度被赋予至上的地位。
汉承秦制,秦制与法家关系密切,法家虽然推崇君主,藉君主推行法制,但法家对君主的个人意志也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商君书·修权》主张:“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7]82。这段文字强调法是国君和臣民共同操持的规则,而公信需要国君和臣民一同来树立。言下之意,法律并不是国君个人独断的意志。进而又提出“为天下位天下”“为天下治天下”的说法,预警了君主私欲膨胀对治国造成的危害:“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7]84-85这段文本显然并不认为君主的私人意志就是法律。相反,天下之利才是法的根本。也就是“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这段文字还警告说君主私欲膨胀、追求私利是非常危险的。被认为法家思想集大成的韩非子,虽以主张君主集权闻名,其实也对君主的主观意志怀有警惕。有学者指出,韩非受黄老思想影响,认为法之上还有更高的规则,即“理”“道”。《韩非子·解老》说道:“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福,犹失其人民而亡其财资也。”(15)参见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6,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6页。表面上,韩非子在解释老子之思想,但他既然认同这说法,可谓借老子抒发己见。这个说法崇尚“道”“理”,认为天子如果违背“道”“理”,恣意而为,则有祸殃。这显然是试图对君主的个人意志进行一定的约束。韩非甚至寄希望于一套以柔克刚之“术”对君主专制的权力进行限制和控制[8]。
在汉代逐渐获得至上地位的儒家,对这个问题也有一套认识。除了早期朴素的民本思想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外,汉儒糅合阴阳五行,试图以神秘的天意来约束皇权,其代表人物就是被称为“群儒首”的董仲舒[3]2526。徐复观指出,董仲舒一方面倡导并维护君主集权,另一方面又对皇帝个人的喜怒意志保持警惕,希望将皇权约束在形而上的“天”之下,进而约束在儒家政治理想之中[9]212。《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说:“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6)参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0页。苏舆说“此篇非董子文”,并指出若干疑点。估计苏氏认为这段内容批判君权,有离经背道之嫌,因此否认出自董仲舒,但又拿不出实质性证据。但这段文字恰恰符合董仲舒演绎天哲学的本意——以天意来监督君权。这段话认为君主需遵从天意,而天的意志是“为民”。由此再阐发出去,刚好接续了《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0]的理念。因此,徐复观将董氏“天”哲学之本质总结为“近代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求之于宪法;而董氏则只有求之于天”[9]183。
需要指出,这个理想在实践中经常受挫。《史记》记录了董仲舒的尴尬经历——言灾异却被自己不知情的弟子批为胡言乱语,差点招来杀身之祸。“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1]3772-3773寥寥几笔,将个别儒生揣测圣意,扭曲所学来迎合主上的媚态,将董仲舒因理想挫败而受到的巨大心理打击呈现在读者眼前。
回到张释之,我们发现他所言的“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与《商君书》的有关理念颇为契合。但张释之对秦法并不盲从,而是有深刻的反思。他曾经批评过秦代司法的弊端如下:“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1]3330张释之认为,秦代司法表面上很严格,但只是追求字面上的规定,以严苛为能事,缺乏治病救人的恻隐之心,因此不可维系。他对恻隐之心的重视无疑来自儒家,来自孟子。孟子认为“恻隐之心”就是仁的美德。以婴儿跌入水井,引发旁观者的同情为例,孟子生动地说明恻隐之心内在于人性:“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4]237可见张释之博采儒法两家之长,将“仁”注入了天下所公共的法,赋予后者一颗道德的灵魂。这正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四、重新理解罢黜刘贺事件
在罢黜刘贺的事件上,霍光显然是有规则与章法的,其间固然是霍氏的政治势力和大胆权谋推动了罢黜的实现,但霍光采取了两个方法来赋予自身行为一定的正当性,超越了宫廷政变。首先,援引伊尹放太甲故事为自己背书,从儒家理念中得到一定的支持,而儒家理念在当时具有权威性;其次,以和平手段,通过集体上书、通过严肃的程序实现罢黜,从而产生一种秩序感、规则感。这些特点导致唐人给予霍光极高的评价,将其视为以“道”来匡正君主的典范:“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义,霍光废昌邑之乱。”(17)参见李华《中书政事堂记》,收入董诰主编《全唐文》第四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03页。关于政事堂的研究,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兼论中古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改变》,载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霍光与伊尹、周公同被视为唐代议事机构“政事堂”的先贤楷模,而这个机构有权议论君主行为是否符合“道”,朦朦胧胧地具有一些约束君权的意味。
因此笔者认为,除了前人所揭示的权谋等考量外,罢黜刘贺事件还可以从法制的角度进行解读。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汉代皇权并非绝对权力,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尊重乃至遵守既有法律,而霍光以维护一朝制度为借口,通过一套程序罢黜天子,具有一定的法制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