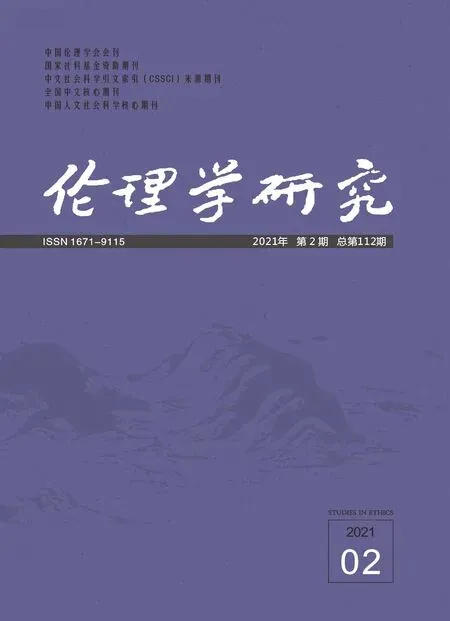消极的与积极的:谎言的区分及其道德意义
——兼论如何理解康德的谎言禁令
2021-11-26
真诚与诚实是受到高度推崇的美德,但是,谎言的存在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康德认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撒谎,因为说真话是“一个神圣的、无条件颁布命令的、不能通过任何习俗来限制的理性诫命:在一切说明中都要真诚(正直)”[1](P436);而撒谎,“作为一般而言蓄意的不真实”,哪怕是“旨在一个真正善的目的”[1](P439),都应被看作“一般而言的人性遭受的不义”[1](P435)。甚至当朋友藏在我的家中,追杀朋友的凶犯向我询问他在何处,我仍然不可以撒谎。这一严格的、不近人情的谎言禁令引发了广泛的质疑与批评。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下文简称《论说谎的所谓法权》)中对这些批评的回应并不成功,因为上述情境中对凶犯说真话违背了人们的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事实上,人们大多认同撒谎救人的应变策略,并认为类似情境中谎言是可以得到同情与谅解的。康德的严峻立场及其引发的激烈批评隐藏着诸多未经澄清的问题:是否所有情境中的谎言都能够一概而论?谎言都具有共同的本质,还是仅仅具有“家族相似性”?如果对谎言进行区分,区分谎言的原则是什么?康德谎言禁令所禁止的是何种谎言?本文从说谎者在具体情境中的地位特征(主动与被动)出发,将谎言区分为消极的与积极的,并将消极谎言的话语情境区分为面对灾祸与抵御邪恶,以此区分来阐明不同谎言的道德意义,努力化解康德谎言禁令与日常道德情感和价值直觉的矛盾与争议,从而正确理解谎言禁令的内涵与外延。
一、主动与被动:行动者地位及其道德意义
无论是在哲学家们高扬人的主体地位的论述中,还是常人对自己作为行动主体的觉察中,人作为道德主体常常被看作行动系列或因果链条的发起者。但是,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人们总是在某种给定的情境中进行道德抉择,这种给定的情境要素给予人们有限甚至局促的选择空间。在这种落差中,行动者的抉择的道德价值与行动者地位(sta⁃tus of agent)具有本质关联:主动发起一个行动系列与因果链条,其行为的道德性质主要决定于发起者的动机(准则)与手段;被动地回应一个给予的甚至强加的行动系列与因果链条的行动者,其行动之道德性质则更多地决定于行为情境中的相关给定要素,正是这些给定要素限制了行动者的选择,进而对其行动的道德价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例如,一个抢劫者发起一个暴力行动,抢夺了他人的财物,这一行动的道德性质决定于抢劫者的动机与手段;被抢劫者被迫采取保卫自己的行动(虽然可能被迫诉诸导致伤害或致命的暴力)的道德性质,更多地决定于他所面临的被抢劫的具体情境要素。
在上述案例中,人们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出发,认同行动者地位(主动与被动)对人们的抉择与行动之道德价值的决定作用。正因如此,人们才能够在道德与法律意义上拥有在某些情境中使用暴力的权利,从而能够证成“正当防卫”概念;在此概念中,虽然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司法实践,但都从类似的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出发,支持暴力活动的受害者拥有保卫自己的权利,即使这种自卫行动对侵害者造成了严重甚至致命的伤害。处于被动情境中的行动之道德性质更多地决定于具体情境中的约束条件,这种约束条件不仅能够证成暴力在某种被动情境中的合法性与道德性,人们甚至还会高度赞扬某些在此类情境中挺身而出者,称赞当事人临危不惧,或者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帮助或奖励。
行动者主动与被动的地位特征,与道德哲学基本难题有着密切关系。如我们所知,在一般情境中被广泛认同的道德规范,如“不能伤害他人”“不能损害他人财物”“不能撒谎”等,总会在某些行动者处于被动地位的情境中,被认为应该予以放弃或者搁置,从而引发了道德哲学的基本难题:是否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规范?或者以康德的概念来提问,是否存在真正的完全义务?在道义逻辑的命题方阵中,道德规范及其例外可以如此表述:必须不伤害他人(必须非P),(在正当防卫中)可以伤害他人(允许P);这两个命题是矛盾关系,分别位于道义逻辑对当关系图(正方形)的右上角与左下角。实际上,这也是道德难题的基本逻辑结构:一个必须肯定或否定命题(必须P 或必须非P)表述的普遍规范是成立的,但是,它的矛盾命题,即允许否定或肯定命题(允许非P 或允许P)在某些特殊情境中却也能成立。人们总是可能遇到或者设想一种特殊的被动或被迫的情境,使得某种道德规范所禁止的行为成为可以接受的选择。例如,人们大多认同如果撒谎能够救人的话,是可以撒谎的。
正是在上述实践困境与理论难题的背景下,约瑟夫·弗莱彻认为人们在道德抉择时有三种思想路线:“(1)律法主义方法;(2)反律法主义方法,与前者相反的极端,即无律法的或无原则的方法;(3)境遇方法。”[2](P9)律法主义方法指的是无条件地遵守普遍道德规范的方法;反律法主义方法认为并不存在具有指导意义的普遍道德规范;所谓境遇方法,则是“介乎律法主义与反律法主义的无原则方法之间……境遇论者在其所在社会及其传统的道德准则的全副武装下,进入每个道德决断的境遇。他尊重这些准则,视之为解决难题的探照灯。他也随时准备在任何境遇中放弃这些原则,或者在某一境遇下把它们搁到一边,如果这样做看来能较好地实现爱的话”[2](P17)。境遇方法对律法(道德规范)的态度实际上类似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处于尊重律法和“搁置”甚至“放弃”律法这两种做法之间。境遇方法尊重准则的指导地位,但并不固守这些抽象准则,甚至极有可能在实践中“放弃”或“搁置”律法。弗莱彻深刻地指出了在某些特殊情境中律法(必须P)及其对立面(允许非P)所构成的逻辑矛盾与道德难题。
作为拥有主体地位的行动者,人确实能够在感性世界中发起一个因果链条或行动系列;但是,更多的时候人们却是无可奈何地被卷入一个因果链条或行动系列,以被动姿态、在给定情境中做出有限的选择。强调人们的主体地位的时候,人们就类似于康德所讲的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主体;强调人们卷入并非自己发起的行动系列与复杂事件的时候,人们的处境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Gewor⁃fenheit)入世界之中,或者处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临界处境”(Grenzesituation),在这种处境中,“我们必有一死,我必受苦,我必须战斗,我必须服从偶然性,我无可改变地卷入罪责”[3](P19-20)。甚至在某些悲观情境中,“临界处境——死亡、偶然性、罪责或世界的不确定性,使我们面对着失败的现实”[3](P22)。因此,作为真实生活世界的有限存在者,在很多情境中人们并没有能力成为康德所说的因果链条或行动系列的发起者;恰恰相反,人们往往被抛入或者卷入某一个不知是谁发起的事件系列,在给定情境中被迫做出有限选择。
康德在论及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与善良意志的时候,强调理性存在者能够在感性世界中发起一个因果序列,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类历史与生活世界的严峻现实;人们常常直面灾难的打击与邪恶的侵袭,经常面临如下道德情境:除了做出从善弃恶的抉择之外,还被迫在诸善之中取其重,或者在诸灾或诸恶之中取其轻。康德在“门口的凶犯”这一思想实验中坚持说真话的立场,的确严重背离了人们的道德情感与直觉,从而引发了广泛而猛烈的抨击。康德对普遍规范的坚持是可以理解的;从定言命令的概念源流来看,这一坚持也来自律法主义的影响。因此,强调具体行为情境的境遇主义对康德提出的批评是很有力量的:“律法主义者说,即使他对一个逃出收容所的人讲了该人试图杀害者的去向,而该人据此找到并杀害了那个人,他至多只犯了一个罪孽(谋杀),而不是两个罪孽(连同撒谎)!”[2](P17)
二、积极谎言与消极谎言
如上所述,行为者的主动与被动的地位特征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某些情况下甚至能够决定行为之道德价值。例如,暴力行为在主动还是被动的情况下发起,谎言是在何种具体情境中产生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谎言概念本身就带有负面的道德色彩,根据诚信规范的普遍立法化要求,任何情况下话语中如果包含“蓄意的不真实”,言说者都会被定义为撒谎者,由此背负着负面的道德评价与感受。事实上,说谎概念中包含的负面道德评价与人们在某些情境中被迫说谎的道德经验,让许多坚守诚信美德的人们产生了深深的道德困惑。但是,对那些并不在乎诚信美德的人来说,反而不会有这样的困惑。
康德并未区分说谎者在具体情境中的主动或被动的地位特征,只是简单地将说谎定义为“(在该词的伦理学意义上)作为一般而言蓄意的不真实”[4](P439);但是,这种“蓄意的不真实”是主动发起的、通过获得对方信任以实现欺骗之意图,还是被动应对的、以避免灾祸或者抵御邪恶为目的,康德并未进行区分与讨论,因而将“撒谎以借钱”与“撒谎以救人”看作是同一种撒谎行为。事实上,在人们的话语行为中,“蓄意的不真实”也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积极谎言(active lies):主动地发起一个话语行为,内在地包含着“蓄意的不真实”,却想通过获得对方的信任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因此可以称之为真正的欺骗;第二种是消极谎言(pas⁃sive lies):被动地应对某种给定的迫切甚至危难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只存在有限的选择,以降低损失(灾祸)或者避免伤害(邪恶);这种话语因为包含“蓄意的不真实”而被称之为谎言,但是,很难说是真正的欺骗或者欺诈,人们大多会认为这种谎言是可以获得谅解甚至为之辩护的。
在康德的讨论中,他以如下案例为典型谎言:“在我需要钱的时候我就去借,并且答应如期偿还,尽管我知道是永远偿还不了的。”[5](P41)这种情境中的谎言当然是主动的、通过获取他人的信任来得到利益的欺骗。被动的“蓄意的不真实”则出现在被称之为“门口的凶犯”的思想实验之中:康德认为,当凶犯追杀我的朋友,朋友藏在我的家中,我也应该在面对凶犯的询问时说真话。康德坚持在如此情境中也必须说真话的原则激起了广泛抨击:置朋友的生命于不顾而坚持说真话,与人们的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产生了尖锐矛盾。在“门口的凶犯”这一思想实验中,坚持说真话的是自己,被追杀的是朋友;如果稍微更改这一条件设置,则可以清晰地呈现消极谎言在此危难情境中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假设凶犯追杀的不是朋友而是我自己,并在我的藏身之处附近问“你藏在这里吗?”此时,被追杀者是否应该坚持诚实原则以如实回答?如果被追杀者以保持沉默回避了这一问题,那么,当他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向后门处抛扔物体吸引凶犯,从而让自己能够从前门脱身,他是否违背了诚实原则?
事实上,行为意图中的“蓄意的不真实”并不仅仅存在于话语之中。让我们考察另一类似的情境:一辆车明确地向某人撞来,此人先向道路左边闪避,但这是“蓄意的不真实”,他只是想将车辆引向左边;他很快又向右边闪避,结果该车在惯性作用下掉到左边池塘之中。很显然,任何对这种“临界处境”(Grenzesituation)中的“蓄意的不真实”进行谴责的道德话语,都直接违背了人们的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如果这种临界处境之中的行动可以包含“蓄意的不真实”,那么,话语中的“蓄意不真实”又应该如何看待呢?话语本身就是行动,人们时刻都在“以言行事”;如果不能以撒谎来救人,那么也就不能以撒谎来救自己,此类情境下人们似乎被剥夺了求生的权利。事实上,任何道德规范都不应该给予个体如此沉重的、不公平的约束:向伤害自己或朋友的人坚守诚信,甚至放弃自己或朋友求生的权利。在真实的生活世界中,无论是法律规范还是道德舆论,都允许人们在此类情境中使用武力保卫自己或朋友。相比而言,撒谎其实是代价更低、损害更小的自卫措施。不仅如此,人们在危难情境中还可以采取比撒谎更为激进的行动对抗侵害,也能够得到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的支持;否则,善良意志就真的会成为像康德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软弱无力的存在。
如上所述,确实存在着某些特殊情境,身处其中的人们如果坚守某些普遍的道德规则,就需要付出巨大的、难以承受的牺牲。因此,人们怀着惋惜之情赞赏“尾生抱柱”的守信行为,也并不会苛责不愿意牺牲生命的权宜策略,譬如换个安全位置继续等待恋人。这种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也是合乎康德所讲的“应该蕴涵能够”原则:“纯粹几何学拥有一些作为实践命题的公设,但它们包含的无非是这一预设,即假如我们被要求应该做某事,我们就能够做某事。”[6](P40)命题“假如我们被要求应该做某事,我们就能够做某事”是一个充分条件假言命题(肯定前件就能肯定后件),该命题的逆否命题(否定后件就能否定前件)就表述为“如果我们不能够做某事,那么我们不被要求应该做某事”;这就意味着在“门口的谋杀者”这类情境中,说真话属于不能够(因为人们不能置朋友的生命于不顾而对凶犯说真话)。因此,人们在这类情境中就“不被要求应该做某事”,即不被要求应该在此情境中说真话;要求在此类情境中说真话,实际上意味着牺牲朋友的生命。
我们已经清楚地区分了积极谎言与消极谎言及其各自的道德意义。那么,是否所有被动的、应对给定的不利或危险情境的“蓄意的不真实”,都能够得到辩护呢?在流行的谎言分类中,有一类谎言被称为善意谎言,或者白谎(white lies),它被定义为“无害的、微不足道的谎言,尤其是当说话者为了减少对别人的伤害时说的谎言”,或者“是一个不会伤害任何人的谎言,特别是说话者为了避免伤害别人的感情时说的话”[7]。善意谎言的定义强调避免或减轻伤害的动机,并没有从说话者的行动者地位出发来阐明此类谎言的道德价值。在善意谎言的典型情境中,人们为了减轻或避免伤害而被迫说谎,确实属于消极谎言的范畴,例如医生为了让病人免受心理冲击而隐瞒病情。当然,即使这种情况下的善意谎言也面临争议,毕竟病人的知情权在此没有得到尊重(人们有权要求知道真相,哪怕真相就是死亡),尽管医生的行为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谅解。因此,需要澄清善意谎言与消极谎言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事实上,虽然善意谎言大多是消极谎言,但并非所有的消极谎言都是善意谎言。在面对侵害时进行自我保卫或保护他人的情境中采用的消极谎言,并不符合善意谎言的内涵与外延,却是能够得到道德情感与直觉的辩护。因此,有必要对消极谎言的类别及其道德价值进行深入讨论。
三、两种消极谎言:面临灾与恶的道德抉择
消极谎言与积极谎言的区分虽然也存在微妙与复杂的情境,但总的来说,还是能够较为清晰地区分获得利益与避免伤害这两种动机:以获得利益为动机的主动撒谎就是积极谎言,以避免伤害为动机的被动撒谎就是消极谎言。为了避免伤害儿童的幼小心灵而撒谎,此时撒谎者的内心充满温柔与关爱,确实是康德所说的“纯粹善良的意志”了,这样的谎言可以被称为善意的谎言(white lies)。但是,上述被迫撒谎的情境只是消极谎言所产生的情境之一,并且是道德特征较为简单的情境。康德认为,从概念的微妙差别出发,可以将生活世界中发生的、拉丁语称之为“恶”(malum)的事件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别:“恶(Böse)与祸(Übel)[或苦(Weh)]”[6](P81),这一区分具有深刻的道德意义。在汉语中,人们将不好的事情称之为天灾人祸,天灾就是上述概念中的“祸”(Übel);但是,汉语中“人祸”的意义要比恶更为宽泛,将某些因为人为的失误(并非故意)而造成的灾难也称之为人祸,而不仅仅指人类的邪恶行为带来的伤害。在产生消极谎言的情境中,让人们处于被动地位的情境或者是灾祸,或者是邪恶;前者主要表现为天灾或疾病,后者主要是人类不法行为的威胁与侵害发。应对这两种情境而产生的消极谎言,有着极为不同的道德意义。
首先,让我们来看灾难情境[祸(Übel)]中人们被迫说出的善意谎言及其道德意义。灾难情境中的善意谎言实际上是道德价值的排序与取舍:是遵守诚信义务、保全自己诚实品格呢,还是更多地照顾他人的利益、感受或尊严?这种被迫情境中产生的谎言,为他人着想的动机是真实的。这种谎言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谅解(forgivable),因为这种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出自纯然善良的动机。例如,医生考虑到患者的心理状态与治疗效果而隐瞒严重的病情,向病人传达积极信息,鼓励乐观态度。虽有争议认为这一做法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权,并将患者置于需要哄骗的弱者地位,人们却也能够考虑到医生的善良动机而谅解这种行为。需要强调的是,在此我们说的是“谅解”,乃是因为这种谎言的道德性质并没有改变,它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谎言。从康德定言命令的诸多派生形式来看,善意谎言仍然“由于纯然的形式而是人对他自己人格的一种犯罪”[4](P439),也就违背了“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6](P39)这一形式要求;但是,它好像内在地合乎了“人是目的”这一要求:“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5](P48)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能获得某种程度的谅解。
其次,在面对恶(Bose)、面对不法行为侵害的时候,人们被迫说出的谎言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善意谎言,因为它不再具有“微不足道的”“为了避免伤害别人感情”等特征;不仅如此,这种面对恶的侵袭与逼迫而产生的谎言往往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在“门口的凶犯”这一思想实验中,人们面对凶犯的询问,权衡这一“临界处境”中的诸多要素与行为准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朋友的生命安全将会在此情境中成为撒谎的动机,此刻的行为准则应该是:“为了朋友的生命安全,我应该向凶犯传达‘不真实’的信息”,或者“为了不让世界上多一桩凶杀案,我应该以‘不真实的’信息来引导凶犯离开现场。”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导致撒谎的行为准则,恰恰能够合乎定言命令的形式化要求,并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我愿意任何人在上述特定情境中以此方式保护朋友的生命安全,无论我是面对凶犯的当事人,还是被保护的那位朋友;甚至凶犯也会愿意以此方式保护自己的朋友,并且愿意自己的朋友以此方式保护凶犯本人。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灾祸的谎言可以被称之为善意的谎言,因为这些谎言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灾祸对当事人的伤害,哪怕只是为了避免他人面对残酷的真相,这种善良动机也让撒谎行为得到了谅解(forgivable)。面对邪恶的时候,如果谎言能够保护当事人以及其他相关者避免受到邪恶的伤害,那么这种谎言就得到了辩护(justifiable),因为其行为准则能够符合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的形式要求。严格地讲,这时的谎言已经不同于康德所说的“蓄意的不真实”,而是真正的“被迫的不真实”,这种话语策略是这种情境中代价最低的自卫方式。因此,这两种撒谎行为之道德价值的区别已经很清楚了:前者(面对灾祸情境的善意谎言)是可谅解的,后者(面对邪恶情境的自保谎言)才是可辩护的,这种谎言能够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justification);换句话说,这种情境中说谎并不是勉为其难地违背较轻义务(对凶犯的诚实义务?)去履行更重义务(保护朋友的生命!),它本来就是人们在这种情境中的合乎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的选择。
灾祸与邪恶分别决定了面临它们的情境中被迫之谎言的道德价值,因此,两者应该被谨慎地区分,以确定撒谎行为到底出于何种情境所迫。设想一种情境:某人因为股票大跌而准备跳楼自杀,人们在楼前进行劝说,这种行为情境是被迫于灾,还是被迫于恶?股票大跌虽然是灾,但是因此而自杀却是不折不扣的恶(虽然是对自己行恶),此刻撒谎以救人是在此“临界处境”中的正确选择。在此情境中撒谎说自杀者的股票已经涨回来了,至少可以让他在当下放弃自杀冲动,这样的动机(准则)是可以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的。但是,如果某人知道了股票下跌,但为了照顾当事人的感受或者避免成为传递坏消息的不祥之人,撒谎说股票没有下跌或者已经涨回来了,这样的谎言虽然有善意动机的因素,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因为这种“不真实”的信息可能会误导对方的决策。因此,这种谎言尽管有可能因其善良动机获得一定程度的谅解,却终究难以在道德上得到辩护,因为传达“蓄意的不真实”的信息侵犯了人们的知情权。
四、定言命令的普遍立法化要求及其限度
如上所述,消极谎言也区分为两种情境:面临灾祸的被迫撒谎与应对邪恶的被迫撒谎。但是,并非所有消极谎言都能够获得道德辩护(justifica⁃tion),面临灾祸的被迫撒谎通常可以称作善意谎言,能够因其避免伤害相关当事人的善良动机而获得谅解;但是,面临邪恶的被迫撒谎却是能够因其危难情境而不再被认为包含着“蓄意的不真实”,而只是“被迫的不真实”,因为此时的真实信息会成为帮助邪恶伤害自己或无辜者的工具,如我们在“门口的凶犯”这一思想实验中看到的那样,如实回答凶犯的问题会帮助凶犯找到并杀害自己的朋友。因此,贡斯当批评康德在此情境中也必须说真话的立场:“说真话是一种义务;但只是针对对真话有一种法权的人。但是,没有人对伤害别人的真话拥有法权。”[1](P434)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境之中,人们并不对凶犯负有诚实义务,因为凶犯不仅意图谋害他人的生命,还将他人的诚实当作完成谋杀的手段,这两点意味着凶犯的行为准则不仅不能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同时还违背了“人是目的”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回答问题的人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应该是什么呢?当他人索取真话以完成邪恶的目的,并且回答者明知真话可能帮助对方达成邪恶目的,此刻的对话关系已经脱离了彼此负有真诚义务的“你—我”关系,回答者的行为准则就应该是:“如果真话会成为达成严重的犯罪(有人犯下重罪)与伤亡(有人失去生命)的工具,我就不应该提供这样的工具。”事实上,这一准则能够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并且获得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的支持。康德的定言命令有三种派生的表述形式,即“普遍的自然法则”“人是目的”与“自律原则”。三条派生形式均可用于检验上述准则:“不提供帮助邪恶者达成犯罪之工具的信息”这一准则能够成为普遍法则,并且将朋友的生命作为目的(同时拒绝帮助凶犯达成犯罪也可以说是以凶犯的人性为目的),以及出于自己在“临界处境”中为自己立法的意志。
康德在“门口的凶犯”这一思想实验中坚持认为应该说真话的立场,与人们对他的诸多批评之间的矛盾,可以归结为一个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普遍化的道德规范的施及范围到底如何确定?换句话说,应该以道德规范的要求对待哪些人?哪些情境或哪些人可以被排除在外?对那些并不准备遵守德性法则的人(如在门口追杀朋友的凶犯),我们是否仍然应该以普遍道德规范要求的方式对待他们?换句话说,能否普遍地要求人们对所有人都说真话,甚至包括追杀朋友乃至自己的人?这一要求是否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与现实性?
在康德看来确实应该如此:说真话的义务不能有例外,即使对“门口的凶犯”也应该说真话。对康德的批评大概有两种观点。大多数批评者认为,说真话的义务在救人的情况下是可以有例外的,人们不能教条地看待道德规范,要根据情境来做决定;弗莱彻关于境遇伦理的思想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中国古人关于“经与权”的思想也解释了规范与例外的关系。另一种批评则认为,说真话的义务当然是不能有例外的,否则任何道德规范都能在某些情况下找到例外的理由,道德规范的普遍必然性何在?但是,人们对凶犯并不承担说真话的义务,因为凶犯的动机违反了定言命令的要求,并且不以自己与他人的人性为目的,将自己置于彼此承担诚实义务的道德共同体(康德所说的“目的王国”)之外。因此,人们对凶犯的“被迫的不真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撒谎;因为道德义务都建基于特定情境与人际关系之中,如果凶犯利用他人的诚实来达成邪恶目的,那么,他也就无权要求他人以诚实相待。
两种批评的立场其实有着共同之处:在某些情境中人们不能以普遍的道德规范所要求的方式对待某些人。孔子说过,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因此,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这种谚语式的表达,在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汉谟拉比法典》)现代行为科学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促进合作而非背叛的最佳策略,并非一味地善良与忍让,始终以善良与宽容的态度对待那些不遵守道德规范的人,恰恰相反,是采纳类似上述所说的“一报还一报”策略,并且这一策略是合乎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的:“‘一报还一报’的稳定成功的原因是它综合的善良性、报复性、宽容性与清晰性。”[8](P36)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在其他的重大问题上也持有相似立场。例如,康德坚定地支持应报正义的原则:“但是,公共正义会把惩罚的何种方式与尺度当作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呢?这只能是平等的原则……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如果诽谤了别人,你就是诽谤了自己……如果你杀了别人,你就杀了你自己。”[9](P99-107)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康德坚持死刑的必要性:“那么他们应该在处死监狱里最后一名谋杀犯之后,再执行他们解散的决定。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自己言行应有的代价……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将全部被认为参与了这次谋杀,公开违背了正义。”[9](P107)康德如此严格地坚持应报正义以及死刑的必要性,实际上意味着这样的判断:那些不把他人的人身中的人性当作目的的人,就无权要求别人把他的人身中的人性当作目的了。事实上,康德并不将死刑与谋杀这两种终结生命的行为看作是同一种行为,因为死刑在法律意义上区别于谋杀。死刑与谋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理,面对邪恶的消极谎言与其他谎言在道德意义上也有本质区别,只是这一区别没有死刑与谋杀的区别那样事关重大,人们并没有以不同的概念进行命名。但是,出于保护自己与他人的善良动机的“被迫的不真实”,本质上区别于意图谋财害命的“蓄意的不真实”。
康德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不仅与定言命令的思想一致,符合人们的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同时获得了广为认同的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等司法实践的支持。我们可以认为,某些情境中人们不再有义务对待某种行为人,这种行为人因其行为对道德规范的背弃,不再享有同一道德规范赋予的权利,虽然这种义务与权利在一般情况下原本是存在的。譬如,骗子在欺骗我们的时候,不能要求我们仍然对他负有诚实义务,如实提供让他的骗局得以成功的信息;这也合乎保护个人信息的初衷。康德认为,从诚实义务作为普遍规范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应当对追杀朋友的凶犯诚实相待;但是,这一要求实际上违背了定言命令三种派生形式的要求(普遍规律、人是目的与立法意志)。不仅如此,在此情境中对受害一方课以最严格的道德约束,实际上意味着善良意志的软弱无力,连保护自己的权利都被束缚,坐视自己的诚实被邪恶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无能为力。
五、康德的迷误与谎言的概念
康德在论述道德法则的自明性时说道:“用不着多大的聪明,我就会知道做什么事情,我的意志才在道德上成为善的。”[5](P19)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点恰恰体现在人们在“门口的凶犯”这一情境中不约而同的选择:撒谎以保护朋友的生命;人们确实“用不着多大的聪明”,就知道这是正确、成本最小并且最不会后悔或内疚的选择。康德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人们的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尖锐对立,他自己的辩护确实难以自圆其说。康德在此问题上出现迷误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将“普遍立法化”这一检测行为准则是否合乎定言命令之形式要求的环节,与简化具体行为情境要素之后的简单化准则产生了混淆;也就是说,本来应该问“你愿意每个人都在如此情境中这样行动吗?”,实际上却成了“你愿意每个人都在任何情境中这样行动吗?”。所以,在“门口的凶犯”这一思想实验中,行为准则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的检测过程本来应该问“你愿意每个人都在如此情境中撒谎救人吗?”,实际上却误以为是问题“你愿意每个人在任何情境中撒谎吗?”。显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对前一个问题是可以做出肯定回答的,对后一个问题显然应该做出否定回答。当然,康德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迷误对他的道德哲学作为整体的合理性并不会产生影响,笔者在另文中对这一迷误及其理论根源进行了深入探讨。
人类道德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谎言的广泛存在,儿童从三岁开始就能撒谎了。据心理学家们统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撒谎次数惊人,甚至在很多情境中人们认为撒谎才是正确选择。对于个体来说,诚实美德的表现,就是承认自己曾经撒谎。正因如此,康德在后期的《伦理学讲义》中也改变了对谎言的看法,认为人在某些时候可以撒谎。康德还说过,人应该说真话,但是没有必要将所有的真话都说出来。也就是说,某些时候撒谎,或者隐瞒真相,是可以的。但是,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事急无法”,就是说,紧急情况下也是有道德规范约束的。事实上,任何行为都有一个准则,同时也有一个该准则能否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问题,如上文所述,在人命关天的情境中撒谎以救人的准则,可以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因此,并不是说“事急”就“无法”,任何事情都应该并且必须有法,例如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就是两种事急之法。
那么,能否认为人们在某些特殊情境中可以撒谎,这样的谎言能够得到同情与谅解,不会让言说者因此背负长久的难以得到谅解的罪恶感呢?这并不仅仅是关于康德谎言禁令的理论问题,而是日常道德生活中的实践问题。诚实与诚信永远是被高度推崇的美德,因为人们通过话语建立起与他人的信赖关系。真诚与真实的问题不仅关乎话语与言说者的道德品质,也决定了人际关系与社会整体的诚信氛围。如何区分与看待真实存在的谎言,也有着重要的道德意义。如上文所述,谎言区分为积极谎言与消极谎言。积极谎言就是主动的、以骗取他人的信任来获利的谎言,完全属于康德谎言禁令所禁止的行为,而且不能有例外。消极谎言就是人们在某些“临界处境”中被迫撒谎。消极谎言又可以区分为面对灾祸的被迫撒谎与面对邪恶的被迫撒谎。面对灾祸的被迫撒谎可以称为善意谎言,虽然它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谎言,但是,它或者因其“是无害的、微不足道的谎言”而不受追究,或者因其避免伤害的善良动机而得到谅解。
面对邪恶情境的“不真实”信息,不再真包含于康德讨论谎言时所给出的“蓄意的不真实”这一概念的外延,而是严格意义的“被迫的不真实”。这并不是在为谎言辩护,而是为处于邪恶的逼迫之情境中弱者或受害者的生存权辩护,事实上,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此类情境中成为弱者或受害者。因此,这种撒谎不再是积极意义的撒谎,不是为了欺骗他人的“蓄意的不真实”。但是,谎言概念的使用已经形成了习惯,人们将话语行为中的“不真实”笼统地称之为撒谎,并不会像区分蓄意伤害与正当防卫这样的重大概念一样,对“蓄意的不真实”与“被迫的不真实”进行严格区分,并分别为之命名,这样的话语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终究是细微琐碎的。因此,当人们在面对邪恶的情境中以谎言或者说“被迫的不真实”自保或者救人,同时却可能承担着谎言概念带来的负面道德评价与内心感受。事实上,在撒谎可以救人、说真话则放弃朋友的思想实验中,大多数人的选择如同康德所说的那样,“用不着多大的聪明,我就会知道做什么事情,我的意志才在道德上成为善的”。在上述危急情境中,人们在道德直觉与情感的推动之下,知道拯救朋友的生命才是最为正确的事情,而且只有这样做,“我的意志才在道德上成为善的”。不仅如此,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选择是自然而然的,“用不着多大聪明”,也不必费过多的思量。很少有人会真的背离道德直觉与情感,弃朋友的生命安危于不顾,仍然坚持抽象的谎言禁令,对追杀朋友的凶犯说出朋友的藏身之处。事实上,在上述情境中仍然坚持谎言禁令的选择,甚至会让大多数人感到困惑与不安。推动大多数人做出选择的道德直觉和情感,与抽象规则之间的矛盾,上述概念与真实的背离,应该就是康德的谎言禁令产生道德困惑与理论争议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