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中的零余者形象、零度幽默与美学实践
2021-11-25孟欣
孟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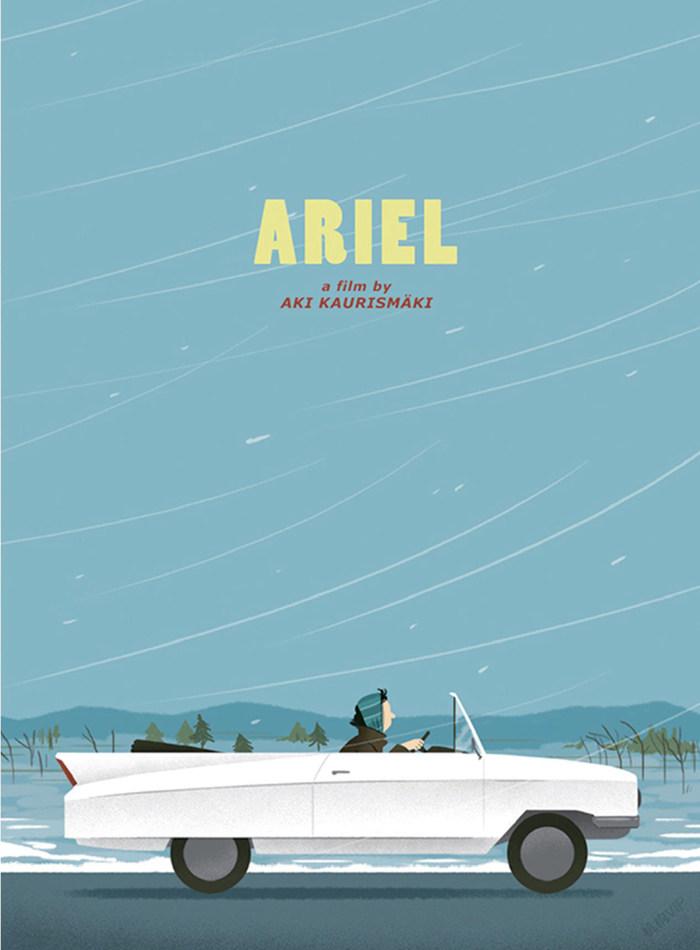
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ki)是当代世界影坛著名的芬兰籍电影导演,也是欧洲艺术电影的代表性大师,曾被瑞典名导英格玛·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誉为“北欧最具大师潜质的导演”[1]。考里斯马基的影片通常以庸庸碌碌、生活不幸的小人物为主人公,在独特的冷幽默中进行美学实践。尽管很多芬兰人由于考里斯马基对社会问题的发现和放大认为他丑化了祖国芬兰,但他的影迷仍遍及欧洲乃至全世界。
一、滑稽、荒诞而可亲的零余者形象
阿基·考里斯马基于1957年4月出生于芬兰奥里马蒂拉,在投身电影事业之前,他立志成为作家,曾经从事过送信件、洗碗等底层工作。这些工作经历使他充分体会到世俗社会的酸甜苦辣,令他明白即使是在福利制度完善、人均收入排名欧盟前列的芬兰,也存在许多脱离社会体制的零余者。在与哥哥米卡·考里斯马基(Mika Kaurism?ki)一起成立影视制作公司后,考里斯马基将自身对芬兰的体会拍成了电影,并在其中着重关注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命运,以充满幽默而饱含同情的方式展示他们失败又倒霉的人生经历,并借此赞美他们在困境中的坚韧顽强。阿基·考里斯马基在数十年漫长的电影生涯中,拍摄电影长片、纪录片与短片共计将近40部,所制作的影片数量一度达到芬兰电影生产总数的1/5。考里斯马基的电影经常以批评性眼光看待芬兰政治和社会,无论是“失业三部曲”,还是“工人三部曲”,片中的人物在生活的重压下卑微胆小、唯唯诺诺,与社会格格不入;外国观众在观看考里斯马基的电影时,有时将它们视作芬兰国民生活的范例,这也招致部分芬兰观众对考里斯马基的批评。事实上,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中永远涌动着一种来自零余者的暖流,可亲可爱的角色透露出导演的平民意识与人文关怀。即使层层累积的重压已经将零余者推到崩溃的边缘,但他们仍能在功名利禄与遁世之中为观众指出一条明路,抵达柔软的人性深处。
考里斯马基电影中的人物往往身份卑微,他们在导演对小人物不留余地、极致冷漠的境地表述中,事业、感情与生活都一败涂地,毫无社会地位可言。正因如此,绝境所反衬出的人在遭受命运与他人的践踏时,人格深处展现出的坚韧与尊严也格外耀眼。他执导的电影《罪与罚》(1983)中的主人公在枪杀导致前女友车祸死亡却逃脱制裁的富商后,游离于城市阴影中,终日在孤独与彷徨中渡过,最终选择自首并拒绝了女友的等待;《卡拉马利联盟》(1985)中17个名为弗兰克的人向梦中的乌托邦进发,却屡次遭遇自杀、枪击、暴力事件、监禁、强制婚姻等现代社会给边缘化个体带来的危险;《天堂孤影》(1986)中的男主人公尼卡德是环卫公司垃圾车的驾驶员,他先后经历了合伙人暴毙、失业、破产、入狱等挫折;《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1989)中几个摇滚乐队成员在贫困的故乡饱受饥饿,决定去美国碰碰运气,贝斯手在出发前夜就被冻死,其余人穿着不合时宜的怪异装扮在美国饱受歧视;等等。考里斯马基塑造人物的重要方法是展现角色人生的衰落,他们的命运往往从勉强生活到事事不顺,在无穷无尽的挣扎中似乎总往坏的方向发展。故事从角色的低潮期进入,比如失业、失恋或者淹没在扭曲的世界,继而在错误的选择中陷入惨境,并且越陷越深,这就是考里斯马基角色人物的基调。这些无本质差别的底层小人物往往遭受毫无理由的苦难与暴力,但无论在电影中遇到多少失败,他们总是对生活充满期待,尽管这些念头在严酷的现实前太过天真,但他们总是继续前进。这正是考里斯马基在犬儒主义的世界中呈现信念的方式,他引导观众像欣赏他人的成功一样欣赏他人的失败,无论某个角色看上去多么愚蠢和失败,显得多么多余,但只要他们乐意,他们的坚持就会在悲观世界中带来乐观的精神。
考里斯马基电影中的零余者大多平凡单调,他们总有着木讷无表情的脸和毫无起伏的说话腔调。他们的世界围绕单调的线索展开,对话总是有条有理,没有明显的情绪特征。考里斯马基要求演员只使用最低限度的戏剧水平发挥,并借此产生更强烈的内在戏剧冲突,甚至让演员故意将台词读得不甚通顺,磕磕绊绊。这样一来,即使是在角色周围的世界崩塌时,他们对待世界的方式也平淡无奇,似乎生活中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生存本身。但生活的反复无常和挥之不去的厄运,使得他们人生的唯一目的也变得如此艰难。在这种描写失败的癖好之上,考里斯马基凭借“挣扎着生存”的观念取得成功,他总是详尽地为观众展示厄运是如何降临到那些其实一无所求的人身上。在以小人物的艰难求生为主题的电影中,他的故事编排与镜头语言并不复杂,他在事件简单明了的发生之外,格外注重渲染由于事件发生在挣扎求生的人们身上带来的讽刺。各种正处于糟糕境地中的零余者角色满足于最低限度的生存,舒适奢侈在他们的世界里并不存在,他们的需求使他们没有心思理会自我,由此产生一种幽默的荒诞感。如同《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中的摇滚乐手急切地前往纽约改变人生,却忽视了自己夸张滑稽的“飞机头”“火箭鞋”一般。
二、乐观精神与零度幽默
考里斯马基电影的喜剧性存在于主角对未来的期望中,他们的困难产生喜剧,但他们并不沉溺于苦难,也不削弱自身的价值,而是在不懈的努力中争取改变自身的命运,在失败中不断尝试,从而显示出喜剧的价值。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提出,“不包含任何隐秘处或任何隐秘”的、“毫不动心”的“零度写作”[2],“从这个意义上说,考里斯马基电影中的幽默可以被视为‘零度幽默,在幽默背后看不见导演的刻意为之,片刻的喜感就是生活本然的样子,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言说和修饰”[3]。考里斯马基喜欢让小人物面对超出他们应对能力、无穷无尽的考验,并在这一过程中令人物角色通过考验得到自我提升的能力,让他们显得无辜、天真而可爱,充满自然而令人愉快的喜剧感。考里斯马基的電影中,喜剧元素与荒诞的事物无处不在,如《升空号》(1988)中男主人公在春宵一度后被手枪顶着醒来,镜头拉远时却发现是情人的儿子在与他玩游戏,懂事的孩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早餐,手枪则早就坏了;《我聘请了职业杀手》(1990)中将工作当作全部人生的水务局老员工在遭到裁员后失去人生全部价值,他在屡次自杀失败后请了一名职业杀手杀死自己,却在意外的恋爱中重新燃起了生存的意志,恰恰在此时,已经接到任务的杀手失联了……在这些小人物焦头烂额的生活中,凡事都不着痕迹地潜藏着幽默感。这种喜剧性手法的运用,让影片能够调节苦闷压抑的氛围,用会心一笑来缓和人物挫败给观众带来的焦虑感,这也是考里斯马基最常用的技法之一。
喜剧是一种伟大的人文艺术,是能以戏谑而荒诞的语气谈论生命中不可承受的智慧,为人物增添了一层光环,也在导演、电影与观众之间建立了共同的纽带。故事片和喜剧类型电影的幽默感往往来自观众对类型化情感的预期,但考里斯马基影片中的幽默感则来源于电影情感叙事从有化无、由大化小的过程。简单直接的实用主义功能在遇到冲突的时候,会更倾向于按照类型方法进行叙事,其结果是使得某一本该充满喜剧意味的情境被空洞化,从现实的情境中剥离,这也令其中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无趣;考里斯马基则反其道而行之,在本该在情感充沛的段落令演员表现得面无表情、不痛不痒,这正是“零度幽默”的喜剧性之所在。《希望的另一面》(2017)中的小推销员维克斯特伦靠一笔打牌偶然赢得的钱盘下一间并不赚钱的小餐馆,首个光顾的客人按照服务生推荐点的“大餐”竟然只是煮土豆、罐头蔬菜和沙丁鱼,服务员还冷淡地回他“我们的厨房是混合型的”随后走开。客人只得无奈地为自己倒酒,庄重的西餐礼节为这个并不相衬的简陋场景令观众为了客人的遭遇会心一笑,也增强了观众与维克斯特伦之间的感情联系,令观众认识到看似手握巨款的维克斯特伦仍然前路未卜,保留着一己之身的卑微,悲哀伤感的幽默也带来了迷人的魅力。如果观众将电影中的一切视为玩笑,电影中将无法产生任何人为安排的戏剧性场面,取而代之的是用幽默的眼光打量一切的“零度幽默”,以及其中独属于小人物的乐观精神。这些小人物的生命中充满无可诉说的苦难、难以掩盖的悲伤与无奈,但其中随处可见的幽默感,令观众与人物一起将不幸转化为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在无奈的耸耸肩后继续前行。考里斯马基把喜剧作为一种工具,他影片中的一切都具有零度幽默的潜质,仿佛随时会失去严肃感,而诙谐的风格能令观众为任何失去严肃感的荒诞事物会心一笑,继续以乐观而顽强的态度对待生活。在“零度幽默”的风格中,人物的出糗和对他们的同情心在自然平实的风格混杂,形成了考里斯马基电影叙事的基本框架,并引出相应的叙事主题,渲染荒谬的气息。
三、极简风格美学实践中的人本主义
作为一位个人风格强烈的作者导演,考里斯马基作品的编剧、导演、剪辑通常全部由他亲自操刀。他的电影素来以极简主义美学闻名,简洁的对话、朴素的表达方式以及大量静态镜头的运用都保持着最小限度的情感外露。考里斯马基的电影美学继承了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自然主义风格,镜头多使用长镜头与固定镜头,场景调度自然而简洁,在去冲突与矛盾的现实主义气质中将故事娓娓道来,被评论家赞誉为“沉默的诗歌”。如同简明淳朴的故事一般,考里斯马基的电影画面没有过多修饰,也看不出人工光照的痕迹,庸庸碌碌、为生活愁苦不已的小人物的行动构成了电影的主旋律。与贝拉·塔尔(Béla Tarr)等喜欢令镜头跟随角色运动的调度方式相比,考里斯马基偏爱单镜头固定机位,甚至常常以固定镜头为前提,人物在“画框”内出入,很多剧情的交代甚至直接利用了画外音。《升空号》开头,男主角卡苏里南工作的煤矿停业,毫无出路的工人人心惶惶。一名失去希望的老矿工与卡苏里南在小酒馆的床边喝酒,并将自己的车钥匙留给了他,随即给枪上膛,走进象征危险的红色大门。镜头此时平摇到卡苏里南独自一人的近景,他旁若无人地抽着烟;画外的一声枪响后镜头再次跟随卡苏里南起身的动作摇回卫生间门口并反打切换到他的面部表情,暗示老矿工已经自尽。《尤哈》(1990)结尾处,被花花公子辛麦卡骗走妻子的尤哈拿着一把锋利的斧头找上了辛麦卡,辛麦卡惊慌失措地逃进了厨房的储物间,尤哈在微微仰角的近景镜头中拉开了储物间的白色拉门,他不完整的面部与在白色背景上剧烈摇晃的影子形成了强烈不安的氛围,他持斧走进室内,门关闭,画面黑色渐隐;画面渐显后,镜头角度微微下调到正常高度,同景别内的白色大门打开,尤哈走出,胸前举起了一把沾血的斧头。这一事件与《升空号》中老矿工的自杀一般,是由重要人物的死亡标识出的重要转折或高潮,但在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中,这样重要的事情仿佛被熟视无睹,摄影机甚至并未对其进行正面展示,仅仅展现了事情的起因与结果。考里斯马基创作的故事始终围绕着人们的各种局限,他电影的制作风格由此具有明显的可辨识度。他以简约的摄影與调度形成了一种自然单调的电影制作风格,因为这正是人们生活本身的平淡和无趣。考里斯马基的电影看似在嘲讽残酷的世界中顽强生存的小人物,但实则以充满同情的方式展示了他们在每况愈下中笑对缺憾的能力,让观众坚强地找到全人类共通、只有在失败中才能寻找到的幽默感,从而把不堪回首的往事变成玩笑。
与片中主人公遭受的困难与挫折相比,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大部分影调显得较为明亮,彩色电影更加惯用饱和色彩,与柔和的阴影跟亮光产生对比,这些丰富的色彩结构填补了情感表达上的留白。破旧的房间里光线暗淡,交通工具年久失修无法正常运转,人物则在蓬头垢面中庸庸碌碌,所有这些生活中的奇形怪状之物都以它们的丑陋时刻提醒观众它们的真实;与此相对,高饱和度的色彩则显示着它在电影形式中的代表性。在《火柴厂女工》中,女主角家庭装修以冷峻的灰、白、蓝色调为主,表现了禁欲严苛的家教环境;酒吧中则出现了五颜六色的人群,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女主角身着浅卡其色的衣服郁郁寡欢,这既符合人物身份,也与她生活的孤独苦闷状态相契合;她在恋爱后挑选了一条色调明亮、饱和度高的桃红色裙子,却在格格不入的家庭中被掌掴。《薄暮之光》中一直关心男主角的快餐店店长有着一头耀眼的金发,身着红黄相间的工作服,与男主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考里斯马基电影中的色彩有着强烈的造型、表意功能,大红与大绿被用来突出背景,淡粉色与薄荷绿则指向人物,具有调和环境与角色内心情感的作用,明暗、冷暖、对比色相得益彰。考里斯马基还喜欢将镜头对准单一物品,突出其造型感,比如被踩在地上的鲜花、播放着新闻的电视机、火柴厂运转的机械流水线等。在固定镜头中,这些物品为严格而固定的趋势所主导,就像角色一样被固定在某一确定的情境中,毫无生机。考里斯马基提醒着观众,他电影中的角色与物品一样并没有特别之处,只是借由电影手段从背景中凸显了出来。生活是奇形怪状、丑陋而残酷的,但正是因为生活是丑陋而残酷的,从其中能够找到美的存在才弥足珍贵,如同他镜头中的人物总是在悲伤之中仍能找到来之不易的快乐一般。考里斯马基嘲讽好莱坞故事片中的无病呻吟,并着眼于自然主义的电影所能展现的美,这些带着窘迫、压抑与悲伤的美因其真实而获得更深的共鸣。《升空号》的结尾处,经历失业、被抢劫、入狱、出逃、朋友死亡后的卡苏里南终于登上了偷渡船升空号重获自由。伴随着朝霞静静停留在海港的升空号,白色的船体与红色的烟囱、黎明的深蓝色天空形成和谐的对比,船上的灯光映照在海水上,显出粼粼波光。尽管在影片大部分时间中,包围在角色身边的总是一片衰败,但那些短暂的美丽却因此更加耀眼。
结语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不仅表达了对现实的失望情绪与批评意见,还通过对零余者形象的幽默性塑造,展示了更多带有希望的可能性,他的幽默是小人物在悲伤境地中隐约闪烁的一线光明。近乎抽象主义的极简美学使电影超越了对个人的快乐光彩的展现,从而在更为现实的境遇中找到最终通往人文主义的希望。
参考文献:
[1]李铁.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艺术研究[D].沈阳:鲁迅美术学院,2017:31.
[2][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8.
[3][塞尔维亚]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历史悲剧的维度[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315.
【作者简介】 孟 欣,女,江苏扬州人,青海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青海民族大学校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研究“英美文学精品课程建设”(编号:2016-JR
KC-04)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