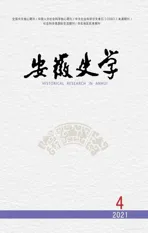孔子的礼乐美学思想
2021-11-25赵敏
赵 敏
“礼乐之治”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学者陈昭瑛认为“礼乐之治”是孔子的理想政治,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认为“礼乐之治”是“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孔子的礼乐美学思想提出一些个人见解。概括而言,孔子以“中和”为原则,以“德义”为灵魂,以“尽善尽美”“天人合一”为最高审美境界,形成了他的一系列礼乐美学思想。
一、情理相融、同异相生的辩证统一思想
孔子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礼乐的治世作用。如果说周公制礼作乐从制度上对传统礼乐进行了理性规范,那么孔子引“礼”归“仁”,则从情感上使传统礼乐文化提升了理性内涵。先秦儒家认为“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2)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46、544页。孔子意识到礼乐源于情感,并可传导情感,进而提升塑造新的高尚情感,正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礼乐完善个体的“君子人格”,如春风化雨,可以使人“日用而不知”,最终可达修己、安人的政治理想。
孔子重“礼”,认为人们只有守礼有度,言行举止不逾矩,社会才能得以稳定和谐。但他更崇尚“乐”的地位,认为“乐”能有效发挥伦理教化的作用,在涵育“君子人格”时具有更高的境界,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就是指“乐”,心怀大道与仁德,以悠游的态度润泽于“艺”,于审美化境中达于理性境界,是乐的化育功能。从郭店楚简:“有知礼而不知乐者,无知乐而不知礼者”(3)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和《礼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4)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46、544页。等资料都可窥见孔子尚“乐”的态度。
事实上,春秋时期“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5)郑樵:《通志·乐略第一·乐府总序》,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83页。先秦儒家认为“乐和同,礼别异”,舒缓典雅温和的“乐”能使人们放松戒备,减轻疏离,便于沟通交流,从而使社会处于温情脉脉的氛围之中,少却剑拔弩张的紧张;而“礼”则具有区别等级伦序的作用。孔子主张礼乐相须为用,因为“乐胜则流,礼胜则离”,一味地强调“和同”则容易使人陷入不加节制、混淆尊卑等级界限的境况,而礼事太过,则易使各等级之间的关系趋于疏离。只有礼乐皆得,方可涵育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即《论语·宪问》所言“文之以礼乐,可以为成人矣”。孔子还强调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事实上,他本人也是这么做的,如被宋人包围时,仍弦歌不辍,“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6)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第3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4页。被困于陈蔡绝粮的困境下,还在不停地歌唱、弹琴,“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7)《史记》卷47《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30页。
二、以“德义”为灵魂的教化思想
孔子所主张的礼乐教化,非唯人们熟稔“升降趋仰”之仪节仪容,更重要的是懂得礼乐所蕴含的自然法则、宗法伦理及德义,希望经由礼乐不断地丰盈人们的道德情感,完善德性修养。正如《乐记·魏文侯篇》所言:“君之听者,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也。”孔子主张以礼乐教化民众,其意在于“育德”,“德”才是礼乐的旨归,“礼云礼云,玉帛云呼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非玉帛之器,而乐亦非钟鼓之属,礼乐深处自有“德义”。《礼记·郊特牲》记载:“宾入大门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乐阕,孔子屡叹之”,孔子之所以对这种典雅的礼仪屡次赞叹,不仅缘于盛大的礼乐场景富于极强的感染力,更在于其对“德”的感发,对“善”的鼓舞。这种雍容典雅、欢乐祥和的礼乐胜境引导出了人们内心的良善真情,彰显了礼乐所深含的德义,在润物无声中教化了民众,明晓了伦理,和谐了社会,使得“德育”目标得以实现。
三、中和有度、文质彬彬的审美原则
孔子主张以“德乐”涵育君子人格,那么何谓“德乐”呢?首先,孔子认为体现“中和”之美的“乐”才是“德乐”,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淫”,“过度”之意,孔子认为欢乐的情绪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过而失其正,同理,悲伤过度则会害于和。雅颂之乐中正平和,典雅端庄,能使人心气平和,安分守礼,涵育良善美德、良风美俗,进而和谐社会邦国,致天下差序井然,“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而郑宋卫齐等音淫于色,扰乱民性,使人失德,“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8)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第551页。春秋后期,生产力得到发展,体现奴隶主阶级意志的分封制和雅颂之乐已不能满足新生阶级对政治文化生活的需求,以音调新奇、节奏丰富而深受新阶层欢迎的“郑卫之音”开始出现,新音乐因重于娱乐而轻于道德教化,被称为“溺音”,因而孔子主张“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
“中和”之美即是孔子中庸思想在礼乐观中的体现。在孔子看来,“中和”乃天下之达道,不仅是君子所必须修养的人格美德,同时也是涵育这种美德的“艺”所应该具备的美学核心概念。《汉书·礼乐志》:“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春秋中后期“礼崩乐坏”,天下失序,儒家所主张的“六经之道”旨在为天下重返王道政治提供经世路向,尤其是“礼乐”更是在危境中承担着醇厚民风、育德归厚的紧急教化作用。所以孔子的中庸思想是有其历史客观原因的,他认为礼乐之属只有具备“中和”之美学属性,才能具备涵养君子“中和”美德的教化功能。
孔子对“中和”之美的要求不仅体现在“乐情”之中,还体现在“乐”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中。在孔子看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论语·雍也》),如果过于追求质朴的内核而不加文饰,则会显得粗俗鄙陋,反之,如果一味追求外在的仪容文采,则会失去内在质朴的品质,显得浮夸,只有文质俱佳,内外兼修,才能成为谦谦君子。这既是孔子“君子人格”的标准,也是他认为培养“君子人格”的礼乐所应具备的艺术属性。
四、差序格局的伦理要求
“孔子的道德系统里决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9)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差序格局是孔子对礼乐的伦理要求。西周礼乐的使用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场合要求使用特定的乐目、乐器、乐悬、仪文和程序,这些礼乐规范具有法律的作用,一旦有悖,将受严惩。这种严密的规范一度对周王朝政治的稳定起过极大的维护作用,但春秋时期,王道式微,诸侯士大夫用乐中的僭越行为屡见不鲜,孔子对此深恶痛绝。如《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是周代天子祭祀祖先之乐舞,季氏乃鲁卿,在家庙中僭用天子之礼,引起了孔子的愤怒。同时,周代只有天子祭太庙撤祭馔时才能唱《雍》,而鲁国三桓祭祖时,却也唱《雍》诗来撤祭馔,所以孔子发出“奚取于三家之堂”的质问,即《论语·八佾》:“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再如,《左传·成公二年》:“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曲县,亦作“曲悬”,同“轩悬”。周代乐悬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周礼·春官》曰:“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可见,仲叔于奚“请,曲县,繁缨以朝”实乃要求配享诸侯的礼乐待遇,卫侯竟答应了这一僭越无理的要求,所以孔子闻之曰:“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五、尽善尽美、天人合一的审美圣境
“尽善尽美”是孔子对礼乐的最高审美要求。这种理念体现于其对祭祀乐舞《韶》与《武》的评价中,《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古之王者有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之习制,《韶》是舜之乐名,崇舜之至诚至孝,揖让受禅,能继尧德化天下,而不以天下为己有之圣德。孔子谓《韶》“尽善也”是从其“质”,即内容上进行评价的;而“尽美矣”,是从其“文”,即艺术形式上进行评价的。孔子曾对《韶》之艺术特征进行描述:“温润以和,似南风之至。其为音,如寒暑、风雨之动物,如物之动人;雷动兽禽,风雨动鱼龙”(《孔子集语》),可见《韶》之音舞极尽其美。《武》是周武王之乐,描写武王以戈矛杀伐定天下,未若揖逊而得,孔子认为其音舞虽极尽其美,但终有惭德,所以谓其“尽美矣,未尽善也”。由此可知,“美善合一”是孔子对礼乐的重要美学要求。孔子对《韶》与《武》的评价不仅在中国美学史上首次提出了“美”与“善”两元评价标准,而且“尽善尽美”理念也对整个中国古典文艺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纳“礼”归“仁”是对周代礼乐制度的继承和超越,不仅强调了礼乐文化对个体生命的关照,指明了礼乐实践的精神基础,还把礼乐与天道结合,使其礼乐思想更具生生不息的阔达天地境界,这彰显在他对《周易》的德义阐释上。《周易·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意即天道不言,只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瞬息不停,生生不已。孔子认为缘于人之情性的礼乐合于天道,是天地万物和谐共生、能育能化的反映,具有和同止争的作用,这使得孔子的礼乐思想呈现出通达坦荡、万物一体的博大深广气质。这种富有天地境界的礼乐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审美圣境。
孔子的礼乐思想闪耀着崇仁尚德、情理相融、同异相生、序化相成、生生不息的美学色彩,其礼乐思想对新时期如何以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立德树人,培养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所需的新时代“君子”,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