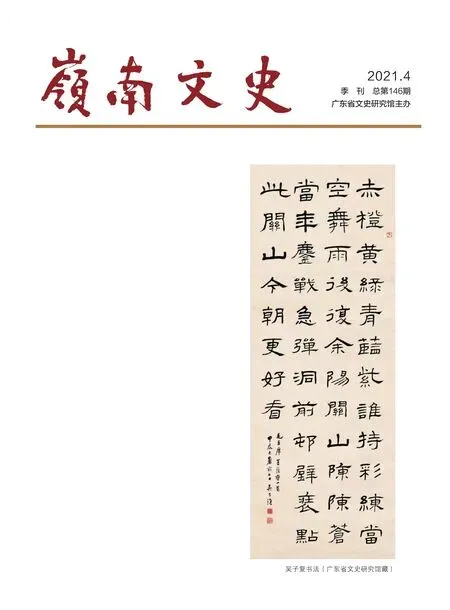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所记若干史事辨正
2021-11-25李吉奎
李吉奎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
陈少白是孙中山早期同学、战友,“四大寇”之一。他所著《兴中会革命史要》是研究辛亥革命与孙中山革命肇始阶段为数不多的记述,历来受研究者重视。不过,由于它是陈晚年受邀所作的口述回忆,缺乏日记、札记等资料作凭据,记述难免有不准确或失实之处。有学者对书中所记个别问题予以订正,但对全书迄无较全面厘订的文章问世,有必要对该书所记若干史事可疑之处进行讨论,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一
1929年6月,时任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下称党史会)主任的邵元冲,借孙中山奉安典礼陈少白被邀请到南京的机会,在6月21日,派党史会的速记员许师慎约陈到邵寓午餐,并述孙中山最初的革命思想及运动。午后三时顷告别。“所述至同盟会成立前止,其中多可补党史之阙失,如谓孙公上李鸿章书曾经王韬润色,伦敦被难实孙公自赴使馆运动等,皆足补时闻之阙。”[1]这种口述多次进行,每次整理稿出来后,邵元冲都亲加校阅。邵于8月14日、9月2日往陈少白住所商榷史料事。这本书在邵元冲日记中,曾有几个名称,如“兴中会史稿”“革命史料”“兴中会略史”“孙中山先生革命史实”等。
陈少白的最后岁月居北平养病,1934年12月24日去世。邵元冲在致唁之余,还议论了一番。他赞扬陈少白“恬退不伐”“孙公驻节桂林时,曾招少白作累月之谈;北上卧疾时,少白亦往视之。前数年孙公奉安时,少白来京,余曾约其作数次谈话,关于《兴中会革命史要》(以下简称《史要》)其中事迹,大都较可凭信,此一部分史迹,得藉余而保存,亦为余效于党者,而少白更得以不朽矣。”[2]
邵元冲对陈少白评价颇高,对自己经手的约五万字的“史要”一书,也充分肯定。陈少白所述史事之成书,显然不是有言必录,经过剪裁。如据邵日记,1929年8月14日上午访陈少白一谈,“并商榷革命史料事,少白并言郑陶斋(官应)轶事(谓孙公于上李鸿章书时,曾假资四百金,郑临殁时焚其借券)。”[3]郑官应(或作观应,1842-1922)是孙中山的香山同乡,早期维新派重要人物,亦是孙中山入世之初的重要关系者之一,但在1894年之后,孙郑二人毫无交往痕迹,料想必有缘由。陈少白所言此事,不论真伪,写出来都对孙中山形象不能加分,故邵氏除在日记中留下记述外,并未添载在“史要”中。
《兴中会革命史要》口述整理成稿后,陈少白应是审订过,因为他在1934年年底才去世。1935年出版的《陈少白先生哀思录》收入此书稿;同年,南京《建国月刊》社出版了此书,但因邵元冲于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中丧命,故1941年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的本子,与邵氏便没有直接关系了。但他留下这段历史,功不可没。采访的速记者当然也是最初成稿整理者许师慎,后来成为党史会的重要干部与孙中山研究专家,党史会纂修林百举所遗《林一厂日记》多见许氏活动,无疑他也是“史要”成书的功臣。[4]
二
《史要》凡十二部分,姑称十二章,每章长短不同,有的章分几个段落,本文称之为节。[5]兴中会的下限,应是到中国同盟会成立为止。何以《史要》只记述至1901年杨衢云被刺为止,原因不详。《史要》提供的资料来源有来自耳闻者,有亲自经历者,也有来历不明者;未能参稽档案、公文,这点似可肯定。对《史要》要点作逐条考订,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本文只是从其叙述发展的脉络,对其中一些重要史事,认为有疑问的作些辨正。[6]
陈少白对孙中山在香港雅丽氏学校学习及毕业情况有如下记述:“平时无论什么学科都是满分,即一百分。毕业时,只有一科是九十几分。”“校中教员及考试官就为他开一个会议,觉得这个学生是本校中最好的学生,学科中大部分是满分,只有一科稍为欠缺些,似乎是美中不足,会议结果,他们就送给他几分,使他得到全部满分的荣誉。所以在毕业证书上是注明‘满分’的(这张证书,英文是校长写的,中文是我填的。)。”[7]罗香林为撰写《国父的大学时代》一书,曾在香港大学医学部查找了当年就学该校(雅丽氏学校,即西医书院,后成为港大医学部前身)时的五年就学成绩登记及毕业证书底稿。据罗氏所载,孙中山在1887年春入雅丽氏学校,1892年毕业,就学五年半。这一说法引起学者讨论。实际情况极大可能是,学校正式开学(10月)之前,随着医院开办,便开始招收学员,事属草创,至8月31日始开会研究如何办学问题,至10月1日正式开学,学员(学生)12名。正式开学后,便逐年(学年)有成绩登记表。中经淘汰,毕业时仅剩孙中山与江英华二人。《史要》说孙在学除一门九十几分外,都是满分,此说不确。据载,第一学期的植物学和药物学分别是43分与39分,不及格。不过后来未再出现此现象,年年成绩都是第一。全部满分说之不确,还由于第三学年康德黎主讲的“实用初级外科”90分;何启主讲的“法医学”98.5分;第四学年“产科”口试笔试各为80分;外科笔试口试及临症合计百分比数142分。又:1891年“公共卫生学”86分。显然这些都是高分或居第一,却不能认为是满分。
至于陈少白所说他填写的中文注明“满分”的毕业证书,似系毕业执照。原文如下:“香港西医书院学院,并讲师考试各员等,为给执照事:照得孙逸仙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俱皆通晓,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发给执照,仰该学生收执,以昭信守。”[8]罗香林书讲到上述执照的英文本增加有“并由书院当局授予香港西医书院医学及外科等硕士(Licentiate)之学位称号”一句。已故陈锡祺教授曾查译原文,认为“Licentiate”并不含“硕士”之义,全句应译作“有开业行医资格者”的意思。[9]事实上,在罗香林之前,对孙中山所获学位的不准确称呼,已广泛使用,至迟在1912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甘作霖译《伦敦被难记》,就称“阅五年而毕业,得医学博士文凭”。[10]陈教授查对1897年伦敦出版的英文原著,汉译应是“经过五年(1887-1892)学习之后,我领得有资格在香港开业行医的毕业文凭”,并无博士的字样。该书为何会译成(或杜撰)这一学位,已无可考。但因为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界有一定地位,经此传扬,为日后在孙逸仙头上戴上博士头衔,无疑是大有作用的。此前,有没有称孙为博士的呢?《史要》(六)《第一次之广州起事及其失败之经过》一节中,对1895年广州重阳起义的密谋流产,陈少白说:“因为我到了香港,广州的事情已闹出来了,人也捉去了,机关也封了,花红单也贴出来了。邓三伯(指邓荫南)亦回到香港找着我说:‘传说孙博士也捉去了。’我觉得事情不好,孙先生迟迟不到,恐真有不测。”[11]对孙中山的学医所获学位,陈少白是最了解的人之一,按理,他回忆邓荫南的原话,不会有错;即使邓说错了,他也不该照邓说重复不误。或许,邓是最早称孙为博士的人,时在1895年。
实际上,孙早年称自己所获学位是很准确的。我在参编《孙中山年谱长编》时,因翻译日本外务省档案,发现1900年8月29日孙中山从日本秘密返抵上海入住日本人在沪开办的旅店“旭馆”时,登记册上写着:“横滨市山下町一百二十一番(孙逸仙)医学士 中山樵 三十四岁”。[12]登记出于孙本人之手,很实在,迄今他也就用过这么一次。不过,入民国后,随着国内外使用孙逸仙博士愈来愈频繁,约定成俗,孙本人也欣然接纳了。有位孙中山研究的学者指陈,孙本人从未自称为博士,此说不堪准确。众所周知,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便是孙逸仙博士与苏俄派至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共同具名发表的,孙的身份是博士,而不是中国国民党总理。[13]“宣言”不必是孙起草的,但至少是他确认的,易言之,也是他所使用的,故认为孙从未使用过博士这一头衔便不是事实了。
三
《史要》在讲到香港兴中会、广州重阳起义和杨衢云的时候,陈少白态度明显是偏颇的。首先,是完全不提及辅仁文社。当1895年初香港兴中会成立时,辅仁文社已活动了3年多(1892年3月成立)。兴中会在广州的活动由孙中山负责,杨衢云在香港主持招集会党、筹款购械事务。省港两地的佐理者分别是孙的人和原辅仁文社的人,两派人脉显然。杨衢云争总统、拉金主(如李纪堂)、与康派联系等活动,背后的支持者是谢缵泰。民初曾任北京政府稽勋局长的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等书中,记述了香港兴中会、辅仁文社、杨衢云、谢缵泰、李纪堂等事迹翔实。[14]《史要》将杨写成胆小、争权、嗜利,“被摈”,显然与史实相去甚远。以言杨衢云虽担任了香港兴中会长、虚拟的总统,但缺乏领袖气质或可,但极之描绘为一个小人则断乎不实。他在港担任的角色未必完美无缺,省城电告货物勿送以待后命,结果未执行,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尚不明确。事败后悬红海捕者皆逃,孙杨亦然,不可偏责。杨逃至南非,沿途多处增设兴中会分会,是他作为会长的权责所在,理应褒扬。一黎姓侨商追随杨至日本,卒至破产,是杨人格魅力所在,《史要》以杨作棍骗视之,实乃大谬于不然。《史要》记孙深责杨之种种不是,杨未反咬,是其知己所为有不是处,亦身为香港会长如今寄人篱下,反咬无益,此智者所宜持之态度。孙中山每月费用可由平冈浩太郎供给;但杨无可指望,在横滨以开馆授徒糊口,自食其力,有什么可指责的?
《史要》第六章题为《杨衢云之重来日本及被摈》,[15]作为革命史一章,实大可议。陈少白在书中历数杨之种种过失,是真是假,姑不去议。但该章题目便难成立。什么叫“重来日本”?1898年3月下旬之前,杨并未到过日本,现在听说孙文有“世界”了(陈说“外国报纸喧传说孙先生已筹得二三百万块钱在手,预备再行革命”——不知是哪份报纸?)便不辞跋涉,前来会孙。相信这话不假。香港会瓦解了,再难集结,到日本来“归队”,继续从事重要活动,作出重大贡献,决非“被摈”,这是有十足史料为据的,即收拾在《孙中山年谱长编》第一卷中的排比类编,即可说明一二。
四
陈少白在《史要》中讲到,广州重阳起义未经发动即告失败,他与孙中山、郑士良三人急于逃命,买了日本货轮“神户丸”的票(按当时中日之间来往尚无需护照),经十四天抵达神户。“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我们那时,虽然不认识日文,看了几个中国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见‘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耀在眼前。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张报纸以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印象印在脑中了。”[16]这些文字,经过冯自由的敷陈,说是“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按日人初译英文Revolution为革命,但揆诸《易》所谓汤武革命之本义,原专指政治变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译名既定,于是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咸通称曰革命。今国人遂亦沿用之。”[17]
对于陈、冯二人的说法,史学界历来深信无疑。日本自明治以后,脱亚入欧,翻译出版了很多西书,包括用“当用汉字”对译了西方名词,如新名词科学、自然、社会、阶级、民族、生活、经济等。这些新名词,通过各种渠道输入中国,丰富了近代中国词汇,变成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用中国固有的“革命”一词,等译英语Revolution,确是日本人的贡献。但是其起源是否如陈少白所言1895年到日本看到日本报纸后确认其义开始启用呢?世上真有有心人去寻根溯源,导致陈少白说之被颠覆。神户大学教养部安井三吉教授查阅了当时的日本报纸,仅在1895年11月10日的《神户又新日报》上,找到一篇题为《广东暴徒巨魁之履历及计划》,[18]所指其首领范某,通篇并无革命党、孙逸仙字样,而内文所记,系指未遂广州举事,惟系道路喧传,符合访员之德性。
安井教授将查找到的上述资料收在《孙文与神户简谱》(刊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孙文与神户》,1985年,神户新闻出版中心)。为编孙中山年谱长编,我将安井查到的资料译成中文,请马宁教授(已故)校对,予以收入,后来又收进拙著《孙中山与日本》一书中。安井教授澄清了陈少白、冯自由的说法,但他未进一步查考最早是何人、何时将孙中山与革命联缀在一起。孙中山与“革命”话语可说多到无法统计,寻找最早,当然要排除其本人(或他人)追述的文字,应当从当时的函札、出版物、档案文献中去查考。伦敦被难后,1896年11月间,孙给翟理斯写的自传中提到他要复三代之规,步泰西之法,是应天顺人之作,却未及“汤武革命”一词。1897年1月《伦敦被难记》出版,也未出现“革命”一词。同年3月1日,孙中山与英国学者合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一文中,两处出现“革命”字样,但更多是使用“革新党”用语。考虑到在孙中山的政治辞汇中革命、革新、改良、改革、维新是可以解释为同一意思,[19]此时孙认同使用“革命”的英文辞汇,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同年秋孙中山抵日后,与宫崎寅藏多次笔谈,讨论过去与未来举事,却无一次涉及“革命”。只是到1901年春与美国记者林奇谈话,才出现“革命”的说法,而此前日本人已将孙文称作“革命党”了。
1898年2月3日,犬养毅致函陆实,请为照顾“广东革命党员”孙逸仙、王质甫、陈少白,费用由平冈浩太郎负责,“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已暗中作此计划矣。”[20]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日本人最早称孙为“革命党”的确实史料。5月11日,宫崎寅藏将《伦敦被难记》译成日文在福冈玄洋社机关报《九州日报》上开始连载,取名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次日改题名为《清国革命党主领孙逸仙幽囚录》,迄7月16日载完。在1899年1月17-20日进行的横滨大同学校领导权争夺斗争中,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向外务省大臣青木周藏的报告中,称孙派为革命派,康派为改革派。这是日本官方首次对孙如此定性。
孙中山从传统反满,到严格意义的民主革命,认识上、实践上都有个过程。檀香山、香港兴中会章程都未标示“革命”目的,横滨兴中会未见公布什么章程。但兴中会誓词中的“建立合众政府”,正是要变革政制,以美国联邦制度为模式,要达到这个地步,不用革命行吗?所以这个誓词及由此发展成同盟会誓词的十六字纲领,实际包含了民主革命诉求。到1901年4月,孙中山与林奇谈话才正式讲到革命问题。征诸以上各端,虽然否定陈少白有关1895年神户开始确定革命党概念的说法,但肯定孙中山首倡革命于举世不言之中,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
五
1898年冬至1899年春,兴中会横滨分会倡议办的大同学校,在聘请康徒徐勤等人任教之后,被夺去学校领导权,因传说康将任宰相,兴中会主要负责人冯镜如等以前途可观,便相继投奔康派,分会名存实亡;康徒(怀疑是徐勤)还在天津《国闻报》刊文《中山樵传》,极力丑诋孙文,欲使之人格扫地。由是,陈少白认为:“于是两方面就成了水火,成为不解之仇,这时候孙先生早已搬到东京,我也到东京。”[21]情况是否真的如陈少白所说的那样呢?由于保革两派的关系牵涉到国内的政治动向,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1895年2月,为准备广州重阳起义,孙中山派陈少白赴上海联络同志。
1899年四五月间,受孙中山派遣,陈少白到香港办报,除偶然来日本公干外,至次年秋间惠州起义,他大部分时间在香港,包括1899年10月主持成立兴汉会。因这一缘故,孙中山在日本的许多活动,陈便未介入,甚至不知情。这种状况,便局限了他口述历史的范围和准确性。
事实上,梁启超与康有为不同,梁与孙中山曾经商讨过“合作”的情事,当然也互有过节。孙中山与梁启超有多次的接触、商讨,来往不少。
现在我们能看到梁启超留下有关孙中山的几封信,两封是有关联系见面,1899年三四月间梁致孙函;两封是1899年秋为介绍访日的四川督署官员周善培(孝怀,赴日考察学务)的梁致孙函。[22]其约谈第一函内称:“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梁所说方略“随时变通”,一点不假,半年多后在檀香山便应验了,合作破局。梁不改“保皇”,到了檀香山,瓦解了兴中会的发祥地,甚至劝孙中山参加“勤王”。
不论孙中山是否再度听到梁氏的劝诱,都不存在与康梁进行军事合作的意向,他要单独干,既而决定安排人员发动惠州起义。
在《史要》中,陈少白说:“过了些时,梁启超从外国回来,到了香港,冒着日本人的名字,住在外国栈房香港酒店里。他派了张煜全来见我,说他不便走动,请我到栈房里去会他,有事商量。我便跑到那里,见了面,还是讨论那合作的事,结果还算圆满。当时徐勤也在香港,梁启超就请我和徐勤把合作章程拟好,再等两方面通过之后,好按着进行。梁启超还有专函交代徐勤,然后离开香港。我便找徐勤同他商酌,他当了面并不说别的,只不愿把章程起草,屡屡催他,总是推诿。合作之说,只好作罢。”[23]此次梁陈香港之会,内情究竟如何说不明白。此时梁确实由沪赴新加坡时路过香港,[24]梁陈会见,完全有可能。但问题是,“刺康案”及香港海面船上决策发动惠州起义后,陈少白已十分清楚,两派关系恶化到什么程度和本会的行动;他虽未必知道梁在檀香山瓦解兴中会之事,但作为报馆负责人,当深悉长江事败已使两派唯一有交集之举已经终结,且亦未经孙授权,他何能贸贸然与梁商讨合作且订“章程”?梁氏东返后,对两派动向,也应当清楚。他对两派合作之心或许未泯,但明明知道负责港澳保皇会事务的徐勤是康门反孙第一干将,把合作“章程”之事交给他去办,这不是“与虎谋皮”吗?政治智慧之高如梁氏者有此一举,真是匪夷所思。但是,对陈少白而言,他所经历的两派合作到此为止。
梁陈商合之事未成,孙梁关系却日见交恶。梁孙分别居处京滨。1901年4月9日至6月5日,孙中山曾离日赴檀一趟。据载,孙发现该地兴中会被梁等保皇会骗夺,曾函梁,责其背信弃义,由是双方斗争日趋激烈。至1902年3月18日,章太炎在日看到这种状况,致书上海吴君遂,内有“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25]为了革命前程,孙中山必须战斗。1903年10月,他又回到老基地檀香山,召集旧部,[26]重振旗鼓,将老同志程蔚南主办的《隆记报》改组为《檀山新报》,亲撰论文,批驳“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谬论,号召侨胞“毋惑保皇,奋起革命”。经过激烈较量,革党势力逐渐在檀香山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中国同盟会成立,两派论战全面展开,保革势力此消彼长,由外而内,反清革命洪流已不可阻挡。
综上所述,可见保革两派关系从1898—1900年在竞争中谋合作,充满斗争,并非如陈少白所说那样,1898年大同学校校权之争后,两派即成水火,“成了不解之仇”。
六
《史要》第十一章讲惠州起义,主要是讲“两广独立”密谋与惠州起义的前期行动。有关策划“两广独立”,陈少白认为是何启向他提出,经向孙中山报告同意,联络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曾广铨,同时与港督联系后进行的。美国史扶邻教授所著《孙逸仙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部分章节,参以英方档案,已详加考证明白。陈书所说此项密谋发端于“庚子年五月,北京入了联军的手”,湖广、两江、两广三督都按兵不动(指东南互保,不与洋人开战);又说“际此中央无主,正宜讽其(按指李)据两广,宣告独立以维治安”。[27]陈少白这些回顾是有问题的,即:香港何、陈策划“两广独立”并通知孙中山的时间,是否在“庚子五月间”;李鸿章是否曾与闻此事缺乏史料以证,即使通过刘学询了解到孙方密谋,此议亦是一厢情愿。
庚子五月,是公历6月16日至7月15日。据谢缵泰所记,4月18日他已与杨衢云商议“惠州运动”的事。易言之,4月中旬,已开始谋划惠州起义之事。孙中山等人是6月8日乘轮南下的(6月17日抵达香港海面)。这一天,是阴历四月二十二日,此时非但联军尚未入京,即清廷亦尚未对外宣战,故说五月之事,不准确;以言孙南下议“除康”之事可,言与李谋“两广独立”之事则不可,陈少白绝不可能将五月所议定之事,在四月向孙报告。但孙刘李之间在孙南行之前当已有定议,否则怎么可能孙所乘轮刚抵香港海面,孙的代表三名日本浪人即转乘广州派来的“安澜”兵轮赴省城,抵达后与刘作彻底之谈,然后次日到香港,领了刘给的三万元,随即赴新加坡,于是有“刺康”这一案子。由此可见,孙南行之前,他并无与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甚至建设一“共和政府”的计划。既然如此,又为何能在“刺康案”后乘轮抵港当日(7月17日)晚上,便在接得李鸿章北上过港不停留信悉,便研究惠州之事呢?实际上,陈少白记事,确有不准确之处。
史扶邻教授根据英国保存的档案得知,港督卜力从4月至6月休假,7月2日才回到香港。此前,6月22日,暂时代管香港政府的陆军少将盖斯特曾向殖民部提议,制止李鸿章北上(李已于7月8日任命为直隶总督)。但此建议被否定(建议未涉及革命党人)。卜力刚回到香港,革方代表即与他联系,但卜力向伦敦报告的却是两周内湖南和南方将爆发反清起义。13日,坡督瑞天咸电知卜力,孙一行已动程赴港。卜力即电伦敦,李孙若能缔结一项盟约,对英国的利益是最好不过的。17日,卜力又电伦敦,意在扣留次日过港的李鸿章,但为伦敦所禁止。于是,有17日晚孙中山及其同志(杨、陈、谢、郑及数量可观的日本浪人)会议,决定发动惠州起义之事。
昔日儒学传统,士大夫表面上都讲究名节。李鸿章历仕三朝,中兴名臣,家族亲戚、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与之敌视者亦比比皆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谓五六月间联军陷京之前谋“两广独立”,于理于势,已属虚妄;至8月15日,联军入京,西太后携光绪出京西逃。在此之前之后,避祸惟恐不远,李氏要与乱党合谋异动,窃谓虽至愚者亦不为,况老奸巨猾如李鸿章乎?次年9月李卒,谥文忠,岂浪得虚名?6月17日夜,刘学询与日本宫崎等三浪人之所议意在“除康”,无关“两广独立”,亦可证。
“史要”有关惠州起义部分,有三点值得注意。
(1)完全缺叙浪人参与其事。根据日本官私文书所载,与惠州起义有关的日本浪人达二三十名。18日(或19日)在“佐渡丸”上孙中山主持的会上决定:福本诚(日本人)留在香港做准备,如果准备不能如意,则以现有力量举事。举事以郑士良为主将,原祯(日本人)、杨衢云为参谋,福本为民政总裁、日本人平山周副之。其余日本参与者如玉水、野田、伊东等留香港等待举事。[28]孙中山革命三十年,护法战争(1917年始)以前依靠日本浪人、军人是常态;1916年(山东)反袁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主干亦是浪人。不能因为此辈是侵华急先锋,在中国干尽坏事,便不提及这段历史。
(2)《史要》提及(起义)“我军从三洲田向东前进,几日间经过淡水、白芒花、黄沙洋,而到三多祝。我们希望能冲到福建省内,孙先生在台湾就可以过来接应,枪炮弹药,及将领人才,亦可以一齐带过来了。”接着,他便插入陈廷威、杨衢云欲与南海知县讲和、无关战事的记述。随后说:“但当时我们后方接济系用船只沿着海岸送去,因为军队走远了,大家不接头,前方子弹用尽,等了几天,尚无消息。敌方兵力又日厚,我们军队,到底非经练之军,不能久持,遂纷纷退了回来。”退到新界,便埋械散众。按该书所记,闰八月十二三日,陈带着几个人由香港油麻地出发,越过大山,一同到三洲田,到十五日(10月8日),就在那里发动。如此说来,他是起义的直接发动者。但是,不知道他为何不提惠州一带,按原计划是向北(可能是配合广州史坚如炸署督德寿),也不提及由于不知究竟应如何走,由郑士良专赴香港向台北孙中山请示一事。孙中山依照台北日本殖民总督方面意见(到厦门抢正金银行,内有巨款),向厦门。于是义军往东。但随后孙让日人山田良政持电告郑士良:情况变化,后援难期,请司令自行决定行止。孙的指示今人多种著述都有论述。而陈少白回忆不及此,当有原因。
(3)至于《史要》所记孙中山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接洽过,很赞成孙的革命主张,答应起义后相助,所以孙将起义部队沿海向东前进,如果义军打到厦门,儿玉就可以渡过台湾海峡,亲自督师。商量已定,孙先回日本,转赴台湾去。[29]这段记述有问题。孙中山居日时无任何记载说1900年以前见过儿玉。儿玉与后藤新平(民政长官)在密谋厦门东本愿寺纵火案后支持土屋光春旅团出兵厦门,但日本内阁更换,伊藤新揆及青木外相考虑与华北侵华联军协调对华谈判,反对日本在福建扩张引发他国不满,指示撤军。儿玉因此不满内阁决定,居东京,只是指示后藤与孙联系,日本让孙引义军去厦门抢日本银行以扩大战局找藉口的计划破局,故孙止军赴厦。所谓日酋很支持孙革命主张之说,似不足采信。
《兴中会革命史要》没有记述兴中会1901年以后至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的后半部史事,原因不详。就现在人们能看到的部分,对有些重要记述不完整、欠准确,为还原历史,进行考证与纠正,是必要的。尽管如此,该书史料价值还是值得肯定的。所议失当之处,仍希读者指正。
注释:
[1][2][3]《邵元冲日记》,王仰青、许映湖注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46、1192、558页,1990。
[4] 黄季陆等撰《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一书(“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台北,1985年再版,第4页)序,记“史要”一书系许师慎笔录。
[5] 即:一、孙先生最初之革命言论与行动(含:(一)幼年之家庭与学校生活;(二)香港之求学时代—革命思想之发源;(三)医校毕业与在广州澳门行医;(四)上李鸿章书之经过;(五)组织兴中会与筹备在粤革命;(六)第一次之广州起事及其失败之经过。)二、孙先生之抵日本及漫游欧美(含:(一)到日本后之行动;(二)由檀香山至美国英国及伦敦被难之经过。)三、在日本之活动(含:(一)联络留日华侨及日本志士;(二)与康梁交涉之经过。)四、台湾方面之活动。五、保皇党之占领横滨学校。六、杨衢云之重来日本及被摈。七、余之再赴台湾及返香港。八、革命党与保皇党交涉之经过。九、联合三合会哥老会之经过。十、再与康梁等之交涉。十一、惠州起事之失败与史坚如殉难。十二、杨衢云之死。
[6] 本文所征引的文字,系据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下称《辛亥革命》资料丛刊本,共八册),1981年印刷本第一册。
[7][11][15][16][21][23][27][29]《辛亥革命》资料丛刊本第一册,第36、32、54、63-67页。
[8]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增编版,第59页,1984。
[9] 陈锡祺:《关于孙中山的大学时代》。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集,第5页,1983。
[10]《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第50页,1981。
[12]《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第236页,1991。
[13]《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第51-52页,1985。又,谢缵泰于1924年在《南华早报》刊出英文日记体裁的早年回忆录《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内文屡见“孙逸仙博士”用语。初稿是否如此,不详。
[14] 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冯自由。据时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纂的林一厂日记所载:(1943年1月21日),“上午9时到总纂办公处,许(师慎)处长来谈,……张主任委员(继)来言,与冯自由晤面,谈及史事,冯意:一、陈少白所述杨衢云事太偏,杨当时在港有一部分势力,故总理乃让伯理玺天德之名,即其后杨氏被杀,情亦可悯,修史时似应从宽。二、郑贯公与陈少白有意气,故陈少白所述郑事,尤不公道,修史时宜特注意郑事迹,宜加表扬。三、兴中会确在檀香山成立,若甲午前已在澳门先成立,则总理亦断无于甲午年上书李鸿章之事。以上三点,与余意全合。”(见林一厂著、李吉奎整理,中华书局,上册,第67-68页,2012)
[17]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第1页,1981。冯书初集出版于1939年,但作为专文刊于《逸经》,当早于1939年,应在1935年《陈少白先生荣哀录》一书刊出后。
[18][28] 详见李吉奎著:《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第8-9、112页,1996。
[19] 详见李吉奎著:《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中山大学出版社,第317页,2001。
[20] 彭泽周:《犬养毅与中山先生》。《大陆杂志》第53卷第3期。第97页。转见李吉奎著《孙中山与日本》,第34页。
[22] 见《梁任公年谱》第一册,第330-331、331-332页。
[24] 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4页。
[25]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第76页,2113。
[26] 未参加檀山保皇会的兴中会会员有:郑金、郑照、李昌、程蔚南、许直臣、何宽、李安邦等人(见《我的曾祖父孙眉》,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