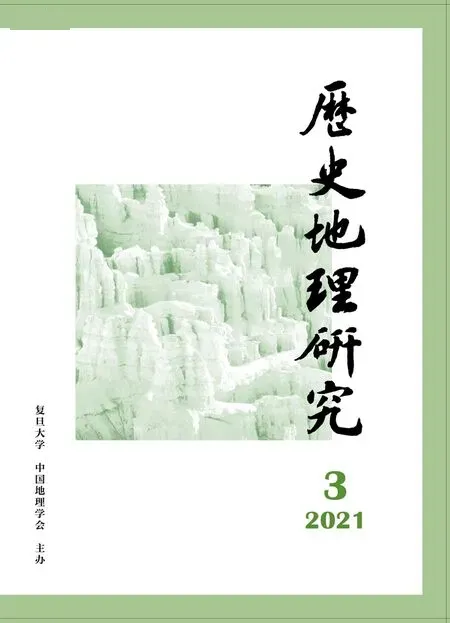历史地理学的开创与传承: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
2021-11-25李孝聪
李孝聪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一、从爱国到报国——三位先生的共同特点和独特贡献
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学者的成长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他们三位跟着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我们祖国面临日本侵略的时代,因此当我们谈及他们的学术时,一定要关注到时代对他们成长与学业的塑造。三位先生共同的特点就是爱国,从爱国到报国,在学术研究中求真理、为祖国服务。从国家危亡到新中国建设,他们的学术进展始终与国家的历史发展紧密相连。例如,抗战时期,他们关注边疆问题,《禹贡》半月刊中有边疆史地专号,在顾颉刚先生的引导下,三位先生研读与边疆史地相关的典籍、翻译国外有关著作,进而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发表,这些学研工作实践实际上给谭先生他们后来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再如侯先生虽然没有参加革命,但他曾经为抗日根据地输送过学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大致来说,新中国成立前,三位先生不断进行学术训练、传承学理,传承的不仅有传统的沿革地理与史地研究,特别是清人的考据之学,还包括近代西方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学科开始发展,国家在政策上对老一辈知识分子和学者十分重视和支持,在此背景下,三位先生把自己的学术专长和学术志趣与国家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各自开拓出新的学术领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
具体到各位先生的研究。与治理黄河相关的研究是谭先生的贡献之一,即有关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与下游河患的相关问题,它涉及当时移民、人口等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当时他写过关于东汉以来黄河为何安流问题的探索性论文。史先生从黄河的侵蚀与堆积探讨黄土高原地貌的历史变迁及其治理,以及治河方略,其调查分析之细致,当时几乎难有望其项背者。他从事陕西军事地理的研究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相关,当时国家面临来自北方苏联的军事威胁,组织构建“三北防线”,史先生受兰州军区司令员之邀对陕西军事兵要地理进行考察,因此我们看到史先生有些关于黄土高原历史军事地理的相关论述。而侯先生迈入沙漠历史地理及治沙的相关研究实际上也是在国家向沙漠大进军的背景之下,因为国家需要,他组织专业学者构成的团队进入毛乌素、乌兰布和沙区。2018年,我曾经带队重走侯仁之先生之路,先到历史上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再到呼和浩特、包头,然后去河套乌兰布和考察汉代的城址和鸡鹿塞,最后再去看狼山的双阙。当我爬到当时侯先生站过的那个山梁上,才发现那里曾经修筑过一道边墙,倘若不是考察亲历,没有人会提到这个发现。当然也正是受到侯先生的影响,我才会更加重视做历史地理研究过程中的实地考察。
此外,谭先生很早就开始了有关中国陆地边界和海疆的研究,因为谭先生要重新整理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图》,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他必须要在历史疆域政区这方面有一个严肃而谨慎的学术观点,而不是盲从于潮流,这一点我们今天的人想要做到都是不容易的。除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外,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协助王重民先生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承担其中的地理类,以此为基础,他在改革开放之后集合复旦的一批学者重新整理编撰《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下了极大的功夫,这又是谭先生一个艰苦的开创之功。它不仅为学人利用清人的学术成果提供了便利,而且避免后人把前人已经解决的问题当作新的问题来做重复性研究。现在很多年轻人自以为的开创、原创研究,实际上清人就已经讲过了。
侯先生的研究则展现出超前的学术思想,在许多研究领域更具有开创之功。以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为例。城市地理是侯先生的看家本领,他在去利物浦求学的时候其实已经决定了要做北京城的历史地理了,而在国外的导师达比又是剑桥学派具有开创之功的学者,他也写过英格兰历史地理的相关著述,因此他一步一步去引导侯先生把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做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对于国家来说,是与首都城市规划建设紧密相关的,而对于侯先生来说,则是一辈子的学术追求,我们望尘莫及。
谭、侯、史三位先生在爱国理念的指引下进行传承学理的学术训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国家建设需求从事各自擅长的研究,在项目组织下不遗余力地培养后学,这是他们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做出的重要贡献。老先生们将我们这些后学扶起来,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继续前行。
二、“好为人师,又善为人师”——两位先生的教书育人之道
借用顾颉刚先生的话,谭其骧先生是“好为人师,又善为人师”。谭先生治学很严谨,他在培养后学的时候,如果发现做得不对,他就要严格批评。而在我师从侯仁之先生的二十多年,侯先生从来都是夸奖,而不批评,使我感觉这一点两位老先生是不一样的。
谭先生很谦虚,他会循循善诱地教你、指导你,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们在谭先生面前就像小孩子,他们是大学者,我们只是刚入门的学生。1987年,史念海先生在西安成立历史地理研究机构,我代表侯先生参加在西安举行的会议,谭先生也去了。会议期间,会议组织与会代表去户县楼观台考察,谭先生因中过风,腿不便走太多,与史先生坐在庭院里聊天,我也凑过去听他们讲什么。我刚刚从甘肃靖远地区考察归来,感觉《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北宋秦凤路地图里的城址画得不太准确,譬如:会川城,顾名思义应该在两条河川交汇的地方,可是历史地图上的位置却在黄土原上。我就此向谭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谭先生问我的依据是什么,我回答说我去实地看了,在河边找到了城址还拍了照片,谭先生说:当时我们给城市治所标位的时候,全靠《大清一统志》记载的四至里数,去估量距离,再结合实测军用地形图去定位这个城的位置。谭先生赞赏我能够结合实地考察来验证历史地图的准确性,还说如果以后我发现这八卷本里面有其他什么错误就都记下来告诉他。1988年,《中国历史地图集》修订版刊出,竟然按照我提出的意见将第六册中定位失误的北宋会川城、新泉寨和金新会州、新泉城等的位置全部都改正过来了。这对我来说是不得了的事情,当时我仅仅是一名初入历史地理学门的小助教啊!作为知名历史地理学教授,谭先生能够听得进晚辈指出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失误,如果没有开阔的胸襟是不容易的。这是令我一生难以忘却的事情。
侯仁之先生则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学者。在我和侯先生相处的几十年里,他经常都是表扬,一次都没有批评过我,因为他是一位不太喜欢批评他人的学者。因此,侯先生让我在工作中充满自信心。侯先生的超前认识还体现在他对于计量革命带来冲击的态度。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走向计量革命,计量地理学也在同一时期产生。当时中国的学术发展通常会滞后一些时间,大概到80年代计量史学也开始了。计量革命对地理学的冲击就是强调一切都要量化,所谓“没有经过计量就不算科学”。所以,计量地理学出现之后,原来靠一把地质锤、一个罗盘、文字描述而得出结论都不符合科学的要求了,一定要有数字,并经过量算。那个时候侯先生也受到了影响,他要求历史地理研究也要通过数据得出结论。但是,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说,典籍文献记载中的数字往往存在很大的问题,一些史学界的老先生认为无论是正史还是档案、笔记中的人口统计数字都不可信,所以凡是将计量用到史学中的研究在当时都受到了质疑。侯先生对计量方法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但并不抗拒,并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主动接纳新的研究方法。在他晚年主要是从地球表层的环境演变来思考,注重吸收第四纪地貌学的研究成果。
三、传承学理与谨慎前行——谈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
老先生们奠定下来的学科基础就是经世致用,而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学科领域也越来越宽,这是我们后学要继承下来的,相较于单纯地坐在书斋里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更应该把自己的学问变成服务于国家的一种力量。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学科发展中应该有所强调:研究国家真正需要的东西。老先生们自身的学术成长就有一个明显的传承和开拓的精神,因此我们也必须要有传承,没有传承何谈开拓?
谭先生在复旦留下的无论是研究领域、理论还是方法,都一定要有人继承,然后再不断扩展。而开拓更多地是指眼界的开拓,即研究中要有新的问题意识、新的方法。侯先生50年代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认为,如果历史地理学不能自立门户,还是作为“历史学的附庸”,那么还只是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在这方面,老先生都纷纷不遗余力地证明历史地理学不应该属于历史学,而应该属于地理学,所以六七十年代学科的界定也基本是这样。
但是,那只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现在讲“新阶段、新格局、新思维”,就不能还是只去强调学科归属问题,但从目前各大历史地理学研究单位来看,历史地理可能更加契合历史学的学科范式。地理学从计量革命以后,强调行为科学,后来就有行为地理学,再往后发现其弱点又出现了综合系统研究。在这样的影响下,近年来对地理信息系统、遥感等方法的应用走到历史地理学术舞台上。但是做人文的研究,不是说不能运用这些新的技术手段,而是首先在硕士、博士培养过程中不能缺少对原本系统性的史学文献、沿革地理的训练。如果学生在典籍史料这类基本素养上出问题,那大概是无法成长为合格的学者的。那么,沿革地理不仅仅指地名,还要对沿革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这类问题有历史性的把握。
具体而言,像古地图研究中,不能光看地名的变化,即不能单纯依靠沿革地理的知识,还得知道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事件背景下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要判断地图的成图年代。譬如:最近我在审阅他人撰写的一篇文稿,判断一幅清代彩绘《大河南北两岸舆地》图的绘制年代。这幅清代地图上贴签墨书“拟请于北岸添安炮位”,我很怀疑作者仅仅从图上的地名来推定绘制的年代,判断有误,去查了《清实录》才把这个事件搞清楚。在《清穆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七,同治四年(1865)秋七月丁卯条记载:“又谕王榕吉奏派兵筹防并添拨炮位扼守沿河要隘一折。”原来是因为同治年间清廷为防犯捻军从河南西进,渡河进犯山西,根据山西布政使王榕吉奏请,“自风门口东滩渡及平陆县之茅津渡,永济县之风陵渡,中间大小数十口,绵亘六百余里,与陕西之潼关,河南之灵宝、阌乡、陕州,拨铜铁炮位二百尊,分段安设”。这幅地图就是为了配合王榕吉奏折所述内容而绘制的随折图,绘制时代应当是同治四年(1865)。这就说明,倘若历史学的底子不好,对典籍文献不熟悉,仅仅靠着我上课时总结的那四种鉴定地图的方法,即“地名沿革、避讳字更改、河道演变、入藏记录”也是不够的。所以,利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历史地理基本功的训练,否则做出来的数据和图形是不可靠的,基础不可靠,分析就更加不可靠了。在历史地理学科领域引入数字统计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时,我们必须抱着谨慎小心的态度。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科研体制发生了变化,学者需要通过项目获得研究资金的支撑,是否能够申请到大项目资金支持成了当前学术成就的一个评价指标。这种情况对高校学科建设最大的影响就是越来越不重视基础研究了,所以,时下在地理科学中的历史地理学很多时候就只能作为“地理学的附庸”,在很多项目中也只能做配角。因此,历史地理学者如果不能保持一个对自身特点的清醒认识,将来是没法发展的,我认为:科学或学术研究中不应过多强调学科出身,研究者要具有综合能力,既要有历史学的本领和基本训练之功力,也要掌握地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能,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地理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