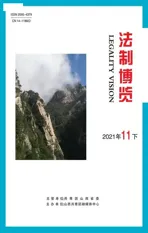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定之新路径
——保护规范理论研究
2021-11-25李婷婷
李婷婷
(沈阳工业大学,辽宁 沈阳 110870)
一、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定标准的历史演进
原告资格作为扣动司法程序的一个扳机,自一出现便深受广大学者的热议。行政诉讼作为监督行政权力与保护公民权利的公法诉讼,其原告资格的判定标准历经了四个阶段[1]。纵览我国这几十年来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定标准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国面对这一问题呈现出原告资格扩大化的趋势。
直接利害关系标准。这一标准最初是行政诉讼法采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行政诉讼原告的判定核心界定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尽管这一标准能够为明显属于被行政行为侵害的权利主体予以保护,但是却忽略了可能的受侵害权利主体。
行政相对人标准。这是继直接利害关系后进一步将原告资格的判定交由法官决断,被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主体,只要满足2个条件:“认为权益受损”和“有具体行政行为”,即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将导致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极具主观性,同样,只针对行政相对人,保护范围可能略窄。
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基于前述原告资格标准的过于自由化倾向,1999年我国的相关司法解释中,针对原告资格的标准采用了“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化了原告的保护范围,但是,也存在以法律明文规定权利为依据限缩公民权利之嫌。
利害关系标准。伴随着2014年我国新修《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也从此前的“法律上利害关系”,重新引申为“利害关系”,判断标准更加主观化,其本质并未有更多改变,该标准一度成为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定的核心。但随着行政诉讼案件类型的复杂化,被侵权种类的多样化,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受侵害主体的权益,赋予相应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便成为研究的重点。
二、保护规范理论引入原告资格判定的必要性
(一)“利害关系标准”的局限性
自2014年我国新《行政诉讼法》对于原告资格采用了行政相对人以及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判断标准后,学术界对于“利害关系标准”达成了一致认可。并基于此,实务中主要采取三要件,即行政机关是否作出了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合法权益、权益受行政行为的侵害程度,来判断原告是否具有起诉资格。
然而,究竟何为合法权益,学术界众说纷纭,存在“法定权利说”“隐含权利说”以及“值得保护利益说”。“法定权利说”以法条明文规定的权利为准;“隐含权利说”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保护范围,除了法条规定的权利,也将隐含于立法目的和原则中的权利纳入其中;“值得保护利益说”在“隐含权利说”的层面上又加大了保护范围。由此可见,针对合法权益的不同理解将导致实务中该标准的判断更多依赖于法官的主观判断。因此,原告资格“利害关系标准”的模糊性将不可避免地与司法的确定性之间产生矛盾。
法律条文的模糊性,加剧了法学理论的似是而非,“利害关系标准”缺乏具体可操作性,难以在个案中达成一致认可,这就要求有更加规范并具操作性的理论来对此加以强化。2017年“刘某明案最高法裁定”便带来了这一希望。
(二)保护规范理论的开放性
2017年“刘某明案最高法裁定”,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定回归至行政实体法,以其中主观公权力的存在作为行政诉权的前提,将客观法规范所包含的私人利益保护目的与可以诉诸司法保护的请求权基础相结合,弥补利害关系标准导致的自由化边缘化问题,将保护规范理论与主观公权力引入并运用到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定上来,引发了学界热议。
保护规范理论作为一种舶来品,最初是源自德国19世纪后期,分为旧保护规范和新保护规范两个阶段。旧保护规范,以布勒的传统“公权三要件”为代表,新保护规范以施密特·阿斯曼为代表,也就是现代的保护规范。而与此理论相伴而生的就是主观公权力概念,即“个人为自身利益,可向国家要求为一定行为、不为一定行为或承担一定容忍义务的法律权能[2]”。
从新、旧保护规范的共同点来讲,两者都主张将个人利益指向转向法律规范的解释。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主要关注立法者的意图,多采用历史解释方法,因此主观臆测的问题便难以避免[3]。而前者,现下通行的保护规范则依赖于对当下利益的客观评价,是采用一种开放的,同时以客观逻辑为导向的逻辑方法来论证原告资格的理论,运用法律解释方法来论证主观公权力,使得主观公权力并非绝对确定,能够根据时代主流观点来发展塑造,进而助推保护规范理论与时俱进。虽然,对该理论的运用现在仍不乏质疑,恐其不确定性。因此,将保护规范理论在中国本土进行适用将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重点[4]。
三、保护规范理论的本土运用
运用保护规范理论来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并不意味着取代此前的“利害关系标准”,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将“保护规范理论”作为“利害关系”的必要补充,弥补此前原告资格判定标准的模糊性,将原告资格的判定纳入全新的视角。通过对保护规范理论进行中国式改造与重述,利用其理论的开放性赋予原告资格新的生命力,利用客观法规范与请求权基础相结合的方式重新框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这是当前原告资格判定问题研究的大势所趋,将为我国的行政诉讼司法实践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
在“刘某明案最高法裁定”前,我国对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判定的利害关系标准大致可以等同于“不利影响”,但在此之后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对于原告利益的保护跳出原有行政诉讼法明确列举范围的樊篱、进一步平衡保障诉权与防止滥诉两者之间关系将助力良多。保护规范理论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所参照的行政实体法及相关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考虑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即所谓的主观公权力,将以此作为断定受行政行为侵害的主体是否可以作为原告拥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资格。[5]对于行政实体法以及相应的法律规范是否有这样的考虑,则需要依靠法律解释的方法。同时,对主观公权力的探究,既要从法律明确规定出发,也要包括那些法律未明文规定但可以通过解释推导出来的权力。
将保护规范理论进行中国化适用,不仅符合国际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扩大化的趋势,而且弥补了我国此前“利害关系标准”的弊端,能够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以外的受行政行为侵害主体的权益,能够将原告资格判定取决于法院和法官的状态,转变为取决于立法与行政,能够考虑立法背后目的、宗旨可能涵盖的私益保护性,将有利于我国法治政府、法治国家的建设。但是,对保护规范这一理论的运用,将对我国的法律解释技术形成新的挑战。我们应该看到,保护规范在我国的发展运用必须历经一定阶段后才能够发展成熟,并逐渐成为与利害关系标准并驾齐驱的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又一大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