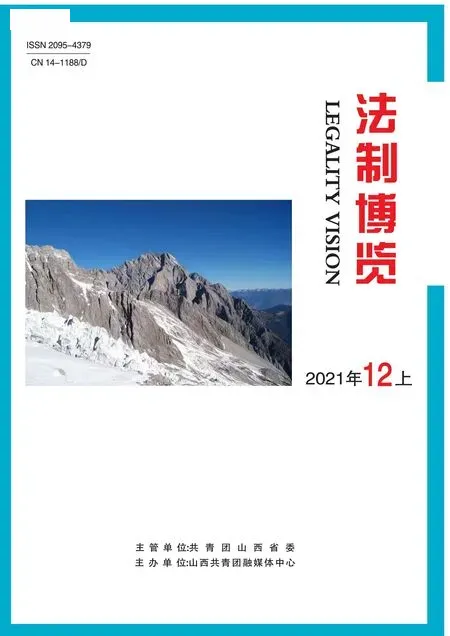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的重构和应用
2021-11-24万文成
万文成
(南京理工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4)
一、问题的提出
在“深圳微源码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商圈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被告研发了一种名叫“数据精灵”的软件。该软件作为一种微信插件,可以提供诸多微信所不具有的功能。原告认为,被告提供该付费软件下载并进行宣传、推广、运营等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益,应当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互联网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1.其是否使用网络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且存在竞争对手;2.其是否利用了技术手段妨碍或者破坏竞争对手提供合法商品或服务;3.上述行为是否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对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造成了不利影响;4.其是否符合诚实信用,不违背商业道德。①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2093号民事判决书。
该分析标准是以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和第十二条的兜底条款为基础而确立的,但是第二条作为原则性规定,具有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认定标准的泛化。第十二条的兜底条款以“妨碍”和“破坏”限定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难以认定竞争行为的正当性,也无法涵盖现实中存在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1]而且,当其他经营者的利益、消费者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产生冲突,该如何平衡也是重中之重。
二、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认定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而用到第十二条的相对较少。截至2021年9月1日,笔者在北大法宝网搜索发现,用到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知识产权案件有上万件,而用到第十二条的案件却不到900件,并且其中过半数附加了第二条,大部分案件使用的也是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兜底条款。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互联网专条是2017年新增法条,2017年以前的案件只能使用第二条的原则性规定;二是法院为了寻求说理上充分、使裁判得以信服,倾向于将第十二条和第二条结合起来认定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三是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类型较少,不能满足现今社会上复杂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需要法官结合第二条和第十二条第二款的兜底条款进行判决。针对以上现象,笔者认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应当以第二条和第十二条的规定为基础,而关于第二条,司法实践中针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形成了一些认定标准和原则,这对认定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存在参考价值。
(一)基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产生的认定标准及反思
首先,在“山东省某进出口公司等与青岛某诚贸易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最高法院认为,适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认定不正当竞争应当同时具备四项条件。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065号民事判决书。其中最关键是第三点,“行为因不符合诚实信用、违背商业道德而不具有正当性”的认定。诚实信用自不必多言,但是何为商业道德呢?首先,其与生活中的一般道德不同,而必须按照商业社会或者市场竞争的伦理标准进行定性和衡量。[2]其次,其区别于社会公德,而限于商业行业,鼓励竞争行为、创新与抢占先机。[3]判断竞争行为是否不符合诚实信用、违背商业道德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平衡过程。
其次,在“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某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等商标权权属纠纷案”中,最高法院提到,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可以不告知网络用户,在取得其他互联网经营者同意的基础上,干扰他人网络经营活动,并且应当确保干扰手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即“非公益必要不干扰原则”。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873号民事裁定书。此原则是利益衡量的体现之一,但是其也存在不合理之处,一是干扰行为的界定不明,因为正常的经营行为也可能对竞争对手产生负面的影响,如何认定其是否为干扰行为,以及其是否合理都是不明确的问题;二是此原则是建立在经营者互不干扰的基础上的,但是这并不符合互联网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行业现状,难以适用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上。
(二)对学界现有认定标准的反思
基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衍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还不足以满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殊性,对此,有学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应当秉持司法的谦抑性,尽量不干预互联网行业的竞争,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利益分析,而非简单地看待相关联的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损失。[4]笔者认为这种想法过于理想化,互联网行业的竞争复杂,缺乏明确的标准而简单说考虑各方利益的想法难以实现。并且司法是抑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有力手段,秉持司法谦抑性对与日俱增、形式多样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收效甚微,反而会助长其气焰,适得其反。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将业绩竞争作为认定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具体标准。[5]但是,这种标准存在其不合理之处,一是业绩认定不明确,以此为标准并没有解决互联网竞争行为不正当性的认定问题;二是单纯从业绩进行认定标准过于单一,仅考虑了商业模式,而忽略了竞争行为本身的正当性。
(三)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的重构
根据前文所述,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原则性规定产生的认定标准都存在适用上的缺陷,学界一些学者针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这种特殊行为提出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的兜底条款对行为作出的限定过窄,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对此,司法实践中最新的裁判思路是结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二条和第十二条,综合认定互联网不正当行为,但是这并不能解决第十二条兜底条款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上述裁判思路值得认可,但是需要对第十二条的兜底条款作扩大解释,以满足现今新兴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性。具体而言,第十二条兜底条款中的“妨碍”和“破坏”行为扩大为损害经营者利益的行为,以此涵盖那些未对经营者正常经营活动阻碍,但是实际损害了经营者利益的行为。当然,考虑经营者利益的同时,还需要对消费者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平衡分析。
总体而言,认定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关键是认定竞争行为的不正当性。而不正当性,首先关注其是否违反法律,其次是否背离诚实信用、违背商业道德,再次是否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对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造成了不利影响。最后,具体个案中还要分析行为类型、商业模式、损害程度、各方利益等具体因素。
三、典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规定了三种特定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这样的规定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虽然法律还规定了兜底的其他行为,但是对于如何认定并没有明确的标准。通过前文对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司法现状和认定标准的讨论,笔者将对现今存在的几种典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分析,以期为司法实践中认定相关行为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一)数据抓取行为
在如今这个互联网时代,用户的各类信息数据是互联网经营者们发展业务、创造收益的重要资源,可以说,数据是互联网领域的核心。在司法实践中,互联网领域产生了许多与用户数据抓取相关的案件,如“魔蝎爬虫案”。本案中,魔蝎公司未经用户许可即采用爬虫技术长期保存用户各类账号和密码在自己租用的阿里云服务器上。②参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6刑初437号刑事判决书。存储的这些数据使其相对于其竞争者处于了不正当的优势地位,构成不正当竞争。但是,如今司法实践倾向于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作为上述行为的规范路径。[6]其不合理之处不再赘述,下面笔者尝试以上文确定的认定标准,对数据抓取行为进行分析。
以爬虫技术为例,其属于一种网页数据抓取技术,只要网页上存在的数据,都可以通过爬虫技术获取。当网络经营者适用这种技术搜索网络上公开的数据时并无问题,但是一旦其恶意抓取自身用户未许可的信息,或者竞争对手的用户数据信息时,其当然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对消费者而言,自身的隐私被侵犯,个人信息安全无法保障;对其他经营者而言,自己用户数据被抓取,丧失了依靠自身宣传等建立的竞争优势。综合而言,此种行径不符合诚实信用,违背了商业道德,损害了消费者、其他经营者等主体的利益,属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广告屏蔽行为
在各个互联网平台,尤其是各类视频网站,广告收益占总收益的很大一部分。以“爱奇艺”为例,其采用了“广告+免费视频”的商业模式,即非会员可以免费观看视频,但是需要观看广告,只有会员才拥有去除广告的权利。但是,大部分消费者不愿意为广告而购买会员,一些网络经营者从中看到商机,广告屏蔽技术应运而生。广告屏蔽技术一方面损害了广告经营者以及视频网站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对消费者是有利的,这里就产生了前文所述的利益冲突,如何进行利益衡量是重中之重。
笔者认为,广告屏蔽行为破坏了经营者的正常“商业模式”,使其用户收益减少,确实损害了经营者的利益。这在短期内对消费者必定是有利的,从长期来看,这种有利形势也可能存续下去。比如经营者在相互竞争中形成了一种更有利于消费者的商业模式。毕竟现如今,“广告+免费视频”中的免费视频仅是一些较为普通,看点并不多的常规视频资源,真正热门的视频还是需要会员,甚至付费才能观看。因此,广告屏蔽行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行为,因为其是基于消费者的需求而产生的,体现了对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尊重。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广告屏蔽行为并不能一刀切地认定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而是结合具体案件,综合广告屏蔽技术提供者的主观意图、损害后果、各方利益等因素进行判断。
(三)链接聚合行为
链接聚合行为中较为典型的是视频聚合应用。视频聚合应用作为一种网络新兴应用,其不同于传统视频应用,而是通过链接形式将各个视频应用的资源整合到一起,使用户能够在一个应用中搜索到其他视频应用的资源。视频聚合应用使用的链接类似搜索引擎使用的链接,其一般分为浅层链接和深层链接。[7]本文主要讨论后者。
首先,针对深层链接中屏蔽广告的行为,不同于前文所述的一般屏蔽广告的行为,深层链接会让用户直接在原应用上直接播放相关视频,这样因屏蔽广告而吸引的用户会直接为视频聚合应用提供流量,为其之后添加自身广告等行为获益提供基础。由此看来,深层链接中的广告屏蔽行为具有主观上的恶意,违反了诚信原则,具有不正当性。
其次,针对深层链接可以直接在应用上打开链接视频的行为。其本质上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具体而言,属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认定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时,往往会认定为不正当竞争。因此,这就涉及此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问题。在视频聚合应用中直接打开链接视频的行为依靠链接视频吸引到了用户,但是链接视频并非视频聚合应用的产物,此行为不符合诚信原则,违背了商业道德,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虽然视频聚合应用方便了用户,使其可以更加便捷地观看到各类视频,但是此时消费者的获利程度明显小于其他经营者的受损程度,难以认定为具有正当性。综上,深层链接行为属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结论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竞争行为日趋复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和第十二条仍有其适用的局限性,本文提出的认定标准相对灵活,最重要的是结合个案进行分析。本文所分析的三种典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仅是现今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司法中还未解决,或者即将诉诸司法的行为。本文仅是提供了一点解决思路,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帮助,要想从根本上完备地解决此问题,还需要学界学者和司法实践中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