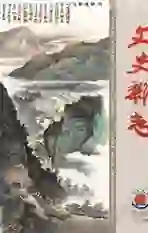《剪灯新话》与明代传奇
2021-11-22周楞伽周允中
周楞伽 周允中
摘 要:
《剪灯新话》是明初瞿佑在文网森严情况下创作的传奇小说集。其故事曲折,叙写闺情至奇艳,在当时风行一时;以后一二百年间,仿效者众,且传至亚洲汉文化圈,成为具有世界性的文学作品。
关键词:
《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校勘;闺情艳语;流播
一
传奇小说在唐代中叶作者最多,自唐以后,便逐渐走了下坡路;宋人模仿的作品虽多,但功力已远不如唐人;元代作者更少得可怜,只有《娇红记》等几篇。直到明初,传奇小说才重新兴盛起来,山阳(一作钱塘)瞿佑(宗吉)的《剪灯新话》倡导于前,庐陵李祯(昌祺)的《剪灯余话》继之于后。他们的作品内容都是烟粉、灵怪一类的故事,很受当时读者的欢迎,仿效者纷起,使得统治阶级也不得不加以禁止。直到嘉靖(1522—1566年)初年,文网较宽,文坛才渐渐恢复了生气,但传奇小说的作者还不多。邵景詹模仿《剪灯》而作的《觅灯因话》,出现在万历时期(1573—1619年),文笔虽别有一种朴素遒劲的地方,但辞藻已较逊。这三种传奇小说,是沟通唐宋传奇与《聊斋志异》之间的桥梁,在文学史上应该说是有相当地位的。
二
《剪灯新话》的作者瞿佑,很早就有诗名。他的作品,还有《春秋贯珠》《阅史管见》《通鉴辑览镌误》《诗经正葩》《大藏搜奇》《学海遗珠》《香台集》《香台续咏》《香台新咏》《存斋诗集》《存斋遗稿》《鼓吹续音》《屏山佳趣》《乐府遗音》《余清詞》《余清曲谱》《天机云锦》《游艺录》《乐全稿》等,现在只有《剪灯新话》《归田诗话》《咏物诗》三种流传,其他多半亡佚了。
相传在他14岁的时候,其父亲的好友张彦复由福建来访。瞿父具鸡酒款待,恰好瞿佑从学中归来,张彦复要试他才学,就指鸡为题,命他赋诗一首,他应声吟道:“宋宗窗下对谈高,五德名声五彩毛。自是范张情义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张彦复大为称赏,手画桂花一枝,并赋诗道:“瞿君有子早能诗,风采英英兰玉姿。天上麟麟原有种,定应高折广寒枝。”他父亲很是得意,就造了个堂屋叫传桂堂,以期流芳。
那时著名文人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号称江南诗坛泰斗和一代诗宗,和他叔祖瞿士衡是知交。有一天,维桢走访士衡于传桂堂,瞿佑见到他的香奁八咏,即席倚和,俊语叠出。维桢击节叹赏,对士衡说:“此君家千里驹也!”自此声名传播一时。但他虽有才学,却生不逢辰,流落不遇,一生只做了些教谕、训导、长史等类的微职。永乐年间,甚至还因作诗蒙祸,被谪戍保安十年,才得放归。
关于《剪灯新话》的作者,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尽管凌云翰在序中说《秋香亭记》是瞿氏自己的写照,犹元稹之于《莺莺传》(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也说:“或谓《秋香亭记》乃宗吉事,使其果然,亦元微之‘会真意也。”),但后来却有人说《新话》非瞿氏所作。《都公谈纂》说:“予尝闻嘉兴周先生鼎云:《新话》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郑公之后,家杭州吴山上。杨廉夫在杭,尝至其家,富生以事他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戏为作此,将以贻主人也。宗吉少时,为富氏养婿,尝侍廉夫,得其稿,后遂掩为己作。惟《秋香亭记》一篇,乃其自笔。”
说《剪灯新话》是杨维桢作,未免有些荒谬。杨维桢文名虽盛,但这一类传奇小说却非他所擅长。他所写的《哑娼传》,文采就远不如《新话》,难怪明朝文人都穆在他所撰写的《都公谈纂》中,也不相信,说“今观《新话》之文,不类廉夫”了。大概因为《新话》出版后风行一时,有些人心怀嫉妒,所以造出这种蜚语,只是想降低瞿氏的声誉罢了。
《剪灯余话》的作者李昌祺,官职比瞿佑要高得多。他是永乐癸未(1403年)进士,做过翰林院庶吉士,还曾参加纂修《永乐大典》的工作,以礼部主客郎中权知部事,外调做到广西、河南左布政使。《明史》有他的传。他的作品除《剪灯余话》外,还有《运甓漫稿》《容膝轩草》《侨庵诗余》等。
李昌祺显然是很服膺瞿佑的,他的《余话》完全是在模仿《新话》,不但篇数相等,而且故事的取材也差不多;只有《至正妓人行》一篇,序文和诗作是《新话》所没有的。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好夸炫他的才学,在作品中穿插进许多和正文没有关系的诗词,因此篇数虽和《新话》相等,篇幅却比《新话》多出一倍。他是一位集句的能手,安磐说:《余话》中的集句颇为可取,“如‘不将脂粉涴颜色,惟恨缁尘染素衣。‘汉朝冠盖皆陵墓,魏国山河半夕阳。对偶天然。”这倒不是溢美之誉。
李昌祺因为官阶较高,不像瞿佑那样微秩末位,而《剪灯余话》中又粉饰闺情,拈掇艳语,便被当时一般卫道之士目为白圭之玷。《列朝诗集》说李氏死后,“议祭之社,乡人以此短之,乃罢。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其然岂其然乎?”《都公谈纂》也说:“景泰间,韩都宪雍巡抚江西,以庐陵乡贤祀学宫,昌祺独以作《余话》不得入,著述可不慎欤!”这都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一般的卫道士,是如何地蔑视和压制传奇小说这类作品的。
《觅灯因话》的作者邵景詹,生平事迹不详。据他书中小引所叙,此书系著于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年)。全书仅两卷,共八篇,文笔较为朴实,很少辞藻点染。大概这时的文体,已濡染八股气息,正如方苞批评明代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年)的文章时说的“气体苶然”了。但它给拟话本小说以相当影响,冯梦龙、凌濛初都曾在这部书中撷取题材。
这三部传奇小说,都曾经给予天启年间(1621—1627年)那些拟话本的小说作者,影响深刻,流传后世的《三言》《两拍》都在其中摄取过素材而予以敷衍。
三
《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在我国早已没有足本流传,明人高儒《百川书志》所载《新话》仅有十一篇;清乾隆时(1736—1795年)的坊刻本,《余话》仅有十四篇;同治年间(1862—1874年)出版的《剪灯丛话》所收二书,都各只有两卷,篇数皆已不足。但在日本,却有庆长、元和间(1596—1624年)所刊活字本,篇数最完全,董康据以翻刻,二书始全璧复归中国。1931年,上海华通书局曾用铅字排印,今已不可多得。1936年,郑振铎为生活书店编印《世界文库》,曾把二书收入第六至第九册内,《余话》并用乾隆本校勘,但并无单行本。中央书店曾据《世界文库》翻印,却只到《莺莺传》为此,并非全璧。
我从1957年校注《剪灯新话》,至1981年重新出版该书,历经24年。我从未放弃过对《剪灯新话》的校注;即使在“文革”之中,还用《佩文韵府》和《渊鉴类函》修正注释,并且通过朋友赵景深教授的介绍,了解到日本汉学专家伊藤漱平的不同意见,从而于再版中予以采纳。
此书的校勘是以董氏诵芬室刊本为底本,而校以《世界文库》,以及乾隆本、同治《剪灯丛话》本。《觅灯因话》就在《剪灯丛话》内。明人徐勃《红雨楼书目》中著录有这书,但一般人很少见到,所以把它附在卷末。除了上述各种本子外,我还曾用其他各种书籍参校,如《金凤钗记》《联芳楼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牡丹灯记》《翠翠传》《绿衣人传》《秋夕访琵琶亭记》《凤尾草记》《琼奴传》《至正妓人行》等,都以《古今图书集成》校勘;《渭塘奇遇记》以《孤本元明杂剧》中的《王文秀渭塘奇遇》校勘;《听经猿记》以《元明杂剧》中的《龙济山野猿听经》校勘;《贾云华还魂记》以《古本戏曲丛刊》内的《洒雪堂传奇》,《西湖二集》中的《洒雪堂巧结良缘》和《古今图书集成》内的《魏鹏传》三种本子校勘。虽然文言和白话不同,但也可以从中校正原书中所载诗词、标点、断句的正确与否。
四
明朝初期,文网较元代更严。朱元璋这位枭雄之主,猜忌阴狠达到了极点,常常疑心人家在那里骂他,笑他曾做过和尚,偷过牛;有好些人因为在表文中用了“生”字、“则”字,被他认为谐音“僧”和“贼”,冤枉杀了头,甚至把“帝扉”当做“帝非”,“法坤”当作“发髡”,“藻饰”当做“早失”,一律加以诛戮。在这样的封建淫威下,一般文人谁都不敢妄弄笔头,免得惹出祸端来,让脑袋搬了家。
盛行于元代的戏曲,这时也遭到了厄运。据顾起之《客座脞语》的记载,当时有这样一种禁令,凡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之道,扮演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杂剧,非律所该载的,都限期送官烧毁;敢有收藏传诵印卖,全家杀绝。在这种严刑峻法下,文人们为了不抵触功令,就模仿唐人的笔法,大写特写佳人才子和风花雪月的传奇小说来了。然而就是这些作品,却真切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男女生离死别的不幸遭遇,以及处于战乱时代的悲欢离合。另外通过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又发泄了作者胸中的郁闷,弥补了内心的失落。
瞿佑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写了这部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共21篇。他写作的动机也许是为了消遣,并没有任何出而问世之意。当时文字狱的祸害,使他深怀戒心,所以写成后锁在箱子里有二十个年头。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传观的人多了,大家都赞美这部著作,怂恿他付印。他虽然同意印将出来,但毕竟还有些戒慎恐惧,所以在序言中用“语怪”“诲淫”一类的话来加以掩饰,避免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
不料出版后,因他文笔清新,故事曲折,兼之粉饰闺情,拈掇艳语,在当时苦闷的政治环境中,引起无数读者的共鸣和喜爱,竟风行一时。这真可以说是他始料不及的。
由于《剪灯新话》的风行,文人们便都竞写传奇小说,其中模仿得较好的是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其完全是在模仿《新话》,题材故事也都差不多,唯一不同处是作者好显弄才华,在作品中糅入、插进许多诗词。这些诗词有些是创作,有些是集句,有些则简直是抄袭而来。例如《琼双传》中,徐苕郎所作的四首花月词,就是抄袭郑奎妻的作品。
《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中有很多优秀的作品。这因为瞿佑和李昌祺所处的时代距离元末明初不远,故而作品中有些内容,乃是元明之际社会生活的写真。因此,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自有魅力,颇为后人玩味。
不过这两部书中也有许多封建的糟粕,其中神仙鬼怪故事竟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这固然反映了一般民众落后的意识;同时无意间也迎合了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宣传、组织群众的手段。当时文网虽严,但对拥护封建秩序,宣扬封建落后意识的文章,却并不禁止,这就可见当时统治阶级的用心。要不是因为后来拟作者太多,弄得瑕瑜不分,我想这两部书本来是不至于遭到禁止的。
五
1991年夏,我从台湾学者陈益源教授的来信之中获悉,《剪灯新话》在亚洲各国流传深广,许多国家将它称誉为“无可与之伦比的,具有世界性的文学作品”。
该书15世纪中叶流传到韩国,小说家金时习随即仿作《金鳌诗话》,成为韩国小说的始祖。16世纪由尹春年订正,林芑集释的《剪灯新话句解》,是韩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注释本。19世纪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还记载说:“今闾巷辈所专习者,有《剪灯新话》一书,以为读此则娴于夷文云。”高丽大学教授丁奎福曾撰文赞美此书,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研究它。这在汉文区内引起极为强烈的震荡。
《剪灯新话》传至日本后,16至17世纪出版的《奇异杂谈集》和《灵怪草》,均选译过此书。江户时代浅井了意的《伽婢女》之中的第三卷《牡丹灯笼》,完全是以瞿佑的《牡丹灯记》为蓝本写作的;不过,小说中的人物、场面、背景、风俗,都显出日本的传统特色。那一时期,以中国明清小说作为蓝本而写作出来的所谓近代型小说,日本人称之为“翻案小说”。
以后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不少内容也是根据《剪灯新话》改写的。此后,三游亭园朝又将它改为“讲书”,题目则成《怪谈牡丹灯笼》。德川幕府时,《剪灯新话》在日本的版本“隽刻尤多,俨如中学校的课本”。1954年日本学者村上知行出版了《全译剪灯新话》,他在序文之中称赞说:“是颗怪异而美丽的星,輝耀着东洋古典世界的天空。”还有的日本人将此书列入“在中国不被重视,却在日本深受欢迎的十部书之一”。久保得二曾经评价道:“《剪灯新话》虽为琐琐的小册子,但它给予后世的影响和果实,实在辉煌。”
1987年法国远东学院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创刊》后,学术界的人士才知道,《剪灯新话》在越南也极受欢迎。越南作者阮屿模仿《剪灯新话》,写作了一本《传奇漫录》,竟然成为该国传奇小说的开山鼻祖。阮屿乃“刻意好奇,做小说以寄笔端,将越南文学带进了一个新的高峰”,使得文学面对动乱的社会现实,让靡丽消闲的气氛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受其影响,后来涌现出一大批像女作家段点氏《传奇新谱》那样的小说。
所以有人说,《剪灯新话》开启了中国在亚洲南北邻邦,共同发展的文化潮流。此语不虚。
六
赵弼的《效颦集》出版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他的所谓效颦,就是效《剪灯新话》的颦,这在他的后序里说得非常清楚。书中共收传奇小说25篇。它和《剪灯新话》不同的地方,就是没有佳人才子的恋爱故事,而是充斥了忠孝节义、因果报应一类的内容,这是很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胃口的。赵弼的思想极为迂腐,他甚至伪造文天祥的《临刑说》和吴潜的《南行诗》,开明人作伪风气之先。书中有三篇和平话小说有关的文字,即《钟离叟妪传》(和《京本通俗小说》中《拗相公》篇同一题材)、《续东窗事犯传》(和《古今小说》中《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同一题材)、《木绵庵记》(和《古今小说》中《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同一题材)。
在这三篇传奇小说中,《钟离叟妪传》最使研究传奇小说和平话的人聚讼纷纭。因为《京本通俗小说》一般都认为是宋元话本,缪荃荪《江东老谭》的刊本也出于影元人写本。如果《拗相公》一篇,是先胎于《效颦集》,那么影元本的说法便根本动摇了;就是其他各篇见于《也是园书目》,素来被目为宋人平话的,也将成为问题。所以孙楷第先生认为,这几篇传奇小说是和《京本通俗小说》出于同一底本,并非赵弼创作;又引《效颦集》中其他各篇出于赵弼自撰的文笔极拙的情况,和《钟离叟妪传》进行比较,发现在结构和笔墨方面,两者大不相同作为佐证。
谭正璧根据孙楷第的说法,认为元明小说,传奇与话本互译,系属常事,因此他断定《效颦集》中的这几篇文章,是赵弼由话本译成传奇。而我们除《效颦集》外,则实在举不出任何其他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此外,在明代,传奇小说和话本是并不分家的,凡是笔写的小说,不论文言或口语,都一律视为话本,例如《清平山堂话本》中《蓝桥记》《风月相思》都是传奇小说,万历(1573—1619年)版《熊龙峰刊话本小说》四种中的《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也是传奇小说,三言中的《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宿香亭张浩遇莺莺》《隋炀帝逸游招谴》三篇也都是传奇小说。洪楩、冯梦龙等作者,既然不把文言的传奇改译成口语以求体裁一律,那么,赵弼何以独独不惮烦地把口语改译成文言的传奇呢?这真是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也是园书目》所载宋人词话十二种中并没有《拗相公》这一篇。我们对《效颦集》中的这几篇传奇小说,是否是赵弼由口语改作文言这个问题,也暂时还只能存疑而已。
七
对日本成篑堂藏弘治(1488—1505年)刊本传奇小说《钟情丽集》,明清人都认为是邱浚的作品。它的写成时代大约在景泰(1450—1456年)初年,叙述辜辂和黎瑜娘的恋爱故事,内容浮猥蝶亵,文字浅近鄙俚,实在是一篇恶札。据褚人获《坚瓠集》说,邱浚少时,他的父亲曾为他求婚于士官黎氏。黎氏讥诮邱浚不配做他的快婿,邱浚遂愤而撰这篇传奇,写黎氏失身于辜辂。辜辂是广东人呼狗的声音。如果褚人获所说属实,则邱浚的写作态度实在非常轻薄。继之而起的有《怀春雅集》《天缘奇遇》《刘生觅莲记》《花神三妙传》《兰会龙池录》《双卿笔记》等几篇传奇小说,内容都和《钟情丽集》不相上下,字里行间充满了淫辞亵语,远远不能望《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的项背。
《怀春雅集》又名《寻芳雅集》,据《金瓶梅词话》序言作者欣欣子说是卢梅湖作的,叙元代吴廷璋与王娇鸾等的婚姻故事。其和《情史》卷十六“周廷璋”条及《警世通信》卷三十四“王娇鸾百年专恨”所叙元周廷璋事,虽然结果有喜剧和悲剧的不同,但时代及男女两主角的姓名均相同,仅改吴廷璋为周廷璋,疑为一事两传。《兰会龙池录》叙《拜月亭》戏曲中,蒋世隆和王瑞兰恋爱一事,内容与戏曲颇多出入。这篇传奇小说和其他的几篇作者都不详,它们的写作时代当为弘治以后,每篇都是单行本,极易散佚;后来得以保存下来,还是得力于《风流十传》《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绣谷春容》《花阵绮言》等诸多选本的留存。
此外,周复俊的《泾林杂记》书已亡佚,仅《古今书集成》中《闺媛典》内辑有数篇,都是抄袭节录《剪灯余话》中的作品成文,只有记唐寅故事的一篇当是出于他的手笔。他是明末《泾林续记》作者周玄的祖父。因此可以推测,他的写作成书时代当在嘉靖年间(1522—1566年)。当时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新兴市民阶级的抬头,连带影响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措施,取消了若干严刑峻法,文网也因之较宽,给书籍的出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此时稿件却供不应求,使得文坛上抄袭和作伪的风气因此加剧。
邵景詹的《覓灯因话》出现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全书仅两卷八篇,其中《贞烈墓记》和《唐义士传》二篇,是从《辍耕录》中脱胎而来的。作者虽然经常把《剪灯新话》放在案头,心慕手追,想续其绪余,但笔力却远不能相副。特别是在《唐义士传》中,他因不能分辨唐玉潜和林德阳二人,究竟谁是埋宋陵诸骨的人,遂把二人混而为一,说林德阳就是唐玉潜的化名,可见浅陋。《觅灯因话》这部书,当是明代传奇小说集的最后一部,这以后是拟话本小说的黄金时代——由于《三言二拍》的相继出版,传奇小说至终明之世已不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