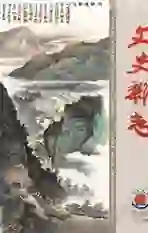《华阳国志》采录前人史料的艺术技巧
2021-11-22王怀成
王怀成
摘 要: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多次表示其宗旨乃“述而不作”,故其辑录历史材料多于个人创作。然《华阳国志》是历史作品,而史学作品是要通过叙事来完成的。《华阳国志》是以时间为线索,以人物和时间为中心,由地理志与人物志连缀而成的一部史书,其叙事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这些故事又往往是常璩直接或间接采自他人之书,其对材料的剪裁表现出作者较高的艺术技巧和叙事能力。
关键词:《华阳国志》;采录史料;艺术加工
《华阳国志》的内容并非都是常璩的原创。面对大量的地方史事、人物、文学等内容,常璩根据不同情况,或直录前人的文字记载,或经考辨而更正、补充前人的记载,或对繁复的史料进行剪辑和组接,以使历史脉络更为直观清晰。常璩创造性地把有关巴蜀先民的神话故事录入文本中,增强了《华阳国志》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更保存了极为重要的上古文献。有的史事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冲突、矛盾,常璩便采取叙、议两分的处理方法,并加以自己的辨析。
一
对部分既重要又无争议的史实,《华阳国志》就将前人的记述予以直录,如《汉中志》中梓潼郡一段写道:
刘先主自葭萌南攻州牧刘璋,留中郎将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张鲁遣将杨帛诱峻,求共城守。峻曰:“小人头可得,城不可得也!”帛退。刘璋将向存、扶禁由巴阆水攻峻,岁余不能克。峻众才八百人,存众万计,更为峻所破败,退走。成都既定,先主嘉峻功。二十二年,分广汉置梓潼郡,以峻为太守。[1]
此乃常璩直接采用前人陈寿的史料,如《三国志·蜀书·霍峻传》就载有此事:
先主自葭萌南还袭刘璋,留峻守葭萌城。张鲁遣将杨帛诱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头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后璋将扶禁、向存等帅万余人由阆水上攻,围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才数百人,伺其怠隙选精锐出击,大破之,即斩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广汉为梓潼郡,以峻为梓潼太守。[2]
一百三十余字的材料,仅十余字不同,亦可见常璩采前人史料之尊重史实。常璩与陈寿都是蜀人,常璩借鉴陈寿的痕迹明显。相比之下,在叙及霍峻以少胜多战胜向存、扶禁之事,常璩比陈寿之语更为凝练,且所记也更为具体精确;尤其是刘备分广汉郡置梓潼郡,常璩指明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则尤显可贵。
对《汉中志》叙张鲁事迹,则带出其祖父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之事,又因之带出张陵创立“米道”始末。张鲁事迹《三国志》有传,而常璩此处仅大略采之,改造之处不少。常璩精粹地概括了《三国志》的记载,而重点突出“米道”的教义与教规;接着又插入张修与汉中太守苏固的战争,而将《三国志·蜀书·二牧传》中的“米贼断道”引入此处。刘琳以为:“按此段事应放在刘焉以张鲁为督义司马入汉中之后,鲁在汉中以五斗米道为治之前。《常志》叙事间有时序不清之病,此其一例。”[3]笔者以为,常璩作此安排,是为了先引出五斗米道,再在此基础上叙“米贼断道”,从而顺理成章地叙述了五斗米道的历史故事。又《华阳国志》节录《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之“璋,字季玉,既袭焉位,而张鲁稍骄恣,不承顺璋,璋杀鲁母及弟,遂为仇敌。璋累遣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为巴西太守,领兵御鲁”[4]一段,常璩在“杀鲁母、弟”之后加入“鲁说巴夷杜濩、朴胡、袁约等叛为仇敌”[5];又将《三国志·魏书·张鲁传》中“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庞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一段放在“为仇敌”之后;又将《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先主更袭取璋”一句置于最后。《华阳国志》虽不专为张鲁立传,但常璩却通过剪辑、补充的方式,摘取《三国志》中同一事件相关联的多位人物的事迹,融会贯通,使得张鲁之事清晰明了,颇有纪事本末之意。如《三国志·张鲁传》之载: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6]
然而《华阳国志》对此段史实的记载却与《三国志》出入很大:
二十年,魏武帝西征鲁,鲁走巴中。先主将迎之,而鲁功曹巴西阎圃说鲁北降,归威武:“赞以大事,宜附托;不然,西结刘备以归之。”鲁勃然怒曰:“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遂委质魏武。武帝拜鲁镇南将军,封阆中侯,又封其五子皆列侯。[7]
张鲁降曹魏一事,陈寿记载的两段对话,明显有史家推测附会与美化之意;故常璩舍之,反而记录了前人史料所无的一段。其所增“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云云,显然要鲜活可信得多。
常璩“志”的部分,是对一地的风土人情及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尽可能全面的记载,但又不拘泥地理范畴的局限。以《华阳国志·汉中志》所叙张鲁事迹为例,张鲁事迹并不是都发生在汉中一地;而张鲁这样的人物,因为既涉及四川地区的五斗米教,又对三国政局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故在常璩看来,是不能割舍的,遂索性插叙其政体事迹。常璩这样的剪辑和处理,无疑使得其地理方物部分亦有丰富而饱满的人物叙事,故事性和思想性不亚于人物传,并保存了《三国志》所未曾保留下来的鲜活史料,所以《华阳国志》的叙事成就自不待言。
二
常璩在《公孙述刘二牧志》之“刘璋志”中,叙述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刘备攻刘璋,庞统献计刘备进取成都,刘备先是采纳,后与庞统对话而发生矛盾,最后化解。此段故事,前半部分叙刘璋不许刘备入蜀,取自《三国志·先主传》;后半部分叙刘备与庞统对话产生的矛盾,取自《三国志·庞统传》。二者结合,是以刘备欲入刘璋据守的蜀地而順便引出刘备的性格,以及庞统的智慧与个性,表现出常璩的叙事能力,可谓高明。《华阳国志》这一节本为刘璋志,但旁叙庞统与刘备甚详细,因三者之间的关联很紧密,故而常璩对《三国志》中《先主传》和《庞统传》的材料所做的拼接也很紧密。再如,《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从题目上就能看出是叙后主事迹的,但用在诸葛亮身上的言语却多于刘后主,甚至录诸葛亮《出师表》全文,亦可证常璩之《华阳国志》对材料的取舍的标准。一些虽不直接相关却因常璩自视极为宝贵的部分,仍尽可能详尽地保留了下来。而这些处理,对《华阳国志》的文学性的增强,显然有益。
保留先民历史、神话、传说,使得叙事的文学成分加强。《华阳国志》前四卷叙地理方物,均祖述巴、汉中、蜀、南中的历史渊源,自远古至于当代的历史脉络及奇闻异说。其中还保存了西南少数民族古远悠久的历史材料和风俗民情。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云:“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试举其例:如巴蜀滇黔诸地,自古为中华民族文化所未被,其次第同化之迹,治史者所亟欲闻也。而古代史上有两大役,实兹事之关键。其在巴蜀方面,为战国时秦司马错之定蜀;其在滇、黔方面,为三国时诸葛亮之平蛮。然而《史记》之叙述前事,仅得十一字。《三国志》之叙述后事,仅得六十四字。其简略不太甚邪?”[8]梁启超只注意到了正史,所以发现正史中有关巴、蜀、滇、黔一带史料的贫乏。其实,正史之外的《华阳国志》,恰好弥补了这一遗憾。如《巴志》叙大禹治水,将军巴蔓子、板楯蛮射杀白虎、巴渝舞、涂山禹王祠等史事;《汉中志》叙张道陵、张鲁之五斗米道、梓潼县五妇山及“故蜀五丁士所拽蛇崩山处”传说;《蜀志》叙古蜀先王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等帝王、五妇冢山等古老的传说,司马错伐蜀、李冰治水、文翁化蜀、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等历史故事与爱情事件,五丁力士开石牛道、李冰斗水神、邛都水神等神话;《南中志》叙竹王传说、神马出滇池等。凡此远古历史、神话传说等故事的记载,皆显示了《华阳国志》的文学色彩,其中部分故事甚至千古传唱,这无疑要归功于常璩剪裁材料的睿智眼光与高超的叙事能力。
三
常璩合理处理史料的载录与辨析的关系,使得《华阳国志》的叙事更洁净与纯粹。《华阳国志》记载的巴、汉中、蜀、南中各地先民活动事迹、历史传说及神话等,往往能引人入胜,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如蜀王妃的故事,《蜀志》载: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作《臾邪歌》《龙归之曲》。其亲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成都县内有一方折石,围可六尺,长三丈许。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桥,亦有一折石,亦如之。长老传言,五丁士担土担也。[9]
这一段记载是关于秦并蜀的历史故事,但将真实的历史人物与奇异事件相结合,似乎荒诞不经,同时又仿佛真实可信,达到了亦真亦幻的境界,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华阳国志》的文学性。又如有关“石牛道”的故事,《蜀志》载: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奉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10]
此事始记载于扬雄《蜀王本纪》,《艺文类聚》“牛”部引《蜀王本纪》曰:
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以为”二字,《太平御览》卷三百五作“以告曰”三字):“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枚”,《太平御览》卷九百作“牧”)于成都(“都”,《太平御览》卷三百五作“郭”)。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末句《太平御览》卷三百五作“将兵随石牛道伐蜀焉”。)[11]
对比两处记载,不难发现,常璩所记自蜀王以“物化为土”的“珍玩”,回报秦惠王的黄金之赠开始,不仅使得石牛故事收尾更加周全,合情入理,而且使得这个传说还透露了蜀王愚昧、蜀地经济文化落后,秦人于此意识到可以轻易攻取之的宝贵历史信息。这也使得“石牛便(粪)金”的阴谋,能够轻易为蜀王相信,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常璩的这一记载,显然是建立在民间口耳传说的基础上的。此外,常璩对这些传奇色彩的故事也很有兴趣,层层递进式地展现蜀王上了当,还懵懂无知,沾沾自喜地嘲戏秦人;而秦人却胸有成竹,为武力进犯蜀地开辟道路,做好准备的故事。其前后照应周密,余音袅袅。当然,常璩为丰富这个故事进行的加工和叙述,较之《蜀王本纪》更加可信可读,文采亦更胜出一筹。此是常璩通过直接叙事与间接叙事相结合所达到的文学效果。
有时候一件史事若在流传过程中有太过抵牾的地方,常璩则往往采取叙、议两分的处理方法,即先全貌保留该流传的原委,然后在结尾部分加以理性的辨析,表明自己对此事件的真正态度。不妨仍以石牛开道故事为例。常璩在《序志》篇辨析道:“《蜀纪》言:‘三皇乘祗车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史记周贞王之十八年,秦厉公城南郑。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说者以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12]如此,则令读者明白,常璩虽在前文生动而完整地保留了蜀人关于石牛开道的传说,但他本人并不相信这一说法。常璩的理由是,《蜀王本纪》既然称三皇时代有车出谷口的记载以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的记载,但谷口即斜谷,也就是南郑,这就说明蜀道的疏通早在三皇、武王时代就有了。常璩接着又指出,历史还记载了秦厉公伐南郑之事,那么,秦厉公的时代蜀道显然也已经开通。所以,关于秦惠王时代石牛开道的说法,并不可靠,故云“不然也”。这说明常璩具有严格的史家辨伪的精神。更为巧妙的是,常璩将对这一史事的辨析,放到最后的总结部分,从而保持了原文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正因如此,这一故事的文学性也得以呈现出来。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常璩针对一些传说的辨析有时也并不到家,正如顾颉刚先生《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史事》一文所称“常氏立此标准而不能严格遵守,故‘蚕丛纵目‘鱼凫得仙‘五丁能移山‘山精化女子‘山分为五岭尚见于其书中,得非作者之一恨邪?”[13]顾颉刚先生视常璩这些辨析不周到的地方为“作者之一恨”;而对于探讨《华阳国志》的文学性而言,我们也可看到常璩在史料的文学性和真实性的关系的把握上,有时还处于矛盾、踌躇的境地而不能自洽。
注释:
[1][3][5][7][9][10][12]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45页,第118页,第118页,第119页,第189页,第188頁,第896页。
[2][4][6]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007页,第868页,第264—265页。
[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11]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6页。
[13]顾颉刚:《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史事》,《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5页。
作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