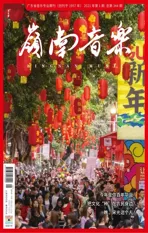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连载6)
2021-11-19文|
文|
第二章 西周至战国的音乐批评(四)
2.左丘明
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都君人(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关于其姓名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曾任鲁国史官,为解析《春秋》而作《左传》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国语》(按照王充说法,其撰写《国语》是为了弥补《左传》的不足),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左丘明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是儒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是一部记述翔实、论述精辟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与《左传》一起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由于史料详实,文笔生动,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孔子、司马迁均尊左丘明为“君子”。班固在《汉书》中称赞道:“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历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等。
一般看来,左丘明作为一位史学家,其记载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事迹,均应属于所记载对象个人的思想观点与历史行为。故,史家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仅以史料、史实的记录者的身份来观照左丘明,而忽视了其作为一个思想者与批评者的存在。笔者认为,面对任何一件史料与历史事件,是否记载?如何记载?以何种角度记载?等等。都取决于史家个人的眼界与方法。而这种眼界的宽度广度与深度,方法使用的准确度与精巧度等等,都是史家个人学养的体现。基于此种思考,笔者将这位“文宗史圣”“经臣史祖”请到“台面”上来,对其音乐批评方面的论述做一个粗略的梳理,一来对之表示敬意,二来以起筚路蓝缕之功效。
①对宫廷乐仪的批评
作为一位与孔子惺惺相惜者,左丘明也是一位敬畏周礼、推崇乐教、遵行乐仪的大儒。以下这三篇文献,就记载了他的这类批评观念: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左传·隐公五年》)
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文公四年》)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左传·襄公四年》)
王公贵族在庭中用乐的“羽数”,是国家制度里关于礼仪的等级差别,万万不可僭越。故,孔子曾有“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名言存世。左丘明在这里记载了一个有令禁止、从善如流的隐公的形象。第二个史料记载的是卫国大夫甯武子来鲁国访问,鲁文公设宴招待并在宴会上表演歌舞作品《湛露》《彤弓》,作为客人的甯武子不作回应,文公便派使者私下探问缘故。甯武子对该场燕乐的演出表达不满:你们这是非正式的、练习的标准和形式,完全没有进入正规演出的状态。于是,便将正式演出时在情绪、态度、仪礼、道具等表演心理与形式上的要求娓娓道来。第三个史料也是关于外交乐仪的:穆叔出使晋国,悼公设享礼招待他。乐器演奏《肆夏》三章,其不答拜;乐工歌唱《文王》三曲,亦不答拜。歌唱《鹿鸣》三曲,三次答拜。韩献子派子员问其缘由,答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这是对当时国家间礼乐行为的现场批评,这种批评多是立足于礼仪与国格的角度而展开。
②对以乐行德的批评
“以乐行德”是国家之间、古代王公贵族之间,相互德化的一个交往手段与治理方式。下面的这些文献记载了古人在这方面的做法:
晋郄缺言于赵宣子曰:“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若之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说之。(《左传·文公七年》)
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广车、軘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凡兵车百乘,歌钟二肆,及其鏄磐,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诗》曰:‘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帅从。’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礼也。(《左传·襄公十一年》)
郄缺向赵宣子进言:过去的卫国不顺服我国,“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不仅如此,还需要对之施以道德感化,具体的办法就是“劝之于《九歌》”(因为“六府、三事”这“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不使之变坏。您的功德没有人歌唱,谁还能来归顺?何不由归顺您的他们,来为您唱赞歌呢?赵宣子非常愉快地采纳了郄缺的建议。音乐的道德感化能量,被晋国的君臣很好地利用起来。在第二条文献中,记载的是“魏绛和戎”的历史史实。鉴于魏绛在对外交往中的重大贡献,晋悼公将郑国进献的一半乐队、乐人奖赏给他。魏绛辞谢,晋悼公说:“赏赐,是国家的典章,藏在盟府,不能废除的。您还是接受吧!”“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在晋悼公看来,魏绛有功于国,奖励理所应当,以乐工、乐队奖励其功绩,也是古代中国社会王公贵族之间的经常性社交活动。以国家奖励的方式,则是不多见的。
③对以乐节欲的批评
“道”与“欲”的矛盾,是人世间的社会伦理基本问题,古代社会如是,现代社会亦如是。对此,古代的先贤无不面对这个难题。以下三则史料,就是“以乐节欲”的批评:
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巨将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德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左传·昭公元年》)
二十一年春,天王将铸无射。伶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窕则不咸,槬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昭公二十一年》)
二十三年,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单穆公曰:“不可……!”“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周语·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
古人对于“道”“欲”矛盾的化解智慧,就在于左丘明在这里引述秦国名医医和的“以乐节欲”说之内:其所推崇的“先王之乐”就是能够“节百事”的音乐品种。在这种音乐里面,五声音阶的进行、旋律流动的快慢、作品首尾的呼应等,都是建立在和谐原则之上的。而“烦手淫声”是能够使人“慆堙心耳,乃忘平和”的,故“君子弗德也”。做事也如奏乐,过犹不及、适可而止。第二、三条史料,联系记载了景王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听从单穆公与伶州鸠的规劝,执意铸造大钟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是“以乐节欲”的反面例证。“钟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就是单穆公与伶州鸠对景王对乐音享乐无度追求的训诫。然,“王不听,卒铸大钟”,“二十四年,钟成,伶人告和”,王洋洋自得,果不其然,“二十五年,王崩”,“钟”终“不和”。乐事与人政的因果关系,被详实地记载下来。
④对以乐治国的批评
儒家强调“礼乐治国”,而对其中“乐”的重视程度,是怎样形容都不为过。在治国的实践中,许多政治家则是直接将“乐”应用其中,此类案例俯拾皆是。以下三则史料,记载的是“以乐治国”的事迹:
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焉?……若君谓此台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楚语·伍举论台美而楚殆》)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周语·邵公谏厉王弭谤》)
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赋《黍苗》。子余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若君实庇荫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强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获集德而归载,使主晋民,成封国,其何实不从。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诸侯,其谁不惕惕以从命!”秦伯叹曰:“是子将有焉,岂专在寡人乎!”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晋语·秦伯享重耳以国君之礼》)
第一则《伍举论台美而楚殆》,提出的批评标准是:不“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以察清浊”的耳朵“为聪”,而以“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为乐”“为美”。第二则《邵公谏厉王弭谤》,提出的是“天子听政”应充分利用各类人才智力优势的道理:列卿献呈民间诗歌、乐官献呈民间乐曲、史官献呈史书、师氏进箴言、瞍者朗诵、蒙者吟咏、百工劝谏……只有将民间心声上达朝廷,近臣尽心规劝,宗室姻亲补过纠偏,乐官、史官各抒己见,元老重臣劝诫监督,天子再斟酌取舍,政事施行才能不与国情相违背。第三则《秦伯享重耳以国君之礼》讲述的是秦穆公以乐识人、辨才,通过对其乐德的考核,最终对重耳委以重任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说明古代的贤者,能够通过音乐作品(创作、表演)的观察,进而知晓乐者的道德情貌,进而为知人善任、国家管理网罗人才。
⑤对闻乐知德的批评
“闻乐知德”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观乐、察人的一项主要的途径与方法,左丘明对此也是深谙其道,其在自己的史学巨著中也有关于此类批评的记载:
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晋语·师旷论乐》
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
师旷通过晋平公喜爱新声的音乐价值取向,进而就可以得出“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的价值判断。其理由是:音乐有“开山川之风”“耀德于广远”的社会功效。透过晋平公的用乐嗜好,就可以判断该国君将“卑乎”!齐桓公问史伯大周朝会衰亡吗?史伯站在事物和谐才具有生命力的角度看待国家的兴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因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故而以乐喻理、比德、附政,得出如下反问:“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一代史家巨擘左丘明,其政治观是儒家的,其人文观是开放的,其艺术观也是儒家的。作《国语》时已经双目失明,他以急迫的历史使命感发奋修史,最终得以完成珠联璧合的《左传》《国语》,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作出重大历史贡献,也为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历史提供了丰富历史史料。
3.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城)。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之孙子思的弟子,儒家学派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代表人,与子思继承和阐发了孔子的学说,在儒学史上形成“思孟学派”,自述“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出身家道没落贫困的贵族,中年周游列国,晚年退而从教著述。宣扬“仁政”,倡导“以仁为本”,在中国历史上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尊称为“亚圣”,与孔子并称“孔孟”。着有《孟子》②,该着属录体散文集,由其弟子共同汇编言论而成。
①批评基于对人学的探究
中年孟子游说诸侯终不得志,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司马迁《史记·孟轲列传》)。孟子的思想根基于孔子,又有所发展。其发展的部分以“人学”成分为着。该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的“人学”研究就已经成为显学,孟子是当时该研究的引领者。孟子充分地意识到“人”的问题重要性,进而在此领域有所推进,成为古代“人学”研究的奠基者。孟子的“人学”体系建立在“性善论”的人性判断之上,以砥砺“至大至刚”人品为目标,以施行“仁政”为核心。
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孟子·滕文公上》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性善论”基于这种判断:“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善心乃人类本性。进而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孙丑上》)“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以上“四心”君子存、小人失,失“四心”即禽兽,就要“反求诸己”,使己“放心”、恢复“四心”。“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如此便“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与此同时,孟子也肯定“饮食男女”、追求成长进步等人性的合理性。诸如:“食色,性也”(《告子上》);“形色,天性也”(《尽心上》);“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告子上》)等,即是。
在“人格”方面,崇尚“大丈夫”。论人格美以尧舜为楷模,以“大丈夫”“大人”为标准:1.何谓“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膝文公下》)。又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2.何为“大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朱熹《孟子集注》云:“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无伪而已。”“赤子之心”即纯洁真诚的“童心”。孟子的“赤子之心”,启发了李贽“童心说”、袁枚“性灵说”。
在“养气”方面,提倡养“浩然之气”。其自称“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何谓“浩然之气”?就是“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正气。此“气”有“天下为已任”的自觉:“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为“平治天下”,先经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的磨砺,后养蓄“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具备这种“气”就可以“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雠”(《高类下》),故而实现“天降大任”于己,进而“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在“仁政”方面,提出“保民而王”。孟子的“仁政”思想基于“性善”的判断:“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孙丑上》)以民为本,是“人学”思想的出发点,提出了超越孔子的“贵民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呼吁,认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要求国君“与民同乐”,关爱百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将“土地、人民、政事”视为“三宝”(《尽心下》)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反对暴政、提倡仁政:“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离娄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
②批评根于对心理谙熟
由于孟子对于中国古代人的心理与人性掌握较为精准,故其音乐批评多从生理、心理、人性的角度切入。让人读来感觉入心、在理,他认为人的感觉系统大多一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尽心下》)。故“圣人,与我同类者。……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告子上》)。在这里,他明确地肯定了人听觉感受音乐之美的天赋,对“音”“声”“乐”的听赏与喜爱是人的本性使然。对此,君王是如此、圣人是如此、常人亦是如此,没有贵贱、贤愚之分。
③批评基于对方法了悟
基于以上对人的生理、心理、人性的掌握,孟子在音乐批评中提出了一种“知人论世”的方法和路径:“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社会的主体是人,社会活动的中心也是人,人就是音乐创作主体和批评主体。因此,孟子在以上的阐述中提出了音乐批评的“知人论世法”。该法要求“颂其诗,读其书”更应当“知其人”“论其世”。孟子要求的“知其人”,就是要求批评者对作者的生理、心理特征、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等有所掌握;“论其世”,就是了解生平事迹,熟悉生活环境、时代风貌、社会背景、历史事件等。对此,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解释道:“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这种方法,就是我们现在音乐批评实践中仍然屡试不爽的“社会历史”“创作心理”的批评方法。故,“知人论世法”一经提出,便被后世批评所普遍接受与经常运用,成为音乐批评的主要方法之一。
基于以上对人的生理、心理、人性的掌握,孟子在音乐批评中还提出了一种“知言养气”的方法和路径:“知言养气说”,来自孟子论述个人修养时的表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所谓“知言”就是:“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要求批评者把握作品的形态语言,以及创作表演作品的人物内心活动。这种从语言形态到内心活动的把握能力,也是音乐批评实践中必须具备的一种鉴赏力。所谓“养浩然之气”就是:主体具备高深的内在修养,这种素质达到最境界之后,就便于通过外部的艺术形态语言,透析内在的心理世界。在孟子之后,“知言养气说”被古代批评家移植到文艺批评的实践中,成为重要的艺术理论命题。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倡导:“务盈守气。”韩愈在《答李翊书》提出:“气盛言宜。”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倡导:“文者气之所形。”谢赫在其所着的《古画品录》中将“气韵生动”作为第一条款和最高标准;“桐城派”在艺术批评总结的“八法”中,也提到“气”。以上诸家批评理论的提出,无不受到孟子“知言养气法”的启发。
基于以上对人的生理、心理、人性的掌握,孟子在音乐批评中又提出了一种“以诗逆志”的方法和路径。在《孟子》中,记载了其与弟子咸丘蒙关于这种方法的对话: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子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上》)
这是孟子师徒之间关于音乐批评方法的讨论,孟子所谓的“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就是运用“知人论世”的理念,以《诗》为批评对象,对批评方法的阐释。要求批评者不能以只言片语曲解《诗》意(即“不以文害辞”),要结合作品在表情达意过程中运用的各种艺术手法综合审视;不能局限于作品辞句本意的解释(即“不以辞害志”),以免妨害对作品情感与内容的理解。正确的诠释与理解的方法,就是“以意逆志”。后人对“意”的理解有:1.读者之意,赵岐注:“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朱熹注:“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朱自清《诗言志辨》认为:“以己之意‘迎受’诗人之志,而加以‘钩考’。”③2.作者之意。结合孟子在《诗·小雅·北山》《大雅·云汉》的批评操作案例,读者的解释与作者的原意的综合更为贴切。关于“逆”,《周礼》郑玄解曰:“逆,犹钩考也。”《说文》解曰:“逆,迎也。”孟子针对当时盛行的主观臆断、断章取义的批评方法,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对于匡正学术批评的偏谬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同时,这种批评方法也存在着牵强附会、天马行空般地解释作品的偏颇,这个问题为后代儒生的偏执批评、曲解作品等,埋下了方法论的种子。
④批评为仁政理想实现
基于“仁政”人文理想,孟子的音乐批评也是围绕这个目标而开展的。与孔子一样,孟子也是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也是将音乐视为实现其社会政治理想的重要辅助手段。基于此,他认为音乐从本质上来看是“仁义”的艺术:“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巳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路之手之舞之”(《离娄上》)。在阐述音乐“仁义”本质同时,也承认音乐对人的喜乐情感的承载作用。这就使得他“仁义”的音乐批评框架有了人性情感的支撑。孟子继承了子产“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的思想,并将音乐表现人的情感的成分,仅限于“喜乐”之情。对于后来的荀子在《乐论》中明确提出“乐者,乐也”的理论命题,以及《乐记·师乙》著名的“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论述,都具有启发意义。经过孟子对“喜乐之乐”的阐释,使得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上形成了一种牢固地肯定“喜乐之乐”,坚定地否定“悲愤之乐”的审美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基于“仁政”理想,孟子还认为,音乐所表现的“喜乐情感”,不能是任意对象的,而应仅限于“仁德”颂扬的“喜乐情感”。这种限定,是对孔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批评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将音乐家、音乐作品具备“仁德”内涵、颂扬“仁德”思想,作为一项基本的批评标准固定下来,进而作为上下各阶层遵守的圭臬。1.将“仁政”理想“下沉”为对每个社会个体的行为规范,就具体落实为“礼”范畴之内“孝悌”规范的树立:“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第一》)。孟子阐释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离娄上》),就是要求音乐表现以上的“喜乐情感”,颂扬以上的“仁德”。2.将“仁政”理想“上升”为对帝王行为规范的要求,就具体表现为“与民同乐”的口号。《梁惠王下》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这段“与民同乐”的对话:
(齐宣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类,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篇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以能鼓乐也?’今王由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基于“独乐乐”不如“与少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的逻辑演绎与判断,进而结论道:“与民同乐”。这是对君王日常音乐生活的规范性要求,这个要求与上面对社会成员的“孝悌”规范合而为一,成为完整的古代社会上下各阶层音乐生活规范的批评标准系统。这个标准系统,也成为其“仁政”人文理想实现的保障。
他的“与民同乐”的音乐批评观念,现在看来也是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的。作为宫廷音乐来看,自从它进入宫廷之日起,就成为帝王及贵族的审美专利品。它的“娱人”“怡神”的社会属性,不能够全面地发挥。孟子看到了这一点,便站在民众利益的基础上,对宫廷音乐的这种弊端提出批评。他的这种批评,对于音乐走向普通民众,普通民众走进宫廷音乐;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通过音乐艺术的中介作用缓和社会矛盾等,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左传》采用版本: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②《孟子》采用版本: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注疏》。
③朱自清:《诗言志辨》,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2008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