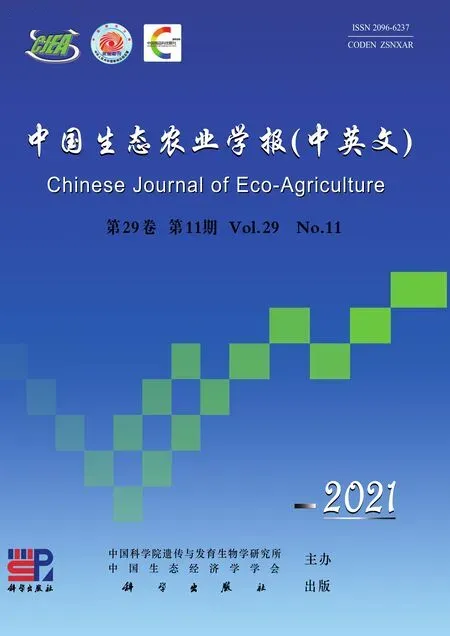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2021-11-17王辰璇姚佐文
王辰璇,姚佐文
(1.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合肥 230061;2.淮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淮北 235000)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污染日益严重。2014年我国化肥施用强度为363.0 kg·hm−2,2015年农用化肥施用量达6022.6 万t。2015年农业部下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此后我国化肥施用强度、化肥施用量逐渐递减,2019年化肥施用强度为325.7 kg·hm−2,化肥施用量为5403.6 万t。尽管农村化肥施用量有所下降,但是化肥施用强度还是比发达国家设立的水污染安全上限值(225 kg·hm−2)高。2013−2019年,农药使用量从180.77 万t 下降为145.6 万t,但是单位面积的农药使用量为8.8 kg·hm−2,依然高于发达国家的农药用量标准。2019年,农药利用率仅为39.8%,未被利用农药进入土壤和水体,会导致土壤和水体污染。此外,我国地膜使用总量位于世界第一位,由于残膜回收率不高,造成农田地膜污染严重。畜禽养殖产生大量废弃物,如果废弃物得不到良好的处理,也将给农业带来严重污染。2019年全国大牲畜年底存栏量为9877.4 万头,约带来28 亿t 废弃物。日前,我国养殖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resource utilization ratio)只有60%,未被资源化利用的废弃物,若不妥善安放、随意排放到水中,也会带来污染[1]。
“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在不断下降,2016年时,恩格尔系数为30.1%,2019年恩格尔系数为28.2%。消费者加大了对优质安全农产品的需求,然而,农业缺乏优质的水土资源,这一矛盾若不解决,将会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聂弯等[2]指出,农业生产应使用比较少的自然资源生产出更多数量产品,对环境负面影响减少到尽可能小。因此,迫切要求加快农业绿色生产转型步伐,努力提高农产品质量;迫切需要加大对农业生产中的生态效率分析,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在生态效率的研究领域,已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农业生态效率20世纪90年代由德国学者Schaltegger 等[3]提出,以较少的农业资源消耗,换取比较多的农业产出。学界往往从微观、中观、宏观等方面对农业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包括影响因素分析以及农业生态效率指标体系等。
微观研究方面,贾琳等[4]对黑、豫、川3 省玉米种植户进行调研,获得517 份问卷调查,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对玉米种植效率测算,提出加大农业技术推广投入,提高农业技术效率。高鸣等[5]运用河南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的数据,测算小麦全要素生产率,提出粮食直补能提高小麦生产技术效率。钟方雷等[6]采用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数据,以80 户农户样本点,测算张掖市3 个县区农业生态效率,研究发现包含外雇机械作业费的服务费用对生态效率作用是负相关的。
中观研究方面,曹慧等[7]测算了松花江、黄河和长江三大流域2004−2013年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提出松花江、黄河和长江三大流域生产技术效率呈递减幅度上升。刘蒙罢等[8]对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发现生态效率具有正空间自相关性;尚杰等[9]分析2009−2018年13 个粮食主产区城镇化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指出人口城镇化率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是负向的,城镇经济密度对农业生态效率起正向作用。
宏观研究上,吴梵等[10]对2008−2017年农业生态效率进行测算,提出农业科技创新对本省的农业生态效率起促进作用,农业机械投入强度降低了本省的农业生态效率,而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机械投入强度对邻省农业生态效率均起促进作用;洪名勇等[11]通过研究发现:从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总体贡献上分析,纯技术效率较规模效率的贡献要大;侯孟阳等[12]测算了1978−2016年农业生态效率,并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的作用,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有空间溢出效应,模型加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二次项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显示出“U”型特征,同时农业机械投入强度的变化对相邻省份的作用为正值,但若考虑直接效应,农业机械投入强度总效应还是负值。王宝义等[13]分析1996−2015年31 个省份农业生态效率,发现农业机械密度对农业生态效率是负向。
农业生态效率测算过去常常采用随机前沿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等,近些年含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由于能很好地处理“松弛现象”问题而日受青睐;但是目前的非期望SBM(slack-based measure)模型则较少将农业生态效率为1 或者超过1 的决策单元做进一步比较,超效率SBM 模型能够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农业生态效率量化方面,非期望产出指标选取上是有差异的,王迪等[14]、于婷等[15]选择农业面源污染为非期望产出指标,认为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对农业效率影响差异大;刘应元等[16]、田伟等[17]以农业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在科技与生态效率方面,陈新华等[18]提出科技进步是生态效率增长的源泉;严翔等[19]发现科技创新效率对生态环境存在门槛效应,且为同向,呈倒“U”型。郭莉等[20]指出中西部地区环境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差异明显;李冬冬等[21]研究发现科技投入对环境治理具有显著作用;孟凡生等[22]认为研发投入与能源生态效率有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研究在不同程度上论证科技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生态效率成果颇丰,研究农业机械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较多[10,12-13],但研究农业科技对农业生态效率效应的相对较少。尽管吴梵等[10]研究指出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生态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但该文的研究认为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生态效率是线性的假设,事实上,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生态效率可能是非线性的。常见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Simon Kuznets curve,EKC),加入二次项主要是描述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有可能是曲线关系,如二次函数关系,两者之间究竟是U 型还是倒U 型取决于一次项与二次项的系数。参考侯孟阳等[12]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的研究,本文认为以往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生态效率的研究,缺乏加入农业科技创新平方项进一步研究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也缺乏从东中西部内部,解析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门槛效应的差异。
基于以上基础,本文将农业碳排放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23],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 测算2000−2018年中国省际的农业生态效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并剖析东中西部地区门槛特征。期望在以下两个层面有所突破:首先,不同的农业科技投入水平意味着不同地区对农业重视程度的差异,从而对应不同的农业生态状态,在所构建的面板模型中加入农业科技投入水平的平方项,检验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与农业生态效率的关系。其次,按照东中西部3 组,根据面板门槛回归分析东中西部内部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对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异质性,揭示东中西部门槛特征的差异,探索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与农业生态效率关系的内在机理。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农业生态超效率SBM 模型构建
DEA是农业生态效率测算常用的方法。然而,这一方法在处理“松弛”问题、比较效率≥1 的决策单元方面,与超效率SBM 模型相比,后者优势较明显。故本文选择超效率SBM 模型测算农业生态效率,模型构建如公式(1):
式中:农业生态效率用AEE 表示,决策单元个数设为n个,m个投入、r1个期望产出、r2个非期望产出共同构成每个决策单元,x是投入矩阵中的元素,yd是期望产出矩阵中的元素,yu是非期望产出矩阵中的元素。
1.2 计量经济模型
本文建立标准计量模型如公式:
通常采用对数形式:
式中:T、N分别表示农业科技投入和技术水平,a、b分别为T、N的弹性系数,d为常数项。本文以农业生态效率(AEE)为被解释变量,以单位面积农业科技投入量(TES)反映农村科技投入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105元·hm−2);以农业机械投入强度(MII)反映农业技术水平(kW·hm−2)。对公式(3)进行扩展:
式中:KT(元)表示农业科技投入规模,即农业科技投入量,由于省际农业科技投入数据部分缺失,参考吕屹云等[24]用省(自治区,直辖市)科研费用支出的7%作为农业科技投入规模的变通量;MCI、CPS、ADR 分别代表复种指数、种植结构、农业受灾率;α0代表截距项,α1−α6代表弹性系数,i代表省份,t为时间。
为了更加全面地考量农业生态效率的差异性和依赖性,将空间效应加入到标准计量模型。根据空间相关效应来源的不同,空间计量模型可分为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
1.2.1 空间计量模型
1.2.1.1 空间误差模型(SEM)
式中:AEEit为农业生态效率,W代表空间权重矩阵,λ表示空间误差系数,ξ 代表随机误差向量,ui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
1.2.1.2 空间滞后模型(SLM)
式中:W为空间权重矩阵;WlnAEEit为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滞后项;ρ为邻近省(直辖市)观测值对其他省(直辖市)的空间溢出的方向和影响,其大小反映溢出程度;α0为截距项,α1-α6代表估计系数;εit为随机干扰项。
1.2.1.3 空间杜宾模型(SDM)
该模型同时考虑了AEEit因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造成的空间溢出效应,X表示其他解释变量与空间权重矩阵交乘项的集合,γ表示各交乘项的估计系数。SDM 可将空间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溢出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
1.2.2 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参考Hansen[25]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东中西部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将农业科技投入水平(TES)为门槛变量和关键解释变量,设置门槛模型:
鉴于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生态效率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故在线性模型基础上加入农业科技投入的平方项ln2TES,理论模型如下:
模型(9)、模型(10)中,τ为门槛变量,η1和η2为待估算的门槛值,I(·)为指标函数,α0为截距项,α1-α9代表弹性系数。
1.3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全国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由于港澳台地区数据缺乏及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本文研究区域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0−2018年的数据进行农业生态效率测算,数据来源于各省各年的统计年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参考已有的研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等,构建的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其中,农业要素投入指标包括以土地、劳动力、机械动力、灌溉、化肥、农药等;期望产出指标选择农业总产值指标,参考李波等[23]的碳排放模型测算系数;非期望产出指标选取农业碳排放指标,农业碳排放的测算选取了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灌溉耗电耗水、翻耕流失等6 类直接或间接的碳排放。

表1 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指标体系Table 1 Indexes system of 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 in China
2 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各地区农业生态效率测试结果
本文使用DEA-SOLVER Pro 5.0 软件,采用超效率SBM 模型,测算2000−2018年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农业生态效率,并进行对比分析。按照我国在1986−1990年提出三大经济带划分,东部包括辽、京、津、沪、冀、鲁、苏、浙、闽、粤、桂、琼12 个行政区,西部包括西北的陕、甘、宁、青、新和西南的川、云、贵、藏、渝1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包括黑、吉、晋、蒙、皖、豫、鄂、湘、赣9 个地方。各地区农业生态效率测算结果及变化如图1所示。
通过测算发现:2000−2018年,全国农业生态效率均值均没有达到超效率水平(农业生态效率>1)。东部农业生态效率平均值没有达到超效率;但其中北京、上海、山东、江苏、广东、浙江每年的农业生态效率都是超效率,均值分别为1.391、1.318、1.124、1.051、1.196 和1.091(各地具体农业生态效率见首页二维码附表)。天津2016−2018年农业生态效率分别为0.402、0.305 和0.438,其余年份均是超效率;海南2011年后农业生态效率没有达到超效率,其他年份均为超效率;福建除2000−2002年、2005年为非超效率,其余年份均为超效率;辽宁2000−2002年农业生态效率是超效率,2003年起农业生态效率是低效率;河北、广西2000−2018年农业生态效率都比较低。
中部地区2000−2018年农业生态效率平均值没有达到超效率。其中,内蒙古在2000−2007年农业生态效率是超效率,2008年以后,农业生态效率为低效率,其农业生态效率最高值达1.057;河南省除2015−2018年4年之外,2000−2014年农业生态效率都是超效率,其中2005年农业生态效率值最高达1.094;湖南除2017−2018年外,2000−2016年农业生态效率是超效率,2000−2018年间均值为0.927;湖北省2000−2018年间,有8年农业生态效率是超效率,研究期内均值为0.594;吉林、山西、安徽、江西这19年农业生态效率均是低效。
西部地区2000−2018年,农业生态效率平均值只有2年达到超效率。2010−2014年,西部与东部农业生态效率差距不大,2015年后,西部与东部相比,农业生态效率差距逐渐拉大。从西部内部分析,四川、贵州、西藏2000−2018年19年来的农业生态效率都是超效率。值得一提的是,西藏的生态效率最高达5.7;陕西除2017−2018年外,新疆除2013−2018年外,农业生态效率均是超效率,最高值分别为1.159 和1.171;2000−2018年,宁夏只有2年、青海有5年农业生态是超效率,最高值分别达1.004和1.023;重庆、云南、甘肃农业生态效率都是低效率。图1 显示:2000−2018年从全国层面农业生态效率分析,全国农业环境效率有一定波动,2000−2003年有小幅波动,2004−2008年农业生态效率略有下降,2008−2010年稍有上升,2010年农业生态效率为0.731;之后2011−2014年稍有下降,2015−2017年全国农业生态效率分别下降到:0.5894、0.5839 和0.5159;2018年农业生态效率提升到0.5453。
从国内外文献看,针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波动及影响因素,学界进行了相关研究。尚杰等[9]分析了城镇化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侯孟阳等[12]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如前文所述,陈新华等[18]、严翔等[19]、郭莉等[20]、李冬冬等[21]和孟凡生等[22]的研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实中农业领域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如何影响生态效率呢? 本文借鉴前文测算出农业生态的效率值,在空间分析框架下将农业科技投入纳入农业生态效率优化问题中,深入探究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2.2 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采用全局莫兰指数对农业生态效率(AEE)空间相关性及农业科技投入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2000−2018年农业生态效率莫兰指数均为正(0.004~0.298),农业科技投入水平的莫兰指数同样为正(0.309~0.391),除个别年份外,两变量均在P<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中国农业生态效率与农业科技投入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有必要对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
2.2.1 模型选择与检验
本文在选择模型时,选择常用的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杜宾模型(SD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并建立普通的OLS 模型比较。为进一步分析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在模型中加入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平方项ln2TES。计量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Hausman 检验结果的P<0.05,因此,选择固定效应。
STATA 软件运行结果(表2)比较发现,SDM 模型拟合度R2比SLM 模型、SEM 模型拟合度R2略高,因此本文选择SDM 模型的固定效应模型。
空间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OLS 模型中的农业机械投入强度lnMII 和SLM 模型、SDM 模型、SEM 模型中农业科技投入规模lnKT 的固定效应,均在P<0.01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系数均为负;究其原因,可能存在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忽视生态保护,在农业科技资金使用上存在配置不合理,对农业生态效率缺乏重视等问题,农业生产提高的同时却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上未产生理想的效果。伴随农具大量采用,农业机械投入强度的增强带来柴油消耗、农膜覆盖等增加,增加了农业碳排放。

表2 农村科技投入与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结果Table 2 Spatial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r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put on 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
4 个模型中,农业科技投入水平lnTES 在P<0.05或者P<0.01 显著性水平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农业科技投入水平lnTES 系数为正,表明自2000年以来,我国农业科技投入水平的上升在农业生态效率的提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农业科技投入水平lnTES 的二次项大多数系数为负值,多数固定效应回归系数在P<0.05 显著性水平下检验通过,说明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是“倒U”型。
2.2.2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SDM 模型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如表3所示。
表3 显示:在直接效应下,农业科技投入规模lnKT 和农业科技投入水平lnTES 对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一次项系数通过P<0.01 显著水平,回归系数为2.086;二次项系数为负,即呈现“倒U”曲线。在间接效应下,农业科技投入规模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在P<0.05 显著水平下检验通过,说明我国省域之间农业科技投入规模KT不仅直接影响各省(市、自治区)内农业生态效率,而且通过间接效应影响邻近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生态效率。

表3 农村科技投入与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杜宾模型效应分解结果Table 3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spatial Dobbin model of the impact of r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on 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
总之,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对农业生态效率直接影响是“倒U”型。究竟什么原因会导致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是“倒U”型的关系? 本文试图从东中西部内部解析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门槛效应的差异,进一步阐释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关系的内在机理。
2.3 东中西部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面板门槛特征
本文选取核心解释变量农业科技投入水平(lnTES)作为门槛变量,建立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首先对门槛效应的存在性进行检验,运用STATA 软件,采用Bootstrap 法模拟300 次,经检验发现,模型(9)下,单门槛效应在P<0.1 的水平下显著,双门槛效应在P<0.01 的水平下显著。模型(10)下,单门槛效应在P<0.01 的水平下显著,双门槛效应在P<0.05 的水平下显著,因此可认为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其次,将样本分成东部、中部、西部3 组,利用门槛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其影响机制的区域差异。表4 显示了基于模型(9)、模型(10)的分组回归结果。
表4 显示,东中西部农业科技投入规模(lnKT)对农业生态效率的作用方向存在差异,模型(9)、(10)下,东部农业科技投入规模lnKT 的系数为负,分别为−1.259 和−0.848,在P<0.01 水平下通过检验;中部在(9)、(10)不同模型下,农业科技投入规模系数分别为−5.379 和1.928,在P<0.01 水平下通过检验;西部模型(9)下农业科技投入规模的系数为正,值为0.797,在P<0.01 水平下通过检验,模型(10)lnKT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这可能与东中西部农业科技投入规模的基础不同有关,西部科技投入基础薄弱,一旦投入科技,可能效果就比较显著,东部农业科技起步早,基础比较厚,当农业科技投入到一定规模,再投入,其对农业生态效率作用系数相反,可能的解释是投入要素的匹配度制约了农业科技的发挥。

表4 农业科技投入影响农业生态效率的分组面板门槛回归Table 4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 of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put on 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
东部较中西部农业机械强度(MII)呈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随着大规模的农具的实施,在提高农业生产的同时,会有一定的污染倾向,弱化农业生态效率的提升;从复种指数MCI 分析,模型(9)、(10)下,东部lnMCI 系数分别为0.145 和0.362,分别通过P<0.05 和P<0.01 显著性检验;西部lnMCI 系数分别为0.279 和0.283,均通过P<0.01 显著性检验;中部lnMCI 系数影响不显著。从种植结构CPS 分析,东部模型(10)下lnCPS 系数为−0.360,P<0.05 水平下检验通过,模型(9)下东部lnCPS 系数没有通过检验;中部模型(10)下lnCPS 系数没有通过检验,模型(9)下中部lnCPS 系数为0.494,通过P<0.1 显著性检验;模型(9)、(10)下,西部lnCPS 系数分别−1.493 和−2.168,均通过P<0.01 显著性检验。从农业受灾率ADR 分析,模型(9)下,东中西部均不显著;模型(10)下,中部不显著,东部lnADR 系数为0.246,通过P<0.01 显著性检验,西部lnADR 系数为−0.306,通过P<0.1 显著性检验。从农业科技投入水平(TES)上分析,TES 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故加了平方项。模型(10)中,东部ln2TES 的系数为负,值为−0.065,通过P<0.01 显著性检验;西部ln2TES 的系数为负,值为−0.172,通过P<0.1 显著性检验;中部ln2TES 的系数未通过检验。
比较农业科技投入规模KT、复种指数MCI、种植结构CPS、农业科技投入水平TES 和农业受灾率ADR 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模型(9)、(10)下,东、中、西部lnTES、lnKT 的系数整体比复种指数MCI、种植结构CPS 和农业受灾率ADR 大。由此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农业生态效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农业科技投入规模、农业科技水平有很大关系。
2.3.1 东部地区农业科技投入水平门槛特征
在模型(9)下,东部仅在单门槛效应下显著(显著性水平为P<0.1,门槛值为0.23065%),变量系数显著为正,农业科技投入水平的提升可有效提高农业生态效率,促进农业生态发展;跨越门槛后,促进作用稍微减弱(影响系数由1.275 降低到1.194)。加入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平方项ln2TES 后,模型(10)下,东部在双门槛效应下显著(显著性水平为P<0.05,第一门槛值为0.5517%,第二门槛值为3.6189%),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跨越第一门槛后,促进作用有所增强(影响系数由0.537 上升到0.609);但是越过第二门槛后,受促进作用边际递减的作用,促进作用再降低至0.509。东部地区省(直辖市)均越过第一门槛,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福建越过第二门槛,江苏2018年接近第二门槛,进入作用递减阶段,但是依然体现东部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对生态效率提升的积极作用。
2.3.2 中部地区农业科技投入水平门槛特征
中部农业科技投入水平的门槛效应不稳定。在模型(9)下,中部仅在单门槛效应下显著(显著性水平为P<0.05,门槛值为0.3199%),变量系数显著为正。当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低于0.3199%时,影响系数为4.958,但越过此门槛,影响系数降为4.839,表明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略有下降。与东部比较,中部越过第一门槛时间滞后5~6年。
在加入TES 平方项后的模型(10)下,中部在双门槛效应下显著(显著性水平为P<0.1,第一门槛值为0.0527%,第二门槛值为0.1022%)。中部地区短期增加化肥农药使用量的粗放式农业生产,会造成农业生态效率损失,此阶段系数为−4.359;当处于第一门槛和第二门槛之间,随着中部政府制定的各类农地保护政策的实施,农业生态效率的下降会有所缓解,系数为−4.298,当跃过第二门槛值时,系数影响为−4.185。与东部对比,截止到2010年,中部省域均进入高门槛区(TES≥0.1022%),即农业科技水平比较早地抑制了农业生态效率的提高。
2.3.3 西部地区农业科技水平门槛特征
在模型(9)下,西部仅在双门槛效应下显著(显著性水平为P<0.1,第一门槛值为0.3458%,第二门槛值为0.6288%)。变量系数显著,值为−1.722,跨越第一门槛后,抑制作用增强,值为−1.878;越过第二门槛后,抑制作用进一步增强,系数影响为−2.025。
进一步根据双门槛值将西部样本划分为低门槛区间(TES≤0.3458%)、中等门槛区间(0.3458% 表5 2000—2018年西部地区农业科技水平门槛区间Table 5 Threshold interv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vel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from 2000 to 2018 本文在采用超效率SBM 测度2000−2018年我国东中西部省际农业生态效率基础上,根据莫兰指数对农业生态效率及农业科技投入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剖析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 2000−2018年东中西部的农业生态效率波动明显。其中,2017−2018年农业生态效率略有提升。东部地区和西部的四川、贵州、西藏农业生态效率多数超效率;中部地区的安徽、湖北、江西、山西、吉林等农业生态效率较低,在农业生态资源利用、农业生态配置方面有待于优化和改进。 东中西部比较发现,中部地区农业生态效率一直低于东部、西部,中部的农业发展、资源利用与农业生态环境处于不平衡状态,说明中部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大省,在追求粮食产量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向中部转移的农业布局有关,且东部的农业技术水平底子较厚,研发重点逐渐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造成东部技术进步与中西部比较提升有些缓慢。此外,西部农业生态效率一直在逐渐下降,可能的解释是西部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清洁生产技术也比较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比较弱;另外,与东部比较,西部的农民和政府在关注农业生态保护方面可能稍微弱些。由此可见,农业生态效率不仅涉及碳排放,还涉及到当地经济农业生产条件、政府是否关心以及技术条件等。 从SDM 模型总效应分解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表3)分析,直接效应中,农业科技投入水平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符号相反,为负,即呈现“倒U”曲线,表明农村科技投入最初增加可提升农业生态效率,但增加到一定水平时,反而会对农业生态效率产生负向影响。究其原因,单位面积农业科技投入量(TES)对东、中、西部影响是非线性的,作用方向也有差异。可能一方面与东、中、西部当地生产要素中投入要素的均衡有关,某一生产要素的短板都会制约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并且实证显示东中西部农业科技投入门槛效应差别较大。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村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为“倒U”曲线。这就要求不能盲目增加农业科技投入,而应优先考虑环境保护的前提下发展农业生产,推广有机类肥料产品替代化肥等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警惕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导致农业生态下滑的拐点。 从门槛效应分析,东部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积极作用没有东部稳定,模型(9)模型(10)中时正时负,可能因为中部在推广农业科技时对农业生态保护重视还不够;西部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表现为负向抑制作用。究其原因,可能的解释是西部农业科技基础薄弱,要发挥农业科技的作用,需要各投入要素协调匹配,优化各投入资源,才能起到“1+1>2”的作用。这就要求中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科技投入要兼顾经济与生态效率。 门槛特征的差异也要求东中西部根据各地农业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作用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权衡农业科技、农业生产与可持续等目标的相互协调,根据本地区农业科技现状,通过制度设计和完善农业科技相关政策,合理调控农业科技投入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努力提高农业生态效率。 2000−2018年从农业生态效率均为超效率的省份来看,北京、上海、浙江单位面积农业总产值平均值居于前3,分别为(×105元·km−2)52.510、40.936和30.782;山东、江苏和广东分别为(×105元·km−2)19.787、20.470 和24.674,位次分别是9、8 和6。 西藏2000−2018年年均单位面积机械总动力为1498.09 kW·km−2,值得一提的是,这可能包含了高海拔环境对机械效率的影响;天津和河北单位面积机械总动力分别位于第2 和3 名,分别为1173.56 kW·km−2和1026.24 kW·km−2;北京、山东和浙江单位面积机械总动力分别为990.79 kW·km−2、944.09 kW·km−2和889.49 kW·km−2,分别位于4、5、6 位。 从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上分析,福建和海南较高,分别为52.94 t·km−2和51.89 t·km−2,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分别为50.24 t·km−2、33.33 t·km−2、42.08 t·km−2、43.21 t·km−2、35.64 t·km−2和48.42 t·km−2,分别排在3、18、9、7、12 和4 位;青海最低,为15.41 t·km−2。 从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上分析,海南和福建较高,达3.57 t·km−2和2.44 t·km−2;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分别为1.56 t·km−2、1.70 t·km−2、1.44 t·km−2、1.14 t·km−2、2.39 t·km−2和2.14 t·km−2,位次分别为7、5、9、12、3 和4;宁夏、陕西和内蒙古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都很低,只有0.19 t·km−2、0.28 t·km−2和0.30 t·km−2。 从单位面积农膜使用量上分析,上海和北京单位面积农膜使用量偏高,分别为5.26 t·km−2和4.64 t·km−2;西藏最低,只有0.39 t·km−2;广西、黑龙江和青海单位面积农膜使用量也比较低,分别为0.54 t·km−2、0.58 t·km−2和0.67 t·km−2;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分别为2.80 t·km−2、1.21 t·km−2、2.19 t·km−2和0.83 t·km−2,分别排在6、13、9 和23 位。 自2015年国家大力推广化肥农药使用零增长行动,已取得一定效果。但是从产出分析北京、上海、浙江单位面积农业总产值的产出相对其他省较高。尽管农业生态效率长期是超效率的,但是北京、江苏、广东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比较高。从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上分析,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和广东也比较高;单位面积农膜使用量上,上海、北京、山东和浙江均较高。全国各地化肥农药减量增效任务依然很艰巨,要大力推广绿色高效技术模式,加快实施科学施肥用药技术,抓好示范带动减量增效。
3 结论
3.1 东中西部的农业生态效率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态势
3.2 农村科技投入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为“倒U”曲线
3.3 东中西部的农业科技投入门槛效应差别较大
3.4 大力推广绿色高效技术模式,提高农业生态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