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生命
2021-11-17袁媛
●袁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由植物、动物和人类共同拥有的世界。我们与自然生灵间建立着一种联系,这让人感怀和动容。人类最应该恐惧的是它们在沉默中彻底告别我们。
杜鹃花语
过了漾江镇,汽车开始走向漫长的山路。我们要去看的是生长在漾濞县境内苍山西坡的大树杜鹃。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来苍山西坡看杜鹃了,这里生长的大树杜鹃不同于人工培植的植物,它们珍贵且稀少。更重要的是,在山野之中看大树杜鹃会让人感觉每一种生命都充满着生机,而且这种生机不加雕琢、无处不在,在高寒山水与阳光的光合作用下它们所呈现的是自然最原始的姿态,经过漫长休眠,在春季送上最美的画卷,仿佛一个宁静世界的苏醒。
现在正值春分时节,春分带来的暖气解冻了寒冰下的新芽。大树杜鹃花开,在艳灿的色泽下,与山峰的高度保持着一种势均力敌的态势,它们在阳光下和稀薄的空气里逐渐发育成熟。我们下车又走了一段路才到达杜鹃树的家园。眼前的这些红杜鹃、黄杜鹃、粉杜鹃还有白杜鹃,满满填充着山里大部分的通道,热闹地拥塞着这片荒地与森林的边界。这样,在这个遥远静谧的地界之中,它们结束了漫长冬日的休眠,有的生长在宽阔的坡地上,有的在深邃的沟壑里,有山脊和雨水的保护。这时,风起了,树木发出沙沙的声响,犹如大海的浪声在高山上重现。
同行的王老师说,这里的杜鹃树基本都是年迈的老树。我笑着问道:“有多老才算是老树?”他说,这些大树杜鹃是如此纯粹和罕见,他以前在曲靖师宗见过一棵据称有千年树龄的杜鹃树王,可苍山西坡的杜鹃树不论从粗壮的程度或是树干碳化的程度上看,年代都要久于那棵千年树王,它们古老得仿佛富有某种神性。
我想透过时间去想象这些杜鹃树的经历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无论我怎么去观察与猜测它们,似乎都必须带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但它们比我所知的历史更加古老。有时我们的各种努力与挣扎说到底都似乎是在和时间抗争,但年代、春秋、小时、分秒这些标志时间的词语,在这些树木面前已经没有了意义,时间只是刻度,不会改变它想要坚守的东西。
这是一棵大树红杜鹃,褐色的树皮起了褶皱,有的地方还长满了青苔。我轻轻用手抚摸它,像是和一位年迈的智者握手言谈,即便它沉默不语,其实树给人的手感已经不像是木质,犹如古老的寒石。树上的沟沟壑壑就像脚下的山川一样,风力与昆虫成为这些沟壑的雕刻者。我觉得树皮有时候对于我们就像人类,仿佛也有着千万种深刻的想法,如大脑上的褶皱,也像农民手上的老茧。看似粗糙,实际上却犹如一种精密细软的物质,不断地张开、撕裂和愈合,树脂犹如毛孔溢出的脓液。这些古老的树皮在见证着这棵杜鹃树的出生、成长、衰老与死亡,可谓见证百态。虽然杜鹃树无法拥有脚步声,但却有着活跃的心跳,树枝上娇艳的花朵像是一串串火红的小灯笼,也像是集聚了活跃的血液。这些娇艳的花朵浓缩了阳光最浓稠的质感,花瓣不仅吸取了树中最艳丽的色泽,叶片也非常厚实,新鲜的花朵每一年春天都如期开放,与古老沧桑的树干、树皮形成了强烈的视觉碰撞。一棵棵杜鹃树上有数不清的树干,这些树干相互交叉和纠结,结成了一个结实的华盖,犹如一个巨大的顶棚。大树杜鹃在漫长的时间里茂盛、死亡和重生。直到现在,它们依然自由地生长着。在天空之下,站在一棵苍老遒劲的杜鹃树面前,显得十分具有意味,面对时间和自然,我们人类自身的微渺展露无遗。
透过这边的杜鹃树,可以望见山坡另一头的风景,开阔而清寂。这些丰富的层次为整个风景注入着神圣的活力。从眼前的距离看,最远处是若隐若现的森林,如梦境一般静静卧在流岚之中。对生长在城市里的我而言,那里是多么地遥不可及,仿佛像是另一个国度、另一方大陆以及另一个生活的时代。再近一些的地方是一个略有斜度的山坡,山坡的坡度平缓宽大,坡上有两间简陋矮小的木房子,还有两匹在低头吃草的马。远望过去,山坡呈现一种稍显暗黄的色调,这个色调一直蔓延到我的脚下。去年枯败的蕨草在来年春天并没有成为碍眼的杂败之物,倒是合成了一种永恒且特殊的色调。这些枯败后的蕨草是继杜鹃花后最耀眼的主角之一,我发现它们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娇艳的杜鹃。当我自己真正爬上山坡的坡顶时,眼下漫山都是这种干枯的蕨草和一些低矮的杂草,踩上去,会发出树枝断裂般的声音。我拾起一株干枯的蕨草叶,枯黄里透着暗橙色,叶子的形状犹如杂乱细密的线条。有新生的蕨类则是嫩绿的,刚从土里钻出头来,像个握紧的小拳头。在初春,它们是这个高山最基础和原始的色调,在这看似单调的苍茫之下,依旧暗藏着生机,艳丽的点点花色衬在有些苍黄的色调之中。只要有一点点土壤的存在,似乎再大的飓风也拿它无能为力,就在高山倔强顽强地生长着。我想这特定的生命画卷会容纳特殊的思维,就像这座山容纳了这里无数的生命一样。在如此荒凉而美丽的地方独自度过了半天的时间,这里有吸引人北上的引力,我虽然想成为被容纳者中的一员,但是担心会惊扰到自然,我的心里依然充满着敬畏和歉意。
在山上漫游行走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给人一种时刻需要移动的想法,需要新的热量供给来抵御冷空气在肺腑之中的巡游。我本以为人在运动之时,身体内部的热量会随之增加。在向上爬的过程中却感觉有越来越冷的趋势。我的脸部皮肤有些发红,渐渐可以看到嘴里呼出的白气,这表明周围的气温开始越来越低。我不禁哆嗦起来,随着氧气变得稀薄,这样的高山寒冻着实是刺入骨髓的。高山之上不仅仅只有美丽的风景,它还具有让人难以适应的“野性”。
“叮当,叮当”,一个阿妹牵着她的小马下山来。小马稚嫩的皮毛光滑亮泽,它的背上驮着两个不大的竹箩筐。小阿妹黝黑的脸透着一种懂事的成熟感。她不过六七岁左右的年纪,却很熟练地独自牵着她的马一个人在山上行走,身上的衣服十分单薄。马儿似乎能听懂她的话,像两个感情密切的老友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很久,直到她消失在远处的大树杜鹃林中。在她面前,我承认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已经被压制了——我已经冷得发哆嗦,并且已经逐渐迷失方向,只能依靠智能手机的指南针记忆来时的路,感觉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已经渐渐远离与自然息息相关的那种感觉。
走了一段路,在一棵粉色大树杜鹃下,我还遇见一只正在啃食落花的黑色小山羊。它和阿妹一样还是个孩子。我在慢慢地靠近它,它似乎已经察觉到了我,但却并没有打算立刻逃走,依然在缓慢地咀嚼着。我走到它面前时,它依然没有离开的意思,显然,它并不认为我是一个不速之客。我摸着它的头,一股浓烈的膻味扑鼻而来。它茶色的眼珠清澈如水,粉嫩的舌苔从我手上滑过。我认为我的到来对于它来说,仿佛是一声刺耳的喧哗,会打破这片宁静的风景。我刚要调头远离这个幼小的孩子,一只成年的山羊站在我的身后,它在仔细地打量着我,头上的两只角貌似在等待时机发出进攻。这只小羊应该是它的孩子,那个调皮贪吃导致走丢的孩子。我往前踱步,成年山羊却往后跑了一大段距离,它在观察我是否会伤害它的孩子。它站在远处,这种来自动物身上的焦急与人类母亲的情感一样。直到我走出了好几十米,它很快边叫边跑,小羊似乎听到了呼唤放下嘴中的花瓣。“咩——咩——”这单调的声音里饱含着无数的对话,它眯着眼睛一股脑儿栽到母亲的怀里,这对母子慢慢走入葱郁的树林之中,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爱的回荡,环环回绕。

我在这次“独自”行动中沉浸在自己和自然的沟通中,走着走着,我又发现一大片杜鹃树林。但很奇怪的是,这片树林更靠近山的深处,却开得相对稀少。我走近看才发现,原来人类的干预已经超越了自然界之间生命的竞争与淘汰。这里存留着很久之前被人为砍伐过的痕迹。眼前是几个很老的树桩,剩下大半截树桩是这些老树一直没有腐败干净的尸体。可以看出它在被砍伐之前像个健壮的男人,它的根系盘根交错,霸道地扣住这小片土地,深深地和泥土交织在一起。我们虽听不到它的呻吟和哀嚎,却可以想象它在被拦腰斩断且翻过身面向太阳直至死亡的时候,受着无比痛苦的煎熬。
我还发现,植物的根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集合体,就像达尔文所认为的,这些根部是植物智力的终端,是个会思考的大脑。倘若给予根部一个精准的地下截面,那里定会是个值得琢磨的地方。杜鹃树根在树死亡之后逐年被泥土赶到地表,像条死鱼被扔回了水里。同时大多数树桩、树心已经呈现空洞的形态,外壳的树皮在单薄中显得更加凋零。土壤和空气里混杂的细菌分子还无法在短时间里溶解朽木,上面开始长出雨后新出的小菌。一些小昆虫从木洞里爬进爬出,在阳光照不进去的地方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地洞。裸露在外的树根交错处还有细小的野花次第开放。我在遗憾中又勉强鼓起希望,生命正是在一种不断的交替与转化中获得了永生,这些坚韧的生命也在一些瓦解和重建中得以循环与存在。
这时天色逐渐阴沉下来。在这接近山顶的山坡上,感觉黑暗即将来临,乌云仿佛死死压在山顶之上,在云的上面有暗流般的滚雷声。这也好,我拥有了不得不南下的理由,但在天色渐黑的时候,这周围的氛围似乎更具有了吸引力,每一棵树木、每一株花草、每一块石头都装满了无数幽深的秘密,一些更加原始的声响开始出来和我一起漫游。在这里,我显然是配角与边缘,成为了渺小的生物体。风力逐渐越来越大,眼前的风景不再光洁与平坦,仿佛有了一层忧郁甚至阴森的感觉,甚至脱去了在阳光下那种美丽梦幻的外表,荒凉感愈加明显。这里弥漫着神秘的诱惑甚至是未知的恐惧。慢慢南下山坡的时候,路面因充盈而来的湿寒水汽显得湿滑不堪,这让下山的路越发难走,我过了很长时间才与老师们汇合。“快点啦!”大伙都把双手放在嘴边,对着远处踉踉跄跄下山的我呼喊着。走到相对平坦的路上时,我想到早些年来这里的时候,这里有一道道车轮印子。那些印子显然不属于这里。地表的草皮被活生生掀了起来,露出下面砖红色的土壤,看来有车子频繁直接开到杜鹃树边。这像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挑衅,甚至树下周围还有零星的白色垃圾,还有人为采摘撒落一地的碎花瓣。这些行为堵塞了自然与人类的心灵空间,再加上这一道道让人感觉生疼的印子,像是大自然的控诉。之前还听说还有人经常把改装车开到这里,这些行为看着很标新立异,但却破坏了这里最宝贵的自然环境。这次来,我发现那些疼痛的伤痕上已经逐渐长出新鲜的绿色,山坡上重新散发着清新的气味,大地也渐渐收回疼痛的表情。
山是土地的一部分,土地之上的风景变化莫测,充满着各种瑰丽的幻象,但我在每一次旅途中也感知到土地是实在的,我举起双臂像画框那样把回头的风景框住。在这个大树杜鹃遍地的荒野之中,那种坚韧又充满绮丽的美让人久不能语。我们走时发出的各种声响又一次惊扰了这里,天空显得深沉而静谧,这些天然的大花朵依然安静伫立在那里,一面向着雨水,一面向着阳光。这些无法人工置换或重建的天然完美之景,把强大和脆弱再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采伐之殇
记得小时候放暑假,我和同学到她父亲工作的位于凤仪的采石场,度过了几天难忘的假期。直到现在,我还一直在记忆里搜寻着那样原始而美丽的森林——一片片茂密的植被,明亮的山壁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当时的我酷爱学习地理学科,这片森林对我来说充满着巨大的吸引力。两侧巍然屹立的山谷和结构在行车中变化无穷,那时候的车子没有空调或者还舍不得开空调,车窗全程被打开,伸手就可以轻轻碰到那些盛开的灌木丛。花花草草在山间的各种缝隙中生长,兴高采烈地从各种陡崖上欢快跃下,一直向下汇入到更下面的溪流之中。
到采石场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到了那里,就在一块相对平坦的区域。记忆中那房子实在是太破了,仅仅就是简单的三间房,石棉瓦屋顶十分脆弱,只要风稍稍发力屋顶就会被吹跑。我们被安顿在其中的一间,也是最好的一间。屋里还有简易的高低床,是同学父亲的房间,他是工头小老板自然有最好的房间。她母亲每天为几个工人煮着简单的饭食。这间屋子虽然不大,甚至漆黑破旧,但是团圆了整家人。他们终于团聚了,偎依在一起将心里积累的思念释放出来。
沿着住宿区域再往后走,不远就能听到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原来采石对于人和机器都是力气活。运送沙石的人力推车忙碌地进进出出,由于地面十分不平整,感觉一车的沙石多次差点被打翻。再往里走,又有几个工人对着一块块石头一顿猛凿,用像大钉子一样尖锐的利器用力一劈,那些可怜的石块拼命挣扎到最后还连有一丝的接口,最后轻轻一敲,哗的一声像柴火一样变成两半。有的石块被分解得更快,滋啦一声,被机器切割得整齐方正。旁边的拖拉机正在喷着浓黑的烟,轰轰轰的声音非常刺耳,仿佛在极其不耐烦地等待着石头装车。还有些石头像是刚被拉下手术台的病人,有气无力地被两辆较小的推车推上一辆更大的车子,离开了大山母体被运去更远的地方,成为深埋在水泥里的建筑材料或是和陌生的人类朝夕相处。在接下来的几天,耳边有着无数的噪音,轰隆隆,哗啦啦,这里像是一个大型的塌方现场。这些声音充斥着我的耳朵。大山的腹部被开膛破肚般拉出无数的沙石,“肠肚四溅”的同时,每天周而复始重复着切割、敲打、拉运的工作。其实我没有再深入进去参观采石现场的勇气,因为那里还是一个随时都弥散着浓烟和粉尘的地方,只要一靠近生产作业的区域就要捂紧口鼻。
第二天,我们碰上一场清爽的大雨,工人们回屋子里酣睡着。我和同学在玩耍中缓缓走进这清冷无聊的碎石荒野。大雨里,这里迅速出现一个个大大小小泥泞的泥坑。在一个角落里,堆着无数之前被挖断、晒干的植物,但即使来场大雨也依旧无法滋润这些早已干瘪的躯体。这一区域基本由小山丘组成,山上被挖出的大坑日积月累,在阳光之下反射着刺眼的白光。我抬头一看,被挖开后的岩石这里突出来一块,那里凹陷一坑,散落缀着一些弱小的灌木。有些荒草顽强地从杂乱的石板中争先恐后地探出了头,看上去太像荒芜的墓地里突出的古老的墓碑。树和树之间相隔很远,在开采区内基本没有树阴。平日里,土壤、植物、人仿佛被放在烤炉里烘烤一样,有的地方干燥得有了裂缝,这场雨真是太珍贵了。
好不容易走到开采区的边缘,开始感受到本属夏日的凉爽,润湿的绿植覆盖满整片山丘,形成一大片连绵到远处的林带。机器的停歇终于换来了片刻的宁静,我们可以去找寻本来属于暑假的乐趣。这样的环境毫无修饰,蓬勃有力。这里的森林在原先的沉默中逐渐释放出活力,各种各样微小的声音开始透露着无数生命的存在,空气的味道也随之飘有自然的芳香。一棵棵松树修长笔直,柔软的枝条恰到好处地伸展着,雨滴打落在叶片上,光线在叶片下时隐时现。乌黑发亮的小甲虫爬进黑漆漆的小洞去进行一场短途旅行,继续徒步到阳光难以窥入的神祉殿堂。头顶上面,蜘蛛在树梢忙碌地编织自己的新网,还有很多鸟儿敏捷地张开翅膀,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落下的几片树叶像雨点似的悄然落在树影斑驳的土径里。还有松鼠,尽管它的身子小巧,但好动地在树林里钻来钻去,明亮的眼睛充满着机灵的揣测,给这片森林带来了充满野性的生机。在大树旁边有许多小树和灌木,大树为它们挡住了刺眼的阳光和强壮的山风,在土地自然的间隙中找到了养料和栖息地。吸吮甘霖后的花朵瞬间精神焕发,积极主动地开始装扮着山林,似乎能感受到植物的血液在阳光下正在迅速流动。山风在开采区卷起滚滚尘土,让人不得不捂紧口鼻,而在森林里却像阳光和雨露一样,嗖地一下在美妙的旋律中穿过树冠。雨渐渐停了,细细倾听,森林里继续延续着沙沙的声音。这些平日习惯沉默的声音是自然生命的喃喃低语,如果不走近细听,它们的声音便会逐渐弱化并消失在开采的噪音中。还有这么多悄悄躲在土壤里、树林下的我们从未见过却深陷困境的生命。回头反观开采区就像一片光秃秃的岩质沙漠,荒凉且落寞,充满着一种不安与忧郁的气氛。这些可支撑着这些生物的岩石和土壤正在被逐渐挖走,被拆得七零八落,这些植物和动物仿佛在抓住时机,紧紧追随着后退的绿荫。
同学说以前这边有一片更大的花草林,杂花繁多,还有大片的野蜂在进行着它们与生俱来的采蜜工作。这些健壮的小家伙在人工饲养出现之前就已经在山中经历了岁月漫长的繁衍和换代。我们一眼望去,寻找很久也找不到它们的踪影。其实这些生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敏感和脆弱。记得刚和丈夫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爬苍山,我们沿着栈道行走时,还见过一只一直在树林里窥探我们的小熊猫,它机敏地窥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它橘黄色的毛发在树林里若隐若现。我们很好奇地和它对视,它俊俏的小脸蛋十分可爱,黑黑的小嘴混合着白毛小花脸,眼睛像两颗黝黑发亮的宝石。可还没对视几秒,我正想拿出手机拍照,它突然转头嗖一下就跃回丛林之中。山里的动物在机敏地观察着环境的变化,总在不断适应和寻找着新的生存方式。可人类扩张的进度实在是太快太快了,也许它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走进了不可回头的深渊之中。
当我再走近细看,发现这座山的山体稍显干旱,很多地方阳光几乎没有受阻就直接照射到地面上,有些区域的土壤、岩石和台地上稀疏生长着松树。相比苍山有十八溪,有洱海方向湿润的水汽,这些山丘的溪水并不充沛,虽然这里距离洱海也不算太远。山丘下面和周围还有城镇和村庄,这里的生态环境显得有些脆弱。直到现在,我再重新回忆之前的场景,这些淘金者洪流般涌入到大山之中来寻找财富,对自然的摧毁是无疑的。我在电视上见过,那些山上的石块经历日晒风吹,遇到大雨的时候,仿佛大自然沉重的心跳已经感觉到松动的岩石和树木,即便石块体积十分巨大,也会像沸腾的开水一样倾泻下来,涌向公路、村庄和城市。
夜晚,这里亮起了电灯,终于快要到他们下班的时候了。猫头鹰还会来房顶上发出“咯咯咯”的叫声,这样的叫声在空旷的野外显得非常凄凉。据说之前,大伙会连夜起身拿起碎石头拼命扔向它们。有两次工人们砸伤过几只,活捉拿回去给娃娃玩,娃娃拼命在笼子里塞满玩具、大人们吸过的烟头,甚至还有枯草。猫头鹰关在笼子里再也发不出“咯咯咯”的声音,在病痛中沉默几日后就死了。
现在还正值夏季,炎热让人感到黏腻难耐。在荒郊野外,在床底下、桌底下,甚至在被窝里,随时都会有野蛇。有时候野蛇会把那些大男人吓得嗷嗷直叫。在我要走前的那天清晨,当时天快亮了,听到外面有人大叫有蛇!有大蛇!当时一只大蛇蜿蜒着身躯慢慢爬进了屋里,吓得工人们上蹿下跳。之前工人们遇到小蛇都会拿着棍子将其赶走,后来遇到比较大的会打晕卖给旁边的馆子拿去泡酒。直到工人队伍里来了广东人,他们似乎有吃蛇的丰富经验,所以这次大蛇的运气也并不好。这条野蛇很大,身躯有碗口那样粗,这要是放在灾难片中,人要与这巨型动物大战几个回合,但在现实中由于人数众多,动物显得多么弱小可怜。它几下就被制服了,还有人前去踹了几脚,嘴里骂道:“让你吓人!让你吓人!”大蛇还在昏迷之中就被撕下了血淋淋的皮,那皮的花斑让人觉得美丽而又血腥。这时,空气中雾蒙蒙的粉尘散去了,充斥着残忍的气味。然后,大家纷纷拿起了砍刀,架起了锅炉。锅炉下燃烧的欲望之火化成一丝丝具有复杂意味的烟雾又腾在空中,眼前又像尘土飞扬那般朦朦胧胧。一大锅奶白色的汤沸腾着,我不敢靠近甚至捂住了鼻子努力压制住阵阵发呕的感觉。
在几年后,看到新闻上有开始整顿治理挖山采矿的消息,采石场终于要大范围关停了。那些关于采石场的记忆就这样涌现在了脑海。现在又要投钱、投技术,想把被挖得光秃秃的山包重新披上绿装,这样投入的成本非常大。一次我还和那位同学在超市偶遇,问起她采石场的近况。她说她的父母长年在石场工作,现在他们的肺部都出现了问题,需要随时检查治疗。我们像是不明事理的小孩,渐渐意识到这笔生意并不划算,大自然的身体遭到人类摧残破坏,而大自然的自我修复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开始重新审视并反思我们造成的那些来自大自然的忧伤。
地球村视角
每个生命都在用自己的生存之道在地球上繁衍生息,遍布于地球的每一寸地表。我接下来想要讲述一些零碎的旅程,那些呈现着我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命羁绊的珍贵旅行记忆。
在南太平洋的新西兰,我在这里自驾了差不多三周,深深惊叹于这里美丽的景色和干净的环境,湖光山色令人流连忘返。他们不会将房屋修建在湖边,让人印象深刻的特卡波湖边依旧是一片充满自然气息的荒野,我们停好车子还要走一阵子路才能到湖边。在湖边我还看到了童年歌谣里的鲁冰花。十二月月初则是鲁冰花花期的高潮(南半球这个期间是夏季)。眼下,我们正遇鲁冰花在特卡波湖纵情绽放,花虽安静不语,但一串串随风摇曳,万紫千红。格外耀眼的视觉盛宴就是最好的交流。穿过花丛,近看湖水非常清澈,呈现着和海洋一样的宝蓝色,远远望去还有很多森林通向湖泊。然而我还听说,附近的居民仍然抗议湖水的透明度已由原来上百米降低到目前的几十米,政府也同意增加财政拨款提高湖水的透明度。
记得我们因为天气原因而错过福克斯山的冰川之行,一大早醒来便去了旁边的马涩森湖打发时间。湖边环绕着茂密的森林,我们大概用了两个小时步行环绕一圈。沿途高大的野生贝壳杉和土壤结成同盟,在森林里蓬勃延续着古老的生命,一路为我们遮蔽了头上的阳光,并且净化着空气,清洁着马瑟森湖清澈的水源,让整个徒步旅程清新无比。同时,整片森林的树干上包括地上都长满湿漉漉的苔藓,显得更加原始沧桑。之前,房东告知我们进入森林要仔细清洁鞋底(我们还遇见少数的几名游客在脚上套着鞋套),并且一定要按照步道的指示行走,不能踩踏旁边的原始绿地,防止把复杂的菌群带到这里,或伤害到这里的生物,特别是贝壳杉会因为人类鞋子上的鞋油或者复杂的菌群染上枯死病。
如果在别的地方遇见鸟,我们一般会慷慨地拿出食物喂它们,但在新西兰,森林郊外都有指示牌提示禁止喂鸟。因为这些野生鸟类不一定能适应人类的食物,而且房东说很多鸟类还因为向人类讨要食物而被撞死。我们在森林里遇到过卡卡鹦鹉。这小家伙又馋又凶,毛色相对灰暗,但是在脸部会有一抹亮丽的橘黄色,在灌木里发出“咔咔”的声音,就像有人在旁边咳嗽。我们在南岛还见过贪吃的啄羊鹦鹉。在我们快休息的时候,它呆呆地站在我们的木屋门口。它体型较大,长着灰绿色的羽毛,非常大胆,敢于近距离向人类讨要食物,会摆出一种“谄媚”的和善。我们在僵持的沉默中互相打量着,它见我没有食物便很有个性地掉头走了。后来,当地人说啄羊鹦鹉还会袭击羊群,把羊肉生生拉扯下来叼走。
再说说位于新西兰北岛摩托鲁瓦的萤火虫洞,去之前我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培训,从急救知识到处理各种情况的方法。我们还换上专门的衣服,身上不允许带东西,女性被特别要求须捆绑好头发,不允许过多涂抹化妆品。我们走进有万年历史的钟乳石溶洞,在昏暗中一直走到洞穴深处。经过一段时间的洞穴漂流,当身体被水冻得僵硬之时,渐渐就会发现前面的水面有光影摇动,头顶似乎有条浅绿的光之河在流动。随着周围逐渐暗下来,这些光影变成了漫天闪烁的“繁星”。它们惧怕强烈的闪光灯,我们的向导打开微弱的手电。洞穴的岩石上有一片点状绿白色微光,微光下是无数条长短不一的半透明细丝,从洞顶倾泻而下。每条丝上有许多“水滴”,就像晶莹剔透的水晶珠帘。原来,这些萤火虫在幼虫期不仅能发光,还能分泌附有水珠般黏液的细丝,洞内昆虫循光而来,撞到丝上就动弹不得,萤火虫幼虫便爬过来美餐一顿,在洞穴里安静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在新西兰驾车即使在寂静的荒野也不孤单,野兔会在宽阔的土地跑来跑去,有的还会躲在草丛里数着每天过往的车子。在牧场边,正在吃草的牛羊会向人投来好奇的目光。我们还会走进神奇的山谷和茂密的森林边,芮木、卷心菜树、银蕨延续着古老的生命。墨绿、鲜红、粉紫、宝蓝,各式各样的山林花丛还有湖泊会带来一幕幕震撼的视觉冲击。与此同时,还会遇到各式各样神奇的鸟类,眼下满是自然世界的奇妙与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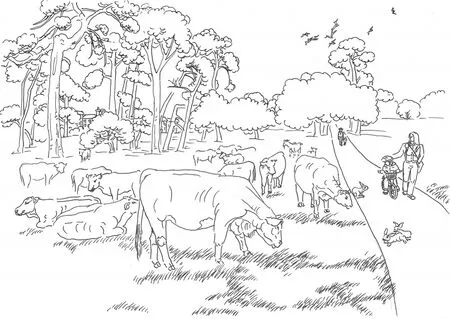
在南方出生成长的我,在严冬时节最稀罕的就是冰天雪地的景象。前年,我和丈夫就去了一趟日本北海道看冰流,还遇见了和冰流一起到访的候鸟。一到冬天,白尾海雕和虎头海雕就会和冰流一起来到北海道。现在也因为森林栖息地的破坏,这些动物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当冰流在眼前浩浩荡荡地缓慢滑过,大面积不规则的浮冰被下面流动的海水雕刻得闪闪发光,有的还嘎吱碰撞在一起又变成了新的形状。此时,海雕们在空中飞来飞去,但它们在天空飞行的高度不高,基本是低空飞行,张开翅膀的它们显得健壮无比。有的缓慢盘旋在冰流之上或站在浮冰上,远看灰黑色的它们静静栖息在那里,和蓝白的冰流形成强烈的色差。用望远镜看,有的海雕的尾巴毛色白亮,有的在脖子下面有大面积的白色羽毛,它们都长着倒钩一样的锋利的嘴巴,眼睛在谨慎机敏地转动,脚部的指甲和跟腱看起来抓力强大。这不,我刚喝完一杯自带的热水,就见一只海雕发现了冰流下的鱼,它的利爪敏捷地伸向水里进行抓捕,周围的一大片海雕集体发出类似犬吠的声音往获得食物的方向飞去。最机敏的海雕紧紧勾住并快速吞下这来之不易的食物。冰流继续前进,纯净得如缎带一般,夹杂着渐变的蓝白纹理,密实而坚固。这些海雕继续“独占”着一块块独立的“领土”,完成着它们丰富的迁徙之旅。
其实人和动物之间的亲密故事不一定在荒野,也可以在城市之中。在伊斯坦布尔坐公交车,如果公交车突然在发动前又再一次停下来,可能不一定在等一位气喘吁吁的人类乘客,而是在等待一只猫,这是我真实经历过的感受。当时我非常惊讶,小猫一步跃上车,迅速找到一个角落,淡定从容得像一名普通乘客一样要到达下一站。来到这里慢慢走遍大街小巷,我发现这里的猫种类很多,习惯和性格也各不相同,但总归一点,它们都和人类非常亲近。我第一次伸手想去摸一只来看我拍照的小猫,还担心它会仓皇而逃,没想到它很放松地将头轻轻上仰,享受着我指尖的温度。
特别是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猫,几千年来和这座城市一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已经是那里生活的一个部分。这与摩洛哥和日本的猫不同,这两个国家的人也爱猫,但摩洛哥的猫显得有些怯生生的,一按快门就跑了;日本的猫更多地在成熟的文化市场里变现为文创产品。唯独伊斯坦布尔的猫和人类一样漫步在城市里。我发现它们生活在咖啡厅楼下和港口边的鱼市,跑进院子里探出头往外看每天过往的人,有的甚至跑到教堂的窗户边晒晒太阳。有的小家伙还霸占摩托车上的座椅,不让人骑车。无论它们在休息、打闹,或在吃东西,它们并不惧怕镜头或是陌生人的惊扰,继续着属于自己的生活。走在街上还可以看到为流浪动物建立的食物站,食物站有丰富的粮食,很多人还会主动把猫粮拿出来给小猫食用。可这些猫并不能简单归类为人们平日所见的家猫或流浪猫,它们可以自由地出入于人类的生活场所,亲密但又保有自由。这是因为猫在这里被无限地宠爱和包容着。我好奇地向房东发问,为何这座城市具有对动物如此大的同情。她用英文告诉我的答案并不是同情而是共情,有人觉得猫是自己和上帝之间的桥梁,对猫的爱有着历史宗教的因素;有人觉得猫是活在世上的另一个自己,这都体现着人依赖着与猫之间的亲密关系与羁绊,那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将猫与城市形成一种紧密长久的圆融。
在这里,几乎很多动物背后都被赋予着神性——这是我刚到尼泊尔加德满都的餐馆吃饭时老板告诉我的。我记下了他的话,并开始了我的尼泊尔之旅。先不说南部奇特旺的野生动物,我们需要爬过丛林去惊扰它们。在尼泊尔的市区里的动物生态就是一个缤纷的世界。
在加德满都和距离它不远的巴德岗古镇,乌鸦会随时盘旋在头顶之上,或者在人行道上跳来跳去,它们好像对人类的生活既不好奇也不害怕。它们穿着黑色的小外套,以至于看不清楚它们的表情。它们会从容地伸展着翅膀,摇晃着脑袋,集体合唱或者单个扯开嗓子发出一种充满着寂寥的声音,让声音填满整座城市。特别在充满神秘感的神庙旁,更会让人产生独特的感受。走过广场,误闯入它们休憩的地盘,整片乌鸦从地面起飞就如同黑浪一般。在对面房子二楼,一个小男孩在写作业,他们家窗户口左边插着国旗,右边有一个乌鸦的筑巢。鸟巢里还伸出一截长长的尾巴,男孩向我挥手示意,指了指鸟巢里的乌鸦,并将食指放在嘴边发出“嘘”的动作。看得出他在小心翼翼守护着家庭成员。在加德满都的斯瓦扬布纳特寺,山顶的平台是观赏整个加德满都风景的最佳位置,还可以看到壮丽的喜马拉雅山脉,这里栖息着许多由僧侣定期喂养的野生猴子。这些小家伙成群结队爬满整座寺庙的区域,有的躲在经幡下,有的拨动了转经桶,有的调皮地拔走了刚点燃的香火。它们还会一路打量来的人,奔跑起来健步如飞,但不会野蛮地攻击人类。这些猴子有老有少,但是总体看上去身强体壮,毛发光洁锃亮,眼神里充满着犀利和机灵。本地人打趣说,这里的猴子或许在佛光之下长大,有着亲切、淡定的性格。在加德满都,还有悠闲的狗走来走去,随处而卧。还有大量的鸽子在广场和屋檐聚集,并落地觅食,呈现着尼泊尔当地独特的人和动物之间特殊情感的难忘景象。
相比加德满都,博卡拉的城市卫生更加整洁,绿色植被更多,在城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抬头仰望到连绵的雪峰。可尼泊尔近些年雪线正在逐年升高,当地人向我指着的鱼尾峰我都快要看不出雪山“鱼尾”的形状了,“鱼尾”在阳光下显得若隐若现。博卡拉当地大量开发大热的旅游项目滑翔伞,每天大量的车将旅客送到山上,还有很多不明事理的原住民会上山进行大规模砍伐。
相比之下,荷兰很会用自己的地理优势壮大环保的力量。我在荷兰的时候,自行车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整个国家地势平坦,无论马路有多宽或多窄,更多的车道都留给了自行车。在阿姆斯特丹,我每天出行逛博物馆都是借房东的自行车。自行车的车围尺寸非常大,就很像小时候父母辈上下班骑的那种“28”式自行车。怪不得大长腿的荷兰人哧溜一下就很轻松地蹬出去了。我在熟悉这种自行车后也能顺利地进行骑行。他们的机关单位、商场、生活区门口没有大量的汽车停车场,反而有自行车停放带。成千上万辆自行车同时锁在门口空旷的广场上,少了机动车的拥挤,自然会有更多的空间留给了大片的湖泊、树木和著名的郁金香花田,让荷兰成为欧洲名副其实的后花园。
记得之前去印尼巴厘岛,和朋友相约在宝格丽酒店喝下午茶,朋友说这里有着一流的酒店和三流的海景。为何一流的是人工景观,三流的却是自然景观?不可掩盖的是,这里的海洋污染确实让人堪忧。我在库塔海滩,看见被冲上岸的塑料垃圾,还有很多被垃圾杀害的鱼类和鸟类尸体,散发着腐臭的气味。我们在学习浮潜的时候,头上还漂浮有垃圾,我还亲眼看见魔鬼鱼在无奈地躲避着海洋垃圾。我的教练告诉我,不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每年确实有大量的海鸟和海龟还会误吞塑料垃圾或被垃圾袋缠绕致死。它们无法用语言和人类进行激烈的争论或抵抗,在无奈和沉默中失去生命。当然,塑料随着食物链的传递到最后也会毫不客气归还到人类的身上。
地球上的生命从绝境中新生、进化、繁衍才成就了自然界的丰富瑰丽。站在地球上不同地区的生灵面前时,我相信这些充满时间意味的生命能为我们带来一些顿悟,尤其是在如今这个急需寻求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