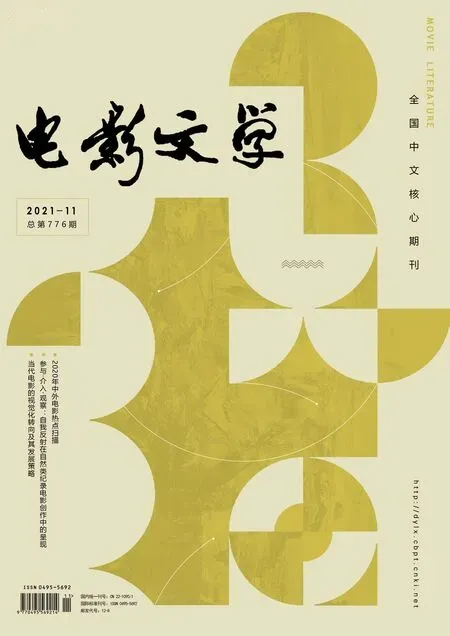《无依之地》的公路片诗意化细节建构
2021-11-14叶艳萍
叶艳萍
(西安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2020年9月,华语电影导演赵婷携《无依之地》参加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并一举获得了最佳影片奖金狮奖,赵婷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语女导演。此前,该片已经获得了第45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人民选择奖、第68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观众选择奖、第46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影片、第30届哥谭独立电影奖最佳影片等重要国际奖项,并成为今年角逐“奥斯卡”的大热影片。《无依之地》改编自美国作家杰西卡·布鲁德的同名非虚构作品,讲述了女主角弗恩失去了丈夫、工作和家园后,开始驾驶着一辆房车四处流浪,一边打工一边旅行,并在此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同样选择流浪的人的故事。其中,弗恩一角由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饰演。作为一个华语女性导演,赵婷选择了关于美国下层人民与少数族裔的题材进行影像书写,并完成得十分出色。这或许与她年少时便到美国求学,较早地接触西方文化有关,从而得以艺术家的敏锐视角对西方社会价值观与普通人的困境有了较为深刻的洞察。
《无依之地》整部影片自成风格,镜头常在极近与极远中切换,对比之中突出旷远天地中人类的渺小之感,尽管赵婷成长于西方文化语境中,但《无依之地》却体现出了东方传统文化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达观之感。影片深刻地探讨了个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居无定所、远离亲朋、失去家园……这些设定使弗恩几乎不被任何关系与观念所束缚,将自我投入大自然中,去探求生命的真谛。
一、镜头语言:人与自然
赵婷导演此前的两部作品《哥哥教我唱的歌》(2014)和《骑士》(2017)曾两度入选戛纳导演双周单元。《骑士》也是一部公路片,讲述了一个牛仔横穿美国公路的旅行故事,导演以女性视角介入西部片类型,在粗粝的类型气质中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作为赵婷的第三部长篇作品,《无依之地》延续了这种影像风格,整体故事架构是简单而深厚的。影片聚焦于一个年长的女性弗恩,她和丈夫生活在内华达州一个叫作恩派尔的小镇,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石膏公司关闭了在恩派尔已经经营了88年的工厂,员工大量下岗,小镇也随之消失了。弗恩的丈夫因病去世,失去了亲人、工作、家园之后,弗恩独自开着一辆房车,踏上了流浪之路。她白天打工,晚上住在车中——这个她称之为“家”的地方,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游牧人。
《无依之地》并不是一部依靠情节推动的公路片,它更像是一部情绪片,也正因如此,被部分影评人批评有“公路景观片”之嫌,但这二者显然是不同的,《无依之地》的镜头虽对准自然,但在对自然的描写中注重的是自然与人的相遇,以及人类个体在大自然中永恒的孤独感。“美国公路片是一种象征美国人民精神理念的特有文化产物,艺术形式可以追溯到美国史诗文学和战后发展历史。受现代主义影响,该类型的主题多倾向于‘逃离’”。显然,《无依之地》区别于此类美国传统公路片,通过与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绿皮书》的对比,我们可以轻易看出这种不同。在《绿皮书》中,人物的旅途有着确定的目的地,在旅途中主人公经历了外部世界和内在自我的冲突,在抵达时实现了自我内心的成长。但“目的地”“冲突”“抵达”这些关键词在《无依之地》中都是不重要的,影片弱化了戏剧冲突和叙事张力,引导着我们寻找解读影片的其他方式。同样,弗恩的上路也并非一种逃离,更像是她将自己“放归”了自然。
影片通过大量特写镜头与远景镜头的衔接调度去表现这种“放归”,在细节之处强化对镜头的处理。“场面调度不仅涵盖了观众看到的内容,还包括了他们是如何被引导去观看。”当观众从特定的机位去观看时,往往会对镜头的变化产生习惯性联想。《无依之地》打破了这种思维的惯性。在影片开头,弗恩在车库前收拾物品,镜头以近景呈现她凝重的表情。转而衔接的是远景镜头,群山、雪地、弗恩和她的车,当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时,个体与自然被放在了叙事天平的两端。接下来,弗恩与男人拥抱,近景呈现;弗恩开车上路,远景呈现;弗恩在荒草堆中如厕,特写呈现,镜头细致地跟随她若有所思的眼神与头部的转动,紧接着又是一个远景镜头,雾蒙蒙的天地之间,电线杆向同一点汇聚。弗恩如厕并转头张望这一人类行为瞬间融入了自然,人类自身的行为特征被消弭了。在这三组特写或近景与远景的快速切换中,影片放弃了中景镜头的缓冲,观众的视觉不断在极近与极远之间跳动,这其实是不符合观众的观影习惯的,甚至显得有点突兀。也正是这种突兀起到了强调的作用。
这样的镜头关系被称为“两极镜头”,有研究者将其定义为“运用蒙太奇的剪辑手法将大特写镜头与大全景镜头,在影视艺术创作过程中连接在一起,构成影片重要的叙事要素”。对两极镜头的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大卫·格里菲斯《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谢尔盖·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1925)等经典影片,一近一远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为影片叙事提供了更多可能。正如《无依之地》的镜头不断在“人物—环境—人物—环境”二者之间转换,使用极简的语言与动作,忽略了“人物关系”“故事背景”等常规的叙事手法。在对弗恩的面部特写呈现中,也通过这种极为细节化的镜头语言将人物情绪融入冷峻的自然环境中。当传统的叙事要素以新的方式予以呈现,影像成为某种诗意的实体,在长镜头拍摄的地平线下,整部影片就像是一首游吟诗,歌颂着人类永恒追求的自由。
二、细节建构:何以为家
正如上文所说,《无依之地》是一部没有“目的”的公路片,女主弗恩并没有试图去探寻一种生命的意义,整部影片所讲述的仅仅是一个“经过”的故事。弗恩经过山水,感受自我,时间仿佛静止般缓慢流淌。她在路上所遇到的人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她,却都没有阻止她继续上路。导演放弃了采用蒙太奇闪回叙述弗恩过去的故事的传统叙事模式,而始终聚焦她当下的旅途,零散的剧情杂糅着纪录式的生活碎片:流水化的工厂作业、车内逼仄的生活空间、星空下的独自沉思……弗恩并非没有机会停下来,但她选择了不断告别、不断前进的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导演通过细节化的文本建构,去表达了“何以为家”的深刻议题。
起初,弗恩并不愿意融入任何群体中去,拒绝了好友琳达·梅一同前往游牧民营地的邀请。但寒冷的冬季气温骤降,生活的窘迫使她终于选择来到这里,面对一个特殊的群体。影片借弗恩的主观视角向我们展现了游牧民群体的生活,以及他们“为什么选择成为游牧民”这一重要问题。在他们中,有患有战后创伤应激障碍的越战老兵,他受不了喧闹的人群;有父母双双罹患癌症去世的黑人女孩,她想要一个人实现和他们开车上路的约定;有被友人的死亡触动,想重新认真生活的中年女人……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远离现代社会、成为游牧人的理由,但相同的是,那些理由都源自一种控诉——对战争、对资本、对压迫。通过这些非职业演员自然的表演,影片表达了对社保福利、对“美元的暴政”“市场的暴政”等制度层面的思考,这也是导演赵婷以一个移民的身份对西方现代文明做出的思考。弗恩在营地的“邻居”斯万基身患癌症,这位75岁的老者准备继续驾车前进,平静地接受死亡。通过斯万基之口,影片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绝妙动人的自然之景:“我看到上百只燕子停在上面,还有燕子在空中飞舞,因为河水的倒映,看起来就像我也飞起来了……”弗恩被深切地触动了,斯万基走后,弗恩重新独自上路,在峡谷、森林、溪流中,感受与自然的互动。
本片名为“无依之地”,但实际上在影片叙述过程中,一直有一种离场的、不可见的“所依”,以物质载体的形式存在,承托着弗恩与土地、与自然的联系,比如弗恩一直细心保存的盘子(奶奶送给她的)和她一直戴着的戒指(保留了对丈夫的思念),影片通过这样的细节呈现构建了人物心理上连续的表意空间。正如在影片开头,弗恩的同事解读自己的文身时说的“家只是一个字,还是你一直放在心里的东西”。家究竟是什么?弗恩称那台并不宽敞的房车为自己的“家”,她认为自己只是“houseless”(无房的)而并非“homeless”(无家可归的),她也确实不是没有房子可以住。她拒绝了妹妹一家和在旅途中暗生情愫的戴夫的邀请,选择了独自回到房车中。我们可以看出,影片一直在强调的“家”的概念,并不是物质上的实体,也不是特定的群体,而是个人内心的精神家园。
在强调剧情冲突的剧情片和忠实记录的纪录片之间,赵婷创造性地选择了一种景观与声音结合的表达方式,从非虚构作品中创作出了弗恩这一虚构人物,用她去深入美国游牧民这一群体,展现他们的悲欢离合。虽然弗恩的出发是被迫的,是对故土消逝所带来的无力感的抵抗,但当她不得不从主流社会中退出后,她开始尝试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塑造一种新的身份,她是流浪者,同时也是对于自由的朝圣者。影片采用流动的音乐去表达一种流动的状态。来自意大利当代古典主义作曲家鲁多维科·伊诺第的钢琴曲无比贴合影片的“流动性”。导演再次通过这种细节化的声画配合建构影片的诗意化氛围,这其中有赵婷东方血液中流淌的侠骨柔情,也有她在接受与审视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对美国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对自由的崇高性的肯定,所有元素共同形成了整部影片浪漫而又悲怆的独特气质。
《无依之地》是一曲老工业区的悲鸣。这一点对于国内观众来说是有共鸣的,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没落后,一代人的生活随之改变。群体性的失业成为时代的记忆,年轻人纷纷离开生长的土地,去找寻生命的新的可能。时代的巨变让“家”的存在变得动荡,本代表着安全与稳定的空间意象开始产生裂缝,由此,“家”的概念产生了异化。在影片中,鲍勃所带领的游牧人群体创造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家园概念——“地球之船”,那是“独立的房子,不产生垃圾,不污染环境,完全自给自足。它会存在很久,比人存在的时间都久”。当然,这是理想化的想象,但充分反映了人们的精神诉求,那是一种对新的家园的美好向往,更是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无声控诉。在工业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环境异化使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下无力抵抗,故乡、家庭等代表着稳定与归属的栖身之所不再能给个体提供稳定的空间,无论是从物理空间还是心理空间。于是弗恩的上路更多带有了抵抗的色彩,把自己交还自然,亦从自然中汲取能量。所谓“无依之地”,并非无所依靠,天地自然是人类心灵永恒的归所。
作为一部公路片,《无依之地》无论从影片形式还是内容上都进行了创新,影片并没有试图以某一段惨痛的人生故事去引发共情,而仅仅是平静地讲述,正如导演赵婷自身的创作理念——“随它流动”。整部影片就如流水一样带领观众去“经过”,经过山谷,经过河流,经过每一个带着故事前行的人,却从不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