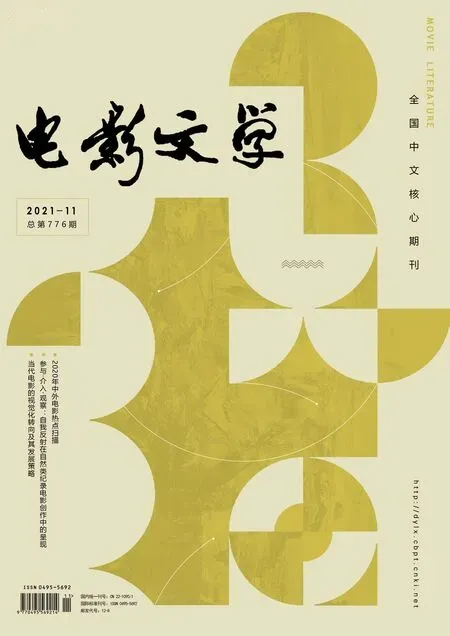《吉祥如意》在虚实之间的体裁实验
2021-11-14刘璐
刘 璐
(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384)
大鹏导演的新作《吉祥如意》1月29日登陆了内地院线,这部影片2020年7月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时,便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引起影迷群体的关注与讨论,并入围了金爵奖最佳影片奖。这部影片共80分钟,分为《吉祥》与《如意》两个部分,时长48分钟的《吉祥》曾作为一部独立影片参加了第55届台北金马奖影展,并获得最佳创作短片奖项。
《吉祥》是一部采用纪录片语法拍摄的剧情片,是一个关于东北农村的故事。导演大鹏本想回到农村老家拍摄一部关于“姥姥如何过年”的影片,为此在外打拼的亲戚们都赶了回来,一个大家族难得团聚了。但姥姥却在这时摔了一跤,性命垂危。本是准备拍摄“姥姥过年”的剧组,意外地变成了一支记录老人离世前后的家族故事的队伍。影片的拍摄主体也由姥姥变成了三舅,叙事主要围绕大鹏的三舅在姥姥离世后该何去何从的故事展开。三舅极重兄妹情谊,曾是家中的支柱,却在中年时期的一场高烧中智力回到了四五岁的孩童时期,成为全家人的负担。在影片中,演员刘陆扮演十年未归家的三舅的女儿王庆丽,她也是全片唯一的职业演员。
《吉祥》的拍摄手法是特殊的,它不是一部纯粹的剧情片,影片的导演干预是极轻微的,或者说,情节的发展并不完全在导演的掌控之中,很多时候摄影机只起到了单纯的记录功能。但它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影片并没有隐藏摄影机的存在,甚至在叙事进程中穿插人物采访,让观众从剧情发展中抽离出来。而后半段《如意》则记录了拍摄《吉祥》的整个过程和《吉祥》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首映时的幕后故事,解读了大鹏作为主创人员将个体私密空间呈现给观众时所面对的撕裂式身份体验。《吉祥如意》最大限度地解读了电影与生活的互文关系,呈现了一个中国式家庭彼此之间的羁绊。在如何面对亲人离去这个看似庸常的命题中,影片以一种宿命式的记录,让我们重新审视亲情,也审视自我。
一、在纪录性与戏剧性之间
“伪纪录片”并不是一种新兴的影片类型,事实上,作为一种叙事类型,“伪纪录片”已经有了不少代表作品,如《女巫布莱尔》(1999)、《死亡录像》(2007)等。安德烈·巴赞在《电影是什么》中已经下了定义:“‘伪纪录片’又称‘仿纪录片’……它的故事多数时候是虚构的,而非真实事件,但它的创作手法和整个风格却与纪录片十分相似。通过运用讽刺或仿拟的方式来分析社会上的大事件或问题,挑战着人们对于既定事实的认知,以及对于纪录片里的核心命题‘真实’的观念。”但显然,《吉祥如意》与前面所提到的经典“伪纪录片”作品是不同的,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吉祥如意》中的故事并非虚构的,姥姥的离去是既定的事实,关于三舅的争端也是家中一直存在的矛盾,影片所呈现的故事背景是真实的。而导演采用了些微的干预手段,突出了矛盾,例如年夜饭上讨论三舅的去留的一场戏。安排大家吃饭与讨论的中心点是导演的用意,但随着矛盾的激化,事态一度失控,二舅妈直接离场并说“不演了”,这是超出导演的预期与控制的,而这一切都在摄影机的记录之下,在《如意》的部分被展示出来了。另一个区别在于,导演大鹏本身也是故事的参与者,创作者的私人感情被投射到影片的叙事中,在摄影机之内,他是送葬队伍中的外孙;在摄影机之外,他是整部影片的导演。《吉祥如意》以一种“天注定”的呈现方式,形成了其独特的、没有参照物的体裁实验。我们不能将其归类到“伪纪录片”类型之中,也暂时无法对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影片游走在纪录性和戏剧性之间,以一种实验性的叙事结构完成了影片的整体叙事。
但《吉祥如意》也采用了“伪纪录片”类型中的常用结构模式,即“戏中戏”的嵌套式结构。“通常被套在里面的故事是通过第一层故事出现的摄影机展现的,而摄影机能够展现的内容一定是‘过去时态’的,即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导演坦言在构思整个故事时就设置了《吉祥》与《如意》两个剧组,一个剧组拍故事本身,另一个剧组拍《吉祥》剧组的拍摄过程。而在《吉祥》片段中,不时穿插进对三舅的兄弟姐妹的口述采访,镜头里出现了导演大鹏提问的声音,他仿佛是刻意提醒观众摄影机的存在。而观众也可以从采访中拼凑出这个大家族的基本情况以及三舅的为人与性格,进而更加深入地进到故事情境中去。在《吉祥》的结尾,三舅王吉祥独自走在大雪中,他一步步稳稳地走着,随口哼着小调,“文武香贵,一二四五”,这是他的兄弟姐妹们的排行与名字,他都记着,却唯独忘了自己。在突出的环境刻画中,王吉祥重情重义却被命运抛弃的悲情形象更加丰满,而他在雪中的独行更显一种孤独之感。随着镜头逐渐拉远、拉远……王吉祥出现在“屏幕中的屏幕”里——《吉祥》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首映上,大鹏面对“你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片子”的提问时愣住了。《如意》的部分开始了。
这一转场极为巧妙,也具有结构性的意义,“戏中戏”的形式打破了观众与影像之间的传统壁垒,让观众直接观看影片的制作过程。而影片在《吉祥》中提出的很多问题也在《如意》中得到了解答。更加有趣的是,我们在《如意》中意外地发现——王庆丽并不是真正的王庆丽,是由演员刘陆扮演的,而真正的王庆丽却在拍摄过程中意外地回到了村子,真“假”王庆丽戏剧性地出现在同一个镜头中,呈现了略有荒诞感的一幕。在《吉祥》的年夜饭一场戏中,“王庆丽”在亲戚们关于自己父亲的去留的争吵中情绪逐渐崩溃,她跪着向大家磕头,说着感谢的话。而争吵并没有停止,“王庆丽”逃离了镜头。在《如意》里我们又看到,饰演王庆丽的刘陆在镜头外仍旧走不出强烈的情绪,而真正的王庆丽此时就在她的身边——她在玩着手机,仿佛此时发生的事与她无关。《吉祥》与《如意》在重复的段落中形成了互文,让我们看到了台前幕后发生的事情,也发出了演员的入戏程度甚至超越了原型人物的“《纽约提喻法》式”的疑问。在查理·考夫曼导演的电影《纽约提喻法》(2008)中,深陷生活囹圄的戏剧导演凯顿想将自己的人生浓缩在一场戏中,而戏剧的主角便是自己。他找来了一个演员饰演自己,去重复体验自己内心的苦痛挣扎。而这个演员在戏剧的结尾,由于入戏过深,替凯顿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步——代替凯顿跳楼自杀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吉祥如意》中所体现的虚实关系与《纽约提喻法》是类似的。演员与原型互成镜像,前者入戏,后者却从自身的成长环境中跳脱出来。这促使我们去思考原型人物王庆丽的原生家庭。父亲得病后,母亲执意与父亲离婚,她被判给母亲,与父亲不再见面。成年后的王庆丽在北京打拼,独自带着孩子,母亲又患了重病……现实的种种不堪压在她的身上,使得她逐渐与故土和这里的人们疏远。刘陆和王庆丽的反应都是真实的,具有源自不同身份下的现实性。在《如意》中,摄影机将镜头对准镜子,“两个丽丽”和她们的镜像在虚虚实实中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联结。
二、在“真实”与“真实感”之间
纵观电影史上有同类型元素的影片,贾樟柯导演的《二十四城记》(2008)也采用了专业演员去饰演有真实故事背景的人物原型,引发人们思考“表演性与真实性”的区别;《大人别出声》(1992)以“戏中戏”的形式呈现了话剧演出的台前幕后,《摄影机不要停》(2017)以30分钟长镜头结合“戏外戏”的形式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观影体验。但《吉祥如意》与它们都是不同的,在这部影片中,观看的本体与客体、参与的本体与客体、观察的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都发生了变化。更加重要的是,导演大鹏作为创作者,同时也是故事本身的一部分。创作者的参与感和抽离感在影片中同时存在,而影片本身也摇摆在“真实”与“真实感”之间进行叙事。
演员刘陆本来要饰演的角色是导演大鹏,她要扮演“北漂”数年回到农村老家过年的女孩,姥姥的外孙女。而就在刘陆提前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的过程中,姥姥因为意外陷入昏迷,她仿佛天意般地真正代替了大鹏的角色——替他见到了姥姥的最后一面。在《吉祥》中,导演隐藏了自己的情感,转而将刘陆的角色重新塑造为三舅的女儿,将镜头聚焦在三舅身上。而在《如意》中,我们得以看到大鹏在这个家族中所处的位置,导演投射的私人情感成为影片的一部分。在他抽离其外的部分,有演员的安排,有剧情的设计,但在他置身其中的部分,我们可以感受到情感的浓烈与真挚。
“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贾樟柯在谈到如何看待“艺术的真实”问题时说:“真实只存在于结构的联结之处,是起承转合中真切的理由和无懈可击的内心依据,是在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令我们信服的现实秩序……我追求电影中的真实感甚于追求真实。”从这个层面来说,《吉祥如意》不能说是真实的,但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它是真诚的。它真诚地呈现出了东北农村中的社会现实。不管是王庆丽还是大鹏,都是抛弃了乡土的人,他们就像不再关心乡土中的事物的每一个观众的影子。但当我们回到那里时,又能熟络地拾起那些琐碎。同时,影片表现了随着年轻人的出走,东北农村老人赡养问题的尴尬现状。此外,影片也真诚地刻画了传统社会的亲情羁绊,以及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间无法割舍的感情,他们彼此指责埋怨,却又彼此依靠。影片还真诚地塑造了三舅这一人物形象,镜头的存在对他来说是几乎可以忽略的,他反复念叨的那句“一二四五,文武香贵”和“明天找妈”,代表着他对亲情最真挚的挂念。
作为一部采用新式语法拍摄的影片,正如上文所述,《吉祥如意》不仅指涉导演和演员,同时还指涉观看者,观众坐在观影席上看“观众坐在观影席上”,这是一种极奇妙的体验,从我们所熟悉的“演员—导演—观众”的观演关系转变为“观众—导演—演员”,而导演同时也是演员,观众成为这段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强烈的参与感更能够调动情感的体验。银幕上的故事不再是遥远的虚构,而体现出强烈的真实感。这段故事是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面对故土与亲情,我们都身处旋涡之中,饱含深情,又无可奈何。
《吉祥如意》开辟了一个电影新范式,正如导演所说,他拍摄的是一场“天意”,这部电影的诞生是无可复制的,需要现实的戏剧性巧合。当我们在讨论影片情节的安排与设计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影片最具有价值的部分。从内容层面上来说,它真实地展现了东北农村乃至无数个中国家庭的伦理困局;从结构层面来说,它又通过虚实的镶嵌转化成了形式上的巨大创新,事实与虚构成为一体对照的两面,共同指向了某种真实。总体来说,作为一次全新的体裁实验,《吉祥如意》是成功的,它拓宽了电影表达的维度,将观众纳入表达范畴之中。同时,影片的表达条件也是偶然得来而不可逆的,整部影片贯穿了对传统叙事模式的解构和对伦理问题的探讨,这在华语电影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吉祥如意》重新解读了“剧情片”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