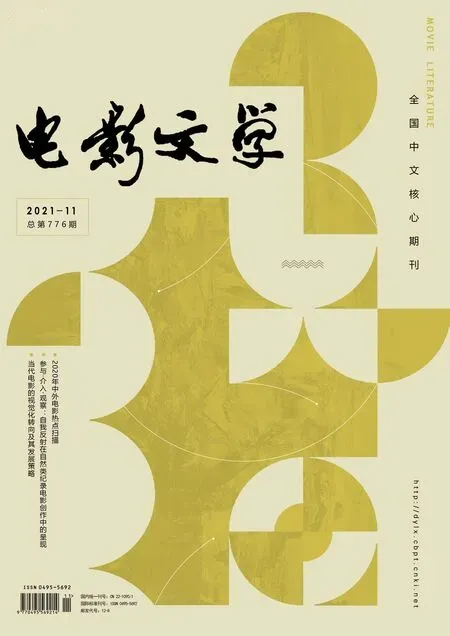农民工电影中的空间政治研究
2021-11-14胡清波
胡清波
(中原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城市空间的现代化演变是一个关系化与生产过程化的动态过程,夹杂着政治、资本与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政治学的反思》中强调:“有一种空间政治学存在,因为空间是政治的。”在这一空间政治学的问题域中,空间不再是客观、科学的物理场所,而是成为经济生产、政治统治与文化观念的权力斗争场域,“既包含有国家、阶级、政党的对抗,同时又有文化对抗、性别对抗、年龄对抗、身体对抗等,社会群体/个体的身份认同,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单面的政治(强者压迫弱者,弱者争取自身的地位),而是延展到对于人的丰富性和人的权利的多面性的强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得到迅速推进,城乡差距和社会阶层分化也日益严重。农民工电影在反映城市外来者边缘化生存处境的同时,也彰显了空间在社会区隔以及个体实现社会身份认同、产生自我归属感、获取情感归依中的重要作用,其中的空间政治主要呈现为文化和生活意义上的微观政治,即“权力的生活化”的空间再现。具体说来,农民工电影对中国当代城市空间政治的表现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期,底层视角下的农民工电影对城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区隔和权力规训做了批判,表达了对城市底层群体的关怀和对现代性的反思;其次是新世纪以来“新主流”转向下的农民工电影,通过打工者具有“传奇”美学色彩的奋斗故事,勾勒了城市外来者在工作和生活空间的流转中实现阶层跨越的逐梦历程,强调了空间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转换所具有的符号性作用。
一、底层叙事模式下空间的社会区隔与权力规训
由改革开放至新世纪,中国城市社会问题的核心逐渐转向权力与资本对社会生活的把持与重构,它们制约着城市空间景观的生产和变迁,也孵化出纵横交错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网络,使中国当代城市化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关于城市外来者的空间叙事显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城市空间显示了空间作用于外来他者的强大权力,它用感官刺激诱惑着外来者,用物质空间隔绝外来者,也用非理性的欲望使外来者迷失自我。”社会—空间和距离的秩序化、排他化,是外来打工者在城市中遭遇社会壁垒和生存困境的重要原因。底层叙事模式下的农民工电影将打工者视为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通过表现他们工作、居住或进行休闲娱乐等活动的空间,揭示其在现代化空间权力分配中的边缘地位,反思城市化进程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空间区隔等问题。
底层叙事下农民工电影所呈现的底层工作空间首先是街道、胡同等开放性的空间意象,这些空间本应为社会大众所共享,却被某些城里人占据为“特权”空间,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干扰、破坏外来者的正常工作。《上车,走吧》中,从乡下来北京开小巴的刘承强和高明因为抢了当地人的生意而不断地受到排挤和暗算,在巴士线路上屡次遭遇恶性竞争、故意剐蹭等,最后赖以谋生的小巴车因被对手动了手脚而彻底报废,高明黯然离开北京,刘承强虽然留在北京,却始终没有稳定的工作,只能漂泊度日。《十七岁的单车》中,当上快递员的农村青年小贵借助快递公司的自行车来丈量北京这座城市,北京狭窄的胡同小巷和宽阔的马路街道都成了他的工作空间,但权力的争夺也在这一特殊场域内悄然展开。丢失的自行车阴错阳差地落到城市青年小坚手中,又被执着的小贵偶然寻获,两个年轻人的命运由此被联系在了一起。作为城市外来者的小贵与本地人小坚关于自行车归属权的争议、二人与小混混们由于社交冲突而产生的混战,本质上都属于社会空间区隔下的权力争斗。电影结尾小贵扛着被砸坏的自行车走向车水马龙的大街,意味着其在公共空间中的工作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影射了打工者在城市空间权力格局中的弱势地位。
建筑工地、工厂车间、矿井矿山等封闭性场所,是农民工电影中底层劳动者遭受权力规训的另一种工作空间。这些场所大多实行封闭式管理,权力集中在管理者或幕后操纵者手中,打工者在此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不许抢劫》中的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做着危险的工作,劣质涂料的有害气体使年轻的小顺子患上了白血病,包工头王奎却一直恶意拖欠工钱。当农民工愤怒地冲到王奎办公室讨说法时,却遭到一顿暴打,导致多人受伤。工厂车间的封闭式管理更加严格,上厕所、吃饭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定,流水线的循环作业使工人们麻木地重复着机械化动作,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年关》里的小工厂老板为了赶工期,命令工人们连续工作五天五夜,使打工者的身体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工人张怀恩因此累得心脏病发作晕倒在地。位置偏远的矿井矿山也是农民工的底层工作空间之一。《谁是卧底》中的小煤矿不仅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还使用暴力手段非法拘禁矿工进行繁重的工作、拒绝发放工资等。在卧底者的层层揭秘下,煤矿的权力主导者从齐老板、郭矿长逐渐指向王副县长,资本的权力寻租和监督机制的缺位使矿工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打工者的劳动场所异化为遭受非法拘禁的扭曲空间。
居住空间也是农民工电影展开底层批判的一个重要空间类型。“居住空间的差异,最能昭示社会的阶层差异。……不同的阶层,一定会占据着不同的空间。但是,这些差异性的空间本身,反过来又再生产着这种阶层差异。”在农民工电影中,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居住空间可以说是最简陋的。《泥鳅也是鱼》中农民工住在杂乱拥挤的集体宿舍,女泥鳅先是把两个孩子藏在木棚里,木棚被建筑施工的吊车吊起,三人差点丧命,然后她又带着孩子住在铁路边即将被拆迁的危房,空间的辗转流离和危机四伏象征了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不许抢劫》中,农民工在简陋的工棚里为工钱发愁,老板王奎则若无其事地待在自己的豪华别墅里,居住空间的强烈对比显示了管理者和打工者们在社会权力方面的巨大差异。进城打工的保姆通常在居住空间上和城里人有较大的重合,因为住家工作性质使许多保姆要和雇主生活在同一套房子里,但这一封闭的居住空间内部也奉行着严密的权力格局,保姆要绝对听从雇主的安排,否则就会被逐出这一空间。《泥鳅也是鱼》中的女泥鳅在雇主家里时刻受到监视,一举一动都要按照女主人的要求来做,当精心伺候的老人去世时,女泥鳅伤心大哭,女主人却感到不可思议,打工者被她视为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自然谈不上平等和尊重。《十七岁的单车》中的保姆红琴由于爱美而经常偷穿女主人的衣服,被对方发现后扫地出门。《大腕小保姆》中的槐花勤劳善良,却多次遭受女主人的排挤和羞辱,最后选择离开。
五光十色的休闲娱乐空间是农民工接受城市现代性启蒙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他们容易迷失其中的危险场所。《扁担·姑娘》中的女孩阮红在莉莉歌厅一再被城里男人欺骗,成为歌星的梦想最终泡汤,歌厅后来被警察查抄,她也随之被带到了感化院。《江城夏日》中的乡下女孩艳红在“天上人间”夜总会当陪酒小姐,还成了黑社会头子“鹤哥”的女友,弟弟却惨死在“鹤哥”抢来的车下。《上车,走吧》中的四川女孩“小辫子”不满足于和男友开小巴的拮据状态,选择去夜总会陪酒,过上了穿着时尚、出入有豪车接送的生活,却失去了最纯洁真挚的爱情。作为一种临时的欲望宣泄场所,夜总会成了一种异质性的边缘化空间。《世界》中的歌舞厅也是有钱有势的老板们用欲望化的眼光凝视打工妹的特定空间,珠宝商张老板在这里看上了小桃,企图用金钱引诱并占有她的身体。这些灯红酒绿的休闲娱乐空间象征着现代化大城市对农村人的吸引力,而一旦农村人在这一空间中迷失自我、自甘堕落,就意味着被城市的金钱逻辑所同化,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范使权力规训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二、“新主流”叙事模式下空间的流转与身份跨越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政策制约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农民工电影的叙事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主旋律化,渗透主流意识形态,体现国家意志;二是商业化,追求票房效果。”在这一“新主流”叙事模式下的农民工电影中,空间政治主要体现为空间的符号性及其与主体身份认同、社会流动等的内在联系。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城市及其内部的各种生活、消费场所都成了符号性的所在,空间的差异意味着身份阶层和物质基础、生活方式和社会交际网络等方面不同的群属特征。作为城市经济、文化、政治活动集中的地方,中心区常常被视为时尚的、高雅的、富裕的、有待进入的空间,代表着位于较高文化等级的上层社会,直接指向一种“成功”的象征或者暗喻。它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诱惑、引导和激发出来,逐步由边缘向中心挺进,形成了不同空间规模上重叠的关系网运动轨迹。“新主流”叙事模式下的农民工电影便塑造了这样一种成功的外来者群像,他们为了冲破固有的阶层限制、实现社会身份的转换,默默地展开着空间争夺战,最终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了底层空间向城市中心的空间跨越,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空间迁徙影像。
电影《我的美丽乡愁》在抒发打工游子思乡之情的同时,着力表现的是离乡进城者融入城市的必然性。女主人公湖南女孩细妹独自来到广州打拼,经过一番曲折才在餐馆找到服务员的工作,认识了一同打工的诸多好友。在这些打工者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朴实的城市梦,胖妹离开餐馆时站在屋顶上对着面前的高楼大厦喊道:“我要挣很多的钱。我要在城里买楼,买汽车。我还要找个最帅的男人跟我结婚。我还要开餐馆。我要变成一个最有钱的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和真诚,细妹最终从餐馆服务员变成了公司职员,工作地点也从喧嚣杂乱的餐馆变成了整洁明亮的办公室。影片结尾是细妹的独白:“我还是哭了,所以没能回家。我打电话告诉妈妈,妈妈说你哭了就是长大了,可以像一条鱼一样去海里遨游了。我只好一直游下去,永不停歇。”随着工作空间的提升,她也逐渐熟谙城市的生存法则,适应了城市生活并为实现身份的转换而继续努力。空间的位移既是对寄寓在不同空间、不同类别人群之间差异性的社会比较过程,又是对同一寄寓空间、相同类别的人群的相似性的强化过程。通过改造旧的认同规则或者发明新的认同基础,去除旧的阶层标签,培育对“我群”的认同,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逻辑。在现代性的召唤下,进入城市的年轻人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受到强烈的冲击,渴望能够迅速融入新的社会群体,与这一市民化之路相伴的是对乡村文化的不舍和依恋以及失去归属感的痛苦,对空间的征服和占有是帮助他们重新获取文化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
《天堂凹》中的农民工德宝曾经在采石场、建筑工地等工作近二十年,为深圳的现代化建设奉献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最终在深圳买房落户,成了这个城市真正的主人。改革开放之初,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深圳,伴随着发展机遇而来的是迅速层级化的社会结构,农民工们在积累个人财富的同时,也在努力追求社会身份的转换和社会层次的“中心化”,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个人对自身的幻想:城市中心的认同、身份的置换、上层化的愿望,等等”。在德宝还是一无所有的农民工时,居住空间是脏乱的工棚、休闲娱乐空间是歌厅门口,由于没钱进不去歌厅,想放松时只能和工友选择在歌厅附近唱歌,有时还会因为声音太大而遭到驱赶。而他始终坚持真诚待人和吃苦耐劳,默默地为深圳的建设添砖加瓦,在内心深处早已把深圳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在不断的努力下,他不仅受到了首长的表扬,还被官方媒体宣传为典型人物,之后成功把家安在了宽敞明亮的新房里。德宝挥洒过汗水的诸多空间都成了他奋力追求城市梦的注脚,也使其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深圳的崛起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从边缘到中心的空间流转勾勒出了德宝在深圳的身份跃升之路,影片结尾一家三口在邓小平广场上游玩的场景,象征着农民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成功实现自我提升。德宝这一底层打工者的奋斗史映射了深圳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和巨大成就,也显示了改革成果的社会共享性,显示了外来打工者融入城市的多种可能性。
《美丽新世界》中的乡下青年宝根,在摩登上海不断刷新着自己的认知,他以都市漫游者的身份窥视着这座城市,同时也“迷恋城市的商品世界,为漂亮的新陈设着迷,并注视着城市生活的高速运转”。从苏州河、待拆迁的老房子到东方明珠、外滩建筑,上海的传统与现代、底层与上流社会等复杂景象在镜头的空间拼贴中得以建构,宝根的现代性启蒙也逐渐完成,融入这个现代化大城市的梦想已经根植于他的内心深处。正如宝根在建筑工地的钢板上对金芳所说:“我来上海就是来找这一堆金子。你知道吗?如果这座楼盖好,在三十七层我有一套房子,在那儿。我能看到上海最美丽的风景。”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在上海这一现代化大城市立足,成为宝根不懈奋斗的内在动力。他像拉斯蒂涅一样有着征服城市的野心,也遇到了金芳这样的“上海土著”,但并没有打算依傍本地人落脚上海,而是始终坚持用实实在在的劳动去追求梦想。在经历过建筑工人、歌厅保安等多重身份后,宝根最终通过卖盒饭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距离在上海扎根更近了一步。而影片结尾宝根“抽奖抽到住房”这一情节虽然具有极大的夸张性,但由于有宝根自身独到的眼光和勤劳、善良等优秀品质做铺垫,观众并不难相信他的“美丽新世界”一定会到来,外来打工者冲破固有的阶层限制、实现社会层次提升的梦想在具有冒险性质的都市“传奇”故事中得以实现。
“城市空间结构是各种人类活动与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投影,包括土地利用结构、经济空间结构、人口空间分布、就业空间结构、交通流动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生活活动空间结构等。”中国当代社会的阶层分化与权力流转、城乡关系的演化和地位失衡等都可以在城市空间的建构和重组中找到印证。底层视角下的农民工电影从工作、居住、休闲娱乐等多个维度审视当代城市空间,揭示了其背后的社会区隔和权力规训等差异政治,表达了对打工者生存处境的担忧,体现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其中农民工在城市遭遇到的社会排斥,从根本上反映的是乡村话语在与城市相遇时的弱势地位,暗含着对城市伦理的质疑对乡村伦理的缅怀。“新主流”电影则通过空间与个人身份认同和阶层流转之间的密切联系,生动地展示出当代城市空间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物质景观或者抽象概念,而是成为一个交织着多重关系、处于不断分裂与建构状态中的动态过程,空间的转换伴随着文化身份的重新建构以及权力、资源的再分配,是城市边缘群体中心化的显性体现。其以城市底层“草根”逆袭故事为基本叙事线索,选择了农民工群体中成功实现华丽转身的典型人物,以空间和社会身份的转换建构起了城市外来者市民化的理想路径,起到积极的励志作用。总体看来,农民工电影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当代城市中的空间政治,丰富了当代电影空间叙事的维度,对于了解中国当代城市化过程的复杂性、反思现代性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正确引导农民工市民化之路等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